朱健康 与“逆境”为伍
华南
沪上7月,绵绵细雨洗去了些许暑热。枫林路两旁的法国梧桐舒展着阔大的叶片,鲜翠欲滴。如果植物也有心理活动,那么这应该是它们心情大好、恣意生长的时候。不过,在现实中,这些法国梧桐还需接受恶劣条件的考验。位于枫林路300号的中科院上海植物逆境生物学研究中心里,朱健康正带领团队孜孜不倦地研究植物面对恶劣条件时如何在逆境中生长。
与植物在自然界中时常要接受严峻考验一样,人的一生也会身处逆境。身为植物生物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国家千人计划顶尖人才入选者、中科院上海植物逆境生物学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朱健康亦是如此。
执着改变的命运
朱健康的人生,似乎是从第一次高考失利开始出现拐点的。
走出农村,一直是少年朱健康迫切的愿望,“农村很苦的”。那时已是“文革”后,土地包产到户,他能吃饱饭,但吃得很差。“中学时住校,一星期回家一次,背一袋子黑面馒头回学校,那就是一周的主食。每天早上往网兜里装一两个馒头,放到学校食堂的蒸笼里,中午下课就热好了。食堂里买2分钱一碗的清汤,汤里只漂着几片菜叶子,我们就就着清汤吃干馒头。高中几年,顿顿如此。”高中快毕业,国家到学校招收飞行员,朱健康体检第一项就没有过关,“那时身高不到一米六,体重才36公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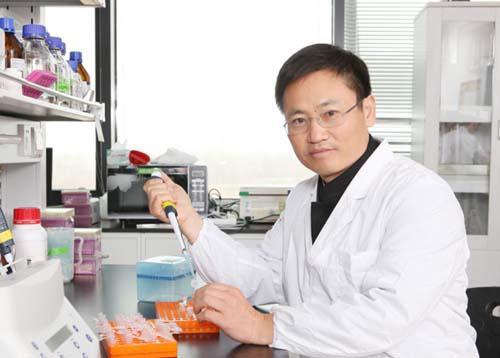
考學是当时农村孩子唯一的出路。考上大学、大专,哪怕是中专,也能成为吃商品粮的“公家人”。
不过,生于皖北农村,朱健康的成长中并没有好的学习环境。高中时就读于乡里的吕寨中学,鲜有人重视,历史上从未有人考上过大学。“也没有资源,没有经费,好一点的老师都调到县城去了。我记得当时有两三门课基本上没老师上”,有老师讲的课也很枯燥。现在已是植物生物学家的朱健康,当年最讨厌的课程之一就是生物课。“要记很多名词,又没太多的原理性、机理性的内容,因此可以说是很不喜欢。”
1982年,朱健康第一次参加高考,生物没及格。虽然是全校第一名,但距离中专分数线还差三分。“在那样的环境里,落榜这件事,现在看也不奇怪了。”今天讲起,他笑着一带而过。但在当年,对于一心想要挣脱农村的朱健康来说,“那打击可大了”。
朱健康选择复读。一番周折后,他被临泉一中的洪新民老师收到应届毕业班里做插班生。与吕寨中学不同,在这里,五六十人的毕业班,每年都有十几个同学考上大学,大家都特别刻苦,天不亮就起来读书,很晚才睡觉。“大家都抱有希望,真是特别努力啊!”
最初,朱健康的成绩在班上倒数,到临近高考时已经名列前茅,但那时他还不敢为自己设定太高的目标,于是放弃了报考清华、北大。但他坚持要学自己感兴趣的专业,在他看来,兴趣比名校更重要。放眼人生长路,追寻自己的热爱比一时的荣光更为宝贵而长远。最终,凭借《中学生数理化》杂志封面上的一张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土化楼的彩色照片,朱健康决定就考这里。“我喜欢化学,接收我去插班的洪新民老师就是教化学的,我中学时上课爱睡觉,几乎每门课都睡觉,只有化学例外。”
1983年,朱健康考入北京农业大学土壤农业化学专业。行将北上求学,整个暑假他都沉浸在喜悦中。比起第一次坐火车的新鲜、走出农村的成功,更让朱健康期待的是终于开始进入自己感兴趣的化学领域。
兴趣是始终不变的追随
为了化学而来,进入大学后,朱健康又发现土化专业也非自己所爱,“觉得不够有挑战,好像很多重要问题都已经被人家解决了”。同时,他被丰富多彩的校园社团生活吸引,兴趣的触角伸得更广更远。在武术社团,朱健康认识了两名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外教,他们是植物病理方面的博士后,同时在农大教英语。他们因爱好武术而结缘,彼此成为好友后,朱健康经常跑到实验室跟他们“蹭”实验,慢慢产生了兴趣。大学四年级时,他放弃了学校保送本校研究生的名额,决心报考北大生物学研究生。

“真正走进生物学以后,发现里面还是很有逻辑性的,有很多重要的问题和未知的东西,慢慢也就有兴趣了。”虽然朱健康也想不起自己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对植物学发生兴趣的,但是在不断与植物对话的过程中,他找到了宝贵的热爱和质疑精神。
伴随着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出国潮,朱健康在北京大学读了一年生物学硕士研究生后,也加入了出国的行列,奔赴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攻读植物学硕士。同那时出国的绝大多数人一样,他感到强烈的震撼和冲击。“那是我第一次坐飞机,到洛杉矶上空,快降落的时候看下面高速公路上车流涌动。当时不知道高速公路,以为道路是大江大河,在流动。”比生活水平的差异更让朱健康感受强烈的,是学术思维和思考方式的改变,不过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自然而然,且充满享受的转变过程。“美国的学术氛围很好。在高校也好、研究所也好,大家关心的就是学术问题,很少关注这荣誉那荣誉、这评价那评价。”老师、同学勇于质疑的科学精神也让他深受触动,在朱健康眼中,这种纯粹、求实的科学态度,特别重要。
有一件事朱健康至今记忆犹新。他在北大读研究生期间,一位“气功大师”到学校做了一次讲座,在那次讲座上,这位“大师”把他绕得云里雾里,一会儿是飞檐走壁,一会儿是包治百病,“我竟然都信了”。当时在场的很多师生和他一样也都信了。
三年后,已是美国普渡大学博士生的朱健康又碰到了这位“气功大师”。“大师”的报告内容与三年前类似,朱健康却越听越烦,“气功大师”说的每一句话、举的每一个例子他都无法相信了。“他所说的每一个实验都没有具体的地点、时间,基本是泛泛而谈,没有出处,一点都不严谨。”比如,“气功大师”说他发功能改变细菌的DNA,以此治愈疾病,但在报告结束后,朱健康问“大师”“DNA是什么”,他却表示完全不知道。
“在出去以后,真的做起研究了,科学素养有了,碰到什么事儿都要自己问问题了。有了质疑精神之后,人会变得较真起来,很容易看到那些虚假的、不可信的,或是新鲜的、奇怪的东西。做科学就是这样,要看证据,你什么数据说什么话,你下什么结论的话就得靠这个数据,你这个数据是不是能支持这个结论。”
在美国期间,朱健康主要从事植物逆境分子生物学研究,在植物抗旱、耐盐与耐低温方面取得了杰出成就。自然界里的植物形形色色,雪山上有植物,沙漠里面也有植物;陆地上有植物,江河湖海里也有植物,它们在各种恶劣的环境里都能生存,而且长得很好。朱健康解释:“植物很少生活在一个所谓的理想条件下,即光、温度、土壤营养成分等都处于最理想状态,这种状态是不存在的。在不是理想的条件下笼统称为‘逆境,比如温度太低叫低温逆境。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有些植物能够适应,有些就不行,这到底是什么原理?在研究、理解了以后,对农业是有指导意义的。”
“我在读博士的时候,跟这方向就有关系,开始接触这个领域,觉得还是蛮重要的,也很有意思,有很多问题没解决,到现在还有很多重大问题没解决,自己当时也有点想法,想尝试着去做点贡献。”
“从我自己的经验来讲,做科研关键是要有兴趣。”朱健康说,“有兴趣才愿意花时间、动脑筋钻研。如果对做的事没兴趣,那么再苦再累也不太可能有大的突破。”追随兴趣一路探寻,这个最初讨厌生物课的青年成为一名植物生物学家。他33岁受聘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植物科学系正教授,42岁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三位在中国内地接受大学教育的美国科学院院士,也是当时最年轻的美国科学院院士之一。
植物逆境研究大有可为
2012年,朱健康回国,着手组建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逆境生物学研究中心(简称“逆境中心”),并出任中心主任。这是全国唯一一个以植物抗逆科学与技术研发,培育抗旱、抗盐、抗冷、抗热、抗病高产农作物新品种为己任的科研國家队。
朱健康解释自己所做的是提高植物在逆境条件下的生存能力。“我们中心提出一个‘Dream Plants的口号,‘理想植物——既高产优质,又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小一点。你做梦去想,最理想的植物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干旱没关系,它抵抗过去了,等到下雨又长了起来,或者水分利用率提高了,可以少灌溉一点。”在全球气候变化加剧、异常天气增多的情势下,要让植物能更好地适应环境,能在干旱、盐碱、高温、低温等不利于植物生长的环境下,使植物能够有很好的产量、质量,少投入、少用农药、少用化肥,减少对环境的污染,不怕天气的忽冷忽热、不惧病虫灾害的来袭,这对我国乃至世界的粮食安全,意义都不言自明。
上世纪90年代末起,朱健康就经常回国进行各种交流、讲学,切身感受到中国科研水平的提升和科研环境的向好。“搞科研是一件很奢侈的事,需要极大的资金投入,不是自己对什么问题感兴趣就能凭个人能力折腾成的,需要很贵重的仪器、昂贵的试剂、大量的经费,都是国家、纳税人的钱,所以我们要负责任。”
在中科院上海植物逆境生物学研究中心网站上,朱健康写下这样的希冀:在世界人口迅速膨胀,环境持续恶化的今天,如果没有革命性的粮食问题解决办法,那么数十亿人口将在未来几十年面临食物短缺的问题。上海植物逆境生物学研究中心的首要使命就是通过不断的创新研究来解决植物生物学难题,为提高农作物产量和农业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此外,将富有创造力和活力的青年科学家们培养成未来植物科学领域的领军人物,也同样是我们的重要使命。
朱健康为这个使命奋斗着。在他心中,国际一流的研究所不仅要能培养出一流的学生,还要把世界各地的一流人才引进来。“过去多少年,我们在国外给别人打工。现在中国的实力强大了,也可以给别人提供好的平台,大家合作解决科学难题。”
如今,逆境中心有将近一半的课题组长是来自海外的非华裔科学家,不同的思维方式在这里碰撞交叉、兼容并蓄。“文化、教育背景不同,思维方式和学术观点也往往不同。大家带着不同的想法互相交流,学术才更有多样性、更有生命力。”朱健康说。
成立6年来,逆境中心聚焦基础研发和转化应用,在新机制、新技术上取得多项突破,让国际同行刮目相看:
——发现分散式的植物胁迫感应机制。此前科学家们只在细胞膜上寻找逆境胁迫感受器,朱健康团队则发现,细胞壁、叶绿体、线粒体、内质网、高尔基体、过氧化物酶体等都存在着各种逆境胁迫的感受器。该发现颠覆了传统认知,从而引导科学家拓展视野、发现更多关键的胁迫感受器,将对该领域的快速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提出植物DNA甲基化水平平衡器这一新概念。DNA甲基化是调控生长发育和环境应答的重要因子,它就像是一个表观遗传的“温度计”,可对生物体生长发育和逆境应答精准调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应用价值。
——发挥跨学科优势,发明抗逆技术、新产品。他们通过化学学科知识体系筛选到能提高植物抗旱性的小分子化合物AM1,具有稳定、高效、使用灵活简单、成本低、通用性强等明显优势,短期内持续喷施就可提高作物的存活率;利用遗传学的技术与方法增强植物抗逆的受体基因,再结合小分子化合物方法,可使植物的抗逆性更上一层楼。
——提出耐逆作物可高产优质化的育种新理念。一般而言,植物的抗逆性与高产优质难以兼得,逆境中心的研究则发现,藜麦、苦荞、糜子等作物既有抗旱性又耐贫瘠,同时又具有营养均衡的特点。这一育种新理念为保障粮食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开辟了一条新途径。
此外,逆境中心在植物抗逆生物技术开发和应用方面也成绩斐然:建立了一项通用、高效地鉴定蛋白激酶底物的新技术,实现了CRISPR/Cas9基因组定点编辑系统在植物基因组中的高效编辑,利用改进的CRISPR/Cas9系统高效和特异性地实现单碱基改变,利用双生病毒载体系统实现CRISPR/Cas9对水稻内源基因的高效定向敲入……这些新技术将成为推动植物科学未来发展的“利器”。
今年5月,朱健康将植物基因编辑技术产业项目落户山东济南,项目目标是5~8年内培育不少于50个主栽品种。

成绩斐然,朱健康却远未满足。有时,他也会焦虑:“做科研不能就为了发表几篇论文,必须要解决真问题。现在,在模式植物上,一些理论上的探索是有些突破的,认识更近了一步,但把这些成果再用到生产实践上,真正达到增产,或者是在逆境下减少损失,还需要更多的工作,我们正在努力。其实理论层面还有很多问题没解决,它是很复杂的问题,解决了几个问题呢,还有更多的问题冒出来。年轻的时候觉得什么都有可能,现在年龄大了,怎么还有那么多问题解决不了。”朱健康有些抱歉地笑了笑,手习惯性地抓了抓头发,鬓角已经有些花白。
从偏居一隅的皖北农村家乡走来,直至成长为著名的植物生物学家,朱健康也曾无数次经历实验失败,也曾实验结果没达到预期,也曾多次被专业期刊拒稿……困难和坎坷,几乎是他每天都要面对的事。不过,在朱健康看来,这很正常,正如植物能在逆境中成长,人生也应该经得起逆境的涤荡。
植物学上有一种现象,植物的幼苗在温室里育苗出来后,都会长得很好,像孩子一生下来在医院和家里面的温床上一样无风无雨。但是每一株幼苗在生长一段时间后,都要经过一个在大田里炼苗的阶段,让它们经受一下不那么好的环境的历练,然后才能真正适应田里的自然环境。“这就是逆境的锻炼。其实人也一样,从小在家里父母关爱着,上学后,老师呵护着、保护着,但人最终要到社会上去的,要有自己的工作、生活和事业,要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经历各种场景,因此人的成长也需要逆境的历练。”
对自己的孩子,朱健康只提出两个“要”:第一是身体要强,这是基础;第二是心要强,能够经受打击。对学生,他也是这样要求。而谈到做一位科学家,必须具备怎样的基本素质,朱健康则收起微笑,严肃地回答道:“坚韧不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