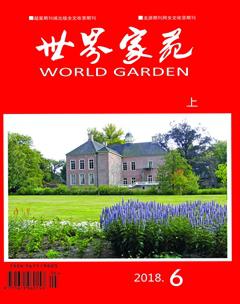日本“女儿节”发展原因初探
摘 要:日本“女儿节”作为日本的一个重大节日,被一般家庭所重视并被隆重庆祝,用来祈福家中女儿健康幸福地成长。然而,日本“女儿节”却起源于已经消失在中国广大汉族区的古代“上巳节”。两者命运的巨大反差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思考。本文对上巳节在中国消逝的原因做了简要梳理,初步分析了日本女儿节不断发展的原因:一为信仰对象的确立与特性,二为庆祝仪式的继承与发展。以此折射出日本文化的特性,同时也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提供积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日本女儿节;上巳节;发展原因
日本女儿节,日语称作“雏祭”,是面向全国女孩的一个盛大的节日,每年都被隆重庆祝。而在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女儿节”并非一个节日,它主要包括三月三日的上巳节、五月五日的端午节以及七月七日的七夕节和九月九日的重阳节。日本的“女儿节”的直接来源是三月三日的上巳节。令人不解的是,在中国这四个重大节日中,唯有上巳节在流传中慢慢消失,其他三个都成了家喻户晓的重大传统节日。幸运的是,它传入日本后,与日本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形式和内容上得到了不断地充实和发展,异变为一种有别于中国传统上巳节的特殊节日,并带有浓厚的日本色彩。本文从一般民俗学的角度出发,寻找日本“女儿节”发展的原因,初步归纳出两大方面,也体现出日本文化的特性。
一、上巳节在中国消逝的原因梳理
中日兩国在文化交流上有着漫长的历史。在节日民俗方面更是有很深的渊源。作为日本五大传统节日的女儿节,其实来源于中国古代的上巳节。作为日本女儿节的原型,甚至可以称之为母体的上巳节为什么在历史的长河中渐渐消失了踪影呢?
中国的许多学者关于上巳节的流变做了大量研究。李心纯(1996),通过考察中日两国三月三习俗的传承与变化,认为:中日两国的三月三虽然同源,但发展脉络不同;一个民族民俗的发生发展过程受社会生产力和物质文化水平制约;节日民俗由单纯地避恶驱邪向娱乐、求美、求发展的方向转换,体现了人的需要由低层次向高层次升华的过程;民俗反映了世风世俗。之后,刘芬芬(2011),运用民俗学理论和非物质文化保护理论,结合田野调查,阐明了中国上巳节的起源、历史变迁,并探究了它的消失原因及在少数民族区域遗留的原因并从文化方面提出了改善方法。唐群(2013)也对上巳节的传承做了进一步研究。在古代民俗习惯的基础上,提出了具体的传承方法——“临水祓禊”“汉服盛装宴游”,并举行穿汉服行笈礼女子会等女性活动。
二、“女儿节”在日本发展的原因分析
在日本,说起三月三女儿节,众所周知,是家中有女儿的一般家庭,为庆祝女儿健康成长生活幸福,于每年三月三日隆重举办的一个传统节日。一般被称为“雏祭”,还被称作“三月节”“上巳节”“雏节”“桃节”“人偶节”等等。日本女儿节通过中日文化交流,传入日本,在平安时期以“流雏”形式被当时的上层贵族接受。经过千百年的历史沉淀,发展成为日本女儿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此这般经过千百年的历史沉淀发展成为日本女儿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女儿节,本是渡来之物,却不断发展变化,深深打上日本文化的烙印,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和式习俗而焕发生机。
(1)信仰对象的确立与特性
现代日本女儿节中,最常见的是坐雏人偶。一般五层15人。摆在雏架上最上层的就是天皇天后两个内里雏。内里是天皇居住的寝宫,一对内里雏威严地端坐在雏架最上层,是幸福的象征。接下来是侍奉天皇皇后的三侍女。衣着相仿,姿势各异。中间的女官端坐着,双手端着酒杯,没有眉毛,是个结过婚的女官。正对中央女官的右边是一个半蹲着双唇紧闭拿着祝酒樽的女官。左边是一个半蹲着,拿着劝酒樽开口劝酒的女官。第三层则是五人啐子,分别演奏笛、太鼓、小鼓、大鼓、谣的五位能乐艺人,表情各异,着实有趣。第四层则是随从,手持弓箭护卫宫廷的人。正对雏架而立时,左边的年轻人是右大臣,留着一席银色长须的是位于右边的左大臣。最后登场的就是三佣人,他们隶属于宫中杂用科,指的是一般庶民。分别是酒后爱发脾气、酒后爱哭鼻子以及酒后痴笑之人,也被称作“三人上户”(上户在日语里表示好酒之人),手持“台笠”、“踏台”、“立伞”,一副武装好出门的样子。如果手持笤帚、簸箕、竹耙,则表示宫中大扫除了。以天皇皇后为中心的人偶雏架,形态迥异,甚是盛大。从天皇的起居生活到娱乐活动再到政事辅佐,男女老幼,以天皇为中心,各司其职。民众毕恭毕敬地祭祀天皇皇后,对天皇的尊敬之情溢于言表,可以说日本女儿节在信仰对象方面已经有了确定的祭拜人物。
而中国古代的上巳节却没有确定的信仰对象。关于这一点,周暁波,在中日三月三的对比研究中,也明确指出中日两国三月三信仰对象的差异。在三月三的初始阶段,中日两国都是没有明确的信仰对象的。中国古代的上巳节,从功能方面,以除魔辟邪为基本思想,却没找到唯一确定的信仰对象,不得不面对宋代朱子学的森严的戒律,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而日本的三月三却在慢慢摸索中找到了精神寄托,创造出来了信仰对象:天皇或亲王。
此外,有的学者还指出上巳节因与中国传统节日清明节时间上接近,从而得出被其合并的结论。在民俗消失的长河中,肯定有一些功能相似的节日互相碰撞,但上巳节和清明节是两种功能差异很大的节日。清明节以祭祀祖先为主,上巳节则是祓禊祛秽进而发展为男女交欢的娱乐性节日。而且时间上相近的合并不能单纯地说明问题。在日本,万物复苏的季节里,也是樱花烂漫的世界。“花见祭”何尝不是春季里亮丽备受日本人喜爱迷恋的一角?而且赏花节也没有被日本女儿节吞并,反而是因为樱花在日本人心中独特的存在而焕发着旺盛的生命力。
日本“女儿节”的发展不仅在于确立了天皇崇拜对象,更在于这一对象的特殊性。
“神话传说是节日的灵魂。”日本民众对天皇的民间信仰来自于古代的神话传说。不管是人格化的神,还是神化的人,天皇在日本人心中扮演着独特而魅力无限的角色。具有人和神两种特性的天皇是民众心中最深处涌动的精神之泉。所以在时代的长河中,天皇信仰自然而然被融入到节日民俗女儿节中。但这并不是在节日形成之初就存在的,而是在人们从内心接受了日本女人节之后慢慢寻觅到的精神寄托和信仰。
(2)庆祝仪式的继承与发展
日本女儿节主要有两种庆祝形式:流雏和坐雏,即流放人偶和摆放人偶这两种方式。
日本女儿节源于古代“流雏”习俗,相传是在平安时代中期,流传着这样的风习:把代表灾祸和不祥的纸质或稻草人偶,拿到附近的河流和海里让它随波流走。一到三月三日这一天,女孩就会把象征自己的人偶捧在手里,轻柔地抚摸一次,对着人偶再吹一口气。代表着一次摩擦一次呼吸。如此这般,就把自己的污秽转移到了人偶身上。然后把这样的人偶放入河水中,随着水流飘向远方,女孩的身心也会变得洁净。借助于这种简单的动作来表达祓禊仪式的神圣和祝愿。
坐雏在流雏的基础上随着时代的推移渐渐登上节日舞台。室町时代,结合中国古代上巳节的“流雏”以及日本贵族社会的“人偶游戏”中的文化元素,整合出人偶的一般形体。江户初期,出现了“立雏”和“坐雏”,摆放的人偶只是一对男女的“内里雏”,也就是现在位于雏壇最上层象征天皇皇后的人偶。此时的人偶除了充当人本身污秽的替身之外,又增添了驱除一生灾祸的祭礼意味,发展成为武家子女以及身份高贵家中女儿的嫁妆,逐渐变得华美奢侈;其中有身着十二单衣的“元禄雏”、大型的“享保雏”等人偶,而且人偶身后的屏风也被镶上金箔,尤为华丽。到了享保年间,如此奢侈之风,引起政府的担忧,于是根据民众的消费水平,政府颁布明文法令限制人偶型号。遵守规矩的日本民众,并没有跟政府唱反调,而是依据规定,将人偶精致化,做成了几厘米大小的“芥子雏”。可见,人偶深得人心,民间人们智慧无穷。江户时代后期,出现再现宫中优雅裝束的“有职雏”和与今天雏人偶密切相关的“古今雏”。到18世纪末,逐渐出现“啐子人偶”,幕末开始增加了官女、随身、仕丁等人偶,即逐渐发展成为我们今天见到的“坐雏”。
总之,“流雏”主要举行“祓禊”仪式,让转移自身灾祸污秽的人偶随波流走达到自身洁净的目的。现在日本女儿节大多以“坐雏”的形式展现。但在奈良县五条市阿田町仍然保留着这样的流雏形式:按家中女儿人数,用千代纸折出相应数字的人偶,并在其头上放上祛病消灾的大豆,放到人偶壇上。4月3日(旧历3月3日)这一天,取人偶于竹皮舟上放流到吉野川。鸟取县鸟取市用濑町现在也沿袭着相同的做法。
从这两种主要的庆祝仪式中,可以归纳出以下两种变化的特点:
第一、形式从简单到多元。从出现先后的形式来看,流雏为最古,也是最简便易行的。制作人偶,于节日当天放入附近水中,既能亲近大自然还能从祓禊仪式中得到净化身心的目的,实用性强。而坐雏虽然在时代变迁中发生着很大变化,但基本形式只是往人偶壇上摆放人偶,同样简便易行。在女儿节的前一两周,家中有女儿的家庭就开始往人偶坛上摆放人偶,一直保存到三月三日当天的黄昏时分。再没有比既能达到节日祭祀祝福目的又易操作更深得人们喜爱的节日了。单纯地摆放动作,至于什么样的人偶坛,什么样的人偶,都是根据家庭的经济状况和个人喜好来决定,没有严格的限制。而且人偶还可以重复利用,今年摆放过的偶人来年可以重新排上大用场。重要的是对家中女儿的健康成长平安幸福的祝愿和对信奉天皇神的心意。另一方面也要求家中母亲好好存放,做好家务整理工作。可以说并不是对日本家庭主妇的硬性要求,反而把家中母亲得心应手收放人偶的过程,转变成对家中女儿礼仪言传身教的绝佳机会。这又体现了具有女儿节特色的教育功能。
第二、传统和现代的融合。日本女儿节历经历史沧桑在今天依旧焕发着活力,在形式方面除了最初的简洁易行之外,积极吸收现代元素更是使其继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元素。日本女儿节在信奉天皇信仰的精神寄托下,积极吸收时代元素,不断学习创新,越来越受瞩目,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也逐渐被异国他乡的人们认识喜爱,展现着无穷的魅力。比如每年三月三日,东京迪尼斯乐园就会举行盛大的活动。从民间邀请303位“民间公主”,和米老鼠唐老鸭等动画明星一起过女儿节。颇有与民同乐的盛大场面。当然,日本女儿节也不是一味地追求时尚,而是在庆祝形式上加以创新,融合新的时代元素,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并充分享受节日的快乐。
日本女儿节作为日本的传统节日,在保护继承传统方面仍是不遗余力。在商业化的人偶中,除了前面介绍的天皇系列的偶人,还增加了日本古典名人的形象。比如由历史上著名歌人柿本人麻吕、小野小町、菅原道真组成的“三歌人”,再加上日本历史上的文学才女清少纳言、紫式部、小野小町的“三贤女”,独具特色,文化韵味十足。同时,在节日饮食上也保留着传统的和食文化。散寿司、菱饼、白酒、米花糖、蛤等,无一不展现着浓浓的日式食物的特色。在一家团圆的餐桌上,人们品尝着节日的味道,享受着传统文化带来的精神上的快乐。
可以说,日本人是“喜新不厌旧”的。日本女儿节,在人偶的形式和与民同乐的方式上紧跟时代的步伐,在不忘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加以精致,形成了独具风味的日本女儿节。另一方面,精神世界也一直被具有神性和人性的“现人神”天皇所滋养。
四、结论
中国传统的上巳节由于种种原因没能适应社会的发展而在中国慢慢消失,传入日本后与日本传统文化相结合,增加了特定的信仰对象,在形式上由简单走向多元,并在此过程中结合日本传统文化,不断适应社会的发展,成为日本独具特色的传统节日流传至今。通过对比该节日在中日两国中的演变,可以看出日本文化的特性,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对中国传统节日在今后的传承和发展做一些有益的思考。
参考文献
[1] 李心纯.从中国古代的上巳节到日本的雏祭[J].日本学刊,1996(2)
[2] 邱雅芬.日本的人形信仰和中国文化的关系[J].日本学习和研究,2010(4)
[3] 苏亚梅.日本女儿节偶人[J].WORLD CULTURE,2008(7)
[4] 方志娟.浅议日本的桃信仰[J].商业文化 学术探讨,2011
[5] 何颖.民间上巳节的习俗流变[J].新西部,2015(17)
[6] 管纪龙.日本传统节日中的中国文化情结[J].江南大学学报,2005(6)
[7] 唐群.上巳节略论及其传承的思考[J].秦汉研究,2013(7)
[8] 周晓波.中日传统节日的比较研究[M].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12)
[9] 千葉公慈.知れば恐ろしい日本人の風習[M].東京:河出書房新社,2012(12)
[10] 武光誠.知っておきたい日本のしきたり[M].東京:角川ソフィア文庫,2008
[11] 董晓萍.中国民俗文化软实力发展战略专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1)
[12] 王金林.日本人的原始信仰[M].宁夏: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1)
[13] 刘德润.日本古典文学赏析[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1)
作者简介
申文静(1994——),女。吉林大学日语语言文学专业2016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日本近现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