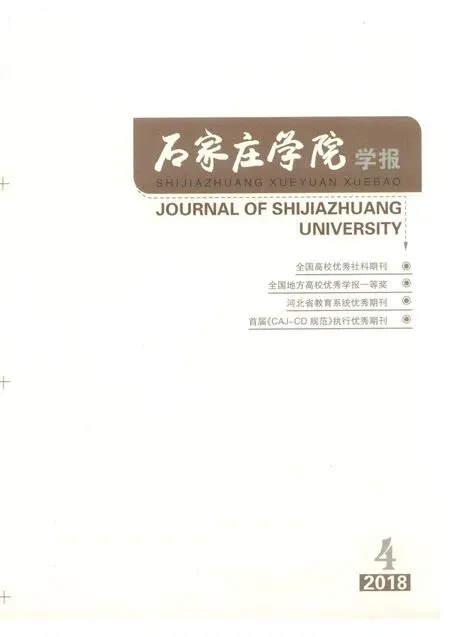理学宗派的文学转向
——南宋艾轩学派的地域诗学属性
常德荣
(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 200020)
宋代以降,江南诸地文学经历凝定、转化、提升,其各具特点的地域色彩渐次形成。作为宋、元、明主流学术思潮的理学,在特定历史时段中,参与进了地域文学的塑造,甚至在某些区域,特定理学宗派与地域文学传统的生成、演变密不可分。因学术观念上的差别,理学各宗派对诗文的态度亦不相同,从而造成理学与文学的关系颇为复杂。有识于此,可更为细致、客观地审视理学与文学的联系。兹就南宋艾轩学派与地域诗学之关联试加揭示。以此为例,展现理学宗派的诗学性与地域化、地域化的理学宗派对地方文化与文学的影响,进而对理学与文学及地域文学关系作一新的研究。
艾轩学派为南宋时期别具特色之理学流派,“终宋之世别为源流”[1]1470。其主要传承脉络为:创于林光朝(号艾轩),一传林亦之(号网山),再传陈藻(号乐轩),三传林希逸(号竹溪)。其成员目前所知有80余人,除个别者外,籍贯或为莆田,或为与莆田山川相连的福清,主要学术活动与影响则集中于莆田地区。
一、道艺双修:诗学生成的学理背景
林光朝受业于陆景端(字子正),陆景端受业于尹焞,尹焞则为程颐高徒。黄宗羲说陆景端“学于和靖(尹焞),学问精深,造履清白,横浦(张载)极称之”,又称陆景端“晚年以和靖之学传林艾轩”,尹焞则“于洛学最为晚出,而守其师说最醇”[1]1001。从学术谱系上看,林光朝乃伊洛正统,但其创立的艾轩学派与程朱一系很不相同,表现出独特的学术品格:其一,强调践履,反对著述,其学说的传扬也主要通过心口授受,而非书册文字;其二,融通释道,尤与道家关系密切;①宋代理学本身是在吸收释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理学家对释道多保持着强烈的批判意识,南宋中期以后更是如此。林光朝及艾轩学派对释道的态度却不遮遮掩掩,旗帜鲜明地兼容之。林光朝很重视《老子》《庄子》等书的辞章、义理,曾系统研读;陈藻也曾有《庄》学方面的著作。艾轩学派对道家思想的不断吸取到林希逸手中得以系统总结,撰成《老子口义》《庄子口义》《列子口义》三书,合称“三子口义”,其中尤以《庄子口义》的影响最大。明代孙应鳌《庄子要删》、清代胡文蔚《庄子吹影补注》等均受林书启发。于此亦可见艾轩学派对中国学术思想的贡献。其三,道艺双修,不崇道贬文、因道废文,注重道与文的交融互补。其中道艺双修的特点尤为鲜明,也是促成艾轩学派衍生艾轩诗派的学术动因。
与程朱一系理学家对科举时文的排斥不同,林光朝将其作为重要讲学内容,传授给广大弟子;①林光朝《与杨次山书》(《艾轩集》卷六)说:“某授徒三十年,不过为场屋举子之习,学问一事虽稍涉其涯,而所以作语及所以传授于人,唯是一律,岂敢辄出场屋绳尺之外也。”又对《庄子》的“文字血脉”十分注意,这是艾轩学派《庄子》研究的特点,被林希逸系统总结,集中反映在《庄子口义》一书中。林光朝还留心于音乐,认为《乐经》之流传从来不是依附于文字,而是借助于音声,只有通过音乐才能发扬《乐经》之义理,因而对音乐产生浓厚兴趣,曾特意以“乐律”问题为策问题目。这均反映出林光朝对言语文辞等“末技”的重视。
宋代《诗经》学兴盛,某种程度上说《诗经》是理学沟通文学的一个纽带。林光朝反复研读《诗经》数十载,形成独立认知。孟子有言“《诗》亡然后《春秋》作”,胡宏对此曾细致解说,②胡宏解释说:“《邶》《墉》而下多春秋时诗也,而谓‘《诗》亡然后《春秋》作’何也?自《黍离》降为《国风》,天下无复有雅,而王者之《诗》亡。《春秋》作于隐公适当雅亡之后,故曰‘《诗》亡然后《春秋》作也。”(见张栻《孟子说》卷四)并得到朱熹等人的普遍认可。但林光朝对此论断却不以为然,他发扬隋末大儒王通的观点,③林光朝《与赵著作子直》(《艾轩集》卷六):“文中子以为诗者民之情性,人之情性不应亡,使孟子复出,必从斯言。”从情性的角度解《诗》,认为情性不亡,诗亦不亡,进而否定孟子言论及同时理学家的相关阐述。基于这种认识,林光朝强调单纯的义理注疏,并不能使人感知诗之深意,说:“郑康成以《三礼》之学笺传古诗,难与论言外之旨矣。”[2]卷首林希逸《诗缉序》他给门徒讲论《诗经》,不囿于《诗序》等前人注疏,而是让学生反复吟咏,在吟咏中感悟诗理、诗情,④如陈叔盥“受《诗》于先生(林光朝),尝与乐轩(陈藻)读《国风》于古寺,吟讽累夕,俄而至《采蘋》,掩卷泣,顿得《中庸》之旨。叔盥喜以告网山(林亦之),网山遂以乐轩见。先生曰:吾尝语若《诗》不歌、《易》不画,无悟入处,今于元洁犹信吾《诗》不亡矣”。(见林希逸《艾轩集序》,林光朝《艾轩集》卷首)引起情感上的共鸣。这种体悟式的治学方式,与文学上的审美体验十分接近。此主张被艾轩弟子所继承,陈藻在策问中开篇立论云:“诗,情性也,情性古今一也。说诗者以今之情性求古之情性,则奚有诸家之异同哉?”[3]卷六理宗淳祐四年(1244年)林希逸为严粲《诗缉》作序,将艾轩的这一观点进一步发扬,提升为“以诗言《诗》”,也即以诗歌的视角看待《诗经》,而非将其单纯视为深奥的义理典籍。
就是说,虽然林光朝为伊洛正传,但在南宋中期那个思想活跃、学术竞胜的时代,他却创制出别具特色的文道理论:传习义理与探究文艺可相辅相成。这一理论被林亦之明确提出。针对程门贬低艺文之论调,林亦之作《伊川子程子论》:
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仲尼之道,吾于程子不敢有毫厘异同之论。然伊川之门谓学文为害道,似其说未必然也。盖自有天地以来,文章学问并行而不相悖,周公、仲尼其兼之者乎。自是而后分为两途,谈道者以子思、孟轲为宗,论文者以屈原、宋玉为本。此周公、仲尼之道所以晦而不明,阙而不全者也。请以《六经》言之,《六经》之道穷情性,极天地,无一毫可恨者。《六经》之文则舂容蔚媚,简古险怪,何者为耳目易到之语,是古之知道者未尝不精于文也。苟工于文章而不知学问,则大道根源必暗然无所识;通于学问而不知文章,则古人句读亦不能无窒碍,是皆未可以谈《六经》也。……学者欲无愧于《六经》,无惭于周公、仲尼,则学问固为大本,而文章亦不得为末技也。[4]卷三
这是艾轩学派道艺双修理论的“檄文”,也是考察宋代理学与文学关系的重要文献。林亦之认为“自有天地以来,文章学问并行而不相悖”,所以学问固然是学者之大本,但“文章亦不得为末技”。《六经》之道与《六经》之文均是儒家之事业,二者不可偏废。在周公、孔子那里,道统与文统是天然合一的,此后裂为二途。程氏虽在《六经》之道上无有遗漏,但忽视了《六经》之文,因此称不上“集大成”。南宋理学家之中,敢于非难程子者并不多见,而敢于在文道关系上与程子针锋相对者,尤显得大胆而另类。更可深思者,伊川嫡传朱熹与当时之浙东学术、江右心学多有尖锐之冲突,而于批驳伊川的艾轩学派独无异词,其中缘由耐人寻味。⑤林亦之卒于1185年,朱熹卒于1200年。林亦之讲学于莆中,莆中与朱熹讲学之所毗邻,朱熹对艾轩学派的学术主张当有所知晓。林希逸《论文有感》云:
纷纷见解何差别,豪杰还须间世生。识在雷从起处起,文如泉但行当行。均为千载无双士,莫问三苏与二程。丹井红泉南谷老,似渠宗旨更难明。[5]卷五
“识在雷从起处起”指邵雍、程颐论道之典,⑥吕本中《童蒙训》卷上载:“一日(邵雍)与伊川同坐,闻雷声,问伊川曰:‘雷从何方起?’伊川云:‘从起处起。’”“文如泉但行当行”指苏轼论文之事,⑦苏轼《论文》云:“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石山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己矣。”林希逸认为他们均是“千载无双士”,既文与道在他看来同等重要;“丹井红泉南谷老”指林光朝、林亦之、陈藻,①林光朝、林亦之长期讲学于红泉、东井间,陈藻葬于南谷。“似渠宗旨更难明”之“宗旨”便是道艺双修之理论,在道统与文统割裂的情况下,这一宗旨没有得到弘扬,林希逸对此十分惋惜。
理学在形成、演变过程中面临诸多挑战,与文学之间的紧张关系便是其中之一,艾轩学派道艺双修的理论则从根本上消解了这一问题,为理学与文学关系开启一种新的发展路向。艾轩学派的三位宗师林光朝、林亦之、陈藻,分别获得文节、文介、文远的谥号。弁子才在艾轩《谥议》中说:渡江以后“逮至隆乾之间,文章之士复振而起”,而林光朝居其一。又云:“道德博闻曰文,能固所守曰节。公之学问溢为词章固已不可掩,而高风特操表表在人,尤非时贤所敢望以及者。呜呼,以如是之节,有如是之文,此公所以特立于孝宗之朝,而无愧于一时诸贤之盛欤!请谥公为文节。”[6]卷十弁子才《谥议》虽然按照传统谥法,“文”并不指文章、文辞,②《逸周书·谥法解》云:“经纬天地曰文,道德博厚曰文,勤学好问曰文,慈爱惠民曰文,愍民惠礼曰文,锡民爵位曰文。”但从牟氏这一解释来看,显然宋人将文章、文辞方面的含义层累到了“文”之谥号中。故而,文节、文介、文远之谥号,可理解为是对艾轩学派道艺双修之宗派特点及其文学成就的盖棺论定。
二、“诗因学成”与“学因诗传”:学派与诗派的互为依托
梳理艾轩学派演变历程,可以发现其与诗歌的关系不可剥离,学派之道艺双修等理念和宗派成员间的紧密联系是诗派生成的基础,诗学观念的凝定和传承则推动并延续了学派的发展。
从艾轩学派所呈现出的“学——诗”关系着眼,可将其划分为前后两个发展阶段。前期姑称之为“诗因学成”的阶段,时间大致从林光朝将伊洛之学引入莆中至林亦之去世,即高宗绍兴八年(1138年)至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年)。在这一时期,艾轩学派的基本思想得以形成,艾轩学术占据了莆中的文化空间,并引起南宋学术界的注目。在进行学术开拓的同时,林光朝、林亦之等人在道艺双修观念影响下,积极从事诗学活动。依托于艾轩学术的强力影响,艾轩诗派随之产生。后期姑称之为“学因诗传”的阶段,时间大致为林亦之去世之后至元初。林光朝于淳熙五年(1178年)去世,而淳熙年间正是南宋理学四大家朱、陆、吕、张思想的成熟期,随着林光朝的离世,艾轩学派对整个南宋学术的影响急转直下。到淳熙十三年林亦之去世,艾轩学派在学理上的建构基本完成,其外向的扩展戛然止步,影响退缩至莆中一隅。这时的艾轩学派,思想上的创新已逐步消退,宗派成员多践履师说,而道艺双修的宗旨使他们将诗歌创作发展为重要的宗派活动;用诗歌记录学道所得,传递彼此间的情谊;艾轩诗学被不断传衍。至此,诗派成为维系学派存在的重要形式。
林光朝在17岁赴京赶考时第一次听闻伊洛之学,24岁时于理学颇有所得。大概也就在此时,林回年辟东井义学,命艾轩为宗族子弟讲学,是为艾轩布道之始。在林光朝开始学术活动的同时,其诗学活动也随之起步。林光朝在学习儒学之前曾沉浸于诗学,自言“幼岁闻李太白、石曼卿之为人,即踊跃道其事。又初读《晋书》,见一样人物如寒蝉孤洁不入俗调,此心甚乐之”[6]卷六《与杨次山书》,李白、石曼卿、晋人风度都具有洒脱浪漫的诗人气质。林光朝在以这类豪杰之士为榜样的同时,对他们所具有的文学精神一定有所体悟。无怪乎在成为理学宗师的同时,其诗文也被时人宗尚。孝宗时,林光朝曾因鲠亮个性且“以文学推重于时”,被丞相虞允文举荐。[7]11799陈宓说林光朝之“文为世所宗”,时人甚至将《艾轩集》视为至宝。[6]卷首陈宓《艾轩集序》
林光朝直到50岁时才中第,其外出为官的时间并不长,一生中的主要时光是在莆中度过的。林光朝生活的时代,莆中地区涌现出一批各有建树的士人,其文化生活与这些乡贤密不可分。林亦之曾说:“在昔乾淳,莆之人物最盛。其间数大老,若文节(林光朝)、次云(方翥)、景韦(郑厚)、渔仲(郑樵),皆千载人物。”[5]卷十二《次云方先生诗集序》林光朝的这些亲密学友,在文学上均有所长。与林光朝亲密往来的地方士人尚有陈昭度、黄公度、吴澥、蒋雝等,他们也是能文之人,与林光朝有着文学上的交流。③陈昭度“为文得古法,简严闲淡,理致深远”(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卷八),林光朝和方翥等人曾至陈昭度家,登堂拜母,谊均兄弟。黄公度,工诗能文,曾寄林光朝诗云:“千载有人扶古道,一时倾盖尽儒冠。不妨我辈诗肠在,要取他年酒量宽。”(见《寄林谦之》)吴澥与林光朝为莫逆之交,著述甚富,今已不传,然据文献载记可知其文思敏捷,援笔立成,诗文极精妙。蒋雝博学强记,“下笔辄数千言,曲尽其妙”。(见《闽中理学渊源考》卷八)
可想见,林光朝是在一个诗文气息十分浓厚的环境中从事学术活动的。或是出于应和朋友间的诗文唱答之需,或是因于自我情性的抒发,林光朝从未中断过诗歌创作。而且其诗作,与一般理学诗人的作品不同,并非有韵之语录,而是情韵并茂。林光朝的诗歌成就得到南宋文人的很高评价,刘克庄认为与林氏同时的众多理学宗师在诗歌上均拜下风。刘克庄对南宋诗学的一些重要观点正是在品评艾轩诗歌时提出的,如云:“唐文人皆能诗,柳尤高,韩尚非本色。迨本朝则文人多诗人少,三百年间虽人各有集,集各有诗,诗各自为体,或尚理致,或负材力,或逞辨博,少者千篇,多至万首,要皆经义策论之有韵者尔,非诗也。自二三巨儒及十数大作家,俱未免此病。”[8]卷九十四《竹溪诗序》作出这一判断之后,笔锋一转,大赞林光朝诗歌之高妙,言下之意是推艾轩为有宋一代为数不多的当行诗人。刘克庄在《艾轩集序》中说:“以言语文字行世,非先生意也。”[8]卷九十四虽说林光朝主观上并不曾想以言语文字行世,而是要以道德学问立身,但他所开创的艾轩学派在随后的近百年中恰恰以言语文字行世。刘克庄在《艾轩集序》中不避重复两度申说“以言语文字行世,非先生意”,透漏出的正是艾轩学派以言语文字行世这一事实。
因为林光朝的示范作用,艾轩弟子们亦多能吟咏抒写,标立风雅。故而以学道为最初目的建立起的艾轩学派,同时也具有了文学群体的性质。在艾轩的众多弟子中,最先成名的当为二刘,即刘夙、刘朔兄弟,二人对林光朝“终身事之”。[9]卷十六《著作正字二刘公墓志铭》刘夙、刘朔小艾轩十余岁,却均先于艾轩去世,林光朝甚为伤痛,“笔濡不忍铭”[9]卷十六《著作正字二刘公墓志铭》。二刘师事艾轩之所得,除了纯正之义理外,便是亹亹之文辞,莆田刘氏始“以文章立家”,所谓“自大著(刘夙)、正字(刘朔)峥嵘艾轩之门,声振乾淳间,已蔚然为文章家矣”。[5]卷二十三《宋龙图阁学士赠银青光禄大夫侍读尚书后村刘公状》林光朝反对注疏析句,而是通过感悟的方式传道授业。有人甚至因感悟而赋咏,因赋咏而得雅号。如魏几“从林艾轩以克己复礼问,艾轩曰:‘五湖明月。’因以颖悟,赋《丹霞夹明月》,有‘半白在梨花’之句,人以‘半白梨花郎’目之”[10]卷八。当然,最能光大艾轩学术的一传弟子当为林亦之。林光朝去世后,林亦之嗣其讲席,继续讲学红泉、东井,使艾轩学术得以延续,而林亦之的文学造诣在众多弟子中也最高。刘克庄称其“论著句句字字足以明周公之意,得少陵之髓矣。其律诗高妙者绝类唐人,疑老师当避其锋,他文称是”[4]卷首刘克庄《网山集序》。从艾轩学派到艾轩诗派的延伸,林亦之是其中的重要一环。道艺双修的观念,也在林亦之手中被强化和明确。
林光朝、林亦之等人所确立的这种讲学论艺风尚,使艾轩学派具备了衍生艾轩诗派的所有要素。林希逸总结说:“老艾一宗之学,固非止于为文,而艾轩之文视乾淳诸老为绝出。一再传之间,如大著、正字二刘,季冶黄怀安,网山、乐轩二先生,黄石吴叔达,是皆笔斡造化者。”[5]卷十二《丘退斋文集序》也就是说,在林希逸这位艾轩之学的殿军看来,经过林光朝、林亦之等人在乾道、淳熙年间的文事活动,艾轩诗派也便于此时顺理成章地出现了。
林亦之去世后,艾轩学派的诗统特征并没有中断,反而有所强化。南宋后期正是借助于艾轩诗派的延续,艾轩学派才没有淹没在朱陆之学中,保持了宗派上的独立性。林亦之之后艾轩学派领袖人物为陈藻。①陈藻生卒年,典籍阙如,然可通过现有资料考知。林希逸序陈藻《诗荃》记:“乐轩虽得寿,后网山死四十年。”乐轩为陈藻之号,网山为林亦之之号。又,林希逸《网山集序》:“艾轩自号网山山人、月渔氏,生高宗丙辰,终孝宗乙巳。”则林亦之生卒年为1136—1185年。既然陈藻后林亦之“死四十年”,则陈藻卒年为理宗宝庆元年,即1225年。又,刘克庄《乐轩集序》(《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五)云:“乐轩七十五乃死。”则可推知陈藻生年为1151年。他幼时即入艾轩之门,虽为林亦之弟子,但也曾亲聆林光朝教诲,深得林光朝的喜爱。②刘克庄《乐轩集序》:“一日(陈藻)侍网山谒老艾,艾受其拜,接之如孙。”陈藻不负厚望,将艾轩之学中的道艺双修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入则课妻子耕织,勤生务本,有拾穂之歌焉;出则与生弦诵,登山临水,有舞雩之咏焉。”[8]卷九十五《乐轩集序》其诗“真朴之处实能自抒性情”[11]1372。他教学授徒之时,将诗法作为一项重要的内容。故而其门徒多有吟癖,诗自成体。在他的引导下,艾轩后进得到了最初的诗学训练,形成了基本的诗学观念。如黄自信:
与其兄某同事乐轩陈先生,以见趣称。早岁有场屋声,亦尝走江湖矣。交游甚众,诸老颇许之。中年喜学诗,尽焚他稿,筑室以“适轩”名。日夕吟咏其间,暇则焚香鼓瑟,有萧然自得之趣。虽先世簪绂华盛,自视漠如也。生平守师学,鄙夷流俗缁黄占卜之事,至死不变。潜心经典,大抵以诗发之,故有《适轩吟稿》《纪行游湘》《游岳》诸集。……今存者一千六十八首,无非输写已意,略不蹈践古人。[5]卷二十一《适轩黄君墓志铭》
又如陈介:
长事乐轩于网山之里……君既有闻于乐轩,不以场屋为意,年三十不应举……杜门课诸
孙,寄情歌咏,于世漠如也。[5]卷二十二《陈判官墓志铭》黄自信、陈介等艾轩后进,并未留下义理方面的著述,这或是秉承反对著述、倡导践履的师训所至。然他们却能发扬道艺双修的思想,经过陈藻的引导,将学道所得和生活感悟以艺文发之。在今日看来,其身份更像是文学家而非理学家。艾轩学派在南宋后期的存在,更多地是由这些能文之士的文学活动所维系的。
陈藻弟子之中,林希逸与刘翼最为著名,尤其是林希逸,对艾轩学派的学术思想进行了全面总结。林、刘二人情谊甚深,往来密切,诗歌是他们联系友谊、交流思想的重要媒介。林希逸《别躔甫》云:“一别三秋喜我过,旧游如说梦南柯。功名会上前缘薄,灯火社中遗恨多。几劫曾为诗法眷,两鳏堪号俗禅和。相看未久匆匆去,可奈能吟不饮何。”[5]卷三二人因故一别三载,见面后感慨人生不偶,而诗歌成为他们共同的精神归宿和情感寄托。每逢生日,二人往往互致问候,写文作诗。这些作品并非全为应酬无聊之什,而是包含着他们对人生的看法及对生命价值的深入思考。林希逸在咸淳元年(1265年)回复刘翼“生日启”的书信中说:
老吾之老,谁此日之肯来;诗人之诗,后数朝而犹至。情知好我,愧曷酬君。伏惟某人,超然心游,久矣神悟。鄙夷场屋,耻为俗下之文;笑傲烟霞,真得吟中之趣。贻半山之绝句,问少陵之残年。与鬼歌
之徒,有叹辛齑之妙。[5]卷十五《乙丑回生日启·与心游刘躔甫书》所发感慨都围绕着诗歌,对刘翼不俗之文品及诗作之高妙大加赞赏。林希逸在1268年的《回生日启》中说刘翼“苦学如甘,爱诗成癖”[5]卷十六《戊辰回生日启》,是对刘氏践行道艺双修思想的称颂。刘翼作诗“初为唐语,后为晋语,晚而傲世自乐,尽去绳墨法度,自为乐轩一家之言”[12]卷三十林希逸《心游摘稿序》。可以说刘翼从陈藻处所继承的正是艾轩诗法,其与艾轩学派的师承关系,很大程度上是诗学层面的。
南宋后期,林希逸自觉整理艾轩学派三位宗师之思想,宣扬其功绩,“下车首为学者言三先生之学”[8]卷九十六《城山三先生祠》,宗派意识特别强烈。嘉定十七年(1224年),林希逸客居寿阳,裒辑林光朝、林亦之诗作,编为《吾宗诗法》,此为艾轩弟子诗派观念的成型。15年后,刘翼尚保留着这个宗门作诗范本。
可以说,道艺双修的理论自始至终都是艾轩学派的重要特质,为艾轩弟子所继承。艾轩后学在诗文创作方面倾注大量精力,且各有标立,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贯彻道艺双修之主张,形成“诗因学成”、“学因诗传”的宗派发展特点,并使艾轩学派呈现出“流而为文”的倾向,明人郭万程指出:“自道学兴,辞命多鄙,光朝之门独为斐然。”[10]卷八宋末元初之婺州学派导引了元代理学的“流而为文”,揆之艾轩学派,这一现象亦甚为明显。于此可见,理学之与文的互为依托,有其深远的学理原因和广泛的现实依据。
三、宗派·亲族·乡党:学派情怀与地域印迹
艾轩学派成员之间既有师友关系,也有亲族和乡党关系,联系十分紧密、持久,以莆中为中心交织起复杂的群体网络。为具体、全面反映艾轩学派的群体联系,谨将《宋元学案》《宋元学案补遗》《闽中理学渊源考》《莆阳文献》、林光朝《艾轩集》、林亦之《网山集》、陈藻《乐轩集》、林希逸《竹溪鬳斋十一稿续稿》、刘克庄《后村集》所载相关资料,以表格形式呈现,参看表1:

表1 艾轩学派群体联系

续表1 艾轩学派群体联系

续表1 艾轩学派群体联系
可以看出,艾轩学派成员之间除了师友关系,还有亲族关系,或为兄弟,或为父子,或为同宗同祖,或为姻亲。除个别人之外,籍贯或为莆田,或为与莆田山川相连的福清,由此构成天然的乡党关系,进而使学派具有鲜明的地域性。艾轩学派成员间的师承关系很是亲密、牢固,一旦确立,终身不逾。如林亦之淳熙年间为莆中亲友、同门写作了大量碑志文、祭文,透露出林亦之生活圈子的族群性;林亦之去世之后,陈藻几乎每年都帅徒众祭扫坟墓,留下了很多祭文;陈藻去世后,林希逸祀之于家庙,并且每次出游归来必先去祭墓。
在这种三位一体的关系网中,艾轩学派逐步与莆中刘氏、方氏、林氏等大家族相结合,使其学思在家族内部沉淀,形成家学传统,更加深入地融入莆中文化。如以刘克庄为代表的莆中刘氏家族,一家三代均与艾轩学派联系密切,①从师承关系等方面来看,刘克庄属于不折不扣的艾轩学派。《宋元学案》等明清理学著作均将刘克庄及刘氏家族列入艾轩学派,正是基于其与艾轩学派的这种师承关系。但本文中,我们没有以刘克庄为例论证艾轩学派及艾轩诗派的相关议题。之所以如此处理,主要考虑是,无论学术还是诗歌,刘克庄均转益多师,他虽长期浸润在艾轩学术的氛围之中,但其思想及诗学活动显然已经突破了艾轩学派,若再以其为论证依据,则反而不便于分析艾轩学派的实际情况。中年以前刘克庄是在艾轩思想影响下成长的,这种浸染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是刘氏家学,二是莆中文化,二者构成了刘克庄生活的主要文化背景。端平二年之后,刘克庄与林希逸亲密关系的建立,使刘克庄更直接地接触到了艾轩思想。也就是说,艾轩思想从不同渠道对刘克庄产生了影响,刘克庄一生之中与艾轩思想始终相伴。而艾轩学术对刘克庄文学精神的影响尤为突出。南宋后期,刘克庄这位莆中士人成为唯一一个称得上“大家”的文人,在诗词文方面均有建树。刘克庄文学成就的获得,虽不能妄下结论说是艾轩学派滋润的结果,但至少可以知道,艾轩学派的文化精神在刘克庄的成长过程中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他身上融混着艾轩思想,他的诗学活动中暗含着艾轩因素。反之,艾轩诗学亦通过这位晚宋文坛巨匠得以进一步浸灌南宋诗坛。或为弟子,或为挚友。刘克庄自言其与林光朝一族“累世通家”、他是林氏“通家子弟”。刘克庄祖父刘夙及叔祖父刘朔终身师事林光朝,其父刘弥正与林成季等人关系密切,刘克庄本人曾师事艾轩派中的数位宗师。②刘克庄《城山三先生祠》云:“余不识三先生,而于艾轩累世通家也,于网山子绮伯(林简)童子师也,于侯(林希逸)友也。”又,《赵忠定公朱文公与林井伯帖》云:“某为童子时,受教于先友井伯林丈(林成季)。”刘克庄曾多次详述艾轩学派的代序传承,言辞之中充满感情;并对林光朝、林亦之、陈藻、林希逸等人之诗文集作有序文,极力赞扬其学术贡献和诗学成就,肯定其道统与文统的合一。刘克庄关于宋诗的某些重要观点,也是在评论艾轩学派的作品时提出的。刘克庄对艾轩学派的推崇,引起元代学者刘壎的注意,说:“予少时熟视《刘后村集》,见其推重艾轩林公甚至,且并及其传者网山、乐轩之属。其称林公或曰老艾。”[13]卷三端平二年(1235年),刘克庄与林希逸结识,遂成密友,刘克庄写给林希逸的诗作有150多首,林希逸写给刘克庄的有70余首。二人的这种友谊一直延续到咸淳五年(1269年)刘克庄去世。临终之时,刘嘱托林为其上《遗表》。卒后,刘墓志铭由林撰写。
宗派间的相互联系是艾轩诗人一生中的重要人际网络,这深刻影响了他们的诗歌写作,使诗歌呈现出明显的宗派性、亲族性和地域性。
艾轩学派的思想特点之一在于奉行践履、反对著述,所以艾轩弟子多没有留存下学术方面的专著,但在道艺双修思想引导下,他们将人生感悟、学道体验以诗发之。于是,其诗作包含有浓厚的宗派气息。读其诗便可了解艾轩学派之学,知晓艾轩学派之代序传承。林光朝重视不言之教,让人在现实生活中感悟义理,而非刻意说教,这与朱子学有很大不同,也很能体现艾轩学派的别派特点。林光朝将此思想以诗言之:
《答人问忠恕而已矣》:南人遍识荔支奇,滋味难言只自知。刚被北人来借问,香甜两字且酬伊。
《答人问仁者安仁》:千年古道万年堤,老牯循循不解迷。牧子不知何处在,乱山荒草鹧鸪啼。[13]卷三有人向他询问忠恕和仁的问题,他并不直接解答,而是用比兴之法,给人以具体的物象、意境,让人从中感受忠恕和仁。诗歌没有说教意味,如果抹去诗题,读者恐不会将其与理学诗联系起来。林光朝曾说:“道之全体存乎太虚,《六经》既发明之,后世注解固已支离,若复增加,道愈远矣。”[6]卷十周必大《神道碑》这是艾轩学派建构其思想体系的立论基础。③魏了翁《答周监酒》说:“向来多看先儒解说,不如一一从圣经看来。盖不到地头亲自涉历一番,终是见得不真,又非一一精体实践,则徒为谈辩文乘之资耳。来书乃谓‘只须祖述朱文公诸书’。文公诸书读之久矣,正缘不欲于卖花担上看桃李,须树头枝底方见活精神也。”其思想与林光朝的“日用是根殊”、直承《六经》反对著述虽不尽同,但基本认知是相通的。又,林希逸《玄扃》:“君从何处叩玄扃,耳学纷纷莫浪听。刬尽念头方近道,扫空注脚始明经。”所表达的也是艾轩学派的这一思想。林希逸《答友人论学》:
逐字笺来学转难,逢人个个说曾颜。那知剥落皮毛处,不在流传口耳间。禅要自参求印可,仙须亲炼待丹还。卖花担上看桃李,此语吾今忆鹤山。[五]卷七
此外如陈藻《艾轩老先生文集刊传,上以揄扬其问学,下则得佛家以法布施之意,前后数君子有是志而不果,今日薄西山,幸一见此,喜成古风三篇以贺,后来之有作者且述下悰云》《悼网山》《别蔡伯畛》等诗,均体现着陈藻对艾轩宗法的认识。林希逸为林光朝、林亦之、陈藻立祠,称三先生祠,又建三文书院,有诗《三文主席刘兄翼运相别》《送三文书院陈上舍入京》《三文祠堂七月二日礼成作》等作,又其《日用》《力学》《心王》《乐轩先师挽歌词》(三首)《乐轩远日之祀岩尹方兄赋以七言用韵一首》《梦西轩旧事》、《戊午与诸友同谒犀斜南谷二师坟作》,或是其对艾轩学术的诗学阐释,或是对艾轩学派基本情况的记录,都属于“宗派诗”。王士禛说:“鬳斋(林希逸)为林艾轩理学嫡派,而诗多宗门语。”[14]卷四准确感知到艾轩学派诗歌的宗派性。因其诗作的这一特点,所以即便没有其它史料,仅通过其诗歌,我们也可对艾轩学派的基本思想和成员构成有一个较为明确的了解。
艾轩诗派主要成员中,除林光朝与林希逸二人曾出仕为官外,其他人多终身布衣。这种生活经历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们的人际交往,使得师友关系、亲族关系、乡党关系构成其主要的人际网络。而师友、亲族、乡党三者间又具有很大的重叠性,由此其诗歌中所隐含的人际关系也更具交互性,同时促成艾轩诗歌的亲族性、乡党性愈加明显。林光朝《道桐庐有诗示成季》《别方次云》,分别为林成季、方翥而作。林成季为林光朝犹子,又是林光朝的得意弟子。方翥为林光朝挚友,又是同乡。林亦之《奉题林稚春菊花枕子歌》《奉酬稚春梅花行》《戏题稚春杜少陵诗集》、《答稚春送瘗鹤铭》《答稚春所寄诗卷》《草堂同爨呈稚春》《稚春母郑氏挽词》等诸多诗歌均是为林光朝子林稚春而作,《林井伯母生日口占》《秋试后再寄林井伯》《送井伯赴上庠》《借册井伯》《暂还网山井伯以诗送别次韵》等则是作予林成季;《寄表弟章由之为理曲堆屋庐》《邑大夫范丈宠示广陵余事泠然诵之历历惨恻如在目中辄赋短篇纪所闻也》《翁丈柔中同侄昭文相访留两日既别赠以诗》《丹井陈子白母挽词二首》等或为亲族或为乡党而作。陈藻《网山先生讳日寄绮伯》,是为其师林亦之子林简而作,《陈叔盥两惠诗以一首谢》《寄刘九》《偶游白渡怀刘九》《黄石还渔溪寄刘九四首》《赠叔嘉叔平刘丈》《除夜寄妻叔刘丈》《叔嘉叔平既斩衰祝之以诗》《值事有感怀渔溪丘德基》《丘德基七十》《丘景运生孙叔南生子戏赠以诗二首》《贺丘子从迁居》《寄叔嘉叔平》《贺叔嘉生日》等诗所涉及之人均是陈藻同乡、同门,《别林肃翁》《刘躔父生男》则是为其弟子林希逸、刘翼而作。林希逸《戊午与诸友同谒犀斜南谷二师坟作》《先母忌日》《刘躔甫七十》《送三文书院陈上舍入京》《三文主席刘兄翼运相别》《和王臞轩旧题紫阁寺诗》《别躔甫》《寄刘躔甫》《送方汝则西上》等诗同样是此类作品。
艾轩学派诗歌所体现的这一人际关系,其发生的自然空间是莆田—福清一带,尤其以莆田壶山及其周边、福清网山及其周边为中心。空间上的局限性,导致艾轩诗歌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莆田—福清一带风物成为其诗作的重要支撑,此方之自然山川、人文风俗成为阅读艾轩学派诗作所当了解的背景信息。林光朝《城山国清塘》情韵悠长,颇能代表其诗歌之特点。诗云:
烛龙醉倒不开眼,遮空万里云张伞。小舟塘外日溶溶,渔歌忽断荷花风。倚岩僧舍扃深户,我来跋涉拳肩股。喘停更促短筇上,怪石周遭卧万鼓。况是秋风到此山,惟有孤鸿时往还。劳劳百年共缠缚,不似青山长自闲。古人古人嗟已远,长歌商颂归来晚。[15]卷三
《清一统志》卷三百二十七载:“城山在莆田县东南二十里,与壶公山对峙,黄石镇主山也,前临国清塘。”[16]《兴化府莆田县志》卷一载:“国清塘……唐贞观五年凿,周回三十里……水与木兰相灌注,澄波碧百顷,壶公、穀城倒影其中。”[17]林光朝讲学之地正是在壶山,可知该诗是林光朝闲暇之时游览城山及国清塘的作品。艾轩之后,莆中士人对这一水塘充满诗情,每每因艾轩而感发题咏,不妨说正是得益于艾轩的讲学与歌咏,莆中国清塘方获得如此浓郁的人文意蕴。①如陈士楚《和林艾轩城山国清塘韵》,有句“欲携三尺弹龟山,淳风一去不复还”,“嗟哉贤圣远复远,天高地下日易晚”;李丑父《城山国清塘》,有句“见说艾轩诗句好,不逢墨迹重徘徊”;余谦一《城山国清塘》,有句“艾轩当年题品处,斜阳无语想高风”。林光朝长期讲学于壶山之红泉、东井,周边之山川景物多浸染了艾轩学派的人文信息。此方之自然景物被艾轩弟子反复题咏,这既增强了艾轩学派诗歌的地域色彩,又使莆中山川具有更浓厚的艾轩学派印迹。如林亦之《重阳次日登城山》《重过红泉》,陈藻《城山》《红泉明日还福清作》《壶山二首》《城山偶题》《城山读书》《谷城山下作》等,均将莆中山川与艾轩宗法相融合。林光朝《与薛守》说:“某生长于莆,今且老矣……有去城市七八十里一处所名麦斜,可以读书终岁,足迹自不当到州郡。”[6]卷六可知林光朝晚年居住于莆田城外一处叫麦斜的地方。因为林光朝的缘故,麦斜这一不见经史的地方亦进入学派诗人的笔下。如林亦之《春晚招石门陈居士(淼)游麦斜岩破新茶因读南华齐物论二首》:“叫破残花深处眠,麦斜岩下毕逋前。”[4]卷一又其《谢林守架艾轩先生祠堂》:“双阙已嗟秋草边,两楹谁作麦堆前。”[4]卷一林亦之《暂还网山井伯以诗送别次韵》:“麦堆去后惟君胜,荔子红时送客愁。”[4]卷一句中“麦堆”当与麦斜所指为一,均是艾轩学派讲学之所。
《福建通志》卷三记载了福清县东的众多山岗,有鹿角山、风火山、网山、龙卧山等。林亦之所居之处便在网山,之所以称为网山,是因为此地居民以捕鱼为生,晾晒渔网之时,漫山遍野皆为渔网所覆盖,故而得名网山。对这种风俗,林亦之诗中有所描述,其《网山二首》之二云:“屋舍高低住,比邻活计同。笭箵嫌月白,螃蟹要霜红。吠犬随村落,卖鱼成老翁。地咸耕种少,海熟抵年丰。”[4]卷一网山周边山川美景,也进入林亦之诗歌抒写之中,如《九月晦日登烽火山》:
兴来走上烽火山,著足不定秋风寒。四边黄茅涓如雨,低头一看毛发竖。几年要到紫莱乡,大练小练并东墙。如今一时在眼傍,白云浮水天茫茫。酒阑更欲吊席屋,无端日脚相催促。一奴魋髻一跛足,逐我下山如野鹿。[4]卷一
尾句的“逐我下山如野鹿”,暗用鹿角山之典。林亦之曾带友人数度游览龙卧山,如乾道三年(1167年)与李谔等游览此山,乾道六年(1170年)与曹不占等人游览此山,淳熙元年(1174年)再次游览,留下《和李监仓欲游龙卧山以海风大作不果往》《丁亥九月十六夜偕李监仓宿龙卧山中,听雨看月同时事也,所谓鱼与熊掌兼得之,赋诗一篇以纪其事》《九月晦日登烽火山》《九月登龙卧山》《九月游龙卧山留一夕明日值雨坐超上人房偶题》等诸多反映龙卧山的诗作。
《清一统志》卷三百二十五载:“渔溪在县(福清)西南三十五里,源出黄蘖山里洋,与苏溪合。又蒜溪,源出蒜岭,亦流入径江。”[16]福清西南为莆田,此处所说渔溪、蒜岭,是往来莆田、福清的必经之地。陈藻曾频繁穿梭两地,或受学或讲学,与渔溪沿边士人交往甚密。①陈藻《惜别赋》序云:“渔溪诸友丱角相从,或相识乍离乍合。今岁偶聚,向时未生或初生者长成,而丱角有逾壮齿矣。二月始集,讲论未几,槐花将黄,次第分散。余世事已懒,笔耕亦倦,日嗜啜茶饮酒,逍遥行坐缔玩溪山之胜耳。”莆田——福清间的山川景物成为其诗歌写作的自然空间,如《渔溪西轩》:“千寻好景群峰起,一抹寒烟半壁留。日影渐高鱼网晒,雨声长响桔槔休。种麻卖布皆贫妇,伐蔗炊糖无末游。狂客寂寥贪看月,初旬已看月如钩。”[3]卷一这是对渔溪沿边景物风俗的抒写,从中间两联可以看出,渔溪地区物产富饶、居民勤苦,捕鱼、耕作、织布、炼糖等工农商业颇为活跃。陈藻《桔槔赋》云:“渔溪之民兮桔槔,一日不雨兮则劳。”[3]卷四可谓与此诗之“雨声长响桔槔休”句互文。又《红泉明日还福清作》《林若愚七十》《黄石还渔溪寄刘九四首》《值事有感怀渔溪丘德基》等诗,同样以渔溪为自然空间展开抒写。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艾轩学派的人际空间是师友、亲族、乡党相交织的群体网络,三层关系体现着艾轩学派的宗派性与地域性特征。这种复杂关系网在莆中的不断编织,及其诗歌与莆田——福清山川人文的紧密结合,最终促成艾轩学派与地方文化的深入交融,及其与地方诗学的紧密联系。
四、借重于学术:儒学传统的树立对诗学的强化
莆中文化发轫于唐,渐变于晚唐五代,而勃兴于宋,尤以南宋时儒学的突飞猛进为标志。②唐时莆中虽出现了林披及其子林藻、林蕴等文士,但只能算作个案,并没有形成特定的文化气候。五代时,王审知统治下的闽中“一境宴然”,形成了福州——莆田——泉州这一文化繁荣地带。在王闽政权招揽流寓士人、重视文教的政策影响下,大批中原名士避乱于这一地带,他们以闽中本土士人黄滔为中心,形成了颇有影响的士人群体。一时间,莆中文事兴盛,文献载云莆田地区“唐季多衣冠士子侨寓,儒风振起,号小稷下”。但晚唐五代莆中“小稷下”称号的获得,并非因为本土文化的发展,而是因为侨寓士人的活动。乾道、淳熙时期,莆中地区涌现多位学者,林光朝外如方翥、陈昭度、郑厚、郑樵、刘夙、刘朔等。林希逸《跋富文方公行状》感慨说:“莆于是时人物如此,是皆千百年间见之士,何其盛哉,何其盛哉!”[5]卷十三他们趣尚相投,相互间有着频繁的学术及人际往来。③方翥乃王蘋学派中人,其“由施庭先以事王信伯(王蘋),遂有所得”。林光朝与王蘋在学术上也有渊源关系。所以方翥与林光朝在学术倾向上大体一致,故而全祖望说方翥“吐弃一切章句,大略与艾轩等”。陈昭度亦“渊源濂洛”,在莆中有极高声誉,林光朝、方翥、刘夙、刘朔等“皆尝至其家,登堂拜母,谊均兄弟”。可以说南宋绍兴到乾道时期,莆中的理学氛围已逐步形成。
因独特的学术主张和广泛的学术活动,④除了与莆中士人交往密切之外,林光朝与逐步崛起于学界的朱熹、张栻、吕祖谦等人也有学术上的交流。曾与朱熹频繁书信往来,又曾与张栻、吕祖谦比邻而居,“日夕讲论”。其学术思想的成熟与朱、张、吕等的深入交流不无关系。林光朝特起于同时论学的莆中士人,在当时学界拥有颇高威望,成为莆中学术的代表。牟子才说:“吾党之士,识与不识皆以艾轩尊之。朱文公谓公为后学之所观仰,叶水心谓公为时人之所推尊,著庭刘宾之则曰艾轩吾师也,故相陈正献公则曰艾轩吾友也,其为人所尊敬如此。”[6]卷十牟子才《谥议》
林光朝及其弟子以莆中为中心,持续数十年讲学其间,对此方儒学推广功不可没。“自南渡后周、程中歇,朱、张未起,以经行倡东南,使诸生涵泳体践,知圣贤之心不在于训诂者,自艾轩始”,莆中士人争相投入艾轩门下,“四方之士抠衣从学者岁不下数百人,时论翕然,有南夫子之号”。[6]卷十牟子才《谥议》刘克庄说:“初艾轩来水南,学者空群从之。而红泉、东井之学闻天下。”[8]卷九十《城山三先生祠》向艾轩问学的有“父行、兄行、子若孙行”[4]卷四《光泽尉朱府君墓志》,“莆人四世,祖孙父子,殆数百人,皆门下士”[4]卷五《艾轩先生祠堂告成》。这是何等隽伟的学术传承盛况。艾轩弟子也扎根莆中,相继讲学,占据着莆中的学术空间,所谓“艾轩去,网山(林亦之)嗣讲业,网山卒,乐轩(陈藻)嗣焉”[8]卷九十《城山三先生祠》。即便是声名不显的艾轩弟子,其讲学规模也十分惊人,如终老布衣的林田,“席下常数十百人,经指授者多为达材成德”[8]卷一百五十《林处士》。艾轩学派遂成为宋元理学的重要一支,明人郑岳说:“倡道濂洛,而龟山、道南一派遂流入闽,罗仲素、李愿中而有考亭,由王信伯、施廷先而有艾轩,与象山、南轩、东莱并峙一时。”“艾轩深造独得,要未易窥,抑犹在朱、陆间乎?”[6]卷十郑岳《艾轩文选后序》
艾轩学术在莆中的长期传衍,终使林光朝成为莆中的文化偶像。不仅学说得到追捧,只言片纸也被奉为珍宝,甚至有人故意假冒艾轩笔札,以至艾轩墨宝真假混杂,难以分辨。①林希逸《老艾遗稿跋》记:“最后细书密行,有论西汉颜注者,有论《大易》乾、坤二卦者,有论颜子学问先后者,此先生为著作与南轩、东莱邻居时也。”林光朝去世之后,乡人为之立祠,陈俊卿为祠堂作记,赵汝愚亲笔书写,朱熹为之题额。周必大高度赞扬林光朝的学行人品:“事亲孝,御下仁,行已恭,执事敬,勇于义,审于思,善并美,具为当世所宗。”[18]卷六十三《朝散郎充集英殿修撰林公光朝神道碑》
艾轩学术在莆中的流播,使莆中士风为之一变。韩淲说:“艾轩林谦之有儒者意脉,所以兴化人至今未泯。”[19]卷中陈俊卿指出,在林光朝的感召和训导下,莆中之士“间有经行井邑而衣冠肃然,有不可犯之色。人虽不识,望之知其为艾轩弟子也,莆之士风一变”[6]卷十陈俊卿《艾轩祠堂记》。淳熙九年(1182 年)永嘉林仲元来守莆中,以厚风俗、敦教化为本,阖郡之士咸造于庭,曰:“莆虽小垒,儒风特盛,自绍兴以来四五十年,士始知洛学,而以行义修饬闻于乡里者,艾轩先生实作成之也。”[6]卷十陈俊卿《艾轩祠堂记》
艾轩学术使莆中士人变得更加看重言行身教,尊奉儒教,崇尚名节。这种士风形成之后,便长期在莆中传承,凝定为此方之民风里俗。后世之人每谈及莆中风俗,无不称扬其贵名尚节的一面,并将这种地方品德归功艾轩学派。元末明初大儒宋濂指出:“莆阳多名族,冠衣济济,读书之声相闻,贵名检而贱浮侈,以此见艾轩之教浃人之深。”[20]卷二《国清林氏重建先祠堂记》其又感慨说:“迄今垂三百年,流风遗俗犹有存者。家谈仁义而悦诗书,夐然非它郡所可及。君子之泽何其深且长哉!”[21]卷九《赠林经历赴武昌都卫任序》明代莆中士人郑岳亦云:“吾莆自林艾轩先生倡明道学,一脉相承如线。”[21]卷十六《明旌表孝廉文林郎云南道监察御史如宾陈君行状》清儒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卷五十总结说:
莆中诸名儒硕彦,其问学大都不仅屑屑章句。……莆自艾轩先生开派,以质行为先,至季世节概愈著。宋元之际,诸儒如存硕果,然公其道以私淑诸人者所在讲席尚多,故明代英才蔚起,士风家法递有师授。[10]
认为莆中儒学历元、明一脉相承,肇自艾轩。将莆中儒学之昌明,归因于林光朝及其弟子之引导。所谓“不仅屑屑章句”,正是林光朝倡导践履之学的结果。
可见,无论南宋人,还是元、明、清人;无论莆中人士,还是他方学人,都将莆中文事之兴盛、儒学传统之渊源,追溯于林光朝。
艾轩学派在莆中的生成、传衍,为儒学发展作出了贡献,更重要的是,它的存在改变了莆中的文化生态,使莆中终宋之世保持着独特的理学环境和文学氛围;经过艾轩学派的长期浸润,莆中文化面貌为之改观,本土文化因此昌盛。“新学小生咸有所师法,非先王之言弗道,非先王之行弗行。人号之为小邹鲁云。”[21]卷九《赠林经历赴武昌都卫任序》五代时期因众多侨寓士人的文化活动,莆中曾被冠以“小稷下”的称号,经艾轩学思的长期沾溉,其雅号由招徕学者讲学的“小稷下”,一变为诗书之乡的“小邹鲁”。这种雅称的改变,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莆中地区本土文化的成熟。而艾轩学派对这种文化品格的形成,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中国传统学术中,儒学居于上游,对其他门类有着强势的影响。借重于艾轩学派树立为莆中儒学传统,作为宗派重要内容的艾轩诗学,地位也无形中被强化、提升,融入此方诗学传统之中,泽惠深远,所谓“艾翁不但道学倡莆,诗亦莆之祖”[14]卷四引林俊语。宋末元初黄仲元、明人林俊等莆中士人的文学成就,人们也往往与林光朝及艾轩学派联系起来。①元代曹志《有宋福建莆阳黄仲元四如先生文稿后跋》:“上接艾轩、乐轩、网山诸老之传,言言根据,字字渊源,汪洋奇崛,自成一家。”明代王凤灵《见素集序》:“若乃微言奥义蓄而约于文词,则自艾轩而上遡于《檀弓》《左》《穀》无异趋者,公有所诵法而然矣。”而作为一种文化,其对莆中士人的文学活动所发生的影响,则更为微妙、深入,对莆中诗学之演变有潜移默化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