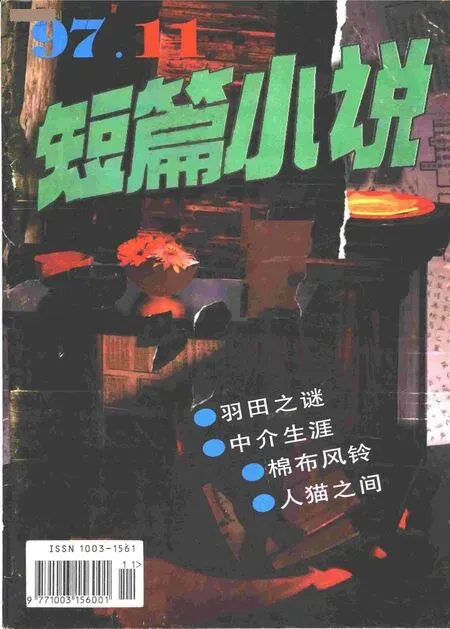袖珍小说四篇
◎赵同胜
俺不认得他
女人撩起补丁摞补丁的褂子,露出的奶子有些空洞,如瘪枣一样的乳头被怀里的娃衔在嘴里,揪心的哭声戛然而止。女人当然知道,那奶子不过个摆设,是挤不出丁点奶水的。娃拼命地吮着,女人感到了一阵钻心的疼,血殷红了娃的嘴唇,娃吮得更卖力了,女人任由着娃的肆无忌惮,眼里有两颗泪珠滚落。
男人一大早就出去了。两天粒米未进,男人急,女人也急,娃更急,娃的急全都融在了那撕心裂肺的啼哭里。
门“咣当”一声开了,女人一激灵。闪身进来的是个神色慌张的汉子。女人赶紧从娃嘴里抽出奶头,用褂子罩住奶子。汉子见状,刚想转身离去,院子里叽里咕噜的声音已传进屋子。女人若有所思,将娃往汉子怀里一丢,顺手拿起了身边的针线。
他的,什么的干活?女人手里的针线吧嗒掉落在了地上,屁股紧顶着炕沿,惊恐地瞅着问话的“一撮毛”,怯生生地回应着,孩子病了,吐血了,俺家男人要带孩子去看郎中哩。
“一撮毛”环顾了一下破败的屋子,狗一样用鼻子嗅了两下,把手一挥,开路开路的。几个端着刺刀的随从扭身就往外走。
乌云压顶。那伙人出得屋门,迎面撞上了一尊“雕塑”,手里擎着一杆猎枪,眼珠子鼓得溜圆。“一撮毛”将阴森森的目光投向女人,他的,什么的干活?语调涨满了杀气。女人的身子在抖,像筛糠,头在晃,和着身子的节奏。俺不认得他!女人嘴唇哆嗦着,话是从嘴缝里挤出来的。
砰!女人吓得一激灵,眼巴巴瞅着“雕塑”应声倒下,“雕塑”手里受到惊吓的山鸡扑棱着翅膀,和着凄婉的哀鸣翔入半空。
小树
与往常不同,这天一大早经过楼道口的人们,眼睛里多了几乎同样的内容。
那是一盆花,准确地说,是一棵小树。花盆很精致,盆上的图案有点特别,卡通的画面,一棵小树许是受到了风的袭扰,树梢宛若飘飞的秀发,直观感觉,小树有些弱不禁风,却顽强地保持着挺拔的姿态,给人一种莫名的视觉冲击。
不难分辨,盆里的树和画上的树如出一辙,我不知道树的品种,但头一眼看到就很喜欢,于是,我忍不住多瞅了几眼。
花盆被放在楼道口小平台上很显眼的地方,过往行人都能看得到。
花是谁放的?为啥放在这里?从人们的眼神里,能猜得出,他们都如我一样,在脑子里打着问号。
见惯不怪,过了些日子,人们似乎就把问号丢掉了,再过楼道口时,眼光里已经少了那棵小树。我也一样。
我是不经意中把那半瓶水倒进花盆的。那天,我想处理掉瓶里喝剩下的水,恰巧发现小树的叶子有点蔫,就随手倒进了花盆。第二天,我惊喜地发现,小树的叶子精神了许多。那之后,我隔三差五就会给小树浇浇水,小树长得枝繁叶茂,很是招人喜欢。
那个纸条是我在给小树松土时发现的,纸条被密封在一个塑料管里。上面的字稍显稚嫩:这棵平安树是我最喜欢的,放在这里寻找有缘人,愿为每一个人祈福送安。小树。
看到这个落款,我猛然想起了半年前晚报刊登的发生在本楼的一条新闻:一个身患绝症的10岁小女孩,把有用的器官捐给了3个孩子。那个小女孩就叫小树。
我盯着眼前的小树呆愣了许久,把纸条密封好,含泪又埋进了花盆。
驼峰的秘密
将进腊月,天寒地冻,她不顾一切地从娘的肚里爬了出来。
蹲在堂屋抽旱烟的爹一撩门帘进到里屋。娘说是个女娃。爹一眼就瞅见她背上的“驼峰”,眉宇间瞬时拧成了一个疙瘩。爹使劲磕了一下烟锅子上的烟灰,一个跨步,抄起她就要往外走,娘顾不得身子虚弱,疯了似的将她夺回,死死地抱在了怀里。
爹的脸上总是洒着厚厚的一层霜,她从没见爹笑过,她以为爹是个不会笑的人。直到那年弟弟出生时,爹像寻到了仙丹似的,一下子治好了面部的僵硬症,爹不仅笑了,笑中还带了泪,那泪流在脸上显得有了光泽。
她看不懂爹了,觉得爹好怪。
一天天长大,她从别人的眼光里读到了自己背上的“驼峰”。一颗叫自卑的种子悄悄萌芽。娘说,她是沙漠里的骆驼,“驼峰”里盛着天大的秘密。她没见过骆驼,也不知驼峰长得啥样。她忽闪着两只大眼睛听得很认真。虽懵懂,但她信了,娘说啥她都信。
爹阴晴的面孔在她和弟弟间游移,每次触碰到爹的眼神,她的泪就不自主地往外涌,可想起娘的话,她把泪又硬生生咽进了肚里。
爹终究没能拧过娘,她幸运地进了学堂,成绩一路拔尖儿,后来还考上了大学。那时,她才知道了那驼峰里的秘密是啥,有了那东西,跋涉的骆驼才能走出荒凉的沙漠。
娘撒手西去时,她哭干了泪,像天塌了一样。
没多久,爹也倒下了。瞅着弟弟和弟媳对爹的各种无情,她看到了爹眼里的浑浊,一撸袖子,就把爹接到了城里。她说要陪在爹身边。爹一脸的茫然。
爹的病是忌酒的,那天爹魔怔了一般,两杯酒下肚,爹抚着她背上的“驼峰”,伴着“呜呜”的声音,两行老泪簌簌滚落。
她觉得爹的眼泪像极了驼峰里的水。
花瓣上浮动的光影
她站在街上。寒来暑往,她都站在街上。
别人嘴里是说成“站街”的。她已经麻木。
站,只是形式,床,才是归宿。除了灵魂,身体似乎并不属于她自己。
那些人像在流水作业,对她来说没什么两样,她是机器,他们也是机器。自打那张面孔在她心里驻扎以后,所有在她身上疯狂的人都无一例外地成了机器。
她又站在了街上,东张西望,顾盼生辉。她当然知道在等什么,可等来等去,满眼都是虚妄,好在她没有颓唐。有信念支撑,是一件很立志的事。
那一刻,想想都能笑出声来。她如往常一样,机械地褪去衣衫。他那傻愣愣的眼光,空洞得近乎失了光泽,全然没有饿狼的样子。此时,她才仔细打量他,白净的脸上涂满了稚气,他应该和她年龄相仿,可她的稚气早就被烟散了。他瞅着她的肩颈,露出疑惑的神情。那是牙痕,“狼”咬过之后留下的。她倏地有了羞耻感,赶忙用衣服罩住。
他说是找娘的,好几年了,有人告诉他,他娘被卖到了这种地方。她有些愕然。他向她投过一束柔和的目光,喃喃道:快回家吧,家里人会想疯的。她心动了一下,缓缓伸出了双臂。他边退边重复着那句话:快回家吧。她的双臂无奈落空。
她再“站街”时,眼神里多了内容。直到若干年后,她被迎面而来的车撞上,那内容依旧在延续。
相比于太平间,化妆间里温暖了许多。漫不经心的入殓师冷不丁看到她的肩颈,眼睛亮了一下,是惊异,表情也随之生动起来。他拿起笔,几经描摹,她肩颈上便开出了两朵莲花,花瓣上浮动着光影,像水晶一样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