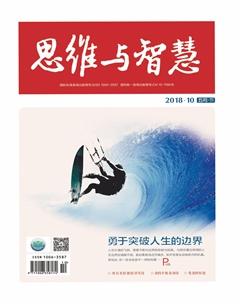选择一座城市,就是投奔一种生活
王开岭
美好的地方一定是养脚的地方。诗意的城市应该是漫步的城市。
我对“散步”一词有着本能偏爱,多年前逛书店,一眼瞅见封皮上有“散步”的两册:宗白华《美学散步》,卢梭《一个孤独者的散步》。二话不说捧回家,果然好書,极好的书。
我热爱散步的人生,信任散步的产物。好的灵感、音符、情愫,就像蚂蚱藏在你的途中,会突然于草丛中跃出。
什么情况下,漫步会成为城市的主题?人会心甘情愿地安步当车呢?
除城不能太大、任意两点间不能太远,还有两条:一、沿途空间应有舒适性和愉悦感,有魅力,不乏味。二、人的生活节奏相对舒缓,不焦灼,不拼急。
后者属时代心境,最难化解,不多赘,只说空间。
一个城市是否对脚友好,是否对漫步发出了真挚邀请,看“人行道”即一目了然。人行道在道路系统中的地位,直接反映出对脚的态度。而普遍现状是:人行道的待遇太差了,较之宽阔的车道,它要么被忽略不计,要么被严重冷落和边缘化,甚至被侮辱。不仅人行道受车道欺负,行人在车辆前也被迫礼让、退避、服从。
在一座美好之城里,道路系统应在细节上处处体现对行人的体恤,人行道应享有特殊的荣誉和尊严。
丹尼贝尔说:城市不仅是一个地方,更是一种心理状态,一种生活方式的象征。
选择一座城市,就是投奔一种生活。
规划一座城市,就是设计一种生活。
柳永有过一篇《望海潮》,写宋朝杭州市景:“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
读罢,我真有股冲动,恨不得即刻动身,奔赴那座古老的城池。
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雅各布斯说出了一重要观点:城市要饱满,要丰富,须保证“大多数街段要短,也就是说,在街上很容易拐弯”。
在北京,真正对漫步发出邀请的是胡同。其一砖一木都有体温,元素鲜活、细节密集,最具酵母气息和微生物色彩,所遇之人也有趣……重要的是,你能与它对话,一副门礅、春联、一棵槐树和一窝喜鹊、一丛墙头草或一只流浪猫,都是一个有趣的信息体。
当走路成为一件乏味的体力活,兴致即衰了。人行道的物理性能再好,也只能满足运动一下筋骨,寂寞而出,索然而归。在广州、厦门和泉州的老城,我邂逅一些残破的旧骑楼,它们身处繁华,临街倚铺,探出一溜檐廊来,衔连几百米,可遮风蔽雨挡晒。据说该设计曾风靡于南洋,和古廊桥相似,它处处体现对行人的召唤与体贴,可谓关怀备至,非常温馨。
北方的林荫道、风雨亭,南方的骑楼、廊桥,都是漫步文化的产物。
另外,要提一下自行车。
在我眼里,这是一种伟大而可爱的发明。它是马匹被取消后、人类脚力获得的最大补偿和抚慰,也是我能接受城市适度放大的原因。仔细看,你会发现自行车很有美感,它转化人的能量,像一双有魔力的鞋子,且清洁可亲,不像汽车那样冷血和暴躁。我宁愿把它视为原始“脚步”的升级版和时尚版,它与人体组合出了一种新的“脚步”。
(刘名远摘自《新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