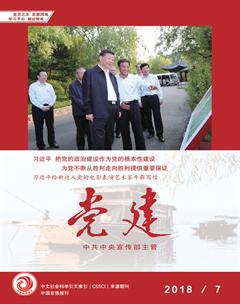李大钊清廉家风代代传
我的祖父李大钊,是河北省乐亭县人。他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和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也是一位著名学者。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祖父虽然早早地就走了,但留下了丰富的革命遗产和宝贵的精神财富,他树立的清正勤谨的家风延续了近百年,传承了几代人。我的父辈都继承了祖父留下来的好家风。我父亲李葆华,曾长期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逝世前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兼党委书记,一生非常清廉,克己奉公,生活节俭。我们第三代的兄弟姐妹中,没有一个是“大款”,大家都以艰苦朴素为荣。
祖父的遗产仅1块大洋
1927年4月28日,祖父李大钊英勇就义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对于他,我是从书中了解的。虽然从未谋面,但我通过文字与祖父相遇了。
大钊祖父很小的时候,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曾祖父便去世了,由他爷爷一手抚养长大。祖父的爷爷非常重视教育。祖父从五六岁便入私塾,到后来去日本留学,他前前后后一共上了18年学。在那个年代,能上18年学的非常难得。严厉的家教,长期的求学,使祖父从小便树立了致力于民族解放事业的远大志向。
留学回国后,学养深厚的祖父担任了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那时他的月工资是120块大洋。再往后,他担任北大教授,月工资涨到200块大洋,加上他在别的大学兼课,每月收入至少有250至300块大洋。
按说,他的收入已经不低了,但因为他把自己工资的很大一部分用在了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建党的事业上,再加上经常慷慨帮助别人,以至于日子常常过得很紧张。
1921年,中共北平支部成立后,他每月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80块大洋作为活动经费。此外,他还仗义疏财,多次资助家境贫困的学生。每到发工资时,祖父就会从会计科领回来一把欠条。后来,为了不让家里断炊,北大校长蔡元培只好嘱咐会计科每月从祖父的工资中拿出50块大洋,单独交给我的祖母。
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在北平逮捕了李大钊等80余名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在狱中,祖父备受酷刑,但始终严守党的秘密。4月28日,北洋军阀政府不顾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将祖父等20位革命者绞杀。祖父英勇就义时年仅38岁。
祖父英勇就义后,家里的遗产仅有1块大洋。由于没钱安葬,只好举行公葬,也就是向公众募集安葬款项。祖父的高尚品格感染了许多人,在为他举行公葬的募捐人员名单上,就有蒋梦麟、沈尹默、鲁迅等人的名字。
我父亲李葆华于1909年在河北出生。十几岁时,他就在我祖父李大钊的引导下走上了革命道路。
祖父被杀害后,一家人从此颠沛流离。我父亲李葆华为躲避抓捕,在友人的帮助下东渡日本,考取了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物理化学系,还在日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我父亲愤然中断学业,迅速回国,投入到抗战的洪流中。
父亲拒绝调新房
我父亲继承了祖父的高尚品质和良好家风,对我们没有什么条条框框的规定,更多的是身体力行,身教重于言教。并且,我父母从小就用祖父的事迹教育我们,要我们严于律己,不断学习进步。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担任过水利部和水利电力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在水利水电战线上奋斗了12个春秋,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是新中国水利水电事业的主要开创者和奠基人。父亲经常深入到各个水库视察指导工作,有一次还陪兼任淮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的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到安徽霍山县的佛子岭水库工地,当时附近没有招待所,两个人干脆睡在一个潮湿的工棚里。大别山区雨特别多,工棚没有防雨措施,漏雨夜两人通宵达旦无法入睡。
三年困难时期,父亲调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他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检查城镇居民的粮食供应配额。他借了一个粮本,到一家粮店买粮。营业员给了他3斤大米、7斤红薯干。父亲说:“不对,国家规定是每人每月7斤大米、3斤红薯干。”两人争执起来……后来问题清楚了,李葆华书记微服私访的故事也在社会上流传开了。
1978年,父亲调到中国人民银行主持工作,69岁高龄和生疏的领域,对他来说,显然是巨大的挑战。然而,在银行工作的4年里,父亲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规划金融业发展蓝图,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金融业的恢复和改革工作,完成了金融业的拨乱反正,推动了金融体制革新的全面展开,也为成功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作出了杰出贡献。
后来,父親还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然而这样一位高级干部,家中却简朴得让人难以置信——老旧的三合板家具、人造革蒙皮的椅子,客厅的沙发坐下就是一个坑。房子是20世纪70年代的建筑。2000年,中央有关部门要为他调新房,他说:“住惯了,年纪也大了,不用调了。”
我的哥哥李青是父亲的长子。哥哥说,他有两件事一直铭记在心。
一件事是,1994年,父亲到杭州开会,时任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到驻地看他,当时在浙江工作的李青也在场。李泽民告诉父亲李青表现很好,父亲马上对李泽民说:“你们对他要严格要求!”
另一件事是,1995年,李青在中央党校培训学习,周末回家看望父亲,一般要骑一个多小时的自行车。当时李青已经50多岁了,骑车一个多小时也挺累的,但父亲并没有因此而照顾李青,父亲从不让他的司机接送李青。
从这些小事和细节,可以看出父亲是怎样严格要求子女的。我们深深地体会到,这是父亲对子女的大爱,是真诚的、严格的爱。
我踏着先辈的脚印往前走
父亲去世后,曾有记者问我:“你父亲给你们留下了多少遗产?”我回答说:“我们不需要什么遗产,李大钊的子孙有精神遗产就足够了。”
其实,从我们几个子女的生活点滴中,就能了解李家的家风。
1987年,我调到安徽省民政厅担任副厅长,曾先后4次主持分房工作,分房近200套,从未给自己要过一套房子,在担任厅局级干部期间,一直住在一套60平方米的旧房里。按照省里的有关规定,我可以分一套新房。1987年至1992年3次分房我都有机会,但考虑到厅里人多房少,每次我都让给了其他同志。直到1998年最后一次分房,那时我已经担任厅长,想到许多年轻科长住房较差、需要改善,我又一次不顾妻子的埋怨,放弃了最后一次分房机会。
别人可能难以相信,一个厅级干部住的宿舍不到60平方米,没有装修,也没有什么好家具,更没有现代化的电气设备。8平方米过道既是客厅又是餐厅,放一张老式的大方桌,连走路都得侧着身。最时髦的就是一个20世纪80年代作为福利发的三人木制沙发,一半放衣服,一半放书籍。后来,省里按规定主动给我补了一个20平方米的小套间,我的儿子才有了一个自己的空间。
我认为,一个人是否富有,更多地在于精神层面,物质方面并不太重要。
2005年7月3日,《中国纪检监察报》曾用一个整版的篇幅登载了一篇题为《在李大钊革命家风沐浴下》长篇通讯。文章主要是写我的事迹。
我一生与自行车有着不解之缘,可以说是感情深厚。
上中学期间,我一直骑自行车来来回回。后来当兵了,有3年时间不怎么骑自行车。1969年退伍到合肥化工厂当工人,后来进合肥工业大学读书,1978年任共青团合肥市委副书记、书记,1983年任共青团安徽省委副书记,1984年任安徽省民政厅副厅长、厅长,我都是骑自行车上下班。
任副厅长期间,一天,厅里一位同志看到我步行上班,便问:“你怎么不骑车呀?”我告诉他:“车子放在楼下被偷走了。”
曾经有一篇报道是这样写的:“前些年,在安徽合肥,总能看到一个身材魁梧、满头灰发的中年人骑车行走在上下班的人流中,路上的交警都和他亲热地打招呼,他就是李宏塔。担任领导工作20多年,李宏塔骑坏了4辆自行车,穿坏了5件雨衣、7双胶鞋。随着年龄的增大,这几年他才将自行车换成了电动车,后来因为上班路途太远,开始坐汽车。他笑称自己会在能力范围内尽量节俭。”
对住,我不讲究,对吃、穿,我也同样不讲究,我不抽烟,不好酒,更不上歌厅、洗脚房。
虽然我家挺节俭的,但我们并没有多少存款。有人会问,钱都到哪去了?
民政廳机关里的不少人心中都有数,在每年“送温暖”“献爱心”的名单中,我的名字都是排在最前面——这样的名单,不是以职务高低,而是以捐赠的数额多少排名的。
还有,如果到农村看到“五保户”家的房子漏雨,到福利院看到老人被子太薄,到“低保户”家看到过年包饺子的面没买,我就会想祖父李大钊救济穷人时的样子,情不自禁地想帮助他们。对我来说,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是一种莫大的幸福!
李家的良好家风,让我们能够心平气静地固守清贫,我们是心甘情愿的,没有任何装潢门面。“革命传统代代传,坚持宗旨为人民。”我经常用这副对联自勉,并以此教育子女,决心把李大钊的良好家风继续传承下去,踏着先辈们的脚印继续往前走。 (责任编辑:刘文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