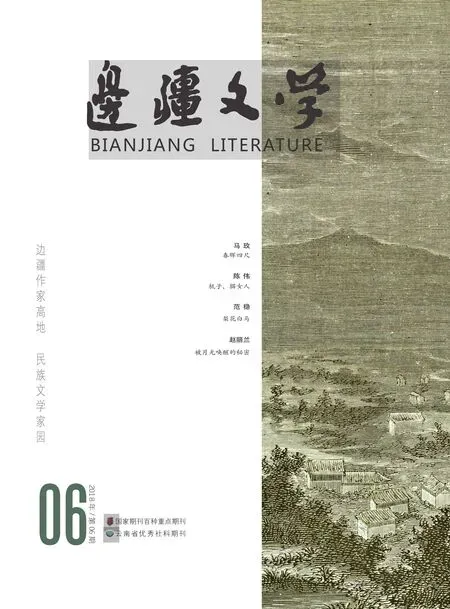被月光唤醒的秘密(23~24)
赵丽兰
我总是源源不断地听到月亮开口说话。
——题记
23. 赶马人
李大坟的山坡上,灌木丛中,生长着许多野葡萄。熟透了的,掉到坑凹里。遇雨,腐烂发酵,变成了酒。山凹里,飘浮着野葡萄酒的香。砍柴人、赶马人、牧羊人路过李大坟,就欢喜得慌。停下来,摘一根空心的草茎。伏下身子,去喝坑凹里的琼浆。醉在灌木丛中。赶马的路途,就有趣多了。这些大大小小的牛马踩出的坑凹,称“牛脚迹窝”。秋季,灌木丛中,深深浅浅的牛脚迹窝里,都是天然香甜的野葡萄酒。
《清稗类钞·粤西偶记》记载:“粤西平乐等府,山中多猿,善采百花酿酒。樵子入山,得其巢穴者,其酒多至数石。饮之,香美异常,名曰猿酒。
原来,世间万物。好酒者众。
人间需要一场醉。它能让迷茫者不用时时保持清醒。清醒,是荒诞的人间,多出的理智。不是因为喝酒,才醉去。而是因为需要醉去,才喝酒。没有谁能灌醉谁,都是自己灌醉自己的。那些醉去的人,在狭小的放纵里,获得暂时的自由。但是,活着,需要清醒。需要回到秩序和理智中来。
赶马人不是本地人。赶马人是小镇上一酒坊的帮工。几年前,酒坊的主人,从外地带他来到小镇,帮忙打理酒坊。酒坊烤出的酒,像酒坊的主人。性烈时喝,每块骨骼都像是烧着了一样,变成了钢筋铁骨。性温时喝,每块骨骼都像是融化了一样,绕指柔一样。
赶马人来到小镇好几年了。赶马人守信诚实,对主人不离不弃。他负责把酒坊烤出的酒,用马驮了。经八哥石岩、千层石,到李大坟。再过陡关,把酒驮到呈贡卖。
月亮升至中天,赶马人吆着马起身。披一身清凉,上路。到李大坟,天刚麻麻亮。那时那地,赶马人就特别渴。他伏下身子,去喝牛脚迹窝里的野葡萄酒。边喝边说,好酒嘞!好酒!赶马人喝一次醉一次。
每醉一次,他都觉得特别有意义。有一种毁灭现世的快感。遍野酒香。清醒时,未敢说出的话。都因醉酒,而美好,而恣意。
和赶马人一起上路的,还有一只八哥。
离李大坟两三公里的地方,有一石崖,唤八哥石崖。栖息着很多八哥。野生八哥食性杂。以蝗虫、蚱蜢、金龟子、蛇、毛虫、蝇、虱等昆虫为食。也吃谷粒、果实。常在翻耕过的野地觅食。或站在牛、马等家畜背上啄食虻、蝇和壁虱。
八哥一直跟着赶马人。赶马人息脚的时候,它就立在马背上,啄食。赶马人渴了。伏下身子,喝牛脚迹窝里的酒。八哥立在他肩上。学着赶马人说,好酒嘞!好酒!
赶马人顺着醉意,睡在野地的灌木丛里。侧身,紧紧地搂着一个包袱。像抱着一个女人,或者一个孩子。包袱里,装着几个死面粑粑,或者一包炒面,一个冷饭团,一件衣裳。
有时,一路跟着赶马人的八哥,也会渴酒。它趁赶马人醉去。从马背上跳落下来,学着赶马人,啄牛脚迹窝里的野葡萄酒。奇怪的是,八哥从来不会醉。喝够了,八哥继续立在马背上。驮子里的酒,随着晃动,逸出的酒香,比牛脚迹窝里的要烈要醇,更像酒一些。也似乎更有意思一些。
八哥一边啄食马背上的苍蝇,一边说。好酒嘞!好酒!
赶马人醒来。太阳已经升得老高。
再不赶路,卖完酒回来,就得两头黑了。再说了,小镇上,赶马人还有牵挂。牛脚迹窝野葡萄酒的香气,在正午热浪的蒸腾下,四野扩散。像一声从小镇传来的急迫的喊声,等赶马人回去。他紧走几步,好从时间上缩短和牵挂着的那个人的距离。矛盾的是,每次到了李大坟。赶马人都要因为喝野葡萄酒耽搁好大一会。他不觉得这是在浪费时间。相反,每次喝醉了,他就觉得有人在跟他讲话。他就不孤独了。他来这个小镇,好几年了。没有人,懂他。他是一个被故乡遗忘在异乡的孤单人。起先,他因为一个人的孤单,爱上了牛脚迹窝里的野葡萄酒。后来,他因为两个人的孤单,爱上了牛脚迹窝里的野葡萄酒。赶马人希望秋天慢一点。希望野葡萄终日不休地成熟,掉落到坑凹里。这样,牛脚迹窝里的野葡萄酒就源源不断,永远都喝不完。
早一些的时候,赶马人返回小镇,天刚擦黑。酒坊里还在烤酒。他摇摇紧闭的大门。来给他开门的,常常是一个女人。女人长相一般,眉眼却也端正清秀。女人的脸,在刚刚浮上来的夜色里,显出欢喜,略带一丝丝惊慌。像做错了事,又得到谅解一样。女人开了门,并不多看赶马人一眼。转身,急急地离开。风拂过女人微胖的腰身,摇摆着,消失在夜色里。这急迫的脚步,像是欲擒故纵的召唤,专等赶马人追上去唤一声,便会停下来。赶马人不出声。女人的脚步也未曾停下来。默契而暧昧。
屋子里,酒坊的主人,正和几个男人喝酒。赶马人将卖得的酒钱,如数交到主人手上。主人要他坐下来,和他一醉。赶马人说,劳顿一天,人困马乏,要去睡了。赶马人和主人,之前,是兄弟哥们。经常在一起划拳喝酒,醉意来得快,去得也快。两人之间的感情,像太阳下的事物一样,简单明白。甚至,好得可以换唾沫吃。后来,主仆的关系,有了尊卑,多了些客套。再后来,从一个月亮很圆的夜晚开始,赶马人和主人之间的关系,蒙了一层灰一样,让人看不清、猜不透。却又雾里看花,花更美。有时,他们坐在一起喝酒,一人一碗。月光从树影里落下来,照在他们的身上。无数斑斑点点,像是无数的破洞。月光和破洞,把他们带到了一种奇怪的关系之中。赶马人的脸,印在碗底,似有躲避。清丝丝的酒里,他看见自己的卑微,随着涌上来的醉意,扩大蔓延。在酒的面前,心,本应该是打开的。赶马人每和主人喝一次酒,心门又关上一点。直至紧闭了,再也进不去。主人一再追问赶马人,是不是待他薄了,可以再给他加工钱。赶马人不说话,只低头喝酒。主人性烈且刚,连干三碗,摔碗破口大骂。都是些决裂的话。大概是因为之间曾经的兄弟感情,被一再遭受隔阂质疑,而伤心。主人想,干完这一杯,割袍断义,何妨。此去,你是你,我是我。然,赶马人任由主人怎样骂,仍然踏踏实实地干活。天不亮,就赶着马翻山越岭,去呈贡卖酒。就是赶不走他。
冬天,水瘦草枯。李大坟的野葡萄枯萎了。雪落高山,霜落凹。那些大大小小的牛脚迹窝里,都是白霜。八哥的身上,也是霜。有时,落在赶马人肩上的八哥,会用翅膀去拍落赶马人身上的白霜。奇怪的是,还是有人看到赶马人摘一棵空心的草茎,伏下身子。边喝边说,好酒嘞!好酒!顾影自怜的样子,看着既让人伤心,又着实有些可爱。
随后,醉了,睡在山坡上。醒来,脱胎一样,换了人间。霜迹覆盖之处,都是美好。愁肠都换成了欢心。
八哥好奇,跳下马背,往坑凹里啄去。却啄得满嘴白霜。赶马人喝的究竟是什么呢。霜,也能喝醉人么?八哥抖净嘴角的白霜,复落在马背上。学嘴学舌的叫一声,好酒嘞!好酒!就是不解酒中其好。
李大坟,顾名思义,就是李家的坟地。何以要冠于“大”,应该是与葬在此地人物的身份有关吧。赶马人曾经研究过这个“大”字。他一个外乡人,觉得这样一个“大”字,是生死之类的意义。人死,入土为安,且为大。有时,赶马人在正午醉去。有时,在大白月亮的夜晚醉去。夜里醉去,都是卖完酒返回的时候。他被冷阴阴的月光冻醒。醒来,马站在月光下,喘吸呼出的热气,扩散在月光里,一缕一缕雾一样飘动着,渐渐消失不见。天上的月亮,似乎就要掉下来,落在牛脚迹窝里,然后碎掉。
赶马人起身,继续赶路。散落在山坡上大大小小的坟墓,月光下,影影绰绰。马和人的影子,被月光拉长,落在坟墓上,比坟墓还要高还要大。赶马人也不害怕。听村里人说,李大坟最先埋的是一位将军。洪武十四年(1381年)九月,明太祖朱元璋任命傅友德为征南将军。蓝玉、沐英为左右副将军。调集三十万军队,从南京柳树湾高石坎出发,征讨云南。始祖李公是沐英的部下。征服云南后,傅友德、蓝玉于洪武十六年(1383)班师回朝。朱元璋念沐英功垂第一,遂命沐英世守云南。始宗李公和子孙就随沐英留守云南,在阳宗镇竹园村安家落户。后来,始祖李公的其中一个子孙被皇帝敕封为武德将军。武德将军去世后,埋在李大坟。有家谱为证:
曾祖之身,皇帝敕封,武德将军。将帅身世,江浙豪门。守疆保土,南京下关,天子亲临,赐宴饯行。洪武吉日,南征滇地,成里崎岖,为国效命。紧随沐英,驻屯强宗,客逝他乡,墓碑为凭。
赶马人站在墓碑前,竟感慨垂泪。出门在外,路人不如乡人,乡人不如亲人。在小镇,和他最亲密的关系,除了一匹马、一只八哥、一碗酒,就是酒坊的主人了。可是,他和主人有了深如沟壑的隔阂。月光下,最亲密的那层关系,或者还有其他的什么?他把答案交给了一只八哥,以及牛脚迹窝里的野葡萄酒。那是一个秘密,要烂在肚子里,要带到坟墓里去的秘密。他想,即便日后死了,从坟墓里把他挖出来,验明正身,要他说出一个惊天的秘密。他仍会三缄其口。人间的许多事,一捏就碎,一说就破。除非八哥和酒替他张口说出。
从始宗李公开始,五百多年了,李大坟的坡坡凹凹,埋的都是李姓人。山坡,应是先有坟,后有名。这许许多多的人间事,最后都归了一抷黄土。
赶马人想,他是一个人来到小镇的。许多年后,小镇是不是会因为他,以及他在小镇的一些人一些事,而留下痕迹。等他客死异乡,埋他的那个山坡,就叫某某坟。等他死去很多年,他的子子孙孙,也都会在百年后,跟随他埋在一起。赶马人加快脚步,脸上浮现出子孙满堂的欢喜。只有八哥看到了他眼中暗藏着的欢喜之下的忧伤。客死他乡,这是他一直无法面对的事情。孤独和卑微,暗中促使着他,要去找到一种平衡,以此安抚他惶惶然不可终日的心。
他在李大坟来来回回,不知走了多少路。新坟变成了旧坟。脚迹踩着脚迹。等死了,来这条路上收脚迹,都得一段日子。一脚踩下去,都会踩到一些秘密。那些不能说出来的秘密,它们在土里埋了多年。终有一天,还得裸露出来。光天白日之下风化、破坏,化成灰。他曾经一脚踩到一把刀。刀已经锈了,发不出光。它的棱角还在,还是一把刀的样子。只要还是一把刀的样子,它就具备成为凶器。具备成为伤口的一种形式,存在于人间。赶马人想像,那曾经的霍霍之声,将月光都磨得有了快口。怪不得,月光会伤人。刀光一闪,人间就有了爱恨情仇。迟早是要这样的。当然,也许还可以换一种方式让子孙后辈复述另一部历史。甜蜜的,欢爱的,销魂的。与爱情或者其他有关。
久走夜路,必闯鬼。锈了的刀,连鬼都不怕。
他扛着一把锈迹斑斑的大刀,赶着马返回小镇。那天生意好,酒卖得一滴不剩。行到千层石。赶马人和自己较上了劲。他在千层石打转,原地绕来绕去,绕了一整夜,都没绕出去。赶马人遇到了“鬼打墙”。鬼打墙,又称鬼砌墙、鬼挡墙。在千层石,遇到鬼打墙的,赶马人不是第一个。千层石四周是壁立的山坡,密林阴暗。吹过来的风,自带一股狠劲,很阴。
天上没有月亮没有星星。他点燃一根烟。光,来自于生命深处,照亮了赶马人的眼睛。在此之前,他目睹人间的黑暗。那走不出的暗黑,恰好吻合了赶马人的气质。烟头的光亮,把他带到了另一种生命状态里。一直以来,总有七绕八绊的障碍,命令他安静下来,不去发声,不去言语。慢慢地,他懂得了在主人的故乡卑微地借宿。燃着的烟头,体积虽小,但却仍是一个燃烧着的物体,是明火。烟头中心温度高达700℃~800℃,而一般可燃物质的燃点都在这个温度以下。鬼怕光,烧红的烟头是有能量的。倘若这烟头能够在赶马人的生命中持续燃烧下去,赶马人的肉体就会被赋予新的生命。烟头烧得很快,烧起来的时候,在暗夜里很惹眼。熄灭下来,未能及时抽身的恐慌也很惹眼。鬼躲在活人的后面,一一记住了。赶马人能够做到的就是逃离。这是一个哲学的悖论。越是拼命地逃跑,越会因为违背秩序,乱了方寸,困于其间。
锈痕斑斑的大刀成为了童话故事里纸做的道具,在鬼魂的面前装神弄鬼。这是一个好玩的命题。一把刀的轻和腐朽,是时间剥离它的价值,让它没有了意义。在李大坟,鬼比人多。
假如人、鬼、神的时空同时存在。那个晚上,赶马人一定存在于鬼的时空。赶马人不仅遭遇了鬼打墙,还遭遇了马屎鬼。他拼命地往自己的嘴里塞马屎,直塞得嘴角淌血。折腾大半夜,仍在原地打圈,走了圆路一样,无法走出去。
天亮,八哥站在马背上,不停地叫唤。好酒嘞!好酒!八哥,唤醒了他。
没有鬼魂存在的时空,多么枯燥无趣,多么了无意义。
最大的那个鬼,存在于赶马人心里。他以为,他不说,便没有人知道。他心里的那个鬼,在赶马人的心中,发出灼热的光芒。戴着镣铐跳舞的快感,就在于镣铐的束缚。
自那次闯鬼后,赶马人心里的那个鬼越长越大。心,终于装不下鬼了。赶马人鬼魂附体一样,整天晕叨叨地胡说胡讲。他仍然听主人的话,按主人的吩咐赶着马去卖酒。镇上的人却注意到了一个细节,一路上,赶马人总是一步三回头,像是有什么东西落下了,舍不得,要折返回去找。如此,走走停停。随着赶马人气场一天一天减弱,八哥的胆却越来越大了。也或许,八哥和赶马人彼此相互懂得的更多了。八哥仿佛连同赶马人心中的那个鬼,也见过了似的。赶马人想,此行,最后醉一次。从此,要扔掉卑微、孤独和心中的那个鬼。一样不剩地和主人摊牌。他要在绝望中主动去寻找希望。从明天,做一个光明正大的人。
过纳雾江,马低下头喝水,并打了个响鼻。赶马人怜爱地摸着马鬃,凑近身子,贴了贴马的脸。仿佛要和马长久别离,再也不见。他想,他流不出的泪,一定有人躲在某个暗黑的角落,替他哭泣。他想,马或者八哥,都应该替他哭过了的。最好没有人替他哭过,如此,秘密便只有他的心知道。他伏下身子,抄一捧水,洗了一把脸。赶马人突然轻松起来,他觉得纳雾江的水,将他身体里的鬼洗掉了,他干净了。从来没做过什么见不得人的坏事。
八哥突然从天空里落到赶马人肩上。叫一声,说,回去,回去,生了,生了。
八哥的话音未落。一声婴儿的啼哭,从村子里传出来。赶马人双膝一软,跪了下去。对着天空,哭出了声。秘密由不得他说不说,都即将要真相大白了。一直以来,面上,他为主人的厚待而忠实、吃苦、耐劳。暗地里,却和主人的长房女人珠胎暗结。此爱便是冤孽,是债,是一切刚刚好的罪孽旧账。即使是跳进纳雾江,也无法洗干净一身的脏。这个刚刚出生的婴儿,这个偷欢而得的骨肉,是人间的一个罪证。他是为了死,来到人间的。这响亮的哭声,不是报喜,明明是报丧。
一醉解千愁。赶马人卸下马背上的酒桶,将酒倒进一个坑凹,俯下身,大口大口地喝了起来。此前,赶马人喝的牛脚迹窝的酒,都是酒桶里倒出来的。野葡萄酒,哪有这么大的力,让他喝一次醉一次。他需要一次一次俯下身,跪倒在大地上,以此向天地忏悔。仿佛以这样的姿势醉酒,可以参悟,可以贴地成空,修成正果,给女人一个光明磊落的怀抱。
那个新出生的孩子,被主人的母亲一屁股就坐死了。这是一种新鲜的杀人方式,闻所未闻。此刻,不是杀人,是维持人间正道。无端相爱的两个人,是邪恶无耻。主人抬着一把刀,追女人而去。镇子上的人,怕酿出血案。将女人藏在了山上的一间空房子里。三个月后回来,疯了一样,没了人形。主人,休了她。
爱恨与情仇,岂只是这场欢爱的坟墓。爱与爱不得,恨也恨不得。生死也不可得。赶马人趁月黑风高,趟过纳雾江,赶马上山。从此,不知去向。生死未知。
这以后,在千层石,屡屡有人闯鬼。鬼喊,大哥,等等我。大哥,等等我。说完,一纵跃上马背。有次,遇到一个胆大的男人,鬼跳到马背上,这个胆大的男人,晓得咋个让鬼变不了形,咬破自己的指头,把血抹在了鬼穿的衣服上。一路把鬼驮到呈贡,卖给了一家酒坊做长工,没日没夜地拉着一头毛驴推磨。几年过去,酒坊的主人嫌他的衣裳穿得又烂又破,帮他换了衣裳,并洗干净。衣裳一洗,就消失了。待明白过来,才知道洗掉衣裳上的血,就拴不住鬼了。鬼又回到了千层石。三更半夜的,常常听见鬼喊,大哥,等等我,大哥,等等我。
没有人说得清楚,这鬼,是不是就是赶马人。
收刀入鞘。赶马人的故事就要结束了。
一个秘密压在我的心头,我恨不得一开始,就直接说出来。就亮明身份。就说出月光下的秘密。
月光下的秘密,终究是需要说出来的。酒坊的主人,是我的老爹。赶马人的相好,就是我老爹的第一房女人。这是一种复杂而危险的关系。当然,如果只放到爱情的范畴里来讨论,这是一种简单而美好的关系。像赶马人醉去,把包袱当心爱的女人搂着的样子。事实上,他真的是搂着心爱的女人。包袱里的一切吃穿用度,都是女人为他准备的。
我之所以说出月光下的秘密,不是为了讨伐或者可怜赶马人,以及和他相好的女人。我是专门为反传统而准备讲出这个故事的。它是一种挑战。挑战道德之下的伟大。他的伟大是没有意义的。我在为一对被道德绑架的相爱人翻案。世间,那些伟大的道德上,开满了恶之花。

郑辉 石榴五 布面油画 50cm×50cm
规矩,限制了自由。需要悲伤吗?需要忏悔吗?爱情,是一个在“道德”或通奸面前,一不小心就污了了词语。当老爹抬着刀,追着刚生下孩子,拖着血身逃跑的女人。他明明早知道,他和女人的爱情,早在他把奶奶娶进赵氏家门时,就没有了。他没有权利,去限制一个被他毁掉了爱情的女人去寻找另一种爱情的可能。这是一种可怜的愤世嫉俗。我可怜他。后来,听村里人,赞美我的老爹。可赞美之处在哪里?苍白的赞美,是怎样的一种价值观。守妇道,立贞节。这是对女人何其大的摧毁。爱情需要通过举行婚姻的仪式感得于认可,得于确立其合法性。虚伪一点说,确立忠贞或永远。反之,就是放荡。将身体的叛逆无限放大。是否从精神上给予了客观的判断,把其视为不羁。一件事情,放在不同价值观判断里,更好或更坏,都是他们。
人,从来都不伟大。伟大,是阶级统治的需要,而塑造出来为统治者服务的谎言。回到真实的人说话,他会爱会恨会贪婪。人性,只要不是大恶。都可以原谅。在情爱的统治关系里,婚姻总是试图统治爱情,男人总是试图统治女人。它抛开了两情相悦而不顾,只强调仪式感和顺从。低眉顺眼的时代,早过去了。婚姻最初的直觉,必须有爱可言。婚姻里的爱,是动态的,不是一陈不变的。
这同样是一种阶级关系,压迫与被压迫。压迫与反压迫。
我希望听到更多关于反贞节的声音。婚姻,是我们拼命为爱情编制的笼子。传统意义上说,是家。反传统意义上说,是囚笼。囚禁自我,也囚禁他者。占统治阶层的那一方,通过囚禁,获得快感和成就。被囚禁的那一方,不过是实施了反叛,却被视为放荡无耻。
多年后,我用文字,将他们更好的那一面唤醒。这不过是一场简单的爱情。我会遭到唾骂,被视为和他们一样放荡无耻。在这个过程中,我唤醒了一个更好的我。我不需要高尚来对我进行审判。
赶马人,这是一个跟我家族气质相反的人。他创造了生命另一种意义的美好,发出那种异化的、忧伤的,被控制在黑暗里的光芒。
24 .亮瓦
母女俩搬进来的时候,房子已经住过很多人。死在老房子里的人,不少。一个戴瓜皮帽的老人,病死在小阁楼里。小阁楼有一道木推窗。推开窗子,便可望见天。天,低低的,一伸手就可以摸到。那个戴瓜皮帽的老人,是房子的一部分。母女俩住进来后,母亲梦到过他。瓜皮帽在梦里说,这房子不算老,但它有故事,它是命的一部分。母女俩住进来,成为房子的主人,也是命的一部分。
房顶的每一片瓦,眼睛一样,带着呼吸、光亮和温度,也是命的一部分。
观一屋之荫,而知天下之变。堂屋的正顶上,有一块亮瓦。奇数为阳,中国传统建筑中多用奇数。阳光或月光透过亮瓦,射进屋内,在板壁或楼板上形成光影。随着光线的移动,母女俩以此估摸一天相应的时辰。一年亦如此,太阳在赤道上方左右移动,从而出现季节变化。夏至之日,光影位置最南。冬至之日,光影位置最北。
亮瓦,是老屋的天窗,也是母女俩心上的窗户。在眼睛一样的天窗里,母女俩是陌生的、危险的、可怜的。这样的两个女人,没有男人可以依傍。怎样在漂亮惹人的状态下,发出光来,去实现自我的独立,并超越光,照亮一些别的什么事物。自我价值的实现,将不用平庸的幸福去衡量,而是用光,去完成一些别的什么。关于生离死别,关于爱情婚姻。
光,透过亮瓦,落在楼板上,有些古旧的意思,甚是好看。老屋面东,还有一扇雕花的木窗。倚窗歪着,恍惚中,以为是深宅大院里某家的小姐,古典素静。是透过亮瓦和木窗的光,成就了人的气质,有了一番古意。人,还是那个人。芸芸众生中,再普通不过,却又耐瞧耐看。
母亲五十岁,女儿二十岁。在亮瓦的光影里,两个女人不说话,低头做手中的活计。女大十八变,不管长得好看不好看,总归要萌动了春心,蠢蠢欲动。去爱,去恨,去狠狠地用力。等有一天,爱也爱完了,恨也恨完了。顿悟超脱的,无关悲喜,来去自由。月下闲话,像是借自己的嘴,讲别人的故事。得空给闲人说说,听者有闲无妨,留只耳朵听听而已。格调上似乎高了一格。将曾经浓得化不开的爱,淡然到且听风呤。这需得有一份功力,方可修得。俗尘中的饮食男女,面对如此淡的风月,却自是多了一份警惕。学不得,也学不会。便依了俗尘,日日凋零,日日盼。却道是: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
爱情,总归是一边茂盛,一边荒凉。一边卿卿我我,一边挽歌绝唱。
深宅大院的小姐,自是学不会的。学形易,学神难。易的东西,只学得个表像,是死的。神的东西,是生命深处的气质禀赋,活的。学不来,天生的,八字里带着来的。
房子,需要有光,于是就有了亮瓦。这还不够,住在里面的女人,也要有光。五十岁的母亲自带光亮。举眉时,好看。皱眉时,亦好看。亮瓦里射进来的光,落在她削瘦的肩膀上,追光灯一样。母亲在光里,又骄傲又好看,具有穿透力。
为了让女儿发出的光如母亲一般高贵骄傲,女儿唤名宝珠。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镇上的大人孩子们,都唤她小宝珠。“宝珠”和“小宝珠”,一个“小”字,就将宠爱和可心的喜欢,区分开来,表达透了。他们溺爱的声音,深情而有所企图地唤出来。镇上的人们,一天天这样喊着。小宝珠就长大了。二十岁,出落得清秀可人。
母亲和女儿所发出的光,似乎从未产生过同质性。她们彼此独立存在于不同的气质禀赋下,状态各异。
镇上的人,家长里短,嚼嚼舌头,便是恰恰好的市井生活。
母亲在镇上一走,蓝布褂子,方口布鞋。走时带风,静时存蕴。像是一只迷失在小镇上的狐狸,孤独优雅。眼波,只留给风。随意看镇上的人们一眼,便被望穿了一样。母亲的眼神和善,不挑逗,不撩拨,大方得体。镇上的女人们看她一眼,又看她一眼,看到第三眼的时候,便招架不住。低了头,只嗑瓜子。瓜子壳,堆了一下巴。
很多年后,当有人这样看我的时候,犹觉得人间又多了一只狐狸。是骄傲,是承袭。是无人能懂的孤独。
镇上嗑瓜子的长舌妇们都说,这女人,有一股子巫气,怎么看都亮闪闪的,晃得人心慌。有人添了一句,她囡小宝珠倒好。大概是女儿不像母亲一样,有一股穿透人间的气韵。有别于大众的异质,难于跟俗尘对话,便是出格的,坏的。显然,母亲超越了所处的环境,成为了大众审美之下的出格人。她的美,像月光一样,美得没有痕迹。却又实实在在抓着俗尘之人的心,生发出忌妒、排斥和不被理解。女儿,顺从了环境,呈现出物体性的存在。是人间烟火中的一分子。
母亲穿过场心,去井边淘米洗菜。一路听着镇上的长舌妇们指指点点,说长道短。气韵,究竟是什么?是不是命里天生的?还是狐狸身上带来的?母亲,是鬼还是狐狸?世间女人,面相各异。有的长着狐狸脸,有的长着猫脸。长舌妇们的话,让母亲又骄傲又害怕。俗尘,似乎抛弃了这样一对母女。她们却又甘愿被抛弃。母亲巫一样的存在感,她们不懂得。也不要她们来懂得。人间有一个眼睛看不到的在场,它存在于气质与气质之间。气质相通的时候,便互为一体,人间就产生了一种新的秩序。如果气质相隔,一步,就是天壤之别。
母亲和女儿,都长着狐狸一样的脸。然,仪容面相却都端正大方。母亲的端庄,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附着在眼睛看不见的地方。抓不住,摸不着。却又实实在在的感觉得到。女儿的清秀端庄,像田野里的一朵小野花,触眼可见,伸手可得,却又长着刺。
母女之间,似乎也是有距离的,隔着一层什么,难于跨过去。母亲是小众的,非主流的,是疏离于大秩序之中的小秩序。女儿是普遍意义的存在,发出的光泽是群体性的。母亲的光泽,淡然、有力,具有穿透性。女儿的光泽,混合在一群女人中间,除了一张狐狸脸,分辨不清哪一束光属于她自己。带着七十年代赋予女人整体的统一规则,被限制在传统价值观所规定的蓝衣黑裤大辫子的审美范畴中。时代令她本份、普通,白白长一张狐狸一样的脸。时代,还命令她将光遮避起来。暗淡下去,才是美德。她的光泽,需要通过开口唤出“小宝珠”,才可看到一束光,经由名字扩散出来。强烈、骄傲,却又短暂。
小宝珠和母亲相依为命。母亲自带光亮,却与小镇格格不入。母亲孱弱单薄,常年胃疼。胃病一犯,就疼得在床上打滚。母亲称胃疼叫心口疼,她捂着心口,蹲了下去,滚落一颗一颗的汗珠子。“心疼”和“胃疼”,是有区别的。胃疼,只是身体的疼。心疼,从身体到了精神,是身心的疼。胃疼不如心疼。母亲让小宝珠用刀背切她的肚子,以此缓解疼痛。这是一种奇怪的缓解疼痛的方式。或许,心坎上的疼,必须动用刀子,才可以治愈。每每,小宝珠拿着一把菜刀,用刀背在母亲的肚子一下一下横切下去。眼泪滴在刀上,滴多了,便没有意义。
小宝珠长大了,需要有一个人来疼她。小镇上,想疼她的人不少。八岁的时候,她就没了父爱。父亲,给她取了一个会发光的名字,把她疼到八岁,就进了劳改农场。
谁也不能带她成长,包括母亲。她的母亲,这个风一样单薄,风一样柔软,风一样惹人疼又惹人妒的女人。注定和她是两种气质禀赋的人。母亲怕风,禁不住风吹,却又无端地站在风口,等风吹过。女儿要将母亲带到尘世的人间烟火中,只有吃饱穿暖了,才有能力去谈心坎上的爱。她只得和宿命较劲,藏起狐狸一样的脸。不期待有人能找到她,发现她,爱上她,心疼她。她要带着母亲,回到人的中间地带。她无法藏起来的,是她发着光的名字。她在名字里获得了骄傲。她感谢她的父亲,给她取了这样一个名字。让她,借着名字,发出光来。
疼小宝珠的,应该是一块美玉。至少也得是一块石头。美玉和石头,事实上,是同一类物体,本质上是分不开的。美石为玉。石头若如获得疼爱和温度,贴着心久了,便也成为了一块美玉。只给彼此懂得的金玉良缘。宝玉含玉而生,却自嘲是一块顽石。顽石和玉,得到了人间的爱,便是玉。得不到,便是青埂峰的一块顽石。荒芜在草泽大荒里。小宝珠在俗尘里,等待一份金玉良缘的爱情。宝珠配美玉。哦,这卑微的人间,等待着发出光来。
你是世界的光,我却在黑暗里走。什么时候,才能在光亮中寻找到归途。这样的话题沉重了。二十岁的小宝珠没想这么多。她天生乐观,她觉得,光一直都在。
母亲和小宝珠坐在亮瓦下。
母亲说,宝珠,等有人疼你了,我便了无牵挂,可以死了,再不拖累你。死了,心坎上的疼,也就不在了。
小宝珠抬头看亮瓦里射进来的光,妈哎!光就在我们头上,一抬头,就看见了。
小宝珠答非所问。她的心里总是亮堂堂的。光,在母亲的心坎上,是一个忧伤的词语。在小宝珠的心坎上,是明亮的所指。
小宝珠再次抬头看亮瓦,妈哎!亮瓦老了,怕是会通洞。我只想找到一个会修亮瓦的人。
二十岁,早该是谈婚论嫁的年纪了。
春天的一个傍晚,邻村的一个男人提着两袋杂糖,来到了老宅。男人一脸横肉,腮帮子上有一条斜斜的刀疤。二十五六岁的样子。
男人单刀直入,说,把你囡嫁给我吧。我是退伍军人,扛过枪,打过仗。枪林弹雨里拼过来的。你囡嫁给我,是福气。
显然,这是一个有经验的男人,说起话来,一点不羞涩。世故而老道。男人自以为有充分的把握,可以用退伍军人的身份有效地控制住母女。让她们心甘情愿。七十年代,根红苗正的身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捕获爱情。男人想,劳改犯的女儿,没有理由不对他的身份动心。孤儿寡母,她们需要一个男人来撑起这个家。革命的光泽,这足以可能改变人的一生。尤其是女人。嫁对了人,便一辈子荣华宝贵,衣食无忧。
母亲只冷冷地问刀疤脸男人,你会修亮瓦吗?
刀疤脸被问懵了。母亲抬头看屋顶上的亮瓦。说,我囡宝珠只想找一个会修亮瓦的人。她怕亮瓦老了,会通洞。
此时,小宝珠刚洗了头。她把头发披散下来,遮住了大半边脸。她在采取临时性逃离的方式,躲避一个上门求婚的男人。刀疤脸不是她要找的那块石头,他一脸的杀气让小宝珠从骨头由内往外冷。他更像一把危险的刀。刀的光泽,会在某一瞬间,亮过珠宝。刀疤脸让小宝珠慌恐。倘若嫁给他,早晚得出事。女人对事物的认知和判断,没有逻辑,但就是出奇地准确。
小宝珠打了个冷颤。妈哎!让他走。
刀疤脸悻悻离去,临走,都没看清小宝珠长什么样。只觉得这个女人跟她母亲一样,心高气傲,不好惹。回头,望母女俩一眼,眼放凶光。跨出门槛,又转身回来,提走那两包杂糖。
当小宝珠六十八岁的时候,给她的女儿讲起这些细节。她多庆幸她朴素踏实的婚恋观,只嫁一个会修亮瓦的男人,便是幸福和福份。她说,刀疤脸后来犯事,死于非命。
人生,有一种事后对话。可以陈述曾经禁忌的话题,或者埋在心底多年的羞耻和秘密。时间裸露出事物的真相,当年,是卑微和羞耻。时间之外,那是多么引以为傲。何况,小宝珠在回忆的时候,更多的是将心高气傲又展现了一遍。
除却心气的骄傲,小宝珠想成为一个和母亲不一样的女人。母亲的远方很远,将心流放到荒原和旷野,还嫌不够。没有人能给母亲明确的远方,没有人能明白风的延伸。三天两头,母亲心口就疼。刀背落在母亲的心口,小宝珠仿佛用这样一种方式,获得了深入母亲身体的探寻。她发现,母亲心坎的光,炽热耀眼,照亮了她,却又不属于她。
一家养女百家求。要疼小宝珠的男人,不止刀疤脸一个。有男人用信封装了两斤粮票,托人送给她。有更大胆的,伸手来摸她的下巴。说,小宝珠,嫁给我。一段时间,她成为了小镇上一个危险的符号,发着光。她越排斥男人们的行为,光芒越发耀眼。她甚至盖过了母亲的光泽。花气袭人。谁都可以借她的光,亮一会儿。谁都没有到达光的深处。
屋顶上的亮瓦真的有裂痕了。它究竟有多少年了,小宝珠不知道。她只知道,在瓜皮帽死之前,屋子里就死过好些人。屋子换主更人,灰尘和蛛网上,都依附着古老的故事。它们跟母女俩没有亲缘关系,却又千丝万缕地联系在一起。它们带给母女俩安全的感知。特别是这亮瓦,是尘世间的带着光亮的一只眼睛。
亮瓦真是老了。小宝珠担心,真有那么一天,亮瓦就通洞了。不仅漏光,还漏雨。接着,漏下来更多的危险。她最担心的,是怕义学山的老悲恶和蛇也会从通洞的亮瓦里漏进来。
屋后,是一座山,称义学山。杂草丛生,有一棵大树,树身上,有一树洞。说是雷劈出来的。夜晚,有猫头鹰在树上不停叫唤。悲恶(音:wu),悲恶……小镇上的人们,唤名“老悲恶”。白天藏身树洞,入夜哀鸣。其叫声怪唳、阴邪,吉凶参半。跟随一只鸟的哀鸣,唳声,无可模仿。母亲有时会在老悲恶的叫声中,淌下泪来,泪珠比眼睛还大。
初夏,有些热了。房顶上传来唰唰唰地贴着瓦檐爬行的声响。随即,亮瓦里的光不见了。母女俩抬头,亮瓦上,盘着一条蛇,手膀子一样粗。圆锥状的头上,一双眼睛圆睁着,射出冷的光。蛇在亮瓦上停下来,是因为亮瓦太光滑了,它无法继续向前爬。母女俩相互对视一眼,抱在一起哭了。这唯一的一点亮光,也被一条蛇,用它丑陋的身子所遮蔽,所阻挡。
怕什么,什么就来了。蛇冬眠了一个冬季,醒了。
母亲哽咽,宝珠哎!找个男人,来疼你。
是啊,这个家,多么需要一个男人。一个能干的可靠的踏实的男人。一个会修亮瓦的男人。
母亲托了媒人,媒人就住在隔壁,一个心直口快的女人,说一口通海话。女人坐在亮瓦射进来的光里,说,我四弟手巧,会做木活,桌椅板凳打得精巧结实,人又实在,在生产队记工分。我四弟还会找漏(找漏,即在雨季来临前,爬上屋顶,找出破损的瓦,修补完整,以防漏雨)。女人说着,抬起头,看一眼亮瓦。这亮瓦是早该修一修了。蛇钻进来,害怕死了。
女人,仿佛看穿了小宝珠的心思。每一句话,都说在了点子上。
要在光的照耀下,才看得到影子。小宝珠看见,母亲、女人以及她的影子,落在楼板上,有古旧的美好。她的心动了一下。那种心动,有着可以依附的质感,踏实而稳妥。
女人的四弟,比小宝珠大三岁,那是一个寡言的男人,但内心厚实。像是心里安放着一片亮瓦,让人感觉到光的存在。有些人一出现在生命中,便可靠近,走向前去,交出心。仿佛前世就注定了姻缘,只等这一世来完成。
小宝珠知道,女人的四弟,就是镇上周师傅的小儿子。周师傅在镇上扳马鞍子,通海人。他扳的马鞍子又结实又美观,做得一手好木活。周师傅死了好多年了。那年送周师傅上山,她还去凑过热闹。她看见周师傅最小的儿子站在棺木前,咬着下唇,硬是将跑边的眼泪逼了回去。周师傅的小儿子,乳名唤小七六。那年,小宝珠十六岁。她站在人群中,看着送葬的队伍,突然想哭。她想到了她劳改的爹,是死是活,都不知道。她无法遮掩住突然而至的脆弱。小七六跟着送葬的队伍走远了,回头,看见小宝珠站在人群中哭。泪水,滴落在手背上,亮亮的、热热的。原来,泪水,也是会发光的。小宝珠揩掉一脸的泪水,突然间有了希望。这是她生命里可以面对一个陌生人哭出来的泪水,有安全和光亮。小宝珠和小七六仿佛在相互给予安慰,带着信任感和踏实感。
母亲提出要求,要倒插门,让小七六嫁过来。女人同意了。
小七六给这个家送来的第一份见面礼,是一挑柴。他放下柴,收了扁担,说,我明天来找漏,顺便把亮瓦也换了。再无多话。
小宝珠看着这个憨厚的男人,黑红的脸膛上,挂着汗珠,阳光下,一闪一闪地亮着。憨厚,是安全的象征。何况,这安全,闪着亮光,即将照亮未知的路途。从此,母女俩,不再是光亮的旁观者,她们即将进入到光亮中,并发现光来。
隔天,小七六溜刷地爬到屋顶上,找漏。小宝珠仰着脸看亮瓦里的男人。或早或晚,人世间就会遇到那个命定的人,这之前,他遥不可及。此时,他就触手可得。她在亮瓦的光亮里,没有了傲气,她想低到尘埃里,只为这个会修亮瓦的男人。小七六透过亮瓦,看屋子里的小宝珠。哦,她多么光亮啊,皮肤发着光,辫子发着光。眼睛里的光亮,像是两簇燃烧的小火焰。
母亲看着这对年轻人,流下了泪。泪珠,依然比眼睛还大。母亲不知道,她的男人,什么时候才能释放回来,一家团聚。
人生了摆着,命生了藏着。命,要在光的照耀下,才看得清晰,看得准确。小七六的大名中有一个“瑜”字,义为美玉,或玉的光泽。这便是恰恰好的金玉良缘。小宝珠不在意他是石头还是美玉,即便是块石头,她也认定了它的好。他们,在以后的日子里相濡以沫,石头也会变成一块美玉。她始终相信,有光为证。
我一直在等小宝珠更详细地给我讲一些他和小七六的恋爱史。小宝珠说,傻姑娘,你没看见噶,亮瓦一直都亮着。你爹,年年都爬上房顶,去找漏。
小宝珠,是我的母亲。小七六,是我的父亲。那个怕风,却又站在风口,等风吹的女人,是我的奶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