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事实与鼠疫之间
贾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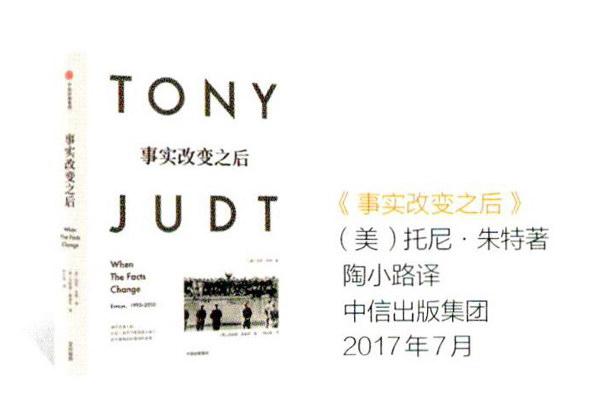
梅纳德·凯恩斯爵士曾说过两句话,前段话引注者众多,后者则应者寥寥。前段话是这么说的,“从长远来看,我们终将难逃一死。”后一段则如此表达,“当事实改变以后,我的想法也随之改变。”
我们不必,也不应将凯恩斯主义之名,硬冠在固有一死的凯恩斯身上,个体间的时代经验与世代间的身份追忆互为表里,当事实面临更替后,选择改变的勇气尤为值得珍惜。
这正是被誉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知识分子的托尼·朱特,希望他的读者所能领悟,并能有所行动的人生箴言。这位在2010年过早离开人世的思想家,并未从公众视野中消失。每当人们哀叹西方世界的道德衰败与勇气匮乏,抑或是人文知识界的犬儒遍地与无意义争执,总有人会适时想起朱特的谆谆教诲和犀利言语。
颇为反讽的是,让一位身患绝症的病者来诊断这个沉疴遍地的时代,这个事实本身就颇具悲剧色彩。
《事实改变以后》即是病人朱特剖析自我与诊断时代,两者合为一体的思想纪实体,由朱特的遗孀珍妮弗·霍曼斯辑录而成。该书记录了自1995年朱特前往纽约大学执教,并担任纽约大学雷马克欧洲研究所主任一职后,在《纽约书评》《伦敦书评》《纽约时报》《新共和》等刊物上发表的各类政治与思想文化评论,以及部分朱特生前未能公开发表的文章片段,并按时间顺序和内容主题,进行了重新编排,使得读者能够更为清晰、更为客观地了解这位知识分子最后的思想图景。
对于不了解朱特的人而言,事实改变无足轻重,对于熟悉朱特人生与文字的人而言,事实改变关乎真诚。在朱特身上。有着20世纪留给知识分子最为鲜明的时代烙印——个人身份的多元特性。作为中欧犹太人的后代,朱特成长于“二战”之后的英国,福利制度与社会民主主义伴随他的童年,并留下至深印象。青年朱特则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狂热信徒,捍卫以色列不受侵犯是他义不容辞的职责。
重归学术界的朱特则是重新发现欧洲的思想探险家和坚定的知识分子批判者,肩负道德责任,反对价值预设的历史虚无观是他鲜明的叙事风格。1995年前往美国并成为美国公民后,朱特也曾为克林顿政府军事干涉波黑人道主义灾难而欢呼雀跃,坚信人权高于一切的时代已经来临。然而随后的“9·11”事件,及其伴随而来的伊拉克战争,让朱特陷入了某种状况的身份窘境,不少朱特的思想对手嘲讽他悄然成为真正的美国公民,他也不再稱美国为“他们”,而是“我们”,这位曾经的欧洲知识分子,俨然已经开始讨论起“我们的生活方式”,令人错愕。
面对这一系列诘难,朱特并没有用立场加以回应,而是坦然接受事实的改变。这也是朱特当年选择纽约,选择建立雷马克研究所的初衷。朱特始终认为,在过去的30多年中,欧洲内部所发生的巨大转变,并非如外部所了解那般线性与进步,而是充满了血腥与动荡。包括学者在内的西方公众,都必须有重新发现、认识,进而重新理解欧洲的紧迫历史责任感。除此之外,加深世界对于欧洲变迁的深刻理解,也是知识分子责无旁贷的任务。这段时间正是朱特撰写他的传世之作《战后欧洲史》的时候,即使在这样的时刻,朱特依然坚持在公共舆论发言,帮助公众审视并观察变动中的欧洲与世界。
对于美国在小布什时期的外交政策,朱特持批判的态度,但有别于左翼知识分子的立场先行。对于美国对外政策当中的黩武主义,朱特认为这只能加速作为共和国的美利坚之衰落,而作为一个帝国的美利坚,则将走向新的孤立主义。
实际上,朱特面临的最大挑战并非来自他的欧洲情结与美国身份,而是他作为犹太人对中东问题的冷峻点评,这点体现在他对以色列处理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审视犹太人的悲情历史与民族神话,批判美国犹太利益集团时那种一针见血式的诊断。他忧虑并警告以色列放弃对于“大屠杀”的念念不忘,谏言平庸之恶终有一天会成为世人对以色列执政者和民众的指摘。对于朱特而言,作为受难者的以色列身份不是可资利用、用之不竭的记忆神祗。
正如霍曼斯在序言中所谈及的,《事实改变以后》是朱特“真诚之心”的产物。朱特并不是居高俯视的观察者,他只是拒绝成为某种观念和立场的说教者和同路人。正如该书扉页引用朱特最为崇拜的法国知识分子与作家加缪在《鼠疫》中的话,“地球上有鼠疫,有鼠疫的受害者,一个人所能做的是尽可能不要与鼠疫为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