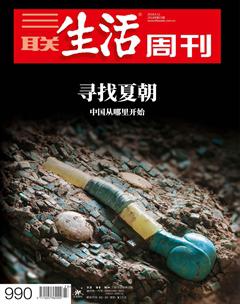读者来信
天才儿童之谜
拥有天赋实际上是具有“主动性”——主动的思考和主动的行动,“超常儿童教育”正是挖掘了孩子们的这种主动性。另一方面,“特别聪明而不努力”的绝对不是天才,只有正视孩子的天赋和努力,才能更客观地评估孩子的潜力。在某课外辅导机构接触过很多家长,听过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家孩子特别聪明,就是不努力。”无论学生的成绩如何,家长至终都不肯正视孩子诸多能力上的不足,这就会导致家长和老师无法客观地制定培养目标,从长远来看反而遗患无穷。
(读者X)
最好的学校
孩子就读的民办学校,从最早由上海一所学校主导、笼络不到生源,到后来本地教育部门主管、民办公助,生源紧俏,以至于听说没有一点关系孩子是弄不进去的。物以稀为贵,这所小学顺理成章地成了本地家长口中“最好的学校”。
所谓“最好”,难免是卖方市场善加利用的广告词,它满足了买方的虚荣。我是到了孩子就要入学时,才开始接触这所“贵族学校”的。权衡再三,我们还是决定让孩子进这所学校。一来那时学校借用的校区离我家近,走路10分钟够了。二来它的双语教学吸引了我。学校从一年级就配有来自英语母语国家的专业外教,孩子们每天可以和外教面对面交流。三来学校兴趣课多,家长不必到外面给孩子额外找兴趣班。至少“广告”是这么说的。
转眼孩子就要五年级了,我没觉得这所学校“贵”在何处,除了学费贵,以及去年启动了全新的校区花了些价钱。以学校独具特色的几个节日来看,渐渐让我感觉都在敷衍,学校和老师得过且过,家长慢慢厌倦。上学期有文体节、英语节,下学期有文体节以及正在如火如荼举行的艺术节,但节日的舞台演变成少数几个学生的表演秀。某孩子钢琴弹得好,每年他都上台演奏一曲肖邦或舒伯特。某孩子跳舞不错,每个节日的舞台都有她曼妙的舞姿。
我家孩子每年艺术节都轮到一个亲子绘画,我连续画了4年,画得我都有点黔驴技穷了。今年亲子绘画唯一有新意的,是器具,画在PVC管子上。最长的管子1.6米,小点的车厢塞不下,我第一次有了换大排量车的奋斗冲劲。去年的英语节我们很重视,有个英语剧比赛,学校专门请人为孩子的班上编排了一个“滥竽充数”的英语剧,我一听觉得挺有意思。孩子只是跑龙套,可为了班级荣誉,我像其他家长一样,不得小觑,天天鼓励她好好吹,千万不能滥竽充数。到比赛那天,班主任要求家长尽量到场,帮助孩子摆放道具、加油、拍照、发朋友圈。到比赛现场一看,我才知道,所谓的英语剧全是对口型,吹竖笛也是做做样子。每个班的孩子们都按部就班、有点混乱地完成了各个环节。表演结束,孩子都说,累死了,总算结束了。
万圣节和圣诞节本来蛮有意思,孩子们放心玩,不像前面那几个节日,名义是玩,总有心理负担,没才艺的自卑,有才艺的特别忙特别累。这几个节日其他小学基本没有活动,只有这所学校有,孩子们挺得意。去年不知哪来一阵风,全国大范围反对洋节,迫于舆论压力,这两个孩子最喜欢的节日宣布取消。
一二年级的时候,孩子每周在校興趣课可选三门,到三年级剩两门,现在一门。有一天孩子充满遗憾地跟我说,等到六年级,她最喜欢的兴趣课就没了,只剩没完没了的作业和测试。我安慰她,真有兴趣,任何技艺都可以在校外学。
前阵子本地又有一家据说理念先进的民办小学开张,报名及面试现场门庭若市,看朋友圈,那场景和我当年经历的相比有过之无不及,录取比例更是接近六比一。闺女对我说:“爸爸,我们同学都不喜欢那所学校,原来我们是最好的,现在不是了。”我知道孩子一直生活在各种对比中,学校和大部分家长似乎一直以此为荣。我告诉她,喜欢的、合适的才是最好的。那所学校现在只有一年级,“你要是觉得合适,就把你送那边重读一年级”。孩子听了一乐,说:“拉倒,还是我的学校好。”(杭州 老九)
保护圈
爱人的工作早出晚归,我的工作经常出差,能陪孩子的时间不多,两个人的收入请不起保姆,双方父母,特别是老妈,义不容辞地担起了照看孩子的任务,一南一北两个老太太,一年两班倒,北方较远,寒来暑往,主要带2月到6月,剩下的南方的阿婆全包,孩子上幼儿园前,正好三个循环。
我和老婆虽然退出了带孩子的一线阵地,但交班不交权,放手不放心,设定标准、检查指导、批评督促,这些工作跟得紧抓得细。奶瓶、碗勺等什么时间烫、烫几遍、用什么水烫,普通尿布和拉拉裤分别在什么场合使用,提示线到什么颜色必须换,屁股盆、脸盆、澡盆、洗衣盆怎么区分,出门汗巾、毛巾、纸巾、湿巾、保温杯、凉水杯、喝水杯等差不多10件套有多么必要,一日三餐,奶粉水不能烫,破坏营养,不能用力摇晃产生气泡,影响消化,菜要嫩、肉要碎、饭要软,油不多不少,盐不咸不淡。睡觉按时按点,外出一天三次,电视能少则少,手机坚决不行。在这些要求的挟持下,两位老人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婆媳关系、母女关系偶有裂痕,翻白眼、生闷气、嘟囔嘴时有发生,但在一切为了孩子的高压下,基本还是做到了忍气吞声。
我们这种情况在院子里很有代表性,有孩子的家家户户,只是略有排列组合、人员分工、轻重程度的不同而已。勉强可以称为凤凰男女的我们,对老母鸡孵蛋带崽那一套非常不待见,认为过时又愚昧,老人们吃苦受累还被说三道四,心里自然极其不爽快,幸好子女们白天上班,管得着但看不着,他们正好可以扎堆吐嘈,加之总有几个带孩子的身份特殊,保姆或者远房亲戚什么的,别人家庭的故事,复杂关系八卦成了他们不多的快乐时光,也许这也是我们这种人员相对集中的大院才有的福利吧。不过有熊孩子们在,快乐一定很短暂。这边厢,张奶奶正抱怨媳妇不肯生二胎,大家议论纷纷、见仁见智,那边李姥姥家的铁蛋哧溜一下从栅栏钻到了马路上,李姥姥大喊一声“妈呀”,飞奔过去,像刘翔跨栏似的,翻过比肩高的栅栏墙,一把抓住马上要跑到双黄线的小铁蛋,迅雷不及掩耳地压下了老伙伴们的一场虚惊。一边嘴狠手轻地打骂着孩子,一边严肃地叮嘱左邻右舍:“可不敢让铁蛋他爸妈知道。”
铁蛋他爸妈知道不知道不得而知,反正我和老婆当天晚上肯定会知道,拿出父母当年训我们的架势,严肃提醒:“一定要吸取教训,举一反三,不可麻痹大意。”
有一次,一个朋友来院里找我,看到大爷大妈们围成一圈,手舞足蹈、低头猫腰,一边笑一边说:“你们院里的广场舞水平有待提高啊!”我不好意思地告诉他:“圈里是一群熊孩子,他们一对一盯阵,也互相挡差配合,争取用纸包住火,免得磕了碰了。”朋友很认真地说:“有老人帮你们带孩子真好,这样盯着也是够累的,不过你们这个保护圈比保护伞可瓷实多了。”听得我骄傲自傲,热泪盈眶。
(广州 暖暖)
不景气的劳务市场
每到周末,早点小吃生意不忙,我就会去离此地不远的劳务市场找点儿活干。前些年,利用空闲时间我常去这个劳务市场打零工,以补贴家用。这些活儿都是些重体力劳动,比如建筑、园林绿化、农田里的农活等等,只要不怕吃苦受累,就能找到活儿有钱挣。但听说如今有人把持控制了这个劳务市场,要想进去找活儿干,必须买个证,不然你爬上车人家就会把你轰下来,闹不好还挨顿揍。于是,我和另一个老乡准备明天一早搭伴去另一处劳工市场。
第二天天刚亮,我俩便骑着自行车出发了。骑了将近半个多小时才赶到,老远就看见马路两边站满了眼巴巴找活儿干的人:有肩上挎个背包带着工具的泥瓦匠;有手里拎着锯子、斧子的木工;余下的都是赤手空拳靠卖力气挣钱的。妇女们大都头上包着一块毛巾,围成几撮观望雇主的出现。
过了一会儿,一辆面包车开了进来,人群马上涌上去。人们问车里招工的干什么活、工錢是多少。那个人坐在车内说:“找两个人到马路边平整土,一天130块钱,谁去我拉谁走。”听完他的报价,众人皆摇头:“还能涨点儿吗?给的太少了。”“不涨了,就这个价。”见他毫无商量的余地,人群慢慢散开了。大概10分钟后,又开来一辆双排。招工的在车上喊:“有去种树的吗?一天150啊,只要男的,想去的赶紧上车。”呼啦啦一帮人爬上了车。我挤到车跟前准备爬车时,那个招工的喊道:“人够了,用不了这么多人,再下去四个。”爬上车的人都无动于衷,他只好挑出几个年纪较大的下了车。剩下我们这些人悻悻地返回市场内。又过了一支烟的工夫,来了一辆私家车,说找三个人到他家蔬菜大棚里割韭菜,工钱是120块钱。一听这话,原本涌动的人群顷刻间恢复了平静。等了大半天,那辆私家车没招到人,开车走了。
到了晌午,我粗略地数了一下人数,有100多人没找到活儿。我向一位紧邻挎工具包的瓦工师傅问道:“师傅,现在大工多少钱?小工多少钱?”那师傅告诉我:“你是新来的吧?大工是260块钱,小工是170到180之间。”我又问道:“你是不是到建筑工地上去?”他说:“现在建筑工地都没人去了,天儿这么热,还有危险,大家伙都找修马路、园林绿化、庄稼地里的农活。妇女们挣的钱少些,也得在150块钱左右,少了没人去。不像以前招工挑我们,现在我们也挑工种呢!”
我跟老乡眼见着打短工无望,便商量着回家。我又瞅了瞅市场内马路边伸长脖子等待找活儿的人群,他们还在期待着今天的生计。
(天津 农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