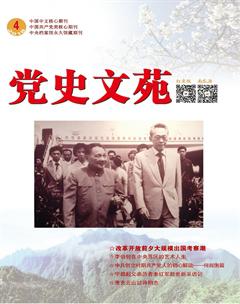中国革命文艺的历史考察
20世纪初期,中国历史便围绕着革命的主题渐次展开。在中国近现代革命语境中可清晰看到,革命政治话语作为压倒性的力量主宰了几乎整个20世纪的中国,成为中国社会最强势的话语。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革命政治逐步主导文艺,并最终对文艺拥有了绝对主导权,文艺与革命宣传之间形成了一种难分彼此的结构性关系。文艺与革命政治的关联已是中共党史上一个颇为关键的现象,这个现象从五四运动后期开始萌生,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苏区蔚然成风,经历了延安时期的强化与改造,至“文化大革命”期间又演变为极端的刻板化。文艺运动的历史不仅是文艺本身的言说,必然还是革命政治的,它囊括了延安思想整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反右”、“文化大革命”等大型政治运动,可以说文艺这条线贯穿了20世纪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一、裂变与新生(1915—1927)
特定文化的产生源于特定的历史基础,它的萌生离不开社会各种要素的综合作用。革命文艺的若干因子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已初见端倪,它萌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后期,继承了五四文化内核中的实用主义、激进主义和平民主义的精神,是从五四新文化母体中裂变出的新生物。
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性质,学界基本达成共识——是一场爱国主义启蒙运动。然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生,究其根源来说,并不是源于启蒙理论本身在中国的成熟,而是源于民族主义诉求的高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等一系列政治危机将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和对社会、民族的责任感发挥到了极致,亡国灭种的局势激发了他们变革的决心。因而,新文化運动带有顺理成章的实用主义目的:通过改造国民性,实现国家救亡和民族振兴的目标。与前代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类似,五四新文化运动尚未脱离政治救亡的窠臼,启蒙思想的宣扬也未曾脱离“功用”这个根本目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归根到底追求的并不是人性或个人精神的完满、现代化,而是竭力寻求如何更有助于救国家,“新文化”是达到这一根本目标的手段,最终启蒙服从于救亡[1]p87。正如台湾学者林毓生所言:“自五四以来中国存在着一种影响颇深的借思想文化解决整个社会改造与重建问题的思路”[2]p45,这种对待思想文化的功用主义传统被后来的左翼革命文化继承并强化下去。
除了功用主义,左翼革命文艺还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继承了断裂与否定的激进主义。学者余英时对此有一个总体性的评价:“中国近代一部思想史就是一个激进化的过程……无论是戊戌的维新主义者,五四时期的自由主义者,或稍后的社会主义者,都把中国的文化传统当作现代化的最大敌人,而且在思想上是一波比一波更激进。”[3]p115五四前期知识界以胡适为代表,宣扬西方自由主义精神,比如自由、独立、博爱、人道主义、多元主义等,反映在文艺上,即“文学革命”,文学创作脱离传统“文以载道”的格局,反传统、尊个性、重生活,是“为人生”的文学,例如,自由恋爱成为该时期文学创作最为重要的素材之一。然而,自由主义者倡导的“一个一个问题解决”的主张,因为愈加严峻的政治形势而渐渐失去了信众——改良看不到希望,国家内忧外患,政治问题不解决,其他的问题也就无从解决。于是知识分子走进了政治的偏激化,寻求全面变革的路,以实现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也只剩下革命一途了。马克思主义给在迷雾中彷徨的知识分子带来了希望,在改良派与革命派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后,革命被认为是迅速而根本地解决国家全面危机的最有效手段,并日渐成为当时主流信念。十月革命的胜利又为中国革命提供了一种成功的典范,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遂转向宣传马克思主义及其提供的社会革命模式,一批五四知识分子转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进而组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五四知识分子开始把激进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与革命的制度化——政党制度——勾连起来,并且依托马列主义价值系统提供的救世启示,强化政党组织提升阶级群众的觉悟,在一个众民合力演进的政治过程中,进行着翻天覆地的社会革命。”[4]
五四新文化中的平民主义也深刻影响了左翼革命文艺。平民主义的观念出现在晚清,在五四时期壮大为一股强劲的社会思潮,并从理论走向实践。在五四这个反偶像崇拜的时代,知识分子们第一次把目光投向平民,将平民作为主要的读者和受众,开展白话文普及、平民教育,组织平民社团等活动,以唤醒民众。一批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工人中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产生了撼动历史的力量。平民主义思潮指导下高涨的群众运动,为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运作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方式,这个方式一直延续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传统。值得一提的是,五四时期的平民主义思潮中,知识分子是作为启蒙者去“化大众”,他们怀着一种舍我其谁的精英心态,这与19世纪40年代的平民主义恰恰相反。
在大革命的旗帜下,国共两党的意识形态具有某种一致性:民族救亡、扶助农工等,并无大的差别[5]p135。这段时间在总体上中国左翼革命文艺尚未脱离五四文化,只是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一个暗涌的支流,但却是五四时期多元文化潮流最重要的一支。
二、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1928—1936)
1927年,国民党实行“清党”、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左翼分子的行径,迫使国共两党由合作走向分裂,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领导革命,以“革命”的暴力形式反抗国民党。不同于五四时期,共产党继承了马列主义意识形态中最核心的概念——阶级斗争,开始带有鲜明的阶级倾向和左的色彩。与此同时,国民党的暴行毁掉了国共合作的大部分基层组织,逐渐沦为一个脱离社会的利益集团,其文化合法性的构建也遭遇失败。20世纪30年代,整个知识界基本上都是“左”倾的[6]p4-6。1928年,文艺界喊出了“革命文学”的口号,以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和对五四“资产阶级”文学的批判与五四产生了自觉的分离,大批五四知识分子放弃自由主义而转向共产主义,一些五四时期重要的文学团体,比如创造社,亦旗帜鲜明地左转,成为革命文学的主力军。然而,在国民党背叛革命、大革命失败的政治危机中,革命文学走向了偏颇。党内在克服了右倾机会主义之后,又出现了“左”倾盲动的错误,对中国革命的内容和形势作出了错误的分析和判断,认为革命已经转变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最后的决战。将“革命文学”当作一场无产阶级的启蒙运动,来清算和消除五四“文学革命”这一“资产阶级启蒙运动”,试图建立纯粹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较五四时期,左翼革命文艺的最大特点在其政治品格,左翼革命文艺重新定义文学,认为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一切文学都是宣传,普遍地而且不可避免是宣传,把文艺看做是阶级解放的武器。五四时期“为人生”的文学遭到了左翼激烈的批判,而被五四强烈抨击的“文以载道”的传统被重新肯定。同时,文艺的艺术水准也有退化为“标语和口号”的趋势。在行为层次上,左翼将文学变成了生产革命的熔炉,文艺争鸣变成了文艺斗争、文艺暴动。到了“左联”时期,作家成了职业革命家,革命行动与文艺创作合为一体,文学创作化为秘密地贴标语、发传单,有的作家甚至牺牲在国民党的屠刀之下,例如“左联五烈士”。在思想意识上,坚持“打倒一切非革命的文学”的决绝姿态,认为文学如果不是革命文学,就是反革命文学,没有“第三种人”或“自由人”存在。这种意识也带来过一些负面效应,例如,把一切中间力量都看做是敌人,在文风上采取了较为激烈的手段,存在着暴力文风及“恐吓和辱骂”论战对手等行为。革命文艺还出现了集团化趋势,文学表达由五四时期的个人叙事转变为集体性叙事,革命、阶级、工农兵等集合性名词大量出现;审美旨趣从五四时期的灵动和浪漫,过渡到对力量、宏大的崇尚;在整体情感基调上,由五四时期的感伤、颓废、柔和等,过渡到激昂、壮烈。
总体而言,党对文化的领导权逐渐加强,实现了党组织对文艺的直接参与和指导,其标志是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这阶段文艺的革命主题完全凸显,明显与五四的启蒙主义渐行渐远,走向了无产阶级阶级革命的路径,为后来的延安文艺作了重要的铺垫。
三、承接与改造(1937—1949)
(一)前延安文艺——五四的“幽灵”在徘徊(1937—1942)
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抗日救国成为中国上下最为紧迫的任务,国共两党结束对抗,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爆发客观上要求民族团结一致,“左联”等文艺团体由于过于鲜明的阶级性不能满足时下全民团结抗日的新要求,纷纷宣告解散。革命文艺的口号也由左翼时期“国民革命文学”改变为“民族大众文学”,新口号不再单一强调无产阶级性质,更加包容,突出各党派各阶层的合作性。
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大批知识分子怀抱着理想主义激情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他们经历了五四的洗礼,尚未割裂同五四的联系,又积极投身共产主义革命运动。这段时间的文艺“一方面震荡着左翼的、革命的激情,另一方面也回响着‘五四的声音”,这种矛盾性体现在启蒙逻辑与革命逻辑的巨大张力之中。在“歌颂光明的同时也要揭露黑暗面”的思想影响下,丁玲、王实味等人的作品对延安社会的不足加以批判和揭露,违背了延安时期团结一致的整体性政治氛围,这促使毛泽东思考新的文艺方向和文艺政策。
(二)后延安文艺——工农兵文艺(1942—1949)
由于这一阶段党的中心任务是抗日战争,需要团结占全国人口最多数的工农大众,用革命的武装来打垮敌人,而五四话语显然已不再适用于抗战的新形势,前期延安文艺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左翼革命文艺之中继承而来的指导思想和创作风格逐渐为毛泽东文艺思想取代,形成了系统化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其起点是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称“《讲话》”),《讲话》强化了左翼革命文艺的几个基本原则,通过延安整风使这些原则成为知识分子创作的铁律。首先,毛泽东把文学与革命政治的关系进一步明确,提出文学要服务并服从于革命政治,规定文艺创作必须服从于抗战这一时代最大的政治,提出“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作品的意义和评判标准在于是否恰当、完满地表达了革命内容。在肯定了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一原则的基础上,毛泽东继承了左翼革命文学的文藝大众化,明确提出文艺须为最广大的革命者即“工农兵”服务,文学和艺术不再是五四启蒙文学那样“化大众”而是“大众化”。但毛泽东比左翼革命文学所达到的“大众化”程度走得更远,“大众”在范围上较五四时期有鲜明的阶级性,是无产阶级的人民大众,尤其是底层的农民。“他的大众化”更为彻底,他并不满足于艺术作品形式和内容的大众化(即为群众喜闻乐见),认定“大众化”的根本问题是知识分子的立场观念、思想感情、身份学识彻头彻尾地无产阶级化,这是地位和归宿的“化”,是彻底告别旧的阶级烙印,形成无产阶级世界观的过程,这时的知识分子已经由五四时期启迪大众的精英身份,转化为无产阶级的“学生”。而更为关键的是,延安整风在知识分子中灌输了党性原则,知识分子不再是五四和左翼时期“亭子间”里独立创作的作家,作家群体也被纳入了党的体系中,主要的文艺团体如“文抗”“文协”等是由党主办和管理,不少作家不仅是共产党员,还是职业的革命家和党的领导人,文学的党性原则和革命主义的价值观逐渐变成了革命文艺家们的自觉。党性的输入使文艺创作更加统一化,这次变革从根本上形成了此后社会主义文艺的创作路径,并为后来相当长时间的中国文艺定下了传统和底色。
《讲话》肯定了左翼革命文学“文以载道”的主体性作用,又将这个作用继续拔高,使政治衍生为一种普泛性的权威话语,渗透在文艺活动的方方面面。《讲话》同时边缘化了左翼文学继承的五四启蒙主义传统:启蒙意识、个性解放、人道主义、自由主义等。“五四”文学是从西方启蒙思想中去寻找思想革命的资源,它以重新确立人的价值为中心,以开启民智、批判蒙昧为基本指向,以实现人的自由价值为旨归,倡导的是“为人生”的平民文学,带有强烈的个性主义色彩,不能适应中国的革命形势,无法产生实实在在的战斗力。而工农兵文艺是以集团化精神来约束个人主义,把个人并入集体中,要求个人服从集体和革命,能为了革命的胜利而勇于牺牲自己,带有强烈的革命功利性和救赎精神,能够切实产生强有力的战斗力和行动力,为处在亡国灭种边缘的中华民族带来希望之火。
四、走向沉沦(1949—1976)
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指引下,向共产主义过渡成为中国人现实生活的主题。但由于“左”的思想的存在,思想文化领域发生了一系列的错误的政治运动,极大影响和损害了革命文艺及文艺家们的创作积极性,最终随着极“左”路线的破产,革命文艺走向了沉沦。
新中国建立起国家文艺生产管理体制,这一体制具有组织化和计划性两大特征[7]p3,把五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30年代“左联”的组织形态、延安时期党对文艺的一元化领导的基本框架,在国家体制层面确立起来,此阶段文艺继续“文以载道”的传统,围绕新生的共和国的合法性论证与新的国家精神的确立而展开,创作主题有两个方面的内容:歌颂社会主义和批判“非马克思主义”。其间虽在1956年前后由于“双百”方针的提出,文艺界涌现出一批带有启蒙精神的作品,但1957年反右后,这样的良好趋势渐渐终止。1958年“大跃进”运动展开,文艺界配合政治的潮流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文艺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期间,文艺仅“为中心工作服务”,为各种政治运动做宣传,文学批评的标准从“政治标准第一”渐渐演化为“政治标准唯一”,在此基础上,几乎对文艺的一切领域都作出了政治性的解读——题材、主题、人物甚至艺术手法,一些知识分子还受到批判和打击。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文艺作品刻板化,作品内容、表现形式等高度同一,例如,规定了“高、大、全”“三突出”“三陪衬”等创作手法。同时,“文化大革命”否定一切其他文艺,例如,左翼革命文艺被称为“文艺黑线”,外国文艺被称为“封、资、修”的“毒草”。“文化大革命”文艺在追求最纯粹的“革命性”过程中,不停地抛弃陈旧、否定现在,在全盘否定他者的同时,实际上也一直在进行着自我的否定,把自身的基础一点点抛弃殆尽了,随着极左政治路线的破产,最终走向沉沦。
五、结语
五四新文学后期逐渐陷入了情感主义、唯美主义的偏执与自说自话中不能自拔,在相当一部分作家那里,个人颓废失意和自由恋爱是唯一的主题,他们对社会的疾苦视而不见,沉迷于吟诵虚幻的“美和爱”,把救亡与启蒙的主题远远抛在了后面。当五四文学对社会的黑暗、人民的疾苦熟视无睹却醉心于不切实际的美和爱,当文艺界选择对民族苦难集体失明而专注于表现个人“浅薄而卑污的感情”时,强调革命、救亡,代表底层人民心声的左翼革命文学便应运而生,强力地扭转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的情感主义、个人主义倾向,将关注的主题指向了斗争、解放、阶级、集体等核心意向。左翼革命文艺极端强调文学的战斗作用,适合了党在大革命失败之后重振革命力量的需要。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强健而有力的延安文艺具有不容置疑的历史必然性与正当性:在民众挣扎于饥饿死亡线上、民族求生于虎狼成群的侵略者铁蹄下、国家苟存于力量悬殊的硝烟战火之中时,谁能否认工农兵文艺的历史价值?谁能无视它的正当性与道义感呢?谁能批评工农兵文艺对统一性与战斗力的强调?因此,革命的产生、发展与兴盛,实际上是历史的理性呈现与文化的智性选择。
但革命文艺也存在内在的矛盾性,体现在它的手段与终极目标恰恰相反,文艺本身是一种解放的力量,但在追求解放的革命中,文学却丧失自由而接受了规训。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革命文艺的主体性与革命统一性的矛盾、革命文艺的审美性与革命泛政治化的矛盾。详细来说,革命文艺是作为被压迫者寻求自身解放的文化,它的目标指向是自由与民主,而革命却客观上需要革命作家自觉化身为革命机器上的“齿轮与螺丝钉”,或是“留声机”,按照既定的轨道前进,并且将作为革命的“螺丝钉”看做是主体获得自由的象征;极左背景下的文艺羁绊于政治功利之下,逐渐丧失了作为艺术应该具有的美学特征,消解着左翼自身的合法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要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在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过程中,要吸收革命文艺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处理好文艺与政治、审美之间的关系。
参考文献:
[1]许纪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上卷)[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0.
[2]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
[3]余英时.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4]黄文治.革命播火:知识分子、城市串党及革命下乡——以大别山区早期中共革命为中心的探讨(1920-1927)[J].开放时代,2011(12).
[5]高华.革命年代[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
[6]旷新年.1928:革命文学[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
[7]李洁非,杨劼.共和国文学生产方式[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作者简介:陆茹(1987—),中山大學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史。
责任编辑 / 马永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