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顺的鼻子
钱 静
1
刘顺下了客车,远远就看到村庄了,最显眼的是水塘东边政府给建的搬迁房,刘顺家是其中之一。人字形的彩钢瓦屋顶,雪白的墙壁,它们像灯盏点亮了山村的灰暗,或像时代的一股鲜亮光束投射到这里来,启蒙山村的快速成长。厨房和围墙还没建好,大约半年后才能住进去。水塘下面,在村委会多年的王医生建起一幢三层混泥土楼房。刘顺进去过,曾经洁白的墙壁粘了许多苍蝇屎,门框上也有岁月积攒下来的污垢。住进去只半年时间,就这个样子了,他觉得糟蹋了好模样。
他站在公路边,深深地吸进一口气,再慢慢吐出来,仿佛让心情平静下来,准备开始另一段生活的跋涉。
刘顺走到村口,一股酒味软软地扑进鼻孔,还有另一个味,带点阴气,阴气到底像什么味,他说不清,总觉得怪怪的。再吸一鼻子,两鼻子,三鼻子,也是这两个味。当然,他闻到的还有别的味道,都是农村特有的寻常味道。对他造成震动的还是前两种。他三天前曾闻到一些,但没有此时清晰明朗,可能是因为哥哥的事影响了嗅觉。刘顺的鼻子向来是敏锐的,一个物件可以闻到三四种气味,有时能闻出第五种,工友在他身边走过,他们吃了什么饭菜,在他的鼻子面前藏也藏不住,一说一个准,就像他亲眼看到那一桌饭菜。一个大学生工友说,他的鼻子天赋异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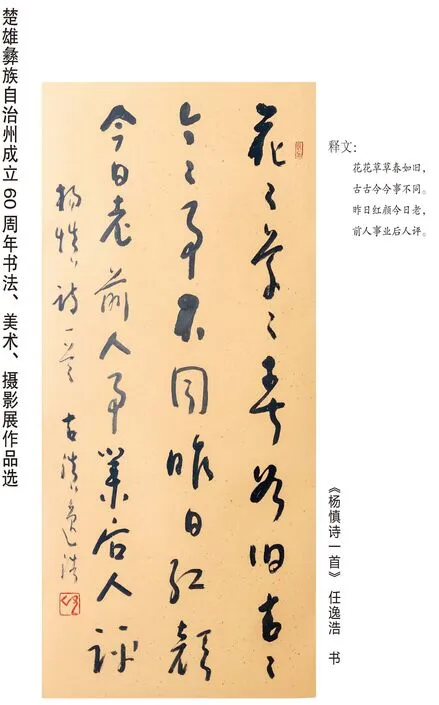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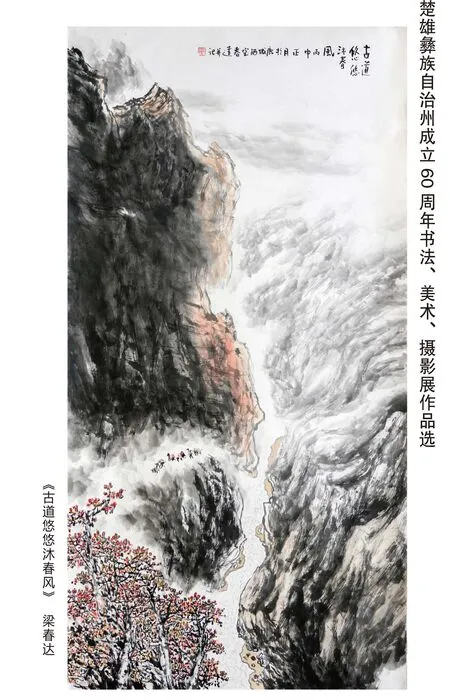


现在,回来了,不再离开这个生养自己的村庄。如果让他选择一生的居住地,他不会选择这里。他更喜欢陌生的地方,也许这来源于他喜欢诗歌的天性。诗歌总是贴附着新的东西,而不是陈旧。但他必须回来。
姐姐十年前远嫁他乡,父亲半年前去世,哥哥三天前死去,家里只剩孤单的母亲。他在城市像一块破柴皮一样漂浮,居无定所,无力带着她。他曾跟母亲说,让她去姐姐那儿,她说,姐姐跟她合不拢,再说,那边两个老人,已经让姐夫皱起眉头,她再过去,晓不得会皱成咋样。她不想看到他们紧缩的脸,就在这儿呆着。更重要的是,她想住搬迁房。三十年都住老房子,现在,政府的强烈光辉照过来了,该享受享受。母亲只五十多岁,如果正常一点,还能劳作,他放心,可她喝酒,不,是酗酒。父亲和哥哥就是在酒上报废的,他不想再让母亲走上他们的老路。
他父亲十五六岁就开始喝酒,喝到四十五六岁,肌肉被酒精抽走了,瘦了一大圈,手抖脚抖,能把平路走成坎坷崎岖的样子,而且两脚平移,像裤裆里夹个石头,已经像个八九十岁的老头。他不能做重活,勉强做些家务,农活丢给哥哥和母亲。后来常卧床上,躺了五个月,死了。哥哥小学毕业就回来,十七八岁时候,能干重活了,干完活计,跟着周围的大人喝起来。这两年,跟表哥黎爱华喝得昏天黑地,白昼不分。村里十七八岁的男子,都喝酒,有几个女人也喝,母亲就是其中一个,醉了,一屁股坐在地上,中年妇女的泼辣劲儿全放大了。在村里,只要有五年以上酒龄的人,几乎都有酒瘾。
从刘顺记事起,村里人就好酒,这些年来越发严重了。他并不拒斥酒,疲劳时喝一点,也是好的,可村里除了吃饭,几个人闲聊要喝,干活的地里也喝,坐在客车上也喝,把酒喝得无处不在,喝得惊天地,泣鬼神。在这远离街市的偏僻地方,干完农活,除了电视,没有别的娱乐。电视是虚的,手伸得再长也够不着,给这些成年人的快乐极其有限,唯有酒能在这枯燥的生活里挖个小洞,对着这个小洞,才得以畅快呼吸,把日子过下去。他们的闲聊需要酒做佐料,没有酒,话语无法继续下去,就像一辆车没有油无法行驶。在这话语的行驶中,相互的情感得到交流,心贴近了,生活才有点温暖,才有点滋味。如果到谁家,没有倒酒,心里总是缺少一点东西,话也无法说下去。常往来的人会直说,倒点酒喝,主人如果说,没买酒,客人觉得索然,一次还可以,两次三次都没倒酒,以后关系就硬了,干农活请人都难请。随时随地的饮酒,瘾慢慢上来了。上瘾的人,都是为了痛快,对自己的命已经不管不顾了,宁愿在酒浸泡下的赤裸快乐里至死不悔,也不愿碰触酒之外的更多东西。
2
刘顺走进巷子,这村中的肠道,弥漫着浓烈的酒气和阴气,仿佛它们就是寄居在这村庄里永不消散的灵魂。
迎面走来十四岁的狗胜,手里捏着一根干枝条,边走边拍打墙脚和地面,仿佛是探寻地下宝藏的勘探队员。狗胜是智障少年,在学校读书时候,考卷上所有填空的地方,都写上 “土” “木”,老师曾在班上说,他是在考卷上盖房子,引来全班大笑。
刘顺的家在村子边上,拐过两个墙角就到。他推开院门,地面的苍蝇跳蚤一样远远跳开。村里的苍蝇烦躁而稠密,像难以驱赶的雾障。整个院子里没有一点声音,只有远处传来突突的拖拉机声,模糊的声响,像带着毛边,或像裹在氤氲里挣脱不开的树影。天空蒙着一层灰白的云,射下来的阳光在院子里不甚明朗。
空了,这个家,一种生活不知要怎样继续下去的茫然和忧郁扑到心头。
三间正房的门关着,只有左边的厨房门半开。他走进去。母亲坐在桌边吃饭,面前摆着一碗猪排骨和一碗红豆汤,豆汤很纯粹,没有一片青菜或腌菜,像这即将开始的寡淡日子。她抬头看他一眼,放下筷子,说,我吃冷饭,晓不得你要回来。她起身去洗锅煮米。他看到母亲的眼皮是泡的,脸也带着浮肿。这不是哭出来的,是酒精催逼出来的。哥哥抬上山的那天她没怎么哭,傍晚就喝酒了,夜间,在几个闲聊妇女中,她还露出缥缈的笑容。
他心里压着气愤问,你又喝酒了?母亲说,喝着一点。
“死了两个,你还不够,还要跟着死,你活够了?”
母亲没有回答,走出门去隔壁屋里舀米,刘顺跟出去。米袋旁就是十公斤的酒桶。哥哥的丧事上,来的人都提一瓶酒,都是村里买的,全倒在二十五公斤的塑料桶里,出殡后的当晚,只剩八九公斤,刘顺把它倒进十公斤的桶里。现在,酒落下去六公分左右,这六公分在三天时间里,一部分招待客人,一部分肯定落进了母亲的肚子,晕染了她空乏的日子,使自己免于寂寥的敲打。他本想把它倒进臭水沟,可来个人,还得去买。
母亲把淘洗过的米放进电饭煲。电饭煲上苍蝇恶作剧似的点了好多粪便。她咋不擦洗一下呢,他心里的不快膨胀开。母亲坐回到桌边吃,他抓下墙上挂着的抹桌布,从缸里舀半瓢水浸湿,细细抹电饭煲。他在城里,有点想念这个家,想念母亲,一回来,看到母亲的样子,那些想念全没有了,像一缕缥缈袅娜的白雾,走近,又看不到了。原本昨天就可以回来,但他想再看看曾经熟悉的城市,以便在今后冗长的岁月中,有个念想,让精神得以呼吸。他在市区里游了三个景点,一直到黄昏才回到旅社。如果汤莉还跟他好,她会陪着他,可她在一周前离开了。他只能独自走进景点。当他站在金殿大门口,回身看城市,想到两句诗:
阳光收留了冬天
总穿透不了蓬勃的城市
公园一角的海棠花憋屈地绽放
等待夏天的火锤
回到家,那萌动的诗兴在酒气和阴气的夹击下,将逐渐飘散。可自己得回来,再失去母亲,他就没有家了。
刘顺吃完饭,走出厨房,桂芝在屋檐下撒麦粒喂鸡。他问母亲,烟山哪里没挖,母亲说,大麦地一块都没挖。这可是一年的衣食饭碗。别人家,每年的烤烟收入多的八九万,一般的也是三四万。家里是最少的,才一两万。他不明白,别人喝酒也能好好种田地,可哥哥和母亲,把田地耽误了,常常醉了睡,睡了软,没精神干活。
3
刘顺和母亲扛着锄头走出家门。天空亮开,阳光照在对面的山梁上,像被稀疏的树木、房屋吸尽了,显出绵软的样子,不像在城市,暗淡的阳光落在坚硬鲜亮的楼房上,折射回来,让它回归到跃出太阳时的坚挺明亮。
母子俩走进一片树林,到了林子尽头,前面是一片核桃树,再过去是一座硕大的山,山坡平缓,长满茅草。刘顺家的地在小路下面,走过二十来米的松林就是,大大小小有六七块。母亲在松林脚开始挖烟山。烟山横向挖,一尺宽,两边挖出浅沟,烟苗就栽在分隔出的条形土丘上。刘顺到下方去,离母亲远远的。
刘顺做过一些农活,但不多,挖了两条烟山,觉得累了。他直起腰,手拄锄把,看看周围还等着挖的地,心就蔫了。也许过半个月,身体适应了这样的劳动就好了。他不再想哥哥和父亲,想也是没用的。他想到的是汤莉,如果她在身边,也许日子会有些色彩,但她投向了另一个男人的怀抱。
刘顺在一个纸箱厂,每天在手动钉箱机上给硬纸板打钉,这还是村里在县税务局工作的远房大伯介绍的。每天上班十个小时,一周休息一天,工资2500元,跟他在机器上打钉的有三个女工,都是结了婚的,下了班就回宿舍。他跟五个男工住在厂里的集体宿舍,与他们交流不多,他是个心事比说话多的人。
认识汤莉是个休息日,他独自一人到城里,进书店里买了一本雷平阳的《云南记》,逛到下午,在一个小吃店里吃了两碗饺子。回厂已经是傍晚。他走在一条煤渣铺的窄路上,路两边是玉米地,右边玉米地上面是一片果林,他曾在果林边读买来的诗集,一直到黄昏才回厂里。离纸箱厂只有一公里的时候,一个女人坐在左边玉米地埂上埋头哭。他走过去,女人抬头看他一眼,脸转向远处,泪水还挂在眼睫毛上。女人看上去三十岁,说不上很漂亮,但也不难看。大眼睛,宽颧骨,哭时下巴往上收,已经显出难看了。刘顺知道,再好看的女人哭起来,五官是浮着的,会被哭拉向丑。一个女人独自在这里哭,总有一些生活的不如意,他觉得应该问一问。他说,咋了,我能帮你什么吗?
她说,你帮不了我,你走。听口音是云南人,但他不确定是哪个地方的。女人皱着脸又哭起来,肩膀一耸一耸的,披肩的长发也跟着抖。刘顺站着,看着西边楼房林立的城市,又看看将落的太阳,转身回到路上,继续向前走。
身后传来女人的声音,你停下。刘顺停下脚步,转身,不确定她是不是喊自己,看看周围,没有走动的人。
女人扭头对着他,你能陪我去喝酒么?他可不想跟一个完全不了解的女人在一起,现在的女人什么鬼把戏都有,她们表面装得像一只楚楚可怜的兔子,内心却暗藏着一只狐狸。他说不会喝酒。
女人用纸巾抹了抹脸问他,是不是在上面的纸箱厂上班?他问她是怎么知道的。他可没见过这个女人。刘顺离她两米远站着,一星纸屑粘在她的颧骨上,微风总是摇不下来,像一面顽固的白旗。
女人说,以前她来这里散步,见他在前面果树边看书。还告诉他,她在左边玉米地那边的建德板材厂上班,是实验室里的检验员,已结婚一年,丈夫是一家制药厂的办公室主任,他们还没有孩子,她要求丈夫和她一起去医院检查,丈夫不肯,说离婚算了,性格不合,实际上,背地里跟一个比她漂亮的女孩好上了。两人今天离了婚。
建德板材厂离纸箱厂大约三公里,两个厂跟城市组成一个正三角的样子。刘顺走出纸箱厂的大门,远远就能看见板材厂外的空地上,堆了好大一片原木。既然是板材厂的职工,也没什么好怕的。他回厂里也是无聊,宿舍里,工友不是看电视就是玩手机上的游戏,几种声音火锅一样搅在一起,根本没法看他的诗集,便答应了。在去城里的路上,他问女人的名字,她说她叫汤莉,是鹤庆县的,板材厂的厂长是她堂表哥,她的工作是检验制成的板材甲醛释放情况,如果未检测出甲醛释放,才算环保的板材产品。
以后的几周,刘顺的休息日都跟汤莉在一起,两人在城里吃饭,逛街,便住到酒店的一个房间里。在开房的时候,他看到她的身份证,1991年出生的。想不到她才二十六岁。
三个月后的一天下午,也就是一周前,她约他在城里见面,跟他说,他俩不合适,分了吧,刘顺脑袋嗡的一声响。
“为什么?”
“不为什么,就是不合适。”汤莉的眼睛看着远处。
他没再说什么。他不是勉强别人的人,虽然心里有不舍。他想一定是自己出身贫寒,前途渺茫,比不上她有个堂表哥罩着。
“好吧,但我要告诉你,你不管对我怎样的态度,我一直喜欢你,今后也是。”
“谢谢。”说完转身走了,下午的阳光生硬地落在她浅蓝色的连衣裙上,她身后的裙子僵硬地摆动。
4
“过去,你走远点,不要过来。”
刘顺直起腰,母亲对着松林喊,接着,丢下锄头,边喊边往地埂下的马路跑,脚步慢下来,不时回头看,沿着马路往村子的方向快步走。可他没看见母亲身后有什么。刘顺全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感觉凉飕飕的,像有一股冷气围着自己。他虽然不相信那邪乎的东西,可说的人多,心里也有点发毛。原来想,看见哥哥或父亲,会高兴,可真看见了,可能像母亲一样吓得往家跑。
母亲跟刘顺说过,在来的那条山箐里,昨天傍晚,李德去看他家的烤烟地,河底走来刘顺的哥哥。他全身起了一片鸡皮疙瘩,赶忙折回来,走几步,回头看,他哥哥不见了。李德在路边折一把飞机草,撒尿冲在上面,甩甩,念几句,把飞机草丢在后面,身上的鸡皮疙瘩慢慢收回去,心里才不怕。刚才母亲看到什么,让她这样惊慌,莫不是像李德一样看见哥哥或是父亲了。
山箐里冲来一股凉风,刚才母亲对着喊的那片树林,枝叶哗啦响。
太阳快落山,刘顺扛着锄头回家。他走的是地埂下的那条马路,那里空旷一些,路两边都是庄稼地。他走一段路,回头看看。
回到家中,母亲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剧, 《男人不可以穷》,对着这片名,刘顺很想笑,但他笑不出来。他闻到一股浓烈的酒味。
他走进隔壁的屋子,把那半桶酒提起,走出院子,汩汩地倒进院门前的水沟里。身后响起脚步声,母亲来抢他的酒桶。
刘顺把母亲的手掰开,直起身,向前走十来米,把酒桶甩到斜坡下,酒桶滚下去,在半腰被一个树蓬挡住了,里面的酒晃来晃去,还汩汩往外流。母亲见里面还有酒,弯腰下斜坡。她揪着酸筋草小步挪,脚下一滑,一屁股坐在斜坡上,慢慢起身,继续往下小心走。刘顺站在坡头,感觉这个老女人没救了。迟早的事,她面前的路,毫不拐弯,笔直地通到那里,而且这路短促,不堪一目。狗胜站在巷子口,看着他和母亲,手里还捏着那根干枝条。他张望一下,甩着枝条走过来。
母亲左手提桶,右手抓着草蓬爬上来,额前的两缕头发掉下来,在一张暗黄的脸前一晃一晃的。那倔强的身影,一副英勇赴死的样子。她爬上坡头,粘了灰土的酒桶提在手里,桶口前面凹下鸡蛋大的一个坑,里面还有半斤左右的酒。刘顺已经出离愤怒,语调反而平静下来,你难道晓不得这酒是假酒,是有毒的酒。她说,别人都喝,没有人说是假酒。
你就相信别人,你从来就没有信过自己,两条命就死在酒上,都不能让你相信?他的愤怒又升腾起来。母亲默默走进院门,膝盖碰到酒桶,酒在里面晃荡,像受到挽留而欢欣雀跃。刘顺看着远处的山和雾霭中的村庄,深深吸一口气,然后憋住,憋得太阳穴的青筋暴起,才用力吹出去。他转身,看到狗胜看着自己。刘顺问他喝酒么,他说不喝。刘顺叫他以后也别喝,对脑子不好。
“二爷,酒里真的有毒?”
“有,喝多了人会死,而且死得快。”
“我爹也喝酒多,他以后也会被闹死?”
“肯定会。”
“这个话不要跟你爹说,说了他会恨我。”
“嗯。”
5
刘顺走进院子,坐在屋檐下。正常烤的酒,一公斤的小麦也就能出三四两,他听说,村里有人在烤酒时放上化工添加剂,可以烤出八九两的酒,翻出一倍还多。一公斤酒十五块,这是多诱人的利润啊,比城里卖菜短斤少两还赚钱。他想去烤酒的三户人家里说,不要再烤有毒的酒了。那些酒他们自己也喝,说是假酒,他们不会承认,还要恨他,闹到不可开交,以后得在这里生活呢,而且还沾亲带故,再说,父亲和哥哥也有责任。母亲喝完那半斤酒,可能会再去买。恨就让他们恨,父亲和哥哥就死在这些毒酒上,不去起诉就算便宜他们了。
他到李建才家。李建才一家正在堂屋里吃饭,让他坐下一起吃。他说家里也快吃得了,说几句话就走。他站在门口,李建才手里捏着筷子来到他面前。李建才四十多岁,皮肤黝黑,背微驼,深眼窝,头发蓬乱,也许从出生就没梳洗过。相貌已经跑到他的年龄前面了。
他很想说父亲和哥哥就死在酒上,但还是忍住没有说。李建才答应以后不卖酒给他母亲。那些若卖给她,出现严重后果,让他负责的话,刘顺说不出口,面对这些说话还算温和的亲戚,他没法说,他也不是随便说狠话的人。
刘顺走出李建才家,又去另外的两家,他们也都答应不卖酒给母亲。
他回到家中,母亲已经把饭菜摆到桌上,一碗腌肉和一碗炒土豆片。她正摆碗,眼神里带着酒意。他愤恨地想,她要时时快乐,天天快乐,直到快乐至死;谁不晓得快乐好啊,可快乐过了头,生活里只有单一的乐,人会傻掉;狗胜其实不傻,他有他的痛苦呢。
吃完饭,母亲做了一些家务,出去了。她喝了酒,喜欢到别人家里闲聊。虽然哥哥刚死三天,但刘顺能想象得到,她在人群里一定是有说有笑。他转念想,这样也好,人总不能生活的痛苦里。
他到现在,也没有从失去汤莉的痛苦中走出来。他知道,汤莉不是完美无瑕的女人,她好玩乐,好虚荣,长相也不是很漂亮,但他还是忘不了她。他不会喝酒,要让这种如撕咬般的痛苦清晰地经历着,这种感觉让他既难受又有一种美妙横穿其间,如果是酒精的麻醉,可能会剥去那层美妙,只剩赤裸的痛苦了,他更讨厌那种状态。刘顺想到那个酒桶。他楼上楼下,每个犄角旮旯找遍,都没有看到。
刘顺上了耳楼,躺在床上看他的诗集,他又看到那首 《光辉》,已经读了好几遍,仍是喜欢。
天上掉下飞鸟,在空中时
已经死了。它们死于飞翔?林中
有很多树,没有长高长直,也死了
它们死于生长?地下有一些田鼠
悄悄地死了,不须埋葬
它们死于无光?人世间
有很多人,死得不明不白
像它们一样
他想到父亲和哥哥,还有母亲,感叹一会儿,又看了几首诗,眼睛迷糊起来,睡着了。
6
刘顺起床的时候,天光大亮,母亲在屋檐下洗脸。他不知道母亲昨夜什么时候回来的,让他有种错觉,母亲一夜没睡过。
母亲起身在铁丝上挂毛巾,面无表情地说,李德昨晚被刘顺的二婶缠了。他问哪个二婶?母亲说,把坝塘挖深的那个你二婶。母亲说过,下雨的夜里,为防止水塘被冲垮,二婶用身体挡住进水的渠口,第二天死在渠口上,死时七十六岁。被鬼缠的事,他没有亲见,半信半疑。
他洗完脸,倒一杯茶水,坐在堂屋里的沙发上慢慢喝。院门咔嗒响了一下,有人三妹三妹地喊。刘顺听出是村长刘永贵的声音。母亲走出厨房,他起身站在门口。
“刘顺回来了?”
“嗯,回来了。”
刘永贵让刘顺的母亲准备两棵树杈枝,赶一下屋里的鬼。还说,村子里到处是鬼魂,这两年不在了好几个,再这样下去要不成,赶完把树枝拿到晒场上,统一装进麻袋里远远地烧掉。他最后说,你家拿两棵树枝。
“二爷,那坝塘还填么?”刘永贵往外走,刘顺对他的背影说。
“昨晚,你妈也见着了,挖坝塘的你二婶缠着李德,不让我填坝塘。不在的人都向我发话了,我敢咋整。”刘永贵说完出去了。刘永贵曾说,这个坝塘挖深后,全村一百多个人口,不到两年时间,死了四个人,超过了以前五年内死的人数。第一个是二婶,死在水口上,第二个是刘永贵的爹,喝了酒开着三轮车,在从镇上回来的路上,车翻到公路下,肋骨断了四根,内脏也伤得不轻,还没送到县医院,人就没了;后面的两个就是刘顺的父亲和哥哥。听村里的李德说,一年内还要死一个人,有人背地里说,是刘顺的母亲。听到这个,村长认为,坝塘里护佑全村的神奇东西被刘顺二婶挖走了,村里死那么多人,拿定了是坝塘干的坏事,决定填了它,他不想再让自己的家族遭受损失。现在,死去的二婶不让他填,还让他跪在她面前发了誓,永不填水塘。在二婶活着时,他没正眼看过她一次。
母亲让刘顺到房子下面取两根桂花树的枝杈。刘顺走到门口,狗胜从左边的巷子走来,手里捏着半截木棍。
“二爷,酒有毒这三个字咋写?”狗胜仰着脸问。刘顺在地上捡个石子,在石板上写给他看,写完,走出村尾,爬到地边的桂花树上折两根树枝下来。他回到院门口,狗胜蹲在地上边看刘顺写下的字边在一旁用木棍划,屁股上面一根有花色条纹的布裤带露出来,像条缠在腰间的蛇。
刘顺把树枝递给屋里走出的母亲。她拿着树枝楼上楼下甩,每一间屋子都甩,在猪圈门口也绕几圈,嘴里叽叽咕咕念叨:冤魂鬼怪快点走,家里不是你呆处,走,走,走。母亲反复念这一句,最后提着爬满了鬼魂的树枝出院门。母亲的手臂斜支着,生怕想像中的鬼魂粘上自己的裤腿。刘顺看着,有点想笑,但又笑不出来。
刘顺回到屋里喝水。喝了两缸水,扛着锄头出去,昨天那块地只挖了一半的沟,得接着挖。他转过一个巷子口,母亲从刘永贵家出来。
他对母亲说,跟他去挖烟山。他感觉像对一个孩子说话。不催促,母亲可能又要在家醉酒,不想做活,他不得不这样说。
母亲让他先去。她走过刘顺身边,他闻到一股浓烈的酒味。他觉得跟卖酒的李建才白说了,她有喝到酒的渠道,他不可能每家都说不要给母亲酒喝,即使每家说到,谁也不敢保证有人不给她喝。只要这三家酒坊存在,母亲就能喝到酒。他拿出手机看看,快到九点,县工商局已经上班。他四处扫一眼,在巷子里举报,被人听到不好。他快步走出巷子,上了坝埂,又往通向山箐的马路走。看看四周没人,打开流量,在手机上查找县工商局的举报电话,找到后,拨了过去。接听的是个男人,刘顺刚说反映一件事,男人就问他的姓名,地址,工作单位。刘顺告诉了他,并把村里三家卖假酒的事说了。男人说,过两天我们去查。
7
三天过去了,刘顺没听到县工商局的人来,一周过去,村里还是没人说起有工商局的来过。刘顺想打电话催一催,可想想,人家不想来,再催也没用。这条路看来是没指望了。
刘顺回来的这些天,白天做农活,晚上哪儿也不去,做做家务,看看电视。村里人见他这样,认为他出过几年的门,有点见识,看不起他们,于是也就不跟他来往,路上相遇,也不大说话。出圈粪时,母亲去喊人帮忙,只来两个跟她常在一起闲聊的妇女,男人都借故说忙不开,没有来。
一天黄昏,刘顺觉得这样封闭自己也不是事。他去黎爱华家。他哥哥活着时常和黎爱华在一起喝酒闲聊。黎爱华三十八九岁,待人平和,三轮车、摩托有点小毛病,几分钟就解决了。从祖辈论下来,刘顺跟他是表兄弟关系。黎爱华倒半杯酒给他,刘顺没有喝。他独自喝着,最后把刘顺没喝的酒也倒进自己的杯子。黎爱华已经离不开酒,每天都要喝点,两三天没喝到酒,手就抖起来,像个老人。他跟母亲一样了,刘顺想。过不了两年,他也会像哥哥一样死掉,留下他待人平和的老婆和正上初中的女儿。听母亲说,他媳妇,为他喝酒干不了活计哭过几次,有两次跑回娘家。他的心沉下来,他们不应该这样的,他们应该健康地活着。黎爱华对刘顺说,你哥在的时候,我们俩经常在晚上喝酒款白话,有时候两个人会坐到半夜一两点,有一晚,到十二点,一人抽了一包烟,一个人喝的酒不下八九两,但就这样款,也不咋醉。他不在之前那个星期,我没跟他在一起,这个倒是确实的,我不骗你。
黎爱华说起刘永贵运送四麻袋粘上鬼魂的树枝的事。这是全村的鬼魂。刘永贵让王福医生的皮卡车送出村,王医生没答应,担心自己的车粘了邪气以后出问题。他又问有三轮车的人,他们都不愿意。他只好让四个人回家拿一根绳子来,把麻袋拴在车后。车是他的马自达CX-7,花了二十四万八千元买来的。四个男人每人拿跟木棒在后面扒着,不让袋子掉到公路下。车子慢,他们还是小跑着,木棒不停地扒。四个麻袋就像猪尿泡一样被闪着银光的小车拖着跑,男人们在灰雾中笨拙地追赶着 “猪尿泡”,不停地弯腰、直腰,像舞台上忙碌的小丑。刘顺后来看到,刘永贵的车前车后、玻璃上粘着一排排画着符章的草纸,在风里,裙子一样荡起来,像个时髦女穿上草裙,妖娆而狂野。
刘顺没有接他的话,说, “被鬼魂缠的事,表哥亲眼见过?”
“见过,李德被缠那晚我在,李建才被缠我也在。”
“什么人容易被缠?”
“经常喝酒,身体弱的人,女人小孩也会。”
刘顺脑子里有了一条线,喝酒,身体弱,精神迷糊,被鬼缠。
一个星期天,刘顺从别的村提回一桶酒,趁母亲进厨房,他把酒提上楼,藏在自己床下。饭后,自己偷偷喝半杯,出了院门。
他去刘永贵、李建才、黎爱华家,和他们聊天,聊他城里的打工经历和家里的农活,更多的是听他们说。他们倒酒给他,他不喝,只抽烟,酒意散了回来。他们到他家里,他拿出从别村买来的酒给他们喝,自己也喝一点。他们说,这酒味道好,你只喝好酒。后来,刘顺去他们家,磨不过他们的盛情,也喝他们的酒,只是少一点。每次喝完,头都疼,喝了几次,头慢慢不疼了。母亲问他,你咋喝酒了?他说,你都喝了,我咋不能喝。她用不解的眼神看他几秒,也就不再问了。
天已经黑了,母亲在堂屋里看电视,刘顺坐在厨房里,头靠着墙,累了似的微闭着眼。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微微睁开双眼,脑门皱了一下。眼前站着黎爱华,还有好多人。他说我在哪儿?两三个人说在厨房,他又问,你们咋都在这儿。母亲告诉他,他刚才被父亲缠了。黎爱华说,是他母亲把人叫来的,并向他叙述他被缠的经过。
他一副父亲的嗓音,要找村里烤酒的那三个人和刘永贵,母亲把他们喊来。他说: “李建才,王福,李盛明,你们三家烤的是假酒,害死了村里的好几个人,再烤这样的酒,你们的命不会超过两年。想多活几年,以后就不要烤酒,烤好的也倒掉。我问你们,以后还烤不烤酒?”
三人低头说,不烤了。声音软软的,像受审的犯人。
“黎爱华,你再喝酒,也不会超过两年,你还想再喝么?”
黎爱华小声说,听姨爹的,以后不喝了。
“刘永贵,你也听见了,你不管好,他们三家再烤酒,连你都活不过五年。大嫂跟我说了,你没有填坝塘,还做得好,不然,大嫂整你了。”刘顺又用他父亲的嗓音和语气说: “我回来,是要瞧瞧刘顺,顺便跟你们说说,现在,见他好好的,我们走了。”周围人等了一会儿,见刘顺父亲不再说什么,确定他走了,才小声说话。黎爱华让刘顺母亲赶快去烧糖水,等刘顺醒来给他喝。话说完,刘顺的脸开始皱起来,嘴里哎哟哎哟地轻声哼叫,很痛苦的样子,哼叫停止,脸上平静下来。
刘顺听完母亲叙说自己 “被父亲缠上身”的经过,没说什么,洗了一把脸,让他们去堂屋坐,很多人走了,留下来的只有黎爱华和李建才。他倒酒给他们喝,他们俩说,不喝了,喝茶水得了。刘顺便泡茶,自己喝母亲端来的红糖水。
黎爱华和李建才走后,刘顺问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母亲,那桶酒喝完没有,她说早两天就喝完。他再问,家里有没有酒,她说有一壶。他让母亲拿来。
母亲问他: “要喝酒?”
“喝什么,我爹都告诉你们了不能喝,倒掉。”母亲拿来一个深绿色军用水壶,问他买的酒呢,他说,我的酒没有毒,留着做活计时招待客人。刘顺把水壶握在手里掂了掂,半壶是有的,拧开盖闻,是酒,但闻不出是不是村里买的假酒。他的鼻子这些天失了灵敏,除非浓烈的味道,其中的细微已闻不出,连那股阴气也完全没有了,他不知道,是那些味道没有了呢,还是自己的鼻子找不出它们来。刘顺拿着绿色军用水壶,走出院门,咕嘟咕嘟地倒进黑夜的嘴里。
8
第二天,刘顺和母亲背着两篮烟秧去地里栽。天晴得好,阳光洒在山箐里,明晃晃的;栽下去看来得浇水,不栽,时节又过了。他的手机响起来。自从回来,他的手机像哑了一样,这是唯一响的一次。突然的响吓了他一下。母亲也好久没听到手机响,抬头看着他,手里的烟秧杵在坑里,忘了扒土。他掏出一看,是个陌生的号码。他喂了一声,有个男人的声音传来,问他是不是叫刘顺,是不是在家,他们是县工商局的,已快到村口,让他带他们去烤酒的那三家。他说,他在地里做活,让他们自己去,告诉他们不要说是自己举报的。男人说,怕什么。他说,我们都是亲戚,以后咋跟他们处。男人硬硬地说,好,晓得了。
背去的烟秧栽完,已经十一点多。刘顺和母亲回去。两人走到坝埂,看到李德驼着背站在水塘边,目光在水面上晃。俩人走到他面前。他说,县工商局的来了,收了李建才和另两家的酒,酒甑丢到崖下了,说他们烤假酒。刘顺问他们用什么检测。他说,就闻一下,尝上一口,就把酒甑抬掉了。
刘顺在手机上查过的,检验酒的质量得靠仪器,要测出甲醇、总酸总酯和酒精度,得有五六天才有结果。他们肯定是嫌路远,也不想多跑,用鼻子跟嘴就测掉了;也许,他们的嘴和鼻子经过多年的训练,跟检测器也差不多。
村里背地说,是刘顺举报了李建才三家的酒,但他们三家又没有去找他说,好像说破了,脸面上不好看。刘顺走在巷子里,每个人都会用直直的目光看他。晚上,黎爱华来家里,刘顺倒了半碗酒给他。他倒回酒桶一点,说,少喝点。
“县工商局的来,是不是你举报的?村里都这样说呢。”黎爱华淡淡地笑着,好像是随便说一下。
“没有。得罪人的事我咋会做?”
“听李建才说,他看见狗胜在石板上写 ‘酒有毒’这三个字,问他咋晓得酒有毒,狗胜说,是你告诉他的,而且你又不喝村里的酒,所以李建才就怀疑你举报的。”刘顺坚持说自己没有举报。
村里人不相信他的否认,跟举报联系起来,也怀疑他被父亲缠的事是否是真的,也许是假托他父亲的嘴来阻止村里烤酒。
李建才在巷子口对黎爱华说: “村里是不能缺酒的,没有酒,请人做活计哪个来?”
“是啊,没有酒,话都找不着说,个个变成哑巴了,村子可以改名字了,叫哑巴村,呵呵。”黎爱华手里夹着烟,脖子一扭,笑了,牙根漆黑,像发霉的树桩。
“酒有毒,狗屁,哪个杂种说的。”李建才骂着,黎爱明呵呵笑。村里卖烟叶每年六七万的人家已经买上了贼亮的小车,路上呜呜地跑,狂得很呢。自己呢,只两三万,吃喝剩下的钱,连一辆三轮车都买不起,到镇上搭个顺风车还得看人脸色。不卖点酒,出酒率低,咋能买一辆三轮车,没车,酒碗都不好意思跟人家摆在一起。假酒咋了,城里什么不假,假化肥,假种子,连人都假。有一年,全村土地都种上豌豆,签了合同的,最后因为扯皮事,老板不来收了,多数烂在地里。管得过来么?人家照样吃香喝辣。李建才这样一想,悄悄做了酒甑,开始烤酒了,另外两家也紧随其后。
酒有没有毒,村里人不知道,他们检验的标准是脑袋会不会疼,但脑袋没有疼过;至于县工商局的检查,他们觉得靠一张嘴就知道有没有毒,不大相信。开始,大家也怕喝到毒酒,买酒要到别的村去,慢慢地感觉麻烦,就近方便。村里人的酒,又跟过去一样喝。刘顺觉得自己白费力气了,但这只在他脑子里一闪而过。
刘顺的桶里还有一半,黎爱华来家,他就倒出喝。很多时候他也喝得迷迷糊糊,去黎爱华家里,他也喝他的酒,开始少一点,后来跟黎爱华的一样多。刘顺的酒喝完,他也不想到别的村买,太远了,而且,村里的酒也感觉没什么,他就去他们三家买了。母亲在刘顺面前很少喝,她比刘顺起得早,刘顺起床,她已喝下五钱酒。有时她对刘顺说,少喝一点,刘顺说,我晓得。虽然晓得,可他每次没少喝。他觉得,这样的日子过下去,也不错,至少汤莉给忘掉了。
9
晚饭后,天已经黑了,刘顺喝了一杯水,准备去黎爱华家,刚走出屋檐,手机响了,这是回来后的第二次响。一个女人的声音,有点熟悉,但一时想不起是谁。柔软的声音里跳荡着轻快。她问他在哪儿,他说在家,问她是哪一位。女人说,你耳朵怎么这样迟钝,比你的鼻子差远了,汤莉啊。汤莉!刘顺散漫的心收起来,脑袋里升腾起一片欢欣的氤氲,快速地拂过全身。他说,我的鼻子不比以前了,连香臭都难闻出来了;你在哪儿。她说,她在县城的旅馆里,明早去他的家,问他在哪个乡镇,哪个村。他告诉她乡镇和村名,说三个多小时能到,在松子林下车,司机知道松子林。
挂了电话,他的身体还处在激荡之中。他不再去黎爱华家,回到屋里,给自己倒上半杯酒,好像要压下那躁动不安的心情,又好像庆祝汤莉的到来。母亲喂完鸡猪,出去交际去了,院子笼罩着黑暗,墙角的小虫叽叽叫。
她来干什么呢,她不是不喜欢我么,他不明白,就像院子里的黑暗,他的目光无法穿透。他只能把思绪拉到跟她交往的日子,他们一起逛街,一起吃饭,一起住在酒店里。有时她让他读诗。诗!他的生活里竟然还有诗,虽然只是两个多月,可在他看来,已经是很遥远的事了。他有点不相信自己曾经喜欢过诗歌,连那首以前熟背的 《光辉》,现在回想,如同被时间风化一般支离破碎。
酒意渐渐扑进他的意识,脑子有些迷糊,他起身上楼,躺到床上,衣服也没脱。
他第二天醒来,天已大亮,想到汤莉过两三个小时就到村里来,他换上一套干净衣服,下楼洗脸漱口。母亲已出门,昨晚,李贵媳妇喊她去出圈粪。
他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漱口了,满嘴的血泡,整张嘴像生命的玄关被捅破。洗漱完,他打开院门,厚实的门板上写着 “酒有毒”。字迹歪扭,这分明是狗胜的笔迹,他见过狗胜写在地上的这三个字。如果被汤莉看见,这可不好,他返身在屋檐下扯了一块脏抹布,把那三个字擦了又擦,直到看不清为止。他走向院门右侧的茅房,木板门上也是歪扭的“酒有毒”。他扭头看邻居家的门也是这三个字。他折身走进巷子,每一家的院门都是它们。这狗胜,搞什么名堂,有毒也跟你没关系啊,你又不喝酒。他不可能都擦了它们。随它们去吧。他钻进邻近的一个茅房。
回到家,刘顺生火煮上一截腌猪腿。又给自己倒半杯酒喝下。电视开着,他看了几分钟,竟迷迷糊糊睡着了。
他醒来,电视还响着,里面一对男女正热烈亲吻。他看看院里,太阳已经升起很高,有点热起来了。他走出屋,院门开了,汤莉出现在门口,身边是狗胜,大概是他带的路。见到刘顺,狗胜走了。
汤莉上身浅蓝色衬衫,袖子带皱边,一条紧身白色裤子,大腿和小腿的肉崩得紧紧的,脚上一双红色半高跟皮鞋,肩上挎着一个橘黄色的皮包,袋子垂得老长;左腮一条两寸长的浅浅疤痕,至少是二十天前留下的。她皱着眉,脸上满是惊异,好像误闯某家院落。刘顺好像没看到她脸上的疤痕,一脸笑,笑得轻佻放肆,完全不是从前沉静忧郁的表情。汤莉抿了一下嘴,显出一丝淡淡的微笑。刘顺对她表情的变化,没什么反应,还是一味轻佻地笑。汤莉慢慢走近院子,目光在院落里快速扫一遍。
她说他变了,脸上还是淡淡地笑着。刘顺的笑一直僵在脸上,锋利的刀子也刮不下来。
“你喝酒了?”汤莉走近他,眉头再次皱起来。
“喝了一点。”
“你没见每家门上都写着 ‘酒有毒’?”
“看见了。”
“看见了你还喝,你不要命了。”
刘顺很熟悉这话,自己曾经也这样说过。他尴尬地笑笑,说进屋喝口水。汤莉走进堂屋,一股刺鼻的酒味迎面而来,她的鼻子使劲地皱一下,抗拒着酒气的撞击。她没坐下,弯腰抓起大理石桌面上的铝杯,凑到鼻子下闻。她咳嗽两下,左手握拳拍着胸脯,转身走出屋。刘顺脸上的笑淡下来。她说,一进村就闻到酒气,粪味,还有古怪的气息,她半小时也待不下去。
她问他闻到那些味没有,他说没有。
“你的鼻子坏掉了,香臭不分了。”她停了几秒,接着说: “刘顺,我就问你一句话,你愿不愿意跟我去建德板材厂,如果你愿意,我跟你好,如果不愿意,就想呆在这儿,那我就把你的电话删掉,永远不要再联系。”
“我想去,想跟你在一起,可我家里,只我妈一个,没人照管她。”
“那些你自己想办法,我只关心你愿不愿意跟我走。”
刘顺低下头犹豫着,轻声问咋又想起他了。汤莉说他不会打人,愿意来找他,是喜欢他的善良,他的思考,还有对诗的理解,能从他那里得到一些别的男人身上得不到的东西,有了那些,她才觉得生活有意思,这是她这一个月来才认识到的,但想不到他变成这样。汤莉从肩上挎着的橘黄色皮包里掏出两本书,说,这是两本诗集,看来你用不上了,我等会儿把它们丢了。
刘顺走过去,说别丢,抓住她手里的书,汤莉的手垂在大腿一侧,随他拿过去。他没有看书的封面。
刘顺再次说,我妈真的没人照管。
“好,你就照顾你妈吧。”汤莉说完转身往院门外走,刘顺看她走出院门,想到什么似的,紧追出去,拉她的手,她甩开,他上前堵在她面前。狗胜在他们身后墙角用木棍在地上划,看到他们,直起腰,走过来几步,站着。
我愿意跟你去,他说,我要把我妈带着走。汤莉脸色柔和下来,她愿意跟你走么?她儿子的幸福她不会不管,他说。她露出一丝微笑,我相信,到了厂里,你的鼻子会恢复成原来的样子。
“二爷,你要出去打工?”狗胜走到他身后,汤莉看着狗胜的脸。
“嗯。”他转向狗胜。
“你以后带我去打工么?我也想去。”
“好, 一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