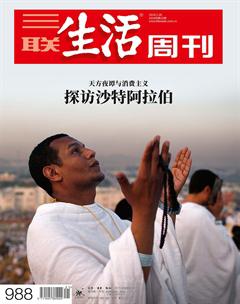杨福喜:挽起传统弓艺
艾江涛

“聚元号”弓箭铺第十代传人杨福喜
聚元号弓箭铺
十多年前,杨福喜把自己的弓箭铺子从北京朝阳区团结湖水利局宿舍大院,搬到了30多公里外的通州区台湖镇北姚园村。
时间推移到1958年,杨福喜刚出生时,他家的弓箭铺聚元号尽管在公私合营的浪潮中刚被改为体育用品合作联社,地方仍在东四南大街原属于清室兵工厂的弓箭大院内。再往前,道光三年(1823)之前,聚元号还是紫禁城西华门内、隶属内务府造办处管辖的弓箭铺。据学者研究,聚元号流传至今的一把制于道光三年的老弓,正是为了纪念宫廷取消弓作、为皇家服务的弓箭匠人离开紫禁城来到弓箭大院这一变动。
位置的不断变迁,既是聚元号弓箭铺历史的折射,似乎也表明着弓箭这一在冷兵器时代最具杀伤力的武器,正在人们的视野中渐行渐远。
比起从前那些地方,北姚园村显得悠闲、静谧。穿过一片树林和庄稼地,当我们还在一排二层平房之间寻找停车位时,身材高大、须发花白的杨福喜已经推门而出。从这座二层平房的外面,完全看不出弓箭制作的任何痕迹,进得门来,看到厅堂中间挂着的牌匾,墙壁上的老照片,弓架上的一排排弓,两边房间和后面院子中堆积的各种制作弓箭的材料与工具,才发现这里竟藏着一家弓箭铺子。
“聚元号,到我这是十代,我爷爷从一个姓王的师傅手里接过来,他是第八代。”虽然聚元号从他爷爷起才改姓杨,但杨福喜的家族做弓箭的历史要追溯到更远。爷爷杨瑞林早年跟随堂兄,也是弓箭大院中全顺斋的掌柜学习弓箭制作手艺。20多岁时,杨瑞林的手艺已小有名气,正好赶上聚元号掌柜由于抽大烟无力经营铺子,于是在亲友的帮助下,以40块大洋的价格,将弓箭铺接了下来。
从晚清到民国,随着近代火器的不断发展,传统弓箭的衰落已成必然。学者谭旦冏在1942年的一份调查报告中悲观地写道:“近年来,全中国制造弓箭的地方,是仅有北平和成都,然而也只是奄奄一息地很难维持下去,有的有人才而无工作,有的有工作而无销路,全消灭或失传是在不久的将来。”北平的弓箭制造便集中在弓箭大院内,不过由于缺乏销路,弓箭铺子已从最初的17家减少到7家。
杨福喜告诉我,他爷爷杨瑞林为人比较活泛,弓箭之外,只要别人喜欢的都做,增加了弩弓、弹弓、袖箭、匣箭、箭枪等新品种。当时,袖箭一类的暗器并不允许公开买卖。“我爷爷怎么办呢?当年我们家有一个小坐柜,前脸像被箭戳得一个一个眼的。他每天早上开门第一件事,就是把那个小坐柜扔在门口。看似随意,实际是给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看。因为坐柜前脸上的眼就是试袖箭试的,行家一看,就知道这家卖袖箭。买这些东西的都是道上的人,那会儿我们结交的人很多,五行八作,上到达官显贵,下到地痞流氓,都得应承着。”

传统弓箭制作中的“刮胎子”环节需用特制的锛子,使弓胎达到“中间粗、两头略扁”
弓箭之外,杨瑞林的成名绝技是制作弩弓。用杨福喜的话说,早年间北京凡玩鸽子的主,都得配备一把弩弓,装上泥丸,将鸽子打蒙,活捉之后用来繁殖小鸽子。也正因此,杨家与同仁堂乐家、京剧演员梅葆玖等大玩家都有很深的交情。此外,天桥举大刀拉硬弓的张国忠,还有以拉硬功出名的朱家哥仨:朱国良、朱国全、朱国栋,韩金铎等艺人,也是传统弓箭的重要客户,不过他们各有各的卖主:“张宝忠爷俩主要拿我们家的;朱家哥仨拿我三大爷家的;韩金铎拿我四大爷家的。”
由于多种经营、广交朋友,聚元号的买卖一直不错。武术名家、后来的国家级射箭裁判员徐良骥对杨瑞林的帮助便很大。“大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当时徐良骥担任贝满女子中学的体育老师,教大家射箭。他让每个学生去聚元号买一张弓十支箭,那些学生就呼啦啦跑到我们店,给了我们家买卖。下一学期,他说不教大家射箭了,教打弹弓,好几十个学生又跑到我们家买弹弓。”杨福喜说。
那时,传统弓箭的客户,除了练家子、天桥艺人,还有不少旨在收藏的外国人。外国客户主要依靠正义路口六国饭店边上的洋车夫介绍,为了卖出弓箭,这些手艺人不得不给他们很大的提成。
就这样,聚元号的弓箭生意一直维持到1949年以后。在1957年公私合营之前,整个弓箭大院只剩下4家弓箭铺,且与杨福喜家均有渊源:“我们家一家,我二大爷、三大爷、四大爷,这样4家,其实跟我们一家差不多。”
由于国家对产品销路的支持,还有“除四害”运动中需要大量弹弓打麻雀,聚元号在共和国成立的最初几年间,迎来了短暂的黄金发展期。杨福喜指着墙上的老照片介绍:“那会儿已经挂上了体育用品第一生产合作联社的牌子。那是我们家最风光的时候,全家月收入五六千元左右,那时一个区长才拿三四十元。”
不久,体育用品厂的重心转移到与人民生活关系更密切的产品,1958年,彻底停止制作弓箭用品。当初的弓箭艺人多数转行为木工,其中就有楊福喜的父亲杨文通。

杨福喜收藏的一把制作于道光三年(1823)的“聚元号”弓
40年与40岁
尽管家中早已不做弓箭,幼时的杨福喜对弓箭却并不陌生。他至今记得,爷爷卧室上方的吊板上放着许多弓箭,有时候老人会拿下来擦一擦,告诉孩子们不同弓箭的名称。上小学后,爷爷还给他们一人发了一套弓箭玩。“我每天背着弓箭,往人家门上射着玩。那时候都是木头门,邻居家的门上很少没有箭眼的。”谈及这段往事,杨福喜不无得意。
父亲有时会和杨福喜讲起以前的事情。那还是在日伪统治时期的北京,13岁的杨文通因为家中经济困难,中学只念了一个月,便回家学做弓箭。过去弓箭制作分为南北两派,南派主要聚集在四川成都,北派则在北京,两派工艺材质大同小异,主要差异在于,前者弓箭制作分离,做弓的专门做弓,铺子里没有箭;此外,为适应当地潮湿气候,增强弓的抗扭曲性,南方弓的弓梢不像北方弓是一个薄片,做得更为宽扁。北方弓箭铺常在一个屋里同做弓箭,便有了所谓“炕上做箭、炕下做弓”的场景。
以大的环节划分,一张传统弓的制作分为弓体制作部分的“白活”与弓体装饰部分的“画活”,那时,除了弓箭铺的掌柜可以兼做,其他师傅往往只做一项。聚元号的师傅,分工细致,有专做箭的,专做白活的,专管画活的。父亲杨文通更多时候跟着家里的几个得力伙计学习手艺。据他回忆:“过去做箭的一个月挣7毛,做弓的挣1块,画活的挣1块2毛。”显然,在过去文化水平较低的手艺行,需要一定美术天赋的画活人才尤为匮乏。杨福喜告诉我,弓箭大院最为鼎盛的时候,有160多个弓箭匠人,却只有一个半画活师傅:一个是聚元号的周纪攀,半个是他偶尔动手的四大爷。
1976年,在顺义插队一年多的杨福喜被招入北京化工二厂工作。1992年,北京化工二厂改为股份制,企业与员工实行双向选择,杨福喜在第二天便提出辞职。喜爱开车的他,很快開上了出租车。
6年之后,杨福喜选择从父亲手里接过传统弓箭制作技艺之时,并没有太多崇高的使命感:“后来我一琢磨,我做这个谁也不招谁也不惹。开始想得很简单,一个是喜欢,另外一个弄好了能弄碗粥喝。”凑巧的是,当时已快从水利局退休的父亲杨文通,由于时间空闲,开始捡起一放几十年的手艺。而让杨文通坚定恢复传统弓箭信心的,还是那年在西山八大处举行的一次射兔子比赛上的巧遇。比赛当天,杨文通所带的一把自制传统弓箭引起了国家射箭队总教练徐开才的注意。两人一聊,杨文通才知道当年聚元号的常客徐良骥还是徐开才的箭术老师。对传统弓箭饱含感情的徐开才勉励这位聚元号当年的少东家,一定要将传统手艺继承下去。
“从1958年停止做弓箭,一直到1998年重新做起来,中间正好间隔了40年,也是我的岁数。”对杨福喜来说,在不惑之年跟随父亲学习弓箭制作技艺并非易事。不管怎样,他在家属院租借了一间小平房作为制弓箭场地,开始学做弓箭了。
可一上手,杨福喜发现弓箭制作并没有想象中困难,用父亲的话说,“好像你以前就是干这个似的”。回头来看,这与他从小跟父亲干木工活所打下的坚实基础密不可分。
重新挂上牌匾的聚元号,在开始一年多的时间里,虽然做出了几十套弓箭,但由于没有市场,完全卖不出去。杨福喜记得,1999年春,在一个朋友的介绍下,他才以3000元的价格卖出第一把弓。聚元号的这第一个客户是京广中心的老板,后来对方又在南方开辟了一个射箭俱乐部,一下要了20多张弓。
后来,徐开才为杨福喜引见了香港著名的传统射艺专家谢肃方。当确认聚元号是传承十代的弓箭铺后,他一次买下17副弓箭,并不断介绍箭术同好前来选购。就这样,聚元号的弓箭逐渐在海外市场有了名气,价格也从2000多元逐渐攀升到上万元。不久,徐开才又将正在中科院做古代弓箭博士论文的义德刚介绍给杨福喜。义德刚的论文出来后,聚元号受到了研究界更多的关注。
与此同时,国家形势对弓箭制作等传统手工艺也越来也越有利。2003年,聚元号弓箭成为“非遗”调研的重要考察对象,3年后,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杨福喜告诉我,如今,聚元号弓箭铺不但每年可以享受3万元的“非遗”津贴,还曾连续享受3次数额达30多万元的项目扶助资金,供弓箭铺购买原材料、制作视频、搜集材料之用。这种在所有“非遗”项目中都颇为罕见的支持力度,无疑免却了杨福喜的后顾之忧。对如今的他来说,制作弓箭所花费的,仅仅是时间成本。
2007年,在“非遗”项目正式发牌3天前,杨文通与世长辞。那一刻,杨福喜才发现,跟随父亲学做弓箭8年的他,尚未完全精通传统弓箭的所有工序,有些地方还要靠回想父亲当初的耳提面命,在实践中慢慢领悟。

“聚元号”弓架上的弓,其中还有一些客人拿来修复未取的老弓
“不要做你驾驭不了的弓”
摸着一把刚刚做完白活的弓,杨福喜告诉我,聚元号所做的传统弓箭,由于弓体采用牛筋、牛角、木质等材料,竹胎在上弦时要反方向弯过来,以最大程度发挥其弹性,学名叫作“筋角木反曲复合弓”。
聚元号弓的制作工序,大体分白活、画活、上弓弦3个阶段。仅就白活而言,又可细分为制弓胎、勒牛角、铺筋、上板凳4个主要环节下的30多个环节。在过去的弓箭行,没有3年多的时间,学徒无法出师。
由于在制作过程中使用猪皮熬制的膘胶,弓箭制造的季节性很强,天气过冷过热都不行。有人曾建议用空调解决这一问题,杨福喜发现效果很差:“我们的东西最好自然风干,从里往外干;人为控制温度,弓是从外往里干,往往外面干了里面还是湿的,造成的问题是弓的力量变化很大。比如春秋季节所做的弓,拉力可达50磅;夏天潮热时做的弓,拉力连30磅都不到。”杨福喜告诉我,为了稳定弓箭的性状,充分观察可能出现的问题,弓箭行的祖训是,一张弓做好后,要在匠人手里放一个四季。如此一来,一张传统弓箭的制作周期往往要一年多之久。
“做弓没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制作的弓箭,要适合你的身高、臂展和力量。我爷爷和父亲常告诉我一句话:不要做你驾驭不了的弓。”杨福喜说。
中国的传统弓箭,一般用劲来计算力量,近代以来,出于与国际弓接轨的需求,才开始采用磅的说法。杨福喜查阅了《天工开物》和《考工记》等古代文献,发现1个劲,一般就是10斤左右。射箭所用的弓一般在3.5~4.5个劲左右,练力气所用的硬弓则更大。杨福喜告诉我,自己在年轻时用5个半劲的弓射一百六七十米没有问题,即使现在,也能稳稳拉开80磅的弓。
对弓箭力量的感知,无论对使用者还是制作者,都同样重要。客人订购弓箭时,杨福喜一般会问他们两个问题:弓箭使用者以及使用地域。为了测试使用者的力量,杨福喜常常建议对方,伸直胳膊拎一袋50斤的大米,如果能拎起并堅持5秒,说明可以驾驭50磅的弓。而了解弓箭的使用地域,便可以在制作上加以调整:如果带到潮湿的南方,需将弓梢做宽,弓身贴上防潮的桦树皮,以最大程度地保护弓箭。
一个弓箭制作师的力量,往往成为其所做弓箭力量的上限。原因在于,在制作过程中,弓箭师傅需要不断拉试以测试性能、调试问题。杨福喜告诉我,在刚做好一批弓箭的那段时间,他每天早上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那些弓挨个拉一遍,有时一拉就是十几二十张。前段时间,张国立在节目《非凡匠心》中,来杨福喜的弓箭铺拍摄自己学习制作传统弓箭的过程。为了测试张国立的力量,杨福喜专门和他推了推手。当天晚上,杨福喜让张国立把做好的弓箭放在床边,告诉他只要听到异常的咔咔声,立刻“剪弦保弓”,结果害得他几乎没睡好觉。
“一张弓,如果说在开始做、做的过程中都不能确定它的力量大小,就不是好手艺。只有达到随便一掂就知道弓的力量,上下最多不超过10磅,才算合格的手艺人。”杨福喜说。
问题在于,在向来“以眼为尺、以手为度”的弓箭制作中,如何控制一张弓的力量?杨福喜告诉我,决定一张弓力量的因素有很多:竹胎的性状、牛角的薄厚、牛筋的多少,但要做到心中有数,只能靠日积月累的经验:“选胎的时候,我随便拿出一块竹子,就知道它适合做几个劲的弓;勒牛角的时候也知道这块勒上去大概几个劲。勒牛角之后,我根据牛角的弹性再决定胎子的薄厚,去多少留多少。可你让我说道理,我说不上来。”
在洒满夕阳的后院中,杨福喜用特制的锛子,一边看着竹胎,一边讲解:“三百六十行中,只有南方做木盆、草原上做马鞍子的,和我们用类似弯把的锛子。每个锛子根据师傅的具体情况设置锛头角度,一般不外借。身大力不亏的人用的锛子叫‘馋锛子,特点是茬口比较大,砍活比较快;身体比较弱的人则用‘懒锛子,角度往回收一点。”说话间,一张中间宽两头扁的竹胎已初具规模。
勒牛角和铺牛筋,是决定弓箭性状的两个重要环节。牛角,在弓体中起到弹性作用,一定要用长度在60厘米以上的水牛角。用锯子锯成薄片,再用电动砂轮打磨光滑之后,涂上融化好的膘胶,在特制的木凳“压马”上,用木头制作的“走错”带动绳索,快速将牛角缠在竹胎之上。这是弓箭制作中最耗体力的环节,勒完一块牛角,杨福喜已是满头大汗。然而直到今天,他仍觉得这是传统手艺中最难被替代、也是最有魅力的一环。
牛筋取自牛背紧靠脊梁骨的那块筋,砸开后需要撕成一丝一丝的条状,这一耗费时间的工序,用弓箭大院流传的话说就是“好汉子一天撕不了4两筋”。牛筋在弓背铺设的层数,直接决定弓箭的力量,一层贴完后起码要等一个星期完全干透后才能贴第二层,因此这也是整个工艺中最耗时间的一环。杨福喜31岁的儿子杨燚,在高中毕业后便跟随父亲学习制作弓箭。他告诉我,由于经常要蘸着滚烫的膘胶梳理牛筋,他和父亲已经练成从蒸锅中直接用手端出热碗的技能。
随着聚元号的影响越来越大,杨福喜在与更多国际同行交流中,时有收获。他发现尽管材质相同,但韩国弓箭特别小,在自重很轻的情况下可以射得很远。更重要的是,人家传统弓箭的制作从未断层。而美国所产用于做弓弦的线,弹性仅为0.2%,大大优于传统棉线高达4%~7%的弹性。让杨福喜欣喜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喜欢中国式射箭,前两年举办的鄂尔多斯国际那达慕大会上,正式要求各国选手采用中国式射箭法。
在我们聊天的当儿,聚元号年轻的传承人杨燚独自在隔壁屋中做着画活,用桦树皮刻了一条龙,贴在弓箭上作为装饰。他笑着对我说,自己在这儿基本处于修仙状态,如果不这样,做不了弓箭这玩意。
(本文写作参考韩春鸣编著的《聚元号弓箭》一书,感谢赵首艺对采访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