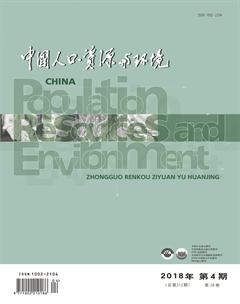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作用效应与能源消费结构演变的适配关系研究
陶长琪 李翠 王夏欢
摘要 文章采用SBM方向距离函数对我国2004—2015年省际全要素能源效率进行测算,通过Bootstrap对结果进行修正,并利用PSTR面板平滑转移模型,探究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作用与“化石能源消费比例”、“化石能源消费规模”能源消费结构两因素演变的适配关系。在化石能源消费由高到低连续变化的不同阶段下,由于环境外部性大小不同、企业“成本效应”不同和“公告效应”的存在,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作用存在相应的差异。结果表明:12年来我国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呈波动变化,总体没有上升或下降的趋势。另外,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作用与能源消费结构演变存在显著适配关系。①单纯以化石燃料消费占比来看,当化石燃料占比处于较高的消费区间,环境规制水平对全要素能源效率呈现负向作用;当化石燃料占比降逐渐降低,此时负向作用减弱甚至开始促进全要素能源效率提高;②在“化石燃料消费占比”、“化石燃料消费规模”结构两因素共同演变视角下,化石燃料消费占比高、规模高,环境规制水平对全要素能源效率也呈现负向作用,当化石燃料消费占比、规模逐渐降低,环境规制水平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作用逐步由负转正,并且促进效用逐步增大。因此,本文的政策结论是:环境规制的调控效果与能源消费结构演变阶段存在适配关系,脱离了“节能”的环境规制效率是低下的,甚至是负作用。因此:①必须立足于一国能源消费结构现状来控制环境规制强度。②只有在严格深化以非化石燃料等清洁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的能源结构改革的前提下,环境规制才能更加深刻而有效地助力我国能源效率的改善。
关键词 环境规制;全要素能源效率;能源消费结构;适配关系
中图分类号 F062.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104(2018)04-0098-11DOI:10.12062/cpre.20171005
作为改革开放30多年不断推行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回报,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2016年,我国14.38%的全球经济总量却消耗了全球22.9%的能源,并“贡献”了30.0%的温室气体排放。粗放生产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严重危害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1983年,保护环境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然而,在耶鲁大学发布的《2016年环境绩效指数报告》中,我国的环境空气质量排名倒数第二(179/180)。此外,我国的雾霾发生频繁,波及范围也在扩大,贡献最大的PM2.5颗粒来自煤炭等化石能源的燃烧。这些现状足以让人开始质疑我国的环境管理政策是否可以有效改善生态环境,有些学者开始反思:与“节能”进程脱轨是不是现行 “减排”政策无法从根源上减少环境的外部性的原因?毕竟环境规制的实施可能因为其技术效应成功,也可能带来资源配置扭曲效应进而失败。目前从我国的能源需求侧来看,煤炭等化石能源依然占据难以撼动的主导地位,能源消费结构、能源强度和能源效率等都存在着较显著的区域差异。因此,不考虑能源结构因素而仅单纯通过增收环境税、加大污染治理投入等加强环境规制水平是否会带来环境改善?是否可以在不考虑能源结构因素下,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改善,进而带动能源效率的提升?回答这些问题对我国履行国际义务和承诺、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文献回顾
1.1 环境规制作用于能源效率的相关研究
早在1977年,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U.S.) and EP Agency[1]对美国20世纪60—70年代的相关数据进行研究,发现环境规制能带来能源效率的提高,并且产生的经济效益远远大于环境规制带来的成本。目前学术界对于环境规制对能源效率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两种不同观点:①从总体来说环境规制不仅可以减少环境负外部性,还可以降低能耗,对能源效率的改善具有促进作用[2-3]。在环境规制作用异质性方面,陈德敏等[4]通过分析我国2000—2010年省际数据、SK Mandal[5]通过研究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印度各联邦环境规制和能源效率的关系,都认为这种促进作用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②环境规制不一定总是促进能源效率的改善。张华等[6]和高志刚等[7]通过我国21世纪初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认为环境规制对能源效率的改善既有促进作用也存在抑制作用,二者之间呈现“倒U”或者“正U”型的不确定关系。究其下降的原因,PI Hancevic[8]通过分析墨西哥1990年的清洁空气法修正案对生产力、能源效率的影响,认为环境规制对能源效率的负作用在于其对生产力造成的冲击。
1.2 环境规制作用于能源消费结构的相关研究
基于我国是世界上煤炭消费大国,现有国内研究主要着重于环境规制对我国煤炭消费的研究。大部分学者认为环境规制能够促进能源消费结构的优化,减少低热值高污染能源的消费[9-10]:如Y Shi等[11]通过分析1998—2006年中国环境规制与能源消费结构的相关性,得出了环境规制水平与煤炭消费规模具有显著的负相关的结论;林伯强等[12]运用马尔科夫链过程模拟得出,在严格的环境治理约束下,我国2030年煤炭一次能源消费占比会下降到47%左右,但由于资源可利用量的限制,该比重很难再随着环境约束继续增加而下降。但Sinn[13]和FVD Ploeg & C Withagen[14]则认为企业也可能出于短期经济利益的考虑,增加化石能源的开采和消费,即出现环境管理中的绿色悖论问题,环境规制的加强就可能在短期恶化能源消费结构。
1.3 能源消费结构作用于能源效率的相关研究
一直以来能源消费结构的改善可以提高能源效率已成为共识[15-16]。 目前学术界就煤炭消费水平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做了大量的研究,如以煤炭消费比例作为结构因素,王喜平等[17]运用方向距离函数模型发现工业中煤炭消费比重增加将导致能源效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史丹[18]认为能源效率的高低与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大小相对应,但与终端煤炭消费的比重并无明显相关关系,这体现了煤炭的提炼、存储、运输技术对提高能源效率的重要性。若以煤炭消费规模作为结构因素,陈关聚[19]运用SFA方法发现煤炭消费量的增加将导致全要素能源效率下降。由于研究方法、视角不同,研究结果不宜直接比较,但关于煤炭消费与能源效率负相关的认识是一致的。进一步,S.Bilgen[20]认为能源结构对能源效率的改善主要是通过对煤炭等能源的替代實现能源消费的环境负外部性减少甚至彻底根除。王兵和谢俊[21]认为减少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增加非化石能源使用的“自然优化”以及对非化石能源的“管理优化”方式就可以提高能源效率。
鉴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认为环境规制水平、能源消费结构对能源效率的促进作用总体上是成立的,然而既有文献存在以下不足:①在研究视角上,既有研究多以“煤炭消费占比”或“化石能源消费占比”等比例指标来刻画能源消费结构,显然忽略了能源消费结构中的规模因素,因此这种研究视角并不完备。②既有研究对能源效率的测算过程中,皆以煤、原油、天然气、电力、核能等5—6种具有代表性的能源作为核算对象,但我国能源统计报表中社会能源消费种类多达29种,因此这种做法显然低估能源消费总量和CO2排放量,全要素能源效率也因此被高估。③在研究方法上,既有文献停留在研究引入环境因素后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变化特征上,并未深入探索环境规制对能源效率变化的具体影响程度与作用机制。虽然,有部分文献开始探索环境规制影响全要素能源效率可能的中间途径,并选择产业结构、FDI等作为视角,但往往忽略产业结构等是通过影响能源消费结构和技术进步来进一步影响全要素能源效率的。而且现有研究忽略我国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调控与经济结构因素演变阶段的匹配性关系。基于这些不足,本文突破既有文献能源核算范围,以17种能源折算的能源总投入和13种化石能源估算CO2的排放量来测算带环境因素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并基于PSTR模型,在能源消费结构因素的规模与比例演变双重视角下,研究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与结构演变适配关系。
2 能源消费结构演变匹配下的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作用路径分析
环境规制属于政府社会性规制的重要范畴,由于化石能源不可持续以及燃烧所造成的污染外部不经济性,政府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限制,实现环境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归纳出环境规制通过能源结构影响能源效率的作用机制:由高化石能耗下的低体制作用路径,随着能源消费结构演化,变成另一种低化石能耗下高体制作用路径。
2.1 化石能源高能耗的低体制作用路径
在化石能源占比和规模比较大的污染密集型经济,投入的非化石能源对化石能源的替代弹性小,对化石能源依赖性大,并由此产生了巨大的环境问题。①根据外部性理论,由于负外部性产生巨大的社会成本,政府的环境规制手段对社会减排的效果并不显著,能源效率提升受限[22-23]。②按照“绿色悖论”理论的“公告效应机制”,在当期,化石能源所有者预期在可见的未来,政府将采取更严格的环境规制,从而在整个时间域上向前移动开采路径,导致当前化石能源价格下降。短期内,更廉价的化石能源刺激需求上升,随之而来的是短期温室气体和污染排放的上升,引发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加剧恶化[24]。③在“遵循成本说”理论中,征收排污税、能源税或强制性的行政手段等可以迫使企业改变其能源要素投入结构,但由于化石能源占比高、规模大,由此带来高额的成本(环境成本、生产要素调整成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在位企业造成很大冲击,降低了企业的生产率[25-26],全要素能源效率也随之下降。此时作用机制表现为图1中的体制1。
2.2 化石能源低能耗的高体制作用路径
随着能源结构的演变,在能源结构中化石能源占比低、规模较小的情况下,经济的非化石能源对化石能源开始呈现较高的替代弹性,对化石能源依赖性小。①在此时外部性的绝对值较小的情况下,政府的规制手段比如征税、给予清洁能源补贴对全要素能源效率提升的效果开始有显著的提高;②虽然“绿色悖论”的效应仍然存在,但是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可以被正面效应所冲销和减弱;③按Porter与Vender Linde等学者的“创新补偿”理论,环境外部性的内部化带来的环境成本在中长期就会被技术创新弥补,由于化石能源占比低、规模较小,环境规制对企业的冲击比较小,因此环境规制无须很长时间便可以带来生产效率、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提高。此时作用机制表现为图1中的体制2。
因此,在能源消费结构的视角下,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非线性效应是存在的。而且这个效应具体是由“外部性社会成本”“绿色悖论公告效应”和“外部性内部化成本”三个效应机制互相制约、冲销、弥补的动态拉锯中产生的。因此这个非线性效应很可能不是一个门槛,而可能是平滑的、逐渐变化的从一个体制变化到另一个体制的效应。两种体制的转换构成化石能源消费结构演变匹配下,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作用路径(见图1)。
3 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测算
3.1 基于Bootstrap修正方法的SBM方向距离函数
基于SBM的方向距离函数是测算全要素能源效率的重要方法。该方法由Fukuyama和Weber[27]提出,并与方向距离函数进行了比较。相对于SFA和其他DEA方法,SBM方向距离函数是一種成熟、客观、可以精确测算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测算方法。不同于传统DEA测算模型,方向性距离函数考虑到环境因素,并实现了对能源等生产要素、产出以及环境(非期望产出)联合建模,将“多投入——单产出”框架下的全要素能源效率计算扩展到“多投入——多产出”框架下。SBM方向距离函数测算模型则更进一步,测算线性约束中引入松弛变量
实现了在真正意义上的Pareto最优的生产前沿面上测算生产单元的生产效率,这对全要素能源生产率等生产效率的精确测算具有重要意义。最重要的是,SBM方向距离函数测算中允许对方向向量
的设置可以重点考察以全要素能源要素为对象的效率评价。因此,运用SBM方向距离函数对全要素能源效率进行精确测算具有重要意义。相比既有关于全要素能源效率测算的研究,本文出于使测算结果更客观精确、贴近现实生产和数据可得性的考量,采用生产中17种能源折算成能源总投入以及13种化石能源估算CO2的排放量。按Cooper[28]的思路,在全要素测算框架内利用(1)式将全要素能源效率TFEEi分解出来:
然而,A Kneip 和 PW Wilson[29]通过Monte Carlo方法发现:相对于决策单元的绝对效率水平,通过这种非参数方法计算出距离更进一步得到的能源效率值是有偏、不一致的。因此,引入Bootstrap的方法对SBM方向距离函数测算结果进行纠偏实不可少。Simar & Wilson[30]首先将Bootstrap方法引入DEA非参数分析中,通过计算决策单元生产效率和Bootstraps抽样方法对θi进行抽样,并用Gaussian kernel核密度估计对Bootstrap样本分布进行平滑处理,来估计总体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概率密度函数,在N次重复迭代过程中得到生产单元的生产效率的区间估计和期望值θi^。
3.2 投入和产出指标说明
本文选取我国除西藏自治区、台湾省、香港和澳门的省、直辖市、自治区(以下简称各省)相关数据作为样本。数据为2004—2015年的面板数据,来源于各省统计年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力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等,投入产出指标界定如下:
能源總投入。以各煤品能源、各油品能源、液化石油气、电力、热力等共17种能源种类核算能源消耗量,这近乎覆盖我国生产活动中能源全部种类。通过折煤系数将各能源消费总量换算成以万吨标准煤为单位的能源消耗量,最后进行加总得到各省能源消费总量(统计年鉴中能源消费总量包含终端消费量,损失量和加工转换损失量)。
劳动力投入:采用各省2004—2015年末就业人口数作为劳动力的替代指标,单位:万人。
资本投入:资本存量的测算采用永续盘存法,在资本流量的选取、基期资本存量的计算上,按张军等[31]做法,采用固定资产形成总额替代资本流量;以 1992年作为各省资本存量估计的基期并采用贴现法来计算;不同省份、年份折旧率来自《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1995》等统计资料。
期望产出。采用各省2004—2015实际GDP,以2000年为基期,单位:亿元。
非期望产出。考虑到引入过多的非期望产出会影响效率测算准确性,因此根据污染物的对环境的破坏程度,采用以下三种非期望产出:
(1)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作为全球温室气体控制的最重要目标,CO2是关于环境规制效率研究的重要监控对象。为更准确估计二氧化碳排放量,本文以原煤、洗精煤、原油、液化石油气等13种能源消耗为对象,根据《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指南》提供的测算方法计算CO2的排放:
其中,Ei表示第i种能源消耗量,本文用能源平衡表中的各能源总消费量代表;NCVi为各能源的平均低位发热量,CEFi为单位平均低位发热量的碳排放系数,单位:kgC/GJ;COFi表示碳氧化因子。各种能源经计算后的CO2排放系数如表1所示。
(2)SO2排放总量。SO2代表工业、居民生活中污染气体排放程度,本文采用各省2004—2015年SO2的排放总量数据,单位:万t。
(3)工业废水排放总量。除了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本文另外将各省2004—2015历年工业废水排放也纳入全要素能源效率测算的非期望产出,单位:万t。
3.3 全要素能源效率测算和结果
基于SBM方向距离函数,取列扩张方向向量对各省全要素能源效率进行分解测算。在Bootstrap方法修正中,本文进行2 000次迭代,并取平滑算子h=0.08。从全要素能源效率变化趋势来看,我国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呈波动的下降趋势,与部分研究[32]得出的:“我国全要素能源效率呈上升趋势”结论不同。这是因为该研究测算仅考虑碳排放因素。各区域全要素能源效率在12年并未呈现出明显的上升或下降的趋势。其中东部地区的全要素能源效率一直稳定在高位,除了2006年的短暂下降。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变化则呈“勺”状,2009年后呈现断崖式下降的原因,是因为东北整体经济效益增速骤降,而工业排放规模反而一直上升。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全要素能源效率虽有些波动,但整体比较稳定。我国2004—2015年全要素能源效率平均水平为0.942 7。从各区域效率水平来看,东部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水平最高,为0.999 8;东北老工业基地次之,为0.972 2;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则处于最低水平。但近年来与东部地区拉开的差距慢慢缩小。与袁晓玲等[33]“西部次于东部,中部最差”的结果不同,中部地区平均水平0.905 6,西部地区最差为0.901 1。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不列出各省的原始全要素能源效率与Bootstrap修正后结果,仅列出区域的计算结果作为对比(见表2)。
4 环境规制对能源效率的作用效应与能源消费结构因素适配关系实证分析
4.1 面板平滑转换模型(PSTR)
在能源结构演变过程中,环境规制对能源效率产生怎样的影响?能源消费结构因素中是否存在阈值?对于探究经济中的非线性效应,目前研究主要采用面板门槛模型和面板平滑转移模型(PSTR)。不同于面板门槛模型的突变性机制转换,面板平滑转移则假设“更多的事物的发展并非是突变,而是连续的、逐渐的从一种机制演变成另一种机制”。考虑到环境规制对能源效率的机制转换可能是非线性连续的,本文以PSTR模型来研究二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尝试将能源消费结构因素下的“化石能源消费占比”和“化石能源消费量”共同纳入转换变量,建立一条平滑曲线来刻画环境规制对能源效率的关系并求得存在能源消费结构演变中的“阈值”。包含r个转换函数的一般形式PSTR模型如下:
下构建线性固定效应模型,用两个模型估计结果的残差平方和构造统计量进行检验,本文采用LM或Fversion-LM(下文用LMf)统计量。如果统计量在设定的α置信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就认为模型存在非线性效应且暂定模型中仅存在一个转换函数g1(r=1)。其次,以同样的辅助回归式,通过序贯检验确定阈值个数m。在对只含转换函数g1的PSTR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后,仍须对模型进行旨在确定是否存在第二个转换函数g2的“剩余非线性效应”检验,方法与确定一个转换函数(r=1)的检验方法相同,若检验存在“剩余非线性效应”(即r=2),则继续对PSTR模型的第2个转换函数g2进行设定检验。
重复上述检验步骤,直至模型接受无“剩余机制”转换效应的零假设。
4.2 化石能源消费比例q1演变下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效应分析
首先,以能源消费总量结构中化石能源比例q1(0≤q1≤1)为转换变量,建立面板平滑转换模型。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各省份之间要素禀赋、政策空间、文化、消费习俗等不可观测非时变的个体因素之间存在差异,需要对模型进行个体固定效应的检验。在原假设为混合效应和备择假设为固定效应的检验中,F统计量为6.83,在1%水平上拒绝不存在省份间个体固定效应的原假设,另外,在Hausman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的检验中,Wald统计量为20.94,在1%水平上拒绝随机效应的原假设。因此不论是从经济意义上还是统计检验上,构建固定效应的面板数据平滑转移模型无疑是正确的。
非线性效应检验中,在H0∶γ=0下,LM统计量在5%的显著水平上拒绝了原假设H0,认为模型设定存在异质性的非线性特征,验证了采用化石能源消费比例作为转换变量的准确性。其次,在默认m=3下,在非线性检验和剩余非线性检验的结果表明,模型仅存在一个转换函数(r=1)。在r=1的情况下,进一步通过检验确定对转换变量中的阈值个数m:依次设定原假设H03∶β3=0;
原假设被接受,而在0.01的显著水平下H02原假设被最强拒绝,因此确定m=2,即模型存在一个转换函数,其中包含2个阈值。非线性效应检验和剩余非线性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阈值确定设定的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因此,构建以化石能源比例作为转换变量、转换函数个数为1(r=1)且含2个阈值(m=2)的固定效应面板平滑转移经济模型如下:
其中,ERit表示环境规制水平,本文参考应瑞瑶和周力[34]的研究,将治理废水投资额、治理废气投资额、治理固体废物投资完成额数据标准化再进行加总,以此来衡量该地区的环境规制程度。
其中,Eij表示i省j污染物单位产值治理投资额,Oi表示i省的生产总值。ERi即将i省的单位产值上j污染物治理投资额比全国单位产值上j污染物治理投资额,再根据污染物种类加总得到。
各地区废水、废气、固体废物投资完成额数据来源于《中国环境年鉴》。q1表示能源消费总量中化石能源消费比例。通过非线性最小二乘法(NLS)估计平滑转移的模型的斜率系数γ和位置参数c1、c2,残差平方和最小目标函数通过网格搜索寻优,经过多次迭代,最终得到残差收敛最小值点。估计的结果如表5所示。
可见,以能源总消费量化石能源比例q1作为转换变量的模型中,环境规制水平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双阈值特征,两个阈值分别为c1=0.886 4和c2=0.927 6。另外由于定义域q1∈(0,1),因此转换函数g1是非对称的。当0.886 4 4.3 化石能源消费结构比例q1和q2规模共同演变下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效应分析 由于能源消费结构包含各种能源消费的比例和各种能源消耗的绝对量,因此以化石能源作为能源结构的代替,不仅要研究化石能源消费比例视角下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非线性效应,更要进一步将化石能源消费的规模纳入,同化石能源消费比例一起,构成能源结构视角,在此之下研究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非线性效应。 在化石能源消费比例q1为转换变量的PSTR模型中,引入化石能源消费量q2进行剩余非线性效应检验,由于化石能源消费量数量级巨大,为了便于对参数搜索,把化石能源消费总量cfe(单位:万吨)对数化,并且用q2表示(即q2=ln(cfe))。剩余非线性效应检验中,需设定缩减因子τ(0<τ<1)对显著性水平α进行修正,本文设定缩减因子τ=0.5。结果表明,LM统计量值为16.890,在1%置信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发现q1为转换变量的PSTR模型对q2变量仍存在显著的剩余非线性效应。通过进一步检验,确定了在q1和q2为转换变量下模型中包含的转换函数个数r=2,并且转换函数g中存在1个阈值c3(m=1),剩余非线性检验和阈值个数确定的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 设定两个转换变量分别为化石能源消费比例和化石能源消费总量的固定效应面板平滑转移模型设定为: 4.4 实证结果分析 在以化石能源消费比例q1为转换变量的适配体制模型下,环境规制力度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双重效应。在化石能源消费比例定义域q1∈[0,1]内,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效应系数β随着转换变量q1相对双门限值c1和c2的位置变化呈现从β=-0.042 6到β=3.691 9的平滑变化;当q1满足0≤q1≤0.81(与图2虚线区间适配)时,与之相适配的环境规制水平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效应函数β(q1)大于0(β(q1)=β0+β1×g(q1)>0),即提高环境规制水平将促进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改善,此时不妨称之为正效应。并且β(q1)随着q1的增加呈现单调递减,可见在不考虑其他因素情况下,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越高,提高环境规制水平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促进作用越小。当化石能源消费占比q1达到q1>0.81时,相应地,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效应逐步平滑转入负数(匹配图2实线区间)。因此在q1∈[0.81,1]的区间内,适配的环境规制水平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作用为负效应,这表明此时如果加大环境规制力度反而会加剧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恶化;其中化石能源消费比例q1达到q1=0.906时,适配的负效应达到最大值-0.042 6。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效应转移函数如圖2所示。 所以在双重转换变量视角的进一步研究中,环境规制力度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也存在双重效应,然而在样本观测值中,有83.64%的样本观测值处于负效应区间,16.36%的样本区间处于正效应区间,但是样本观测值的效应函数处于区间[-0.041,0.535],差距不大;且随着我国核能、风能、太阳能的逐渐普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省份和直辖市例如北京(2011开始)、浙江(2013开始)、广东(2010开始)逐渐从负效应区域转向正效应区域。
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作用效果随着能源消费结构两因素(比例因素q1和q2规模因素)的改变而改变,体现了调控效果与该结构因素演变的适配性。从图3右效应系数的等高线图可以看出,旨在改善全要素能源效率而单纯提高环境规制力度并不一定能够显著达成所愿,并且在二维结构因素不同定义域的作用效果也不同,在与化石能源消费规模、比例高的定义域相适配的负效应区域(图3右图阴影部分),这样的努力甚至会导致全要素能源效率的进一步恶化。这是因为对于化石能源密集型经济,在环境外部性的内部化过程中,环境规制很容易对企业造成生产力的冲击,进而造成全要素能源效率的下降。另外效应函数三维曲面的等高线图(图3左图)显示,效应系数β′(q1,q2)呈现由(0,-∞)向(1,+∞)逐步递减的趋势(注:这里需注意q2=ln(cfe),化石能源消费总量cfe趋向于0时,q2趋近于负无穷大)。即随着化石能源消费比例和消费的绝对量的降低,环境规制水平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正向效应将得到提高,调控将变得愈高效而显著。
5 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先根据既有研究和理论,分析了在能源消费高、低水平下,與之相适配的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高、低体制作用路径,并通过作用路径图作了详细说明。其次,基于我国省级2004—2015面板数据,在作用路径上分别构建化石能源消费比例转换变量因素、化石能源消费比例和规模共同转换变量因素的PSTR模型,证明了在能源消费结构因素演变过程中,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非线性效应,并且研究发现:
(1)能源消费结构因素演变过程与环境规制水平对全要素能源效率作用的适配关系是显著存在的。能源消费结构的演变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效果或调控效果随着能源消费结构(比例、规模两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在能源消费结构的演变过程中,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作用效果在多个体制间呈现的变化是连续的、平滑的,而不是突然从一个作用机制转变到另外一个作用机制。
(2)环境规制调控作用与结构演变相适配的情况下,高举“减排”大旗、单纯提高环境规制水平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改善作用有限,并且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存在双重效应。具体地说,即存在环境规制水平促进全要素能源效率提高的“正效应”和进一步恶化全要素能源效率的“负效应”。在我国化石能源消费高比重和高规模的现阶段下,提高环境规制水平只会带来全要素能源效率的进一步恶化。随着化石能源消费结构改善,环境规制水平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正效应作用逐渐凸显,作用效果越来越大。
(3)单纯降低能源消费比重或者单纯降低消费规模情况下,提高环境规制水平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改善作用有限。从实证结果来看,单纯降低能源消费比重和消费规模确实可以提高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调控效果,但单纯的降低消费比重或规模并没有使环境规制水平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调控效果达到最优,只有实现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和消费规模的“双降”,提高环境规制水平对全要素能源效率才有最好的作用效果。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的政策内涵是: “节能”和“减排”政策是相互匹配的,脱离了“节能”的“减排”行动是非效率的。因此,提高环境规制水平,必须以不断改善、优化我国经济体中的结构因素、深化我国能源消费结构性改革为前提。在“节能”这个小目标的背景下完成“减排”的大目的。具体来说,首先需要 “激励型”工具对能源密集型企业技术创新提供持续的激励,促进企业对化石能源的集约利用和对能源消费结构的优化。其次,实现非化石能源对化石能源在规模上的替代。我国能源政策一直以来都把重点放在促进煤炭等低热值高污染能源在能源消费总量比例上的降低,因而导致我国煤炭等化石能源在消费结构呈现比例降低迟滞,消费规模仍然不断增长的尴尬局面。因此提高清洁能源对化石燃料的替代强度是能源消费结构改革的重中之重。通过实现化石能源消耗比例和化石能源消费规模的“双降”来提高环境规制水平对能源效率的调控效率。只有这样,才能使“减排”政策更深刻地改善中国环境,提高全要素能源效率。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NRC, Committee on Energy and the Environment, EP Agency. Implication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for energy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M]. Washington DC: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977:50-51.
[2]BI G B, SONG W, ZHOU P, et al. Doe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ffect energy efficiency in Chinas thermal power generation?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a Slacks-based DEA Model[J]. Energy policy, 2014, 66(C):537-546.
[3]王婷婷, 朱建平. 环境约束下电力行业能源效率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5, 25(3):120-127.[WANG Tingting, ZHU Jianping. Research about the energy efficiency of power industry under the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s[J].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5, 25 (3): 120-127.]
[4]陈德敏, 张瑞. 环境规制对中国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J]. 经济科学, 2012(4):49-65.[CHEN Demin, ZHANG Rui.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on Chinese total factor energy efficiency:based on provincial panel data empirical test[J].Economic science, 2012 (4): 49-65.]
[5]MANDAL S K, MADHESWARM S.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of the Indian cement industry: an interstate analysis[J]. Energy policy, 2010, 38(2):1108-1118.
[6]张华, 王玲, 魏晓平. 能源的“波特假说”效应存在吗?[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4, 24(11):33-41.[ZHANG Hua, WANG Ling, WEI Xiaoping. Is there really a ‘Porter Hypothesis effect of energy?[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4, 24 (11): 33-41.]
[7]高志刚,尤济红. 环境规制强度与中国全要素能源效率研究[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5(6):111-123.[GAO Zhigang, YOU Jihong. Research abou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strength and Chinas total factor energy efficiency[J]. Comparison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ystems,2005(6):111-123.]
[8]HANCEVIC P I.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productivity: the case of electricity generation under the CAAA-1990[J]. Energy economics, 2016, 60:131-143.
[9]范德成, 王韶华, 张伟. 低碳经济目标下一次能源消费结构影响因素分析[J]. 资源科学, 2012, 34(4):696-703.[FAN Decheng, WANG Shaohua, ZHANG Wei. Analysis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rimary energy consumption structure under the goal of low carbon economy[J].Resources science, 2012, 34 (4): 696-703.]
[10]魏巍賢, 马喜立. 能源结构调整与雾霾治理的最优政策选择[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5, 25(7):6-14.[WEI Weixian, MA Xili. The optimal policy choice of energy structural adjustment and haze governance[J].China population,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5, 25 (7): 6-14.]
[11]SHI Y, PANG N, DING Y. Environment effects of energy consumption structure based on comprehensive grey correlation degree: from 1998 to 2006 in China[C]// Asia-Pacific Power and Energy Engineering Conference. IEEE, 2009:1-4.
[12]林伯强, 李江龙. 环境治理约束下的中国能源结构转变——基于煤炭和二氧化碳峰值的分析[J]. 中国社会科学, 2015(9):84-107.[LIN Boqiang, LI Jianglong. Chinas energy structure change i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constraints: based on analysis of peak coal and carbon dioxide[J].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2015 (9): 84-107.]
[13]SINN H W. The green paradox: why one may not forget the offer in the climate policy[J]. Perspektiven der wirtschaftspolitik, 2008, 9:109-142.
[14]PLOEG F V D, WITHAGEN C. Is there really a green paradox?[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 management, 2010, 64:342-363.
[15]HAN Z Y, YING F, JIAO J L, et al. Energy structure, marginal efficiency and substitution rate: an empirical study of China[J]. Energy, 2007, 32(6):935-942.
[16]魏楚, 沈满洪. 结构调整能否改善能源效率:基于中国省级数据的研究[J]. 世界经济, 2008(11):77-85.[WEI Chu, SHEN Manhong. Can structural adjustment improve energy efficiency: a study based on Chinas provincial data[J]. World economy, 2008 (11): 77-85.]
[17]王喜平, 姜晔. 碳排放约束下我国工业行业全要素能源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 软科学, 2012, 26(2):73-78.[WANG Xiping, JIANG Ye. Research about Chinas industrial sector and total factor energy efficiency factor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arbon emission constraints[J].Soft science, 2012, 26 (2): 73-78.]
[18]史丹. 中国能源效率的地区差异与节能潜力分析[J]. 中国工业经济, 2006(10):57-65.[SHI Dan. Analysis of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energy efficiency and energy saving potential in China[J].China industrial economy, 2006 (10): 57-65.]
[19]陈关聚. 中国制造业全要素能源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面板数据的随机前沿分析[J]. 中国软科学, 2014(1):180-192.[CHEN Guanju. Poly efficiency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total factor energy-stochastic frontier panel data analysis[J].China soft science, 2014 (1): 180-192.]
[20]BILGEN S. Structure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global energy consumption[J]. Renewable & sustainable energy reviews, 2014, 38(5):890-902.
[21]王兵, 謝俊. 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国际比较——基于能源结构视角的实证研究[J]. 产经评论, 2015(2):72-86.[WANG Bing, XIE Jun. Total factor energy efficiency i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on the view of the energy structure[J].Industrial economic review, 2015 (2): 72-86.]
[22]BAUMOL W J, OATES W E, BAWA V S, et al. The theory of environmental policy[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127-128.
[23]PEARCE D W, WARFORD J J. World without end: economics 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45-50.
[24]WERF V D E H, MARIA C D. Imperfect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polluting emissions: the green paradox and beyond[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nvironmental & resource economics, 2012, 6(2):153-194.
[25]JORGENSON D W, WILCOXEN P J.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U.S. economic growth[J].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1989, 21(2):314-340.
[26]BARBERA A J, MCCONNELL V D.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on industry productivity: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 management, 1990, 18(1):50-65.
[27]FUKUYAMA H, WEBER W L. A directional Slacks-based measure of technical inefficiency[J]. Socio-economic planning sciences, 2009, 43(4):274-287.
[28]COOPER W W, SEIFORD L M, ZHU J. Handbook on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M].New York: Springer US, 2011:195-196.
[29]KNEIP A, WILSON SP W. Asymptotics and consistent bootstraps for dea estimators in non-parametric frontier models[J]. Econometric theory, 2008, 24(6):1663-1697.
[30]SIMER L, WILSON P W. Sensitivity analysis of efficiency scores: how to bootstrap in nonparametric frontier models[J]. Management science, 1998, 44(1):49-61.
[31]张军, 吴桂英, 张吉鹏. 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1952-2000[J]. 经济研究, 2004(10):35-44.[ZHANG Jun, WU Guiying, ZHANG Jipeng. Chinese provincial capital stock estimates: 1952-2000[J].Economic research, 2004 (10): 35-44.]
[32]王维国, 范丹. 中國区域全要素能源效率收敛性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Malmqulist-Luenberger指数法[J]. 资源科学, 2012, 34(10):1816-1824.[WANG Weiguo, FAN Dan. Energy efficiency and the convergence of total factor chinese regional analysis: based on Malmqulist-Luenberger index method[J].Resource sciences, 2012, 34 (10): 1816-1824.]
[33]袁晓玲, 张宝山, 杨万平. 基于环境污染的中国全要素能源效率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 2009(2):76-86.[YUAN Xiaoling, ZHANG Baoshan, YANG Wanping. Research o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 China total factor energy efficiency[J].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2009 (2): 76-86.]
[34]应瑞瑶, 周力. 外商直接投资、工业污染与环境规制——基于中国数据的计量经济学分析[J]. 财贸经济, 2006(1):76-81.[YING Ruiyao, ZHOU Li.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dustrial pollution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based on econometric analysis of Chinas data[J].Finance and trade economics, 2006 (1): 76-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