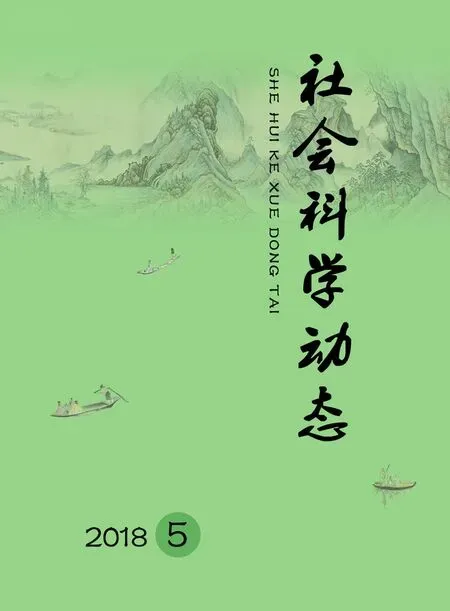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研究二十年
曹万青
1996年长沙走马楼吴简(以下简称“吴简”)的出土,为学术界提供了研究孙吴基层社会情况的第一手资料,也极大丰富和拓展了三国史研究的基础史料。自1999年起,陆续整理出版了《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 (壹、贰、叁、肆、柒、捌)共7大卷20分册。吴简材料的公布与出版,吸引了大批学者进入吴简研究领域,并大致形成两个学术方向:一是文献整理与复原方面,逐步形成“吴简文书学”;二是运用新材料解决传统问题,通过吴简资料与传世文献结合的“二重证据法”,对一些传统观点重新诠释,或对一些争议性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关键证据。
吴简资料整理由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组成的走马楼简牍整理组负责。研究组织主要有:长沙简牍研究会、北京吴简研讨班、东京吴简研究会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湖南大学等高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故宫博物院等单位都有专门研究吴简的学人。这些学者国内以高敏、蒋福亚、黎虎、王子今、于振波等为代表,日本以關尾史郎、阿部幸信、伊藤敏雄等为代表。
据不完全统计,20年来,中外学界共出版吴简研究专著和论文集23部,发表论文616篇①,讨论范围涉及经济史、政治史、社会史、考古学、简帛学、文献学、文书学、医学等方面,主要集中在经济史上的赋税赋役、田租、农业、手工业、商业,政治史上的“吏民”“户籍”“职官”,社会史上的人口、家庭、社会职业等方面,涉及的门类和课题众多,这些研究成果,极大地推进了简牍学、考古学、文书学、语言文字学和汉魏史、三国史、六朝史相关领域研究的发展。纵观20多年来的吴简研究,笔者在感慨赞叹学界所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也不免对吴简研究领域所存在的一些问题感到困惑和忧虑。在为数众多的吴简研究论著中,确有许多不乏真知灼见的研究成果,在开辟吴简研究这一新的学术领域的同时,对于推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深化也不无助益;另一方面,也有不少观点片面、甚至是错误的吴简研究论著,它们所表现出来的不良学风,不仅无助于吴简研究的进一步发展,甚至有欺人视听、误导读者的错误学术倾向,如果任由此种不良风气蔓延,必将阻碍吴简研究的继续深入,其严重者还会危及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因此,对吴简研究二十年来的研究状况进行归纳总结,既有助于深化对吴简已有研究成就的认识,亦可以在总结学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新的问题和研究方向,促进吴简研究的进一步发展。由于成果众多,限于文章的篇幅,加之笔者能力所限,故本文不能够做到全面的展开与分析,谨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介绍、总结吴简二十年来研究的成果。
一、吴简研究的学术史梳理
目前,对吴简研究进行学术史层面梳理的成果,除几篇专题性的文章外,主要是在每年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综述”中有所涉及。兹逐一叙述如下。
在梳理吴简研究成果的专题性文章中,以李凭《1998年简牍整理与研究述评》②为最早。该文对吴简整理和研究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有所涉及,主要包括1999年出版的《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和6篇专题论文,前者为吴简资料整理的阶段性成果,后者以介绍吴简所涉及内容、分类及其史料价值为主。李文认为:“走马楼吴简的发现必将为研究三国时期东吴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职官沿革、历史地理以及简册制度本身等提供丰富的资料,并有利于我们加深对三国历史的认识和重新审核以往的研究。”③
黎石生《近年来长沙走马楼简牍研究综述》④一文,统计了1999年至2001年间吴简研究的成果,计有论文50余篇和日本长沙吴简研究会主编的《嘉禾吏民田家莂研究——长沙吴简研究报告》⑤一集,作者从三个方面归纳了吴简研究情况:(1)关于吴简本身的研究,包括简牍的释读、整理、埋藏原因、释文等情况;(2)“田家莂”研究,主要围绕“田家莂”性质及其形制特征、田家身份及其佃田与租税、田类名称及其含义、长沙郡当时的民俗与社会经济状况等展开;(3)私学、官邸阁及其他研究,讨论了私学的性质及其与举主的关系,官邸阁的功能与设置等其他涉及经济史的内容。
于振波《近三十年大陆及港台简帛发现、整理与研究综述》⑥一文,时间跨度从上世纪70年代到2001年,介绍了近30年来,大陆及港台发现与整理了敦煌汉简、马王堆帛书、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简、吴简等出土文献的情况,介绍了一批高水平的汉简帛研究学术论著,这些整理和研究成果为秦汉史研究提供了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军事等方面的重要资料。
王素《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研究的回顾与展望》⑦一文,介绍、总结了1996年至2003年有关吴简研究成果,如学术界对吴简资料的早期探讨;《嘉禾吏民田家莂》及相关研究,特别是高敏、日本长沙吴简研究会、中国吴简研讨班各自取得的研究成果;解答了吴简三个方面的基本问题:年代、性质与埋藏原因,关于“田家莂”及所涉及的土地的性质,关于私学、己酉丘复民的身份与金民、还民、作部工师及吏民等问题。在文章最后,王素先生对吴简的研究前景做了展望:预计不久将会迎来一个吴简研究的高潮。事实上,后来吴简研究的发展状况的确应验了王素先生的预言。
车今花、于振波《走马楼吴简研究综述——职业、社会身份与阶层》⑧一文,介绍了2007年以前学界对吴简中户品、私学、吏与“吏户”、师佐及其他社会身份的研究情况,本文的突出之处在于第一次指出了史学界在吴简研究上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吏户”是否存在的争议。
何立民《湖南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研究的回顾与反思》⑨一文,系统地总结了1996—2008年的吴简研究,介绍了成果数量与类型、研究领域,并对代表性领域的研究进行了详实的梳理和评论,指出这些研究的学术特点与不足并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高鑫《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研究的回顾》⑩和王琦《十五年来长沙走马楼吴简研究进程综述》⑪,二文的总结比较笼统、都是粗线条的介绍了1996年来的吴简研究成果。
梁满仓《近年来三国历史研究状况》⑫一文,指出近年来吴简研究呈现的四个新特点:高层次的研究机构纷纷建立;国内著名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纷纷进入这一领域;吴简研究持续升温;日本学者对吴简表现出浓厚的研究兴趣并发表了一些成果。

表1 国内历年发表吴简研究论著数量
徐畅《走马楼吴简竹木牍的刊布及相关研究述评》⑬一文,首先,列出了1997—2014年间吴简研究的成果略称。其次,介绍了木牍研究的三个热点:木牍与竹简的编联问题、“叩头死罪白”木牍与许迪案始末、木牍与私学研究的新进展。最后,编列“吴简竹木牍研究参考论著略称目录”,略为遗憾的是作者仅胪列相关研究成果,而未做有见地性的评价。
1996—2016年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综述”,除1998年、2007年外,皆涉及吴简研究,显示出吴简研究逐步升温,已然成为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热点领域。
除了学术类文章之外,在普及吴简知识和整理成果方面,学术界也进行了有益尝试。如王素《长沙走马楼简牍整理的新收获》⑭一文,介绍了吴简的出土、分类、数量、整理进度及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并介绍吴简发现的重大意义。又如王云庆、孙嘉睿《近三十年来我国历史简牍文献的重大发现》⑮一文,先向读者介绍了简牍作为一种特殊的书写材料,在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接着,介绍了近三十年来考古发掘与历史文献研究工作取得的成就:甘肃天水放马滩秦简、敦煌悬泉置汉简、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里耶秦简、清华简、湖南益阳兔子山简牍和江西南昌海昏侯墓葬简牍等。
介绍日本吴简研究者,则有安部聪一郎、杨振红《2011年日本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⑯、津田资久、杨振红《2012年日本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⑰两文,都对年度日本吴简研究成果做了摘要。窪添慶文《日本的长沙吴简研究》⑱一文,不仅对日本学界利用吴简材料取得的成果做了全景式的介绍,还分享了日本长沙吴简研究会的工作方法和特色,展示了日本学者严谨的学风。
对吴简研究所作的评价性分析,有侯旭东《关于近年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观察与思考》⑲一文,该文在着重介绍吴简研究所面临困境的同时,还展望了吴简研究的可能领域,即空间问题、精神世界、考古资料的运用、帝国形态四个方面。何立民《湖南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研究的回顾与反思》⑳一文,也是在回顾吴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总结了吴简研究的学术特点及不足。
上述论文皆为学者个体性的独立研究,此外,学术界还组织了专题学术研讨会、读书班等形式,对吴简进行“集体性”的研究。其中比较有影响的学术研讨会,为2001年8月在长沙召开的“长沙三国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出版了论文集《长沙三国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6年8月在长沙召开的“纪念走马楼三国吴简发现二十周年长沙简帛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出版了论文集《长沙简帛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于振波《长沙三国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㉑,孙东波等《纪念走马楼三国吴简发现二十周年长沙简帛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㉒,对这两次会议有关吴简的研究成果有着详细的介绍和评价。国内吴简研究比较有影响力的团体是北京吴简研讨班,他们通过研讨班的形式,开展吴简研究,并出版了研究成果《吴简研究》 (第一、二、三辑)。
以上即为目前史学界关于吴简研究的学术史梳理成果之概况,吴简研究论著数量可见表1。这些成果或是对某一特定领域研究成果的叙述总结,或是对一定时期内学术史的梳理,或是对材料的罗列堆砌,缺乏对二十年来吴简研究成果的综合性、整体性、总结性的梳理。针对二十年来吴简研究,笔者拟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总结。
二、利用吴简进行的经济史研究
利用吴简进行的魏晋南北朝经济史研究,涉及农业、商业、手工业、土地制度、货币、赋税赋役、租佃、雇佣、屯田、借贷、仓库管理、财务管理、度量衡等诸多方面,并涌现出数量众多的论著,据笔者粗略统计,至少有126篇(部)。由于学者和论著数量众多,兼之本文篇幅所限,无法对上述研究成果做面面俱到的评价,兹选取高敏、蒋福亚两位前辈的吴简研究作为代表,对利用吴简进行的魏晋南北朝经济史研究略加评述。
作为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领域的前辈学者,高敏先生素以研究经济史著称,吴简出土后,高先生即投入吴简研究,前后共发表16篇研究论文,并于2008年出版《长沙走马楼简牍研究》㉓一书,其核心观点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形成了“吏户”,“吏户”具有地位卑微、单列户籍、空户从役和身份世袭等三个特征。高先生这一观点实源于其《试论汉代“吏”的阶级地位和历史演变》一文:
……唐长孺先生和王仲荦先生等史学家。他们以大量的事实,论证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一种以“吏”命名的服役者存在。这种“吏”,不但被使用于各种非生产性劳动,而且也被使用于生产性劳动。……“吏”的劳动是强制性的,……又谓“吏”的来源,除“募吏”外,多系强迫贫苦农民充当,谓之“补吏”;贫苦农民一旦被强迫“补吏”,就被另立户口,与一般平民有严格区分;一户之内,如有一人隶“吏籍”,不仅其本人要终身为官府服役,就连其家属也不能幸免,几乎是“空户从役”;“吏”的卑贱和服役的身分,是世袭性的,父死子及,世代为“吏”;……“吏”是一种特殊的服役者,他们身分的卑贱程度,远在当时的贫苦农民之下,……㉔
高先生认为“吏户”论的观点源于唐、王两位先生。然而据李文才先生的考证,唐先生在“吏户”的问题上是有所保留的,因为唐先生并没有明确使用“吏户”的概念:
……可见,唐先生直到晚年仍然坚持“吏”为“特殊户口”“不列于正式户口”的观点。总而言之,唐先生自1957年提出而后不断论证的这一系列与魏晋南北朝“吏”有关的观点,构成了传统“吏户”论的核心论点。不过,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吏户”论的核心观点皆缘起于唐先生的上述说法,但唐先生本人始终未曾直接使用“吏户”这一名词,而只是将其表达为一种“别于编户的特殊户口”“特殊户口”“不列于正式户口”等。㉕
可见,“吏户”这一概念的提出,是高先生对唐先生相关论点的引申和发挥,并第一个明确使用“吏户”一词,进而形成了完整的“吏户”论。笔者阅读《试论汉代“吏”的阶级地位和历史演变》时发现,高先生在论证“吏”的社会地位卑微时,所选取的“吏”受欺凌、压迫方面的论据都是史实(我们并不否认,在封建官府从事下层职役的“吏”确实有遭受欺凌的事实),但另一方面,高先生忽视了“吏”作为基层行政人员在赋税征收、徭役征发等方面所享有的、较诸一般编户齐民更为优厚的待遇,以及他们欺压普通百姓、作威作福的史实。因而,当吴简材料公布以后,基于其已先入为主地心存传统“吏户”论的观点,高先生在解读这些新材料的时候,继续坚持传统“吏户”论,认为吴简资料所反映的“吏”的情况,符合“吏户”的三个特征。
蒋福亚先生也以研究魏晋南北朝经济史享誉学界,在吴简研究上也取得了突出成就,从2001年起先后发表16篇相关论文,并于2012年出版《走马楼吴简经济文书研究》㉖一书,涉及货币、地租、赋税、租佃、雇佣、屯田、复民、盐铁官营和酒类专卖、“田家莂”性质等内容。值得注意者,蒋先生还以专门章节论证了“吴简中吏户是客观的存在”:
诸吏虽和一般民户的户籍编制在一起,并受乡、里基层行政组织管辖,但此时毕竟呈现若干与民不同的特征,已经有某些特殊群体的迹象,因而只要该乡、里中有诸吏,就必须将吏户和吏口单列出来,并予以必要的统计……凡是户主是诸吏,其身份地位已经影响其户内的妻儿老小,由此为吏户制的出现和形成准备了必要的条件。总之,在户籍中,吏户是客观的存在。㉗
不仅如此,蒋先生还在其他论著中,反复申明“吏户”的存在,如:“自三国开始,封建政府控制的依附民中,还有吏户,他们的数量也相当大。”㉘这是说“吏户”单列户籍。再如:“吏是世代承袭的,父为吏,兄弟子侄都为吏。不允许冒充替代,否则便触犯律令。……他们承担的役十分沉重,既供各级政府及达官贵人奔走驱使,兵役也难幸免,而且几乎是空户从役。”㉙这是说吏户身份世袭。又如:“这一时期,封建政府控制着为数众多的依附民:屯田客、士家、吏户、杂户等,其中有许多是由奴婢组成的。如……孝建二年(455年),宋孝武帝发籍没为奴者为吏户。”㉚这是说“吏户”地位卑微㉛。
由以上可知,蒋先生认同传统“吏户”论,并没有因为吴简的公布而变化,他认为吴简资料进一步证明了“吏户”的存在。
其他年轻学者的吴简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某些具体问题的考察,从不同方面丰富了魏晋南北朝经济史研究的内容,但多数继续认同传统“吏户”论,从而造成在吴简新资料大量公布的情况下,魏晋南北朝经济史的研究并无实质性突破的局面。
三、利用吴简进行的政治史研究
利用吴简进行的魏晋南北朝政治史研究,涉及职官、户籍、吏民、赐爵、法律、军事、行政区划等方面。这也是吴简研究高产的领域,据笔者粗略统计,这方面的论著至少有133篇(部)。由于本文篇幅所限,无法对上述研究成果做出全面、详细的评价,兹选取黎虎先生的吴简研究作为代表,对利用吴简进行的魏晋南北朝政治史研究略加评述。
如所周知,传世文献中关于经济史的内容本身就少之又少,故先前研究魏晋南北朝经济史的学者只能通过史书中有限的记载和吉光片羽的出土文物,探索这一时期社会经济的特点。作为当时长沙郡的官府档案,出土的吴简以近乎完整的面貌呈现给世人,伴随着吴简资料的公布,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这一时期的经济史问题进行研究。相对于利用吴简进行的经济史研究,利用吴简进行的政治史研究则多数流于某些政治现象的考订、补充或校勘,由于制度史研究的难度较大和制度自身的复杂性,如果没有扎实的基础文献功底,再单纯利用吴简这样的带有极强片面性的出土文献对之进行研究,则很难避免管中窥豹现象的出现,体现在利用吴简进行的政治史研究方面,确实就出现了这种情况,一些学者由于功力不逮,其研究往往流于对一些细枝末节甚至是琐碎问题的考订,其甚者或作出与事实完全相悖的“臆解”或猜谜式的“研究”,故吴简政治史研究看似热闹异常、论著颇丰,实际上却鲜有真知灼见,更遑论突破性成果的出现。
在众多参与吴简研究的学人中,真正形成突破性研究的是黎虎先生。黎先生先后发表12篇吴简研究系列论文,不仅否定传统吏户论,在“吏户”“吏民”问题研究上建立了全新的体系性认识㉜,而且黎先生的系列研究在魏晋南北朝政治史,甚至是汉唐政治制度史的领域也形成某种创新性的突破。鉴于学界对于黎先生吴简研究在“吏户”“吏民”问题方面的成就和建立的体系性成果,已有全面、精审的认识和评价㉝,这里仅就黎先生吴简研究在政治史研究领域的突破和贡献,略谈一二。为了便于以下行文分析,笔者根据文章的内容,将黎先生上述12篇文章大致分为三组㉞,加以阐述。
第一组破除传统“吏户”论。《“吏户”献疑——从长沙走马楼吴简谈起》一文中,黎先生在对吴简资料中有关“吏民”占田数量进行统计、排序之后,发现“吏”在士、吏(州吏、郡吏、县吏)、卒(州卒、郡卒、县卒)、军吏、复民、普通农民(男子、大女)等六种“吏民”中,占田数量仅次于“士”而居于第二位的事实,从而得出“吏”的社会地位高于一般“吏民”的结论,在事实上驳斥了“吏户”论中关于“吏户”地位卑微的观点。《魏晋南北朝“吏户”问题再献疑——“吏”与“军吏”辨析》,则对“吏”与“军吏”的联系和区别作了明晰的界定,不仅厘清“吏”与“军吏”之间的关系,还指出传统“吏户”论在具体论证过程中存在明显的错误,即传统“吏户”论所指的“吏”虽然是行政系统的“吏”,然而他们在论证的过程中,却常常以军事系统中的“军吏”史料作为资料依据,从而不仅将行政系统之“吏”与军事系统之“吏”混为一谈,甚而将行政系统之“吏”与军事系统之士卒亦混为一谈。这就道破了某些“吏户”论者的研究方法论,即预设观点然后再寻找史料进行证明,在史料不足以证明的情况下,就通过有选择地引用、裁剪、片面解读史料的方式进行研究。《魏晋南北朝“吏户”问题三献疑——“吏户”论若干说法辨析》一文中,通过对文献资料的考索与分析,黎先生指出:“吏”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兼具相对稳定性和相对变动性的特点,“吏”在“官”与“民”之间流动,下则来自于“民”,或复归于“民”,上升则由“吏”升迁为“官”。另外,“小吏”可以为官,甚至成为高官,既是一种普遍性的社会观念,也是国家政治制度中的正常现象,魏晋南北朝与两汉时期一脉相承。这就驳斥了“吏户”论中“吏”具有世袭性的观点。第二组确立“吏民”一体的社会属性。从正面阐释、论证了三个问题:(1)“吏民”的内涵及其界定(“吏民”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均享有同等权利和义务的编户齐民);(2)“吏民”的社会属性(中国古代社会的基层结构,就是这种“吏民”一体的相互依存,从战国以来,历两汉魏晋南北朝而牢固地、长期地存在着,成为中国古代皇权统治的社会基础);(3) “吏民”的一体性(“吏民”一体的社会结构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又是由中国古代的经济形态、政治制度、社会形态等特点所决定的,这些特点没有改变,则这种“吏民”结构也不可能根本改变)。
第三组对“吏民”问题进行深度考察——“真吏”“给吏”“军吏”。黎先生认为:“真吏”是相对于非“真吏”而言,前者是指真除实授的官员和吏员,后者则指非真除实授的官员和吏员;非“真吏”又有两种类型,一类是冗散无职事者,仅有名义上的官称吏名;另一类,虽有具体职事,但尚未真除实授。这不仅明确了“真吏”与非“真吏”的关系,还驳斥了有些论者提出的“与‘真吏’,相对的是‘假吏’”的错误观点。
吴简中既有“州吏”“郡吏”“县吏”等名词,亦有“给州吏”“给郡吏”“给县吏”等记载。二者之间有何关联,学界争论不休。在《说“给吏”——从长沙走马楼吴简谈起》㉟一文中,黎先生综合吴简资料与传世文献的相关记载,提出“给吏”大致有两种不同类型,一是在本州、郡、县服役的“给州吏”“给郡吏”“给县吏”者;二是被派遣至其他部门或单位服役的“给吏”者。同时,该文第三版在制度史层面具有重大价值,表现为: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吏”的阶层划分,一直是分为长吏、属吏、役吏三层。黎先生对此问题进行了修正,将最后的“役吏”改为“给吏”,一字之改,黎先生实际上已经将“给吏”提升为和察举、征辟等传统选官方式并列的一种方式(或者说是一种补充方式),从而形成对汉代选官制度(乃至整个汉唐选举制度)相关传统观点的重大突破㊱。笔者不禁想起钱穆先生对汉代吏的来源所做的分析,钱先生云:“汉制吏途凡三:一曰郡县吏,不限资格,平民自愿给役者皆得为之。二曰中都官掾属,自丞相以下各官府皆自辟署,或先为郡吏,或本为布衣,亦不限资格,优者则荐于朝。三曰狱吏,犹今时法官,以明习法令名。”㊲两相比照,不难发现钱、黎两位学者的观点虽不尽相同,却也有某些相通之处,可谓英雄所见略同㊳。
“军吏”一词常见于中国文献典籍,然而,“军吏”的范畴究竟是什么?文献并无明确记述。在黎先生之前,学界讨论涉及“军吏”问题者,仅有两文㊴。吴简中尽管有不少“军吏”的记载,但在黎先生之前,并未见专题论述。黎先生第一个对“军吏”进行深入、系统的考察,时间跨度上从先秦到唐,指出了在这一段历史不同时期“军吏”概念内涵和外延的变化:先秦时期的“军吏”,是指军队中除士兵之外的各级军官;战国时期,“军吏”层级有所下移,指将军以下的中下级军官。汉代继续下移,以校尉为将军与“军吏”之分界线,此外幕府中的各色吏员亦可归入“军吏”范畴。魏晋南北朝承袭两汉,也以将领所辖之中下级军官和军府属吏为“军吏”,但“军吏”与将军并非截然划分,具有一定的相对性。以吴简中的“军吏”而言,则属于其时军队之下层吏员,吴简六种“吏民”中,“军吏”的地位、待遇或略高于普通农民和“卒”,而低于“士”“吏”“复民”。唐五代时期的“军吏”,范畴较前有所变化,府署幕僚不能笼统纳入“军吏”范畴,而主要指其中的武职僚佐,文职僚佐不再属于“军吏”。其意义不仅在于进一步丰富了魏晋南北朝“吏”问题研究的内容,更在于对于中古军事制度、中古社会政治史等学术研究领域具有开辟学术新领域的引领示范价值。
由以上论述可见,黎虎先生可视为吴简研究在政治领域取得杰出成果的代表,分析黎先生取得如此成就的原因,实与其研究方法的科学、确当有直接关系,尽管他的多数相关文章均标以“从长沙走马楼吴简谈起”,但实际上他的研究仍然是以传世文献为基础性、核心性的史料,而辅以吴简资料,他一方面利用和研究吴简,另一方面并不拘泥于吴简资料,这与某些学者单纯的就吴简论吴简、忽视甚至曲解传世文献资料的做法,可谓有着泾渭分明的区别。笔者认为,这是黎先生在吴简研究领域之所以能够取得卓越成就的重要原因。
其他学者利用吴简所进行的政治史研究,多为对某些具体甚至是琐细问题的考察,确实也解决了魏晋南北朝史领域某些概念或词语内涵的问题,对于宣传吴简资料的价值、丰富简牍等出土文献研究的内容,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有些资料可以为我们的研究提供借鉴。
四、利用吴简进行的其他研究
以上即为学界二十年来利用吴简进行的经济史、政治史研究情况之大概。除此之外,利用吴简所进行的社会史及其他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据笔者粗略统计,这些研究成果包括大约70篇论文,涉及人口、家庭、姓氏、称谓、移民、社会生活、社会结构、交通、祭祀、占星等诸多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为王子今、于振波两位先生,兹略述其研究如下。
王先生吴简研究成果丰硕,先后共发表20余篇相关文章,涉及经济、政治、社会等多个领域。笔者拟从三个方面对其研究略做说明。
以言其吴简经济史研究,有8篇文章,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为《走马楼竹简“小口”考绎》㊵,该文针对吴简中出现的“小口”“大口”,结合汉代赋税制度中的“大小口有差”的情况,认为孙吴赋税征收也存在类似情形,至于吴简“小口”与“大口”年龄的界定,因资料所限,王先生未做断言,但是他随后又根据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的原则,对吴简中“小女”的年龄进行分析,认为“小女”与“大女”的年龄界点当在15岁左右,进而推断“小口”与“大口”的界定也当如此。这一推论性的观点,有助于我们认识和理解古代未成年人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另外,针对“盐”“酒”同时频繁出现在同一条吴简的情况,王先生撰有《关于走马楼简“盐”“酒”“通合”文书》㊶一文,认为这反映了当时政府对盐和酒生产、流通、消费进行专卖管理的重要信息。他还结合传世文献所见“盐酒务”“盐酒利”“盐酒价”“盐酒钱”“盐酒重额钱”等记载,论证了中国古代经济政策中“盐酒”一体之传统,最后得出结论认为,吴简所见盐酒“通合”文书反映的经济形式,或可看作“盐酒务”一类政策的历史先声。
以言其吴简政治史研究,共有4篇论文,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走马楼简牍所见“吏”在城乡联系中的特殊作用》㊷一文,王先生认为,在秦汉以来逐渐成熟的行政体系中,“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吴简中“乡吏”一方面很有可能是乡一级机构吏人的通称;另一方面“乡吏”不任用本乡人,这些在他乡任“乡吏”的人,依然是“县吏”的身份。他们有督促监督(即简文所见“督责”)乡民按照要求完成赋役的责任。这些“乡吏”面对乡民,是朝廷、帝王、国家的代表;面对郡县官署和上级官僚,则又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乡民的利益。他们作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中间阶层,起到了传达政令、反馈信息、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该文对于我们认识当时的基层社会结构,特别是当时的城乡关系有积极意义。另一篇《走马楼简牍“私学”考议》㊸,针对学界颇多讨论的“私学”,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评述,涉及胡平生、王素、侯旭东、于振波等人的相关研究㊹。在此基础上,王先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包括对“举私学”的正义、“私学”作为身份称谓的涵义等,他认为“私学”并不是与“官学”相对而存在的一个名词,应当按照汉代用语习惯,将“私”理解为专心爱重,故“吴简资料中所见‘私学’称谓指代的社会身份,是民间儒学教育体制下的受教育者。”㊺
吴简社会史研究,共有6篇论文,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论走马楼简所见“小妻”——兼说两汉三国社会的多妻现象》㊻一文,针对汉至魏晋相关正史颇多记载的“小妻”,王先生认为正史所载小妻,主要是上层社会的婚姻情况,而吴简则反映了民间社会的真实面貌。他认为吴简所见“小妻”,即“大妻”或“正妻”之外的配偶,吴简“小妻”的真正数量,可能比我们目前所能够看到的还要多;吴简所记录的“小妻”,反映了两汉三国时期普遍多妻的现象。另外,王先生还针对户籍简中“户下奴”“户下婢”所登记年龄或身高不同的情况,撰有《走马楼简所见未成年“户下奴”“户下婢”》㊼一文,他通过征引《后汉书·刘玄传》的相关记载㊽,对将“户下”视为“奴婢附于良人户口之下”㊾的观点进行了驳正,认为“户下奴”“户下婢”称谓或许可以与“灶下养”对照分析,“户下”与“灶下”可能含义相近,应为其劳作场所或生存空间的位置。至于仅登记身高者,王先生认为可能是奴役者来到主人“户下”时尚在幼年,准确年龄已不可求知,故以“长五尺”“长六尺”之类的身高概数来登记。后面他还引用于振波先生的相关论点,对“户下奴”“户下婢”的劳动能力和生活状况也进行了一些分析,其中不无可取之处。
接下来说于振波先生的吴简研究。于先生共有20篇吴简研究论文,也涉及经济、政治、社会等多个领域,这里仅取其与社会史相关的5篇的论文,略作评价。《略论走马楼吴简中的“户下奴婢”》㊿一文,结合传世文献,对吴简所载奴婢的性别、年龄等信息进行了分析考察,得出了一个带有推测性的认识:如果将豪强大族拥有的奴婢与普通编户齐民所拥有的私奴婢合并计算,估计三国时期长沙地区私奴婢约占总人口的5%。《略论走马楼吴简中的户品》[51]一文,则是利用吴简资料对“户等”这一传统论题进行重新考察,于文首先根据吴简所载民户财产的状况,将他们分为上品、中品和下品三个等级,同时将一些赤贫户划在三等之外,称之为“下品之下”。不过,对于户分九品的传统说法,于文则持否定意见。此外,于文还讨论了孙吴户品与“调”的关系,并具体指出吴简所载“调”的四种情况。最值得关注的是,于文认为当时“下品”及“下品之下”户非常贫穷,官府可能有意安排他们从事“给吏”“给卒”之类的特殊徭役并减免其赋税,起初未必含有歧视他们的用意,但具有特殊意义的“吏户”“兵户”却由此而在三国后期逐渐形成。这个看法显然是受到了传统“吏户”论的影响。另外,此文与前揭《从走马楼吴简看其时长沙民户的贫富差别》[52]联系密切,堪称姊妹篇,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为对前者相关论点的细化。
《略说走马楼吴简中的“老”》[53]一文,所关注的既是中国古代年龄区分这一传统问题,更是对《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中的“小”“大”“老”年龄区分所进行的直接讨论。如所周知,《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中,将所登记的人口区分为“小”“大”“老”三个年龄段,对于“小”“大”所对应的具体年龄,学界早已形成共识,即“小”指14岁以下,“大”指15岁以上,这个共识性观点已经被居延汉简等出土文献所证实。然而,关于“老”的起始年龄迄今尚未取得一致意见,传统看法或以为57岁,或以为61岁,之所以众说纷纭,实与古籍文献记载意存分歧不无关系[54]。于先生此文通过对吴简内容的解析,认为吴简所载缴纳算赋的最高年龄为59岁,进而将吴简中“老”的起始年龄推定为60岁。至此,关于“老”的年龄断限,于前述观点之外又增加了一说。
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普遍存在的早婚习俗,学界的共识之一是,男子十五六岁、女子十三四岁,或者说这是一条围绕其上下波动的婚龄主轴线[55]。吴简中并无有关女子婚龄的记载,于振波根据吴简中所登记的女子身份信息,对其时女性的婚龄进行探讨,撰成《吴简户籍文书所见女子婚龄》[56]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于先生根据吴简中女子在结婚之前,与自己的父母兄弟同住,以“子女”“女弟”等身份进行登记;而出嫁之后,则登记为“某妻”“某母”等情况,再通过与《三国志》 《晋书》等传世文献的比较,最后得出吴简户籍文书中女子结婚的基本年龄为15岁这一结论。
除了利用吴简进行社会史研究外,在吴简的保护[57]、信息检索、三国时期疾病的研究[58]、整理校勘[59]、考古学[60]、气候变化[61]、书法、文书学、简帛学等方面都有众多的成果,仅举几个方面,以飨读者。
鉴于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引用吴简资料出现不同征引格式的情况,为规范格式、方便学人,在《吴简研究》中有《吴简征引格式》一文,学界提出了建议性的吴简征引格式,以方便学者引用吴简资料。楼兰《我国出土简帛文献电子索引建设研究述评》[62]一文,对我国出土简帛文献电子索引建设方面的情况作了概要的介绍,作者认为在吴简信息检索方面,应打破地域、部门之间的界限,建立统一、全面的文献电子检索系统。这方面我们可以参照海外同仁的做法,前揭窪添慶文《日本的长沙吴简研究》一文,还特别介绍了日本长沙吴简研究会的一个工作方法:以共同作业的方式完成了已公布吴简的数据库制作,方便了个人研究。日本学者这一联合作业的工作方法,对我们很有借鉴意义。
在吴简书法研究方面,缘起于三国两晋的书法艺术上承秦汉,下启隋唐,在中国书法史上是一个有破有立的重要时期。汉字书体的发展演变,经过了篆、隶的巅峰,开始了草、行、楷的纷呈变化。各种主要书体都大致定型,隶书完成了楷化,章草转变为今草,行书的演变确立了完备的法度和形成了多变的风格。对于这一时期文字书法的研究,以前主要根据传世碑帖,随着简牍的大量出土,作为时人的日常墨迹,简牍比碑帖更能真实反映当时的书法状况。故针对吴简书法的研究,更能还原这一时期汉字书体变化发展的情况。熊曲《长沙走马楼吴简行书探析》[63]一文,通过对吴简行书的分析,揭示了行书这一新兴书体在三国时期发展演变的脉络。杨芬《长沙走马楼吴简中的隶书遗韵》[64]一文结合东汉到隋这一时期中国文字书法的流行趋势,通过对吴简中隶书书写情况的分析,介绍了隶书从东汉创作的颠峰,逐渐为楷书所取代的历史情况。简帛学是20世纪创建并取得丰硕成果的一门重要学科。吴简的发现与公布,推动了这一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蔡万进《简帛学的学科分支新论》[65]一文认为:随着简帛文书的大量出土,整理研究成果陆续的发布,简帛学分支的划分亟待调整;以往按照简帛内容性质、载体、属性等进行的划分标准,已然不能适应简帛学的发展。作者从简帛具有文物的一切属性和特征的角度出发,认为应将简帛学分为三个分支:简帛文化学、简帛文献学和简帛文物学。
以上为笔者对吴简发现二十年来相关研究成果的粗略概述,由于笔者学力不逮,对相关文章的综述难免挂一漏万,对学者研究成果的理解亦未必尽符合作者的原意。不过,笔者可以保证的是,本文的相关评述是基于对数百篇吴简研究论著的阅读分析,如有未尽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注释:
① 吴简研究论著数目是基于对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维普期刊资源整合服务平台等的检索,《吴简研究》 (第1、2、3辑) 文末所载《长沙走马楼吴简研究论著目录》,对于一些会议论文,以主办方出版的论文集为准,一些文章由作者修订或修改标题后易刊发表(如孙闻博《走马楼吴简所见乡官里吏》,原收录长沙简牍博物馆、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北京吴简研讨班编《吴简研究》 (第3辑) (中华书局2011年版),后收入长沙简牍博物馆编《走马楼吴简研究论文精选》 (岳麓书社2016年版)时,更名为《走马楼吴简所见“乡”的再研究——兼论孙吴时期的乡官里吏》),本文皆采用最后发表的版本,在统计上合计为1篇。对于海外学者吴简研究的成果,受限于笔者的语言能力,谨采用已有的学术史梳理成果进行介绍,截止时间为2017年底。
②③ 李凭:《1998年简牍整理与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1999年第10期。
④ 黎石生:《近年来长沙走马楼简牍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4期。
⑤ 日本长沙吴简研究会主编:《嘉禾吏民田家莂研究——长沙吴简研究报告》,日本东京2001年第1集。
⑥ 于振波:《近三十年大陆及港台简帛发现、整理与研究综述》,《南都学坛》2002年第1期。
⑦ 王素:《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北京吴简研讨班编:《吴简研究》 (第1辑),崇文书局2004年版,第1—9页。
⑧车今花、于振波:《走马楼吴简研究综述——职业、社会身份与阶层》,《湖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⑨⑳ 何立民:《湖南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研究的回顾与反思》,《江汉考古》2009年第2期。
⑩ 高鑫:《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研究的回顾》,《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⑪ 王琦:《十五年来长沙走马楼吴简研究进程综述》,《群文天地》2012年第4期。
⑫ 梁满仓:《近年来三国历史研究状况》,《襄樊学院学报》2011年第9期。
⑬ 徐畅:《走马楼吴简竹木牍的刊布及相关研究述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 (第3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5—74页。
⑭ 王素:《长沙走马楼简牍整理的新收获》,《文物》1999年第5期。
⑮ 王云庆、孙嘉睿:《近三十年来我国历史简牍文献的重大发现》,《文史杂志》2016年第4期。
⑯ 安部聪一郎、杨振红:《2011年日本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13年第6期。
⑰ 津田资久、杨振红:《2012年日本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14年第6期。
⑱ 窪添慶文:《日本的长沙吴简研究》,长沙简牍博物馆编:《长沙简帛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西书局2017年版,第31—49页。
⑲ 侯旭东:《关于近年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观察与思考》,《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2期。
㉑ 于振波:《长沙三国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2期,后更名为《长沙三国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收入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长沙三国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89—496页。
㉒ 长沙简牍博物馆编:《长沙简帛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西书局2017年版,第540—555页。
㉓ 高敏:《长沙走马楼简牍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㉔ 高敏:《秦汉史论集》,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第213—214页。
㉕㉜ 李文才:《评长沙走马楼吴简“吏民”问题研究及其乱象——兼论大陆史学界“吏户”问题研究60年》,《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
㉖㉗ 蒋福亚:《走马楼吴简经济文书研究》,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版,第52—54页。
㉘ 蒋福亚:《魏晋南北朝国有土地上的租佃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
㉙ 蒋福亚:《〈嘉禾吏民田家莂〉中的诸吏》,《文史哲》2002年第1期。
㉚ 蒋福亚:《略论魏晋南北朝的奴婢》,《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5期。
㉛ 在另外两篇文章中蒋先生也表述了相同的观点,如《魏晋南北朝国有土地上的租佃关系》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6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封建政府所以要有如此多的吏,关键在于他们和士家一样,也是封建政府控制的依附民。他们既是各级政府力役的提供者,又从事农业生产,承受极端残酷的剥削。所以有时他们很难和士家区分开来,而被称为‘吏士之家’。”《长沙走马楼吴简所见奴婢杂议》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该文的核心观点是:吴简中有关奴婢的简牍显示,资产不丰的“民户”和身份地位类同官府依附民的“师佐”往往拥有奴婢,说明吴国蓄奴之风甚盛。官奴婢用于屯田,证明吴国的奴婢是从事生产的。更重要的是“户下奴”“户下婢”之类名称,证实此时奴婢已载入户籍,其源头应在西汉。
㉝ 学界对黎虎先生吴简“吏户”“吏民”研究成果的评价,以李文才《评长沙走马楼吴简“吏民”问题研究及其学术乱象——兼论大陆史学界“吏户”问题研究60年》一文最为全面系统。
㉞第一组:《“吏户”献疑——从长沙走马楼吴简谈起》,《历史研究》2005年第3期;《魏晋南北朝“吏户”问题再献疑——“吏”与“军吏”辨析》,《史学月刊》2007年第3期;《魏晋南北朝“吏户”问题三献疑——“吏户”论若干说法辨析》,《史学集刊》2006年第4期;《魏晋南北朝“吏户”问题四献疑》,《宜春学院学报》2016年第10期。第二组:《原“吏民”——从长沙走马楼吴简谈起》,《历史文献研究》2008年总第27辑;《论“吏民”的社会属性——原“吏民”之二》,《文史哲》2007年第2期;《论“吏民”即编户齐民——原“吏民”之三》,《中华文史论丛》2007年第2期;《原“吏民”之四——略论“吏民”的一体性》,《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3期;《关于“吏民”的界定问题——原“吏民”之五》,《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5期。第三组:《说“给吏”——从长沙走马楼吴简谈起》,《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11期;《说“真吏”——从长沙走马楼吴简谈起》,《史学月刊》2009年第5期;《说“军吏”——从长沙走马楼吴简谈起》,《文史哲》2005年第2期;《汉唐时期的“军吏”》,原刊日本《唐代史研究》第9号(2006年7月),后转载于《阴山学刊》2006年第6期。2016年,黎先生整理出版《先秦汉唐史论》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又将此文以《汉唐时期的“军吏”——从长沙走马楼吴简谈起》为题收入其中。
㉟ 按:此文共有三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最初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第二个版本载于《先秦汉唐史论》,为作者于2016年3月“根据新近公布的吴简资料对这一原刊文进行了补充、修改”;第三个版本载于《走马楼吴简研究论文精选》 (上),是在前两个版本的基础上进行了第三次重要修改,并最后定型。比较三个版本,可以发现,不仅第二版于第一版做了根本性的补充和提高,而且第三版较第二版也有重要突破。
㊱黎先生《说“给吏”——从长沙走马楼吴简谈起》一文,后收入《走马楼吴简研究论文精选》 (上),在该文“后论”部分第263页,黎先生探讨了“给吏”能够成为当时官府吏员来源和产生的一种补充方式的原因是:“一则因为它涉及面极其广泛。除了基层普通百姓之外,还有广大的‘诸吏’家属,……二则其所‘给’之‘吏’十分广泛。它涉及以州、郡、县三级为中心的各级地方政权机构乃至其他相关单位或部门,‘给吏’者已成为国家机构必要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三则其征调已经有了一定的规则。……四则两者在任用制度方面具有某些同一性。从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观之,‘给吏’者与察举、征辟之‘吏’一样,也需经过‘署’才能成为正式的‘吏’。”
㊲ 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40页。
㊳ 两位先生观点不尽相同之处,主要表现为郡县吏在钱先生那里被视为徭役或差役,而在黎先生那里则被看做“给吏”,“给吏”的范围涵盖面更广,既包括徭役或差役在内而又不限于徭役或差役;其次,钱穆先生所说的第二、第三点,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归入“给吏”之列。显然,黎先生“给吏”论的相关论断,比起钱穆先生汉代吏的三个来源说,更为全面、科学,也更符合于汉魏南北朝时期的相关历史情况。
㊴ 陈槃:《由汉简中之军吏名籍说起》,《大陆杂志》1951年第2卷第8期。李学勤:《马王堆帛书〈刑德〉中的军吏》,《简帛研究》第1辑,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56—159页。此两文仅对“军吏”的部分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未切中“军吏”概念的实质含义。
㊵ 王子今:《走马楼竹简“小口”考绎》,《史学月刊》2008年第6期。
㊶ 王子今:《关于走马楼简“盐”“酒”“通合”文书》,《盐业史研究》2016年第4期。
㊷ 王子今:《走马楼简牍所见“吏”在城乡联系中的特殊作用》,《浙江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㊸㊺ 王子今、张荣强:《走马楼简牍“私学”考议》,载长沙简牍博物馆、北京吴简研讨班编《吴简研究》(第2辑),崇文书局2006年版,第67—82、75页。
㊹ 胡平生:《长沙走马楼三国孙吴简牍三文书考证》,《文物》1999年第5期;王素:《长沙走马楼三国孙吴简牍三文书新探》,《文物》1999年第9期;侯旭东:《长沙三国吴简所见“私学”考——兼论孙吴的占募与领客制》,《简帛研究二〇〇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14—522页;于振波:《走马楼吴简之“私学”身份考述》,《大学教育科学》2005年第5期。
㊻ 王子今:《论走马楼简所见“小妻”——兼说两汉三国社会的多妻现象》,《学术月刊》2004年第6期,。
㊼ 长沙简牍博物馆等编:《吴简研究》 (第3辑),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23—131页。
㊽ [宋]范晔撰、 [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11《刘玄传》载:“长安为之语曰:灶下养,中郎将。烂羊胃,骑都尉。烂羊头,关内侯。”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471页。
㊾ 陈爽:《走马楼吴简所见奴婢户籍及其相关问题》,北京吴简研讨班编:《吴简研究》 (第1辑),崇文书局2004年版,第161页。
㊿ 于振波:《略论走马楼吴简中的“户下奴婢”》,《船山学刊》2005年第3期。
[51]于振波:《略论走马楼吴简中的户品》,《史学月刊》2006年第2期。
[52]于振波:《从走马楼吴简看其时长沙民户的贫富差别》,《史学月刊》2008年第6期。
[53]于振波:《略说走马楼吴简中的“老”》,《史学月刊》2007年第5期。
[54]关于“老”的年龄断限,古人就有不同说法,如《周礼·太宰职》贾公彦疏曰:“是以郑君引汉法民年二十五以上至六十出口赋、钱,人百二十以算。”根据这个说法,60岁依然出口赋钱,就意味着61岁始为“老”。《通典·食货四》汉仪注:“人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为治库兵车马。”根据这个说法,56岁依然出赋钱,就意味着57岁始为“老”。
[55]朱大渭、刘驰、梁满仓、陈勇:《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2—249页。
[56]于振波:《吴简户籍文书所见女子婚龄》,《走马楼吴简研究论文精选》 (上),岳麓书社2016年版,第605—611页。
[57]胡东波、宋少华、肖静华:《长沙走马楼出土饱水竹简的防腐保存》,《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03年第2期;陈跃辉:《三国吴简腐蚀斑微生物的分离鉴定及其木质素降解性能研究》,中南大学环境工程2009年硕士论文。
[58]高凯:《从吴简蠡测孙吴初期临湘侯国的疾病人口问题》,《史学月刊》2005年第12期;周祖亮:《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疾病词语略考》,《广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巩镭:《汉末三国时期疾病研究》,郑州大学2011年硕士论文。
[59]高敏:《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释文注释补正——读走马楼简牍札记之八》,《郑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王素:《关于长沙吴简几个专门词汇的考释——〈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释文探讨之二》,《吴简研究》 (第2辑),崇文书局2006年版,第258—269页。
[60]宋少华:《长沙三国吴简的现场揭取与室内揭剥——兼谈吴简的盆号和揭剥图》,《走马楼吴简研究论文精选》 (上),岳麓社2016年版,第1—7页。
[61]王子今:《走马楼竹简“枯兼波簿”及其透露的生态史信息》,《湖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62] 楼兰:《我国出土简帛文献电子索引建设研究述评》,《兰台世界》2015年第26期。
[63]熊曲:《长沙走马楼吴简行书探析》,《中国书法》2014年第10期。
[64]杨芬:《长沙走马楼吴简中的隶书遗韵》,《中国书法》2014年第5期。
[65]蔡万进:《简帛学的学科分支新论》,《中国史研究动态》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