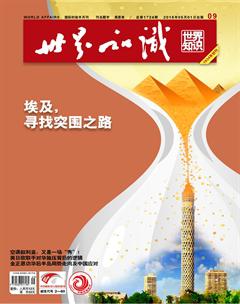英国退欧:在矛盾中踟蹰前行
赵俊杰
自2016年夏英国政府通过全民公投决定脱离欧盟以来,英国脱欧就产生了国际轰动效应,在欧盟引发广泛争议和不满,成为近年来欧洲最具爆炸性的政治事件。今年3月19日,欧盟与英国公布了一份有关英国“脱欧”过渡期安排的协议草案,宣布已就其中大部分条款达成一致,这份协议于3月24日获欧盟批准通过。这意味着英欧已经正式开启了“后脱欧时代”英欧关系谈判。

2018年3月19日,比利时布鲁塞尔,英国“脱欧”事务大臣戴维·戴维斯(左)和欧盟英国“脱欧”事务首席谈判官米歇尔·巴尼耶共同宣布英国和欧盟已经达成了一份有关英国退欧过渡期安排的协议草案。
从脱欧到退欧:英国走到关键路口
英国脱欧之所以在欧洲引发政治地震,自然有其缘由。首先,英国是欧盟的一个“超级大国”,英国的GDP在2015年曾占欧盟总GDP的17.2%。其次,英国是欧洲的金融中心,管理着大部分欧洲的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参与欧盟35%的风险投资。英国退欧后单是年度预算就给欧盟留下了两三百亿欧元的窟窿。再次,英国还是一个军事大国,是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之一,欧洲的安全与防务建设离开英国就是不完美的。英国的科技与创新能力也很强。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正因为英国的分量十足,它选择脱欧必然会引发欧盟的愤怒。欧盟非一般的超国家联盟,它在外交、司法等领域享有某些类似于国家的“主权”,同时还在内部减少成员国间的边境管控,资本、货物及人员等可在欧盟内部自由流动。这些曾令欧盟引以为荣的一体化成就如今却因英国脱欧而失去光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的极右翼政治势力受英国脱欧的影响而蠢蠢欲动,他们纷纷打着民粹主义的旗号,要求本国政府效仿英国搞脱欧公投,欧洲一体化大厦的根基开始动摇。无论从哪方面考虑,欧盟都无法容忍英国首开先河的脱欧决断。经济学人智库有一个评估,在欧盟成员国中,以德国和法国为首的7个国家属“顽固不化派”,主张对英国脱欧给予严惩;以意大利、西班牙为代表的12个国家属“硬骨头派”,主张英国脱欧就不要再回来;只有爱尔兰、瑞典等8个小国属“温和派”,主张与英国“有话好好说”。总的说来有超过2/3的成员国在英国脱欧的立场上属于“强硬派”。

英联邦峰会于2018年4月19日在伦敦召开。图为4月18日,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左一)、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左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右二)与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举行情报合作伙伴会晤。
英国保守党领导人特雷莎·梅临危受命、走马上任,但出任首相后的她内外交困。在国内,硬脱欧缺乏议会和大众支持,她不得不在2017年提前举行大选以期巩固扩大保守党在议会的议席,然而事与愿违、弄巧成拙,保守党在下议院的议席数从330个下降到316个(总席位数650个),差点失去执政地位。在欧洲大陆,欧盟及其大多数成员国对英国步步紧逼,在退欧问题上态度十分强硬,使英国与欧盟的退欧谈判始终充满火药味。
退欧是特雷莎·梅不得不面对的“烫手山芋”。卡梅伦为脱欧公投担责而引咎辞职,特雷莎·梅则为履行退欧承诺而绞尽脑汁。脱欧虽然仅反映了约半数英国选民的政治意愿,但它却以简单多数的民主形式“绑架”了另一半反对脱欧的英国选民的民意。脱欧只是一个决策,具体怎么脱,达到什么效果和目的则属退欧谈判之道。从这个意义上讲,退欧比脱欧难度大许多,能否实现初衷且在多大程度上谋得英国国家利益最大化,正是特雷莎·梅政府面临的棘手难题。从2017年3月特雷莎·梅政府正式开启退欧谈判之门开始,英国脱欧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英欧间第一阶段谈判持续了一年,三大问题基本有了答案:英国政府同意向欧盟支付退欧“分手费”数百亿欧元,承诺300万在英国的欧盟公民可申请永久居留权,保证北爱尔兰和爱尔兰边界“不会被管控”。作为回报,欧盟在2018年2月同意结束第一阶段谈判,并给予英国退欧21个月过渡期,从2019年3月底至2020年12月结束。如果说第一阶段谈判主要是些原则性大问题,那么即将开启的第二阶段谈判主要涉及英欧自贸协定的框架及关税同盟等实质性问题,仅此而论,英国退欧已经走到关键路口。
退欧:在自相矛盾中渐行渐远
尽管英国退欧已属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但实际上从始至终,英国政府在退欧谈判中都处于进退两难、自相矛盾的困境中。保守党政府虽摆出一副硬脱欧的架势,但不时又流露出“欲走还留”的心态。特雷莎·梅在与欧盟谈判初期,曾态度强硬地声称英国不会向欧盟缴纳分手费,即便硬脱欧也在所不惜。但随着事态的发展和欧盟立场的日趋强硬,特雷莎·梅的态度明显变化,毕竟“胳膊拧不过大腿”。英国同意向欧盟支付390亿英镑的“分手费”,通过与欧盟妥协来达到其目的,确保英国离开关税同盟后还能与欧盟保持零关税的合作关系。
自英国正式开启脱欧法律程序之后,英国政坛反对脱欧的声音就从未间断过,这就给特雷莎·梅政府在退欧谈判中施加了很大的压力,致使英国的谈判主张充满矛盾。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声称,应就英国是否该留在欧盟进行第二次公投。英国前副首相克莱格曾出书谈如何阻止脱欧,强调脱欧采取全民公投的方式本身就是个错误,是用简单的方法来解决高度复杂的问题。他认为脱欧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脱欧派”此前对英国选民的承诺将完全无法兑现。
如果把英国政要的此番言论视为向特雷莎·梅发牢騷,那么英国2017年大选中出现的悬浮议会,以及后来英国工党与保守党“叛逆者”议员联手通过的关键立法(规定英国议会对英国政府与欧盟谈判达成的协议拥有最终表决权)才是掣肘特雷莎·梅退欧谈判的杀手锏。面临内外交困的英国政府不得不在谈判中顾及各方的利益诉求,因而出现克莱格说的自相矛盾的政策及立场表述就不足为奇了。
英国政府在退欧谈判中自相矛盾的主张比比皆是。矛盾一,英国声称退欧后将从欧盟拿回英国边界的司法管控权,但同时又称北爱尔兰与爱尔兰之间的边界不会被管控,这就表明英国与欧盟之间还是没有边界。矛盾二,英国在脱欧白皮书中强调,英国将自己掌控自己的法律,脱离欧洲法院的管辖,但特雷莎·梅又表示,在适当的情况下,英国的法院将继续审查欧洲法院的判决,“英国必须尊重欧洲法院在这方面的职权”。矛盾三,特雷莎·梅声称英国会退出欧洲共同市场,但又希望与欧盟达成“比全球任何一个自由贸易协定都更深更广”的协议,强调英欧之间最终能否达成零关税的自由贸易协定对英国来说意义重大。英国保守党议员苏柏利甚至提出一项贸易法修正案,争取让英国在退欧后还能与欧盟组成关税同盟。
但是,欧盟及其成员国领导人从一开始就给特雷莎·梅当头棒喝,让其不要抱幻想。德国总理默克尔曾警告英国不要对退欧后的待遇“心存幻想”。欧盟官方再三强调:1、英国必须为退出欧盟付出昂贵的代价;2、未来任何贸易规则都必须使得成员国比退出国享有更优厚的待遇;3、不要妄想“只遵守有利于自己的规矩”。欧盟之所以态度强硬,一是惧怕英国脱欧引起欧洲极右翼民粹主义和分离主义泛滥(事实已经起到了类似效果);二是担心英国脱欧在欧盟其他成员国内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三是考虑到英国在欧盟的分量及英国脱欧对欧洲一体化事业的伤害,必须要让英国付出高昂代价。
基于这些考虑,欧盟在与英国谈判中总的来看持强硬态度。欧盟高官指出英国如果离开欧盟关税同盟和单一市场,将面临“不可避免”的贸易壁垒,同意让英国在過渡期内仍留在欧洲单一市场和关税同盟已经是一种“恩惠”,英方不应再讨价还价。当然,欧盟也深知惹怒英国两败俱伤的后果,故作出多给英国21个月过渡期的让步,但强调在过渡期内英国需要接受欧盟法律的管辖,但不能参与欧盟内部决策。
“后脱欧时代”英国的前景不容乐观
从脱欧走到退欧,英国最终真正离开欧盟的日子越来越近。第二阶段的谈判迫在眉睫,自由贸易、经济合作及金融投资等成为英欧博弈的主要内容。英国政府目前强调英欧自贸协定必须涵盖金融服务领域,希望保留对欧盟金融服务市场的准入特权(即金融机构只需在一个欧盟成员国申请经营执照,就可向所有欧盟成员国客户提供服务)。欧盟则表示英国退欧后北爱尔兰应留在欧盟关税同盟内,这个主张符合英国、北爱尔兰及欧盟三方的利益。但具体如何做才能避免北爱尔兰与欧盟之间既无“硬边界”,又体现英国司法的属地管辖权,则是个棘手问题,因为北爱尔兰与英国的大不列颠岛部分可能将会被“贸易边界”隔开。
英国政府希望退欧后能够继续享有与欧盟最大化的自贸权限,甚至留在关税同盟内。如果不能,最起码享有欧盟给予瑞士、挪威那样较大的自贸权限。但欧盟的第二阶段谈判准则草案表明,英欧自贸协定将是一种“标准自贸协定”,条件参照欧盟与加拿大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该协定虽取消大部分服务和货物贸易关税,但在金融机构准入等方面要受欧盟法律监管。
“后脱欧时代”,英国的前景不容乐观,其面临着诸多的不确定性因素乃至负面因素。首先,脱欧乃英国一厢情愿的事,欧盟十分不满,故不会在退欧谈判中给英国好果子吃。从一组数据中就能管窥英国与欧盟之间的相互利害关系:2015年欧盟27国对英国出口额仅占欧盟GDP的2.5%,而英国对欧盟的出口额占英国GDP的7.5%;27国对英国的服务贸易额为940亿英镑,从英国进口的服务贸易额则达1220亿英镑;27国对英国的直接投资存量高达9850亿欧元,占欧盟GDP的8.3%,而英国对欧盟27国的直接投资存量为6830亿欧元,占其GDP的比重高达26.6%。显而易见,英国对欧盟的依赖程度更高,一旦退欧损失不小。
其次,英国退欧在欧洲金融界和工商界已经引发恐慌,“逃离英国”渐成气候。欧盟官方已有动作,把包括欧洲银行管理局总部、欧洲药品管理局在内的大机构撤离至欧洲大陆。同时,不少欧盟企业也开始减少在英国的业务。英国方面公布,自2016年脱欧公投以来,有11%的欧盟企业已将部分人员撤出英国,已有14%的欧盟企业减少了在英国的业务。长此以往,必将严重影响到英国国际金融中心及欧洲资金避风港的地位。
再次,英国退欧后势单力薄,恐怕终究会在全球化的大潮中被边缘化。离开了欧盟大家庭,英国想在欧洲东山再起难度太大。从地缘政治影响力来看,退欧后英国虽获得司法独立管辖权,但必将制约英国与欧盟在警务、安全防务等领域的合作。如果欧盟能够渡过难关继续扩大影响力,势必将进一步打压英国在欧洲的政治存在。从经济及科技影响力来看,退欧后英国的金融业及投资贸易多少都会面临“协定真空”。英国与欧盟有诸多的协定需要重新审定,有些行业协定可能暂时会出现空白,这将影响到双边关系的深化。比如,英国和欧盟在研发及科学领域的未来关系如何维系?英国将来以什么身份参与欧盟第九个研发框架计划(FP9)?
此外,英国政府在退欧过程中还有千头万绪的工作要做,既要说服议会通过“脱欧”法案,还要替换数千份欧盟的旧法律法规;既要对移民、关税及边界管控做出新安排,也要想办法留住欧盟企业界的资金及人才;既要保持英国的主权完整,又要在欧洲大陆有所作为。这些自相矛盾的愿望及做法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是英国政府挥之不去的梦魇。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