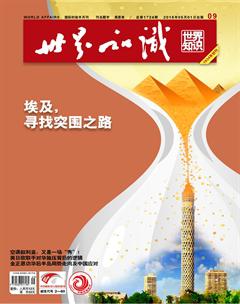俄罗斯与伊朗:战术“联盟”还是战略伙伴?
唐志超
4月14日美英法三国对叙利亚实施“精准打击”后,俄罗斯与伊朗相继发声强烈谴责。俄罗斯与伊朗都是叙利亚问题的重要相关方,两国围绕此问题互动频频。由俄罗斯、伊朗等国主导的阿斯塔纳和谈是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的主要对话平台之一,此外两国还曾是叙利亚几个“冲突降级区”的担保国……

2017年11月1日,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伊朗,与伊朗总统鲁哈尼举行会谈。
近年来,由于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以及伊朗核协议的签署,俄罗斯与伊朗关系快速发展。2017年3月,伊朗总统鲁哈尼访问俄罗斯,俄伊两国在铁路、油气、原子能、旅游等领域达成15份协议。其间,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伊之间的合作十分高效,两国正全力向高质量、新层次的战略伙伴关系迈进。不过,鉴于俄伊关系的现实脆弱性以及历史阴影,外界对俄伊战略伙伴关系的性质大多持怀疑态度。目前,这一关系正在叙利亚战场上经受严格的考验。
五百年的历史碰撞
伊朗是最早的人类文明摇篮之一,相比之下俄罗斯的历史则短暂得多。据历史记载,俄罗斯人与波斯人的交往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不过,俄罗斯与伊朗作为两个国家的正式交往则始于16世纪初期。1521年,伊朗萨法维王朝与莫斯科公国之间进行了首次官方正式接触。从16世纪初到21世纪初,俄伊两国间长达五百年的接触与碰撞,使得今日两国之关系有着丰盈的历史厚度。
从16世纪初到20世纪初的四百年,是伊朗帝国由盛转衰的时期,从萨法维王朝到阿夫沙尔王朝、恺加王朝,这一古老帝国逐步日薄西山,陷入动荡,丢疆失土,而同期俄罗斯人则摆脱了蒙古人控制,积极开疆拓土,大肆发动对外战争并逐步建立帝国。两者一衰一盛,形成强烈的对照。在这四百年间,波斯人遭遇了一系列强大对手:蒙古人、突厥人、奥斯曼帝国、大英帝国和沙俄。虽然为了对付共同敌人奥斯曼帝国,波斯人与俄罗斯人曾多次结盟,但最终伊朗和奥斯曼帝国都不幸地沦为沙俄的主要侵吞对象。在数次俄伊战争后,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沙俄已占领了原先属于伊朗管辖下的大量领土,包括现今的高加索、中亚等地。而且,沙俄也在伊朗疆域之内建立了很高的影响力。1907年,沙俄与英国在一番激烈争夺后签署了瓜分伊朗、阿富汗等地的历史性条约,划分了各自在伊朗的势力范围:北部属于俄国,南部属于英国,中部为缓冲区。事实上,此时的伊朗已沦为英俄的半殖民地。
1921年,哥萨克旅副指挥官礼萨·汗在英国支持下发动军事政变,并最终推翻恺加王朝,建立了巴列维王朝。礼萨·汗执政时期(1925~1941年),他在外交上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摆脱英国和苏联的控制,并转向德国。二战爆发后,保持中立的伊朗与纳粹德国日益接近,引起了同盟国的警惕与忧虑。1941年8月,英苏两国指责伊朗国王勾结德国,分别派军从南北两个方向进入伊朗。礼萨·汗被迫让位于其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并出走海外。二战后,英美军队从伊朗撤离,但苏军没有按协议撤出伊朗北部地区。苏联甚至还扶植伊朗境内库尔德人和阿塞拜疆人建立分离主义政权,这不仅引起了伊朗政府的极大忧虑,也遭到了西方的强烈反对。围绕苏联从伊朗撤军问题,美苏间爆发了战后第一场重大危机——1946年伊朗危机,美国甚至以动用核武器为威胁要求苏联从伊朗撤军。此事件也成为冷战爆发的重要导火索之一。最终,苏联被迫从伊朗撤军,其在伊朗的影响力急剧下降。1953年8月,主张石油国有化的伊朗摩萨台政府被美国中情局策划推翻后,短暂出逃海外的巴列维国王回到伊朗并强化了王权,此后伊朗完全站到了西方一边。1955年伊朗还加入了反苏反共的“巴格达条约组织”。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巴列维政权被推翻,新生的伊斯兰政权执行“既不要东方,也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对外政策,取代了昔日的亲美反苏路线,并一直延续到冷战结束前后。总体上看,伊朗与苏联在冷战时期主要是敌对关系。
苏联解体后,俄伊关系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其实早在1989年1月,伊朗最高领袖霍梅尼就曾致信戈尔巴乔夫,对其改革大加赞扬,表达了与苏联改善关系的愿望。戈尔巴乔夫亲自接见了霍梅尼的信使,并会谈了长达两个小时。冷战结束后,俄罗斯作為苏联的继承国一度在中东事务中充当配角,但不久之后俄罗斯便以大国地位重返中东事务。其中,俄罗斯与伊朗开展了多项务实合作,两国关系不断得到改善。1995年1月,俄罗斯与伊朗签署了向伊朗出售两个轻水核反应堆合同。美国强烈要求俄罗斯取消合同,但俄罗斯断然拒绝。1995年8月,俄罗斯不顾美国的反对,签署了向伊朗核电站提供核燃料的协议。2007年,俄罗斯与伊朗签署出售S-300防空导弹系统的合同。这些合作协议在俄伊关系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象征着俄伊关系发生实质性调整和改善。这一时期,虽然双方在车臣、里海划分等问题上存在一定分歧,同时核电站建设和S-300防空导弹系统的交付受到美国因素的影响而一再延误,但双方在全球和地区事务上有着诸多共同利益,总体上保持了友好合作关系。
日益加强的战略性合作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尤其是叙利亚战争爆发和伊朗核协议达成之后,俄伊关系加速向纵深发展,并日益具有战略伙伴关系的性质。从某种程度上说,当前俄伊关系进入了“蜜月期”,也达到了五百年来的最好阶段。
总的来看,普京所说的俄伊关系正向战略伙伴关系迈进并非虚言。这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双方在应对美国制裁和威胁方面的共同利益日益增大,并相互支持,展开了战略协调与配合。比如,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也门问题、伊朗核协议上坚定支持伊朗的立场。今年2月,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了关于伊朗违规向也门胡塞武装提供武器的决议草案。针对特朗普威胁撕毁伊朗核协议,俄罗斯明确表示反对任何改变这一多边协议的单边行动。第二,近年来,俄伊在军事、情报、反恐、国防工业等领域开展了一系列合作,并签署了诸多重要合作协议。而军事安全合作的广度和深度正是检验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尺度。在叙利亚战场上,俄伊不仅开展了深度的军事安全合作,甚至采取了联合军事行动。2015年,俄伊两国与叙利亚、伊拉克还决定建立反恐联合情报中心。更重要的是,2016年俄罗斯借用伊朗哈马丹空军基地打击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这是伊朗近代以来首次允许外国武装力量使用本国境内军事设施。即便是在伊美关系极其紧密的巴列维王朝时期,伊朗也从来没有同意美国使用其境内的军事基地。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俄伊合作的深度和战略性。此外,俄罗斯还不顾美国和以色列的反对,在延迟近十年后决心履行向伊朗出售S-300防空导弹系统的协议,并于2016年开始交付。第三,俄伊加深了经贸合作,尤其是核能、油气和金融合作。2015年俄罗斯完成并向伊朗交付布什尔核电站。随后,俄伊又签署为伊朗建设更多核电站的新协议。在油气领域,2017年11月俄伊签署了伊朗境内石油天然气战略项目的实施路线图,将共同实施一项投资总额达300亿美元的石油天然气项目。今年3月,俄罗斯扎鲁别日石油公司与伊朗签署了一份价值7.42亿美元的油田开发协议,这不仅是伊朗自2016年初解除制裁之后迎来的第二笔石油外资,也是俄伊两国开展的首笔石油开发交易。除油气开采外,双方还提出将开展技术人才培训、炼油厂现代化改造等合作。第四,俄伊合作不断突破双边范畴,向多边集团化方向发展,加深捆绑。比如,俄罗斯积极推动伊朗加入欧亚经济联盟和上海合作组织。
对于俄伊关系的战略伙伴关系性质,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秘书阿里·沙姆哈尼指出,俄伊关系的战略性特征机制体现在军事安全合作上。双方在军事与安全上的合作关系超越了传统军火买卖关系,已经开始建立国防方面的伙伴关系。俄伊战略伙伴关系不仅涉及两国元首在最高层次的合作,也包括军事领导人之间的合作,比如总参谋长、国防部长等层次的会晤,伊朗国防部长两年内访问了俄罗斯五次。此外,双方还进行了一系列联合军事行动,比如俄罗斯、伊朗、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和黎巴嫩真主党组成的联盟彻底改变了叙利亚战场上的力量对比。
战略伙伴还是战术“联盟”?
不过,外界对俄伊是否是真的战略伙伴有不少质疑。美国《新闻周刊》撰文称,俄伊关系只是“方便的婚姻,而非真正的战略联盟”。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称,俄伊是“战术性联盟,不是战略联盟”。
的确,俄伊关系确实已具有一定的战略性质,但距离真正的战略伙伴关系还有一段距离。归纳起来,原因主要有三个:首先,反美国及西方是驱使俄伊走到一起的主要因素,但这一“反美联盟”有其局限性。俄罗斯虽然在伊朗核协议等问题上支持伊朗,但对伊朗的支持是有限的,在很多情况下俄伊关系还不得不服从于俄美关系。俄罗斯由于美国的因素一再找理由推迟交付布什尔核电站和S-300防空导弹系统就是典型例子。对此,伊朗多次批评俄罗斯。可以说,俄伊双方都不希望将自己紧紧地绑在对方的战车上。其次,两国的军事安全合作是有限度的。国防合作是俄伊关系的重要内容,不过俄罗斯对伊朗提出的购买先进进攻性武器的要求并未予以满足,主要向伊出售防御性武器,并不向其出售最先进的战斗机。第三,俄伊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合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雙方利益和最终目标并不一致。俄罗斯一面与伊朗合作,一面对美国和以色列提出的限制伊朗扩大在叙利亚势力的要求持理解态度,对以色列一再军事打击伊朗在叙力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第四,双方存在信任赤字,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历史因素造成的。虽然双方在政治上一致反对西方,但鉴于“不愉快的历史”,伊朗人对俄罗斯有着根深蒂固的怨恨和怀疑。伊朗商业界也更愿意与西方做生意,而不是俄罗斯。2016年伊朗向俄罗斯开放军事基地一事传出后,伊朗国内一片哗然,其中不乏批评之声。后来伊朗方面就叫停了俄罗斯使用其空军基地。伊朗国防部长达赫甘还在接受伊朗电视台采访时说,俄方将其使用伊朗空军基地一事公之于众,这种举动有“炫耀”意味,“欠考虑”。而在此之前,达赫甘还表示俄罗斯战机想用哈马丹基地多久都可以。
难怪就连俄罗斯前驻伊朗大使马里亚索夫也公开称,当前俄伊关系是战术性的,而非战略性的。俄伊之间的“联盟”主要是针对美国及西方的,还称不上战略伙伴关系。他认为,战略伙伴关系必须建立在具有制度性安排的、强大的贸易与经济联系之上,但俄伊在此方面的联系“并不令人满意”。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东研究室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