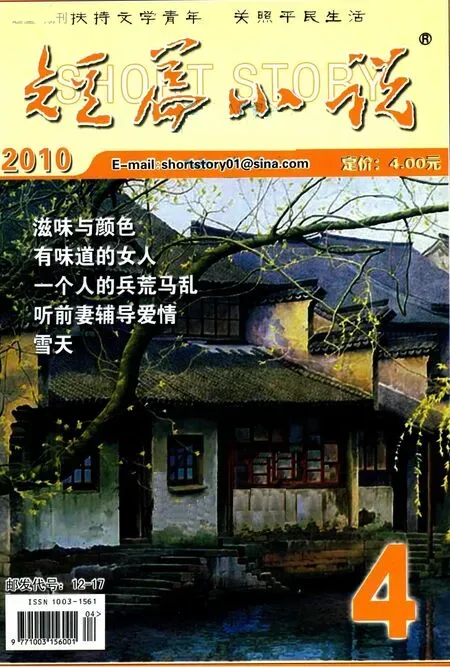红鱼
◎江 岸

1
每年冬季,胡香琴都跑到义阳市,追随表姐刘美兰,在表姐的小澡堂里打工三个月。搓澡不是简单的力气活,而是技术活,但是,没有一把子力气,是吃不了这碗饭的。刘美兰不知用了多少个女搓背工,顾客都不满意。她们给顾客搓背如隔靴搔痒,光在皮肤表层划拉,不除灰,不去死皮,不止痒,不解乏,顾客都纷纷抱怨花了冤枉钱。顾客没感觉,她们自己倒累得娇喘吁吁香汗淋漓,一遍遍用脖子上搭着的毛巾擦虚汗。有一年冬天,香琴到城里来玩,刘美兰正炒了一个女搓背工,缺人手。看见香琴狼犺的身体,刘美兰嘿嘿笑了。香琴高大壮实,像一位重量级的柔道运动员,身大力不亏,天生一副女搓背工的料儿,不干这行还真就屈才了。表姐突兀的笑容把香琴吓着了,她摸摸美兰的脸,问道,姐,你没事儿吧?
香琴经过男搓背工师傅的简单传授,就披挂上阵了。她当然不得要领。她第一次服务就把一个肥胖的老女人搓得杀猪般嚎叫,一身红痕仿佛半扇刚剥了皮的猪肉。
谁知那个胖女人第三天又来了,进门就问美兰,那个小胖妞呢?
美兰不知道她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小心翼翼地问,您找她有事儿吗?
让她一个小时后进来,给老娘搓背。胖女人说着,扬长进了包房。
这是香琴的第一位回头客。有了第一位,就有第二位、第三位……香琴这就算在小澡堂里站稳了脚跟。
香琴跟人出门打工,干什么都干不好,手脚没有人家麻利。没想到歪打正着,干上了搓背工。随着她技术的不断提高,她的知名度也越来越高。现在人们吃得好了,一个个膘肥体壮,不仅男人喜欢搓澡,女人们也当仁不让了。这年头,女老板好找,女领导好找,可像模像样的女搓背工不好找。像香琴这样有力气有技术、又随和又实在的女搓背工,更是凤毛麟角,特别珍稀。可惜的是,美兰的澡堂只有一季的生意。每到冬天,香琴不管远隔百里千里,也不管工资高低,都要主动辞工的,候鸟一样飞回来,飞到小澡堂栖息过冬。在这里,她被人需要。更重要的是,她是表姐的心腹,美兰什么事情都跟她说,她平时也是眼睛睁得大大的,在目力能及的范围内帮美兰盯着,有什么事情,替她扛着。
香琴就有一年没来,那一年,她嫁人了,怀孕了,年底的时候,她挺着大肚子在家养胎。每一次和表姐通电话,美兰就告诉她,有人想念她,不是张姐问她了,就是王姐问她了,都是她铁杆的老顾客。第二年,立秋刚过,她把吃奶的孩子往公婆怀里一丢,出了门,直奔表姐的小澡堂。洗澡的客人还不多,香琴就主动把打扫卫生的活儿揽下来,里里外外清理得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
美兰给她的待遇也不低。搓背工都吃人头费,拿搓背费的提成,顾客越多,拿的就越多。女搓背工就香琴自己一个人,没有人竞争,所有顾客都是她的。另外,美兰还给她一份固定工资,算是她附带打扫卫生的报酬,这可是男搓背工所没有的。香琴每年在表姐这里打一个季度的工,一年的零花也就够了,贴补给娘家一点儿,自己买衣服什么的,都不必向男人伸手了。
屈指算来,香琴在小澡堂工作十多年了,是资深的老员工,也是最不可或缺的人物。她跟表姐干了十多年,她知道,美兰一向低调,和风细雨,不笑不说话,一笑就露出两排细白牙。表姐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和气生财。她这样教育员工,自己更是率先垂范。表姐年轻的时候是美人胚子,现在年龄大了,也肥胖了,却别有一番成熟的滋味。顾客来了,表姐的脸就向日葵一样盛开,对客人绽放,热情似火地搭讪,忙不迭地收押金发钥匙。有时候,香琴在一旁捂嘴偷偷笑,美兰仿佛没看见,客人进了浴室,美兰就瞪她一眼。就这不吓人的一眼,就算香琴见过的美兰最狰狞的一面了。
这天,香琴正在三号包房给一位顾客服务,门被咚咚咚敲响了。第一遍敲门,香琴仍在慢条斯理地替客人拍打后背松筋骨,懒得理。一般她工作的时候,是没有人打扰的。可是,门第二遍被敲响了,敲得肆无忌惮理直气壮,甚至有些气急败坏。她只有放下手中的顾客,拉开了个门缝瞄一眼,外面站着表姐美兰。她慌忙拉开门,与美兰脸对脸站着。
你快点做,完事儿了,来吧台替我。美兰红着眼圈儿,怒气冲冲地说。
怎么了,姐?香琴吃惊地问。她还是第一次见表姐如此失态,如此盛怒,肯定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事儿,打碎了表姐的沉静和温和。
你别问了,快点儿。表姐说着,砰的一声拉上了三号的门。
香琴出来的时候,看见美兰坐在过道拐弯处的一把椅子上。向外,她可以看见吧台,向内,她可以看见所有包房的门。香琴一头雾水,表姐平时都是安静地呆在吧台里,有客人来了就笑吟吟地接待一下,收取押金,分发包房和大厅衣柜钥匙,客人买完单,她笑吟吟站起来送客。她坐在过道里干什么?
美兰见她出来了,呼啦一下站起来,搬起椅子往里面跑,跑到香琴身边的时候,步子没停,只交代了一句话,你去吧台,替我一会儿。香琴没来得及回答,美兰已经一阵风一样刮过去了,她急忙转身,看见美兰一直向里面跑,跑到八号包房门前,把椅子一顿,坐在了门口。
美兰双手掐在腰上,一条腿翘在门把手上,摆出了一个非常凶狠的架势,仿佛要一脚踹破门,冲进去就破口大骂,抬手就开打了。
香琴惊讶地伸了一下舌头,半天缩不回来。她乖乖地跑进吧台,一面接待不时进出的客人,一面侧耳聆听里面的动静。
八号客人是谁,能把表姐气成这样?香琴实在猜不出来。
2
刘美兰年轻的时候,正好是大学生吃香的时候。刚刚改革开放,到处都需要大学生。市里都传疯了,百货大楼有个女售货员读过大学,派到县里当了副县长;市防疫站有个中年女医生更牛气,直接一步登天,到市政府当了副市长。那时候不像现在,当官还靠后台,靠关系,靠钱,靠脸蛋,那时候靠文凭。刘松山做梦都想让刘美兰读大学,读完大学到政府去工作,以后大小弄个官职干干。可美兰不争气,学习成绩不理想,非但没有考上大学,连参加高考的权力都没有。当年,高考之前有预选考试,凡是不够分数线的学生,统统提前两个月毕业离校,和高考说再见。
那时候社会上把没有职业的青年都叫做待业青年。中国人真狡猾,汉字的语义可以被无限扩大或歪曲,那时候把无业青年叫做待业青年,就像现在把失业工人叫做下岗工人,玩的都是同一种文字游戏。说是待业青年,有些人可能一辈子都等不到岗位。他们闲极无聊,就成群结队穿喇叭裤扫街,到文化宫溜冰,到地下会堂跳舞。十八岁的大姑娘,放在街上流浪,迟早会出问题。刘松山急眼了,不管美兰愿意不愿意,把她安排到他服务的小澡堂打扫卫生。
义阳人喜欢泡澡,大一些的单位都有自己的澡堂,完全是福利性质的,职工凭定量发给的澡票洗浴。街上也有几家公共澡堂,供没有单位的老百姓洗浴。刘松山所在的澡堂,就属于市百货公司所有。刘松山年轻的时候,是百货公司的会计,后来年龄大了,就安排他管理小澡堂。他也算动用了手中的芝麻绿豆大的权力,安排自己的闺女做了临时工。他想等自己退休了,让美兰接班,到百货公司去上班。在此之前,也不能把美兰闲坏了,带在自己身边,也能看得住她。
谁知老刘头的如意算盘落了空。
仿佛一夜之间,私人的商店开满了大街小巷,他们态度谦和,价格自由,很快吸引了广大顾客。国营商店岌岌可危,朝不保夕。市百货公司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破产倒闭的,各个柜台都纷纷被人承包了。小澡堂的前途生死未卜,刘松山面临着艰难的抉择。
爸,咱也承包吧。刘美兰说。
承包什么?刘松山慢悠悠地问。
还能承包什么?澡堂啊。
承包这个澡堂,还不饿掉大牙?
事在人为嘛。要不然,咱爷儿俩今后干什么,吃什么?
刘松山前思后想,终于听了闺女的话,把澡堂承包了。也该他们生意好起来。那些单位大大小小的澡堂纷纷关闭了,天上不掉馅饼了。街上的老澡堂大都因城市改造扒掉了,新澡堂都改了堂而皇之的名字,大浪淘沙,水世界,碧水蓝天,功能也改了,不仅仅能洗浴,还能娱乐、运动、按摩、玩小姐。就是洗浴,也分为桑拿浴、土耳其浴;就是搓背,也分为搓盐、搓牛奶。普通老百姓怎么消费得起?这些习惯泡澡的人们纷纷被赶进几个残存的旧式澡堂里。一到冬天,刘松山的小澡堂人满为患。
刘松山承包以后,对澡堂进行了改造。留下一个大厅,保留大池,老年人都有泡大池的习惯。其余的部分,隔成均匀的单间,一共八个包房,每个房间可以安装两个盆池,两个临时休息的床铺。讲究一些的顾客可以到包间洗盆池。原有的工人都被遣散了,平时就剩下他们爷儿俩,开成小旅馆,连洗澡带住宿一起解决,旅客图方便或便宜,还真有不少摸过来住的。每到秋天,澡堂就开业了,只有到了冬天,在家里洗澡冻得不行了,这里才热闹起来。他会请一位锅炉工,一位理发员,两位男搓背工,一位女搓背工。有了这五个人,顶过去二十个人用。女儿刘美兰在吧台收账,他叼着烟卷,躺在大厅一个破旧的躺椅上,和理发师老张头有一搭没一搭地叙话。
刘松山这就算当上了甩手掌柜的。
3
郭卫民盼星星、盼月亮,却盼来了高考落榜的消息。分数出来了,他的分数离分数线仅有三分之遥。更离奇的是,他的政治课成绩只有12分,区区的12分!所有老师和同学都摇头,不肯相信。他的政治课虽然不是强项,但哪回考试也都在70分以上。肯定是评卷的人没写清楚,录分的没看仔细,把72分抄成了12分。如果总成绩加上60分,他一准能上中国一流的大学。
一个老百姓的孩子,谁替你出头呢?认命吧。
当郭卫民满脸沮丧地回到黄泥湾时,他爹一蹦三尺高。你不是说没问题吗?怎么差了三分?八辈祖宗的脸都让你丢尽了。他爹恶狠狠地骂。
其实他们家祖宗的脸没有什么好丢的。这也正是他爹气急败坏的原因。他爹把家族翻身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了。解放前,他爷爷有二亩薄田,土改的时候,他们家的成分被定为富农。后来大队历次的阶级斗争的对象都有他爷爷,他爷爷死了,他爹接过了接力棒,成了黄泥湾新一茬的阶级敌人。要不是英明的领袖邓小平替地主富农摘帽,当兵,考大学,他都没有资格,他一辈子都不可能有翻身的机会。现在好了,可以考大学了,他怎么就那么不争气呢?
郭卫民一怒之下,背起刚刚从高中学校背回的行囊,义无返顾地离开了黄泥湾,走得不知去向。
好几年以后他才知道,那天早晨,也许他前脚刚刚离开黄泥湾,他的高中班主任老师后脚就赶到了他家。学校看他是棵好苗子,不忍心就这么毁了,让他回学校复读,一年的学杂费全免。
他爹激动万分,山前山后呼喊他,除了大山空洞的回音,什么回答都没有。他爹急得跳脚,悔恨得扇自己大耳刮子,扇出了血沫,从嘴角处流出来。邻居都慌了,帮忙寻找,山崖下,歪脖子树下,水塘里,都找遍了,没有他的影子。
改变命运的机会就这样再次和郭卫民擦肩而过。
郭卫民坐汽车到了义阳市,去火车站买车票。排到他了,他递出去十元钱。
到哪里?售票员问。
随便。他说。他还没有想好到哪里去呢。
没有随便这个地方,想好了再来买。下一位,售票员没好气地说。
郭卫民背着行囊,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转悠。他沿火车站对面的新华路一路往西走,走过一座小桥,桥栏上挂着一个纸板,写着几行歪歪扭扭的毛笔字,他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则招聘广告:本澡堂招聘锅炉工一名,应聘者请往前走。“走”字后面一个粗黑的箭头,指引着方向。他按照箭头的指引,下了桥,沿着河走几步,看见一堵破败的砖墙,大门洞开,门楣上写着两个墨迹模糊的大字:澡堂。他探头往门里看看,门边有个躺椅,有个笨熊似的胖老头躺在上面。
请问,是你们这里招人吗?郭卫民壮着胆子问。
胖老头闻声欠起身子,半坐半躺着,眯着眼问,你会烧锅炉吗?
郭卫民迟疑了一下,说,不会,停了停,赶紧又说,不会我可以学。
生瓜蛋子啊,我们这里不要。胖老头说着,又倒回到躺椅上去。
郭卫民还一肚皮火气没地方出呢,这个老胖子如此傲慢,把他惹急眼了。他高声大嗓地嚷,谁一落地都会干活啊?这世界上不是什么事情都有人干吗?你天生就会干活啊?应该也不是吧。你年轻的时候,不是生瓜蛋子吗?
胖老头一听,这是哪儿来的傻小子啊,脾气还不小呢。他有些好笑,又有些好气,费力地站了起来。他的眼前站着一个高大俊美的小伙子,虽然衣着破旧,行囊寒碜,却非常精神,眉宇之间有一股勃然英气。小伙子看他站起来,半是幽怨半是愤恨地盯了他一眼,昂然离去。他心里忽然热了一下。他多么希望有个儿子啊,可他老婆生女儿时大出血,死了,他怕后娘虐待女儿,一直没有续娶,关于儿子的梦想就胎死腹中了。他看见这个漂亮的小子,一股父爱从内心深处油然升腾而起。
臭小子,你给老子站住。他喊出这句话,内心非常受用。这亲切的滋味,多么像骂自家不听话的儿子啊。
郭卫民不服气地停住脚步,扭回头,圆睁双眼,嚷道,怎么,我还怕你不成?
他妈的,你知道好歹吗?老子留下你了,不行吗?
什么,你说的是真的吗?
老子一辈子不说假话。
郭卫民慌忙跑过来,抓紧胖老头的手,鞠了一躬。谢谢你,大叔,他激动地说。
这个胖老头当然就是澡堂老板刘松山。
郭卫民来应聘的时候,已经到了秋天,澡堂快开门营业了。刘松山临时收郭卫民为徒,倾囊相授烧锅炉的技术。到了开业那一天,郭卫民凑合着把锅炉的水烧热了。
4
胡香琴来到澡堂的时候,姨父刘松山已经解甲归田,在家帮助保姆照看外孙了,表姐刘美兰和姐夫郭卫民打理澡堂的生意。澡堂里里外外都装修整齐,外墙贴了白瓷砖,门楣上悬挂一块精致的黑色匾额,上书四个朱红色的行书大字:卫民浴池。这样一来,澡堂倒有了一些雅致的气息了。
顾客和理发师老张,还有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的男搓背工小马、小杨、小朱、小苟、小牛们,都客气而恭敬地把姐夫喊老板,而把表姐喊老板娘。美兰自己没感觉有什么不对,香琴却感觉别扭。
你就心甘情愿地把你和姨父创下的家业交给他了?香琴问美兰。
这有什么啊?两个人一起过日子,什么你的我的?美兰笑笑。
你就对他这样放心,澡堂改姓郭了?
那你说叫什么?叫美兰浴池?那我还不干呢,多别扭。
反正是小白脸,没好心眼,我就对他不放心。
美兰呵呵笑了,对香琴说,那你以后替姐盯紧点,你姐夫胆敢胡作非为,我们就收拾他。
姐,你的事儿,没二话。香琴忙不迭地点头。
香琴心眼再实,时间久了也看出门道了,这个地方的主心骨还是表姐。表姐在吧台负责收银,钱从不过姐夫的手,有时候表姐忙得脱不开身,或者急着上厕所,这个时候顾客来了,她也只喊香琴过来帮忙,而从不喊姐夫。
在吧台里,除了结洗浴、搓背、理发、刮胡子的账以外,还出售其他好几类的商品:诸如毛巾、香皂、洗头膏、牙膏、搓澡巾等洗涤用品,矿泉水、奶茶、雪碧等饮品,还有袜子、裤头、背心、胸罩等小衣物。这个吧台重地,姐夫从来没有擅自进去过,更没有自作主张,收过客人哪怕一分钱。这说明,郭卫民还是让人信得过的,不必要防贼一样防备他。
香琴一点点对姐夫放心了,她感觉表姐的眼光还真不错。这个郭卫民,说起来是个老板,可一直像一个救火队员一样忙来忙去。他的技术无疑是浴池最全面最精湛的,哪里有问题,他就出现在哪里,哪里人手不够,他就第一时间冲上去。他顶多算个二老板,有时就像一个长工,连个工资都没有的长工。当然,他吃的用的穿的,表姐都买好了,不需要他自己操心;每到逢年过节,他家里老父老母都能接到完全能够表达心意的汇款,接到包裹,也都是表姐寄的。他还有什么需要呢?所以他兜里常常一个大子儿都没有,也是正常的了。
这年头,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为了防止他变坏,不让他有钱不就行了吗?再说,他一个大男人,天天脱得只剩一个大裤衩,光着脊梁穿梭在大厅和包房替男人搓背,哪里还有闲工夫学坏呢?在这个弹丸之地,谅他也坏不出什么名堂来。香琴虽然一直看不上郭卫民,美兰却对他很放心。现在连香琴这个傻丫头都对她姐夫放心了,美兰就更没有什么顾虑了。
姐,当年是姐夫追的你,还是你追的他?没事儿的时候,香琴忍不住好奇地问。
美兰不回答,光笑。
香琴是直肠子,想知道什么,必须马上知道,否则茶不思饭不想,六神无主,无精打采。好姐姐,你就说说吧。她摇晃着美兰的肩膀。
美兰被她缠不过,只得说,这你还看不出来吗?
香琴兴奋地问,他追的你,对吗?
什么啊,他当时是一只打工的土鳖,我是什么人啊?老板的掌上明珠。如果不是我主动,他有这个贼心,能有这个贼胆吗?美兰得意地说。
搞半天,是你追的人家啊,真掉价。香琴扑哧笑了。你看我这鬼样子,还是我们家那口子追了我好几年呢。
美兰说,人和人不一样。
我姐夫哪点儿好,你就上赶子追他?就图他高大,白,帅,像画儿一样?
当然,你说的没错,这也是理由。重要的是,他勤快,聪明,能干,学什么会什么,干什么像什么。还有更重要的,他本来应该读大学、做大事情的。他年龄和我一般大,读高中比我晚两年,农村人,启蒙晚。他本来可以读大学的,可能卷子被判错了,才落榜。
这种鬼话你也能相信?
我当然相信。我们课本上的东西,我问他什么,他答什么,没有他不会的。当年我读书时一塌糊涂,很多知识都没有学会,后来问他,他全会。这个能装吗?要不,你装一个给我看看?
香琴朝美兰丢了个白眼,撇了一下嘴。美兰趁她不注意,把一只手伸到她腋窝里,胳肢她。香琴长得胖,痒痒肉多,随便一动就笑不可支。美兰一边挠,一边问,你信不信,你信不信,你信不信?香琴早笑得瘫软了身子,趴到了椅子背上。
5
最近都在传言,这个地方要拆迁。市政府把这一带划为急需改造的棚户区,列为今年城市改造的主要地带。郭卫民是在大厅听一些顾客聊天才得知这个情况的。他经常足不出户,却遍知天下事,就是因为有这个消息集散地。有个老年顾客的儿子就是市政府的干部,他言之凿凿地说,不出一个月,准有行动,还是大动作。这个地方,已经被义阳房地产业头号大亨周建国买去了。
听到这个消息,郭卫民真有些急了。
如果真的拆迁了,没有了澡堂,咱们怎么办?他焦急地问美兰。
美兰笑了笑,说,船到桥头自然直,天塌了有大个子顶着,咱们啊,就是小孩子吃萝卜的办法,吃一截儿剥一截儿。
郭卫民知道,这个地方是后来岳父下了大决心向市百货公司买来的,办理了属于岳父个人的房产证。但是,为了买这个澡堂,家里塌了个天大的窟窿。到现在,还欠着银行的贷款没还上呢。他多想一下子挣下一座金山银山,把这个窟窿填平,但他没有三头六臂。何况,洗浴这个行当压根不是赚快钱的,它需要天长地久稳扎稳打。
那天,他刚从五号包房给客人搓了背出来,迎面碰见两位年轻的女孩,她们互相纠缠在一起,嘻嘻哈哈地往里面走。走过他身边的时候,一个稍微胖些的女孩朝他嫣然一笑。他感觉俩女孩都有些似曾相识,就是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反正人家是顾客,只好回报她一个微笑。俩女孩走过他的身边,他好奇地回头看一眼,恰好那胖女孩也回过头来。
老板,等会儿让搓背的过来。胖女孩说。
我不要那个死胖子,没轻没重的,换个人吧。另一个瘦女孩娇嗲嗲地说。
对不起,我们这里只有一个女搓背工。郭卫民抱歉地说。
那我们就让男的搓。瘦女孩说着,吃吃地笑。
胖女孩挣脱了瘦女孩缠绕的胳膊,在她的背上敲了一下,打开了八号包房的门,闪了进去。瘦女孩不进门,跑到郭卫民身边,压低声音说,真的老板,可以吗?
郭卫民为难地说,俩男搓背工都是童男子,你们愿意,人家好意思吗?
瘦女孩诡秘地一笑,嘲弄地说,老板,你不也给人搓背吗?你又不是童子鸡,应该没问题吧?
郭卫民笑了,说,我不行,我有上级,有人管。吧台那位,看见了吗?我老婆。
瘦女孩不屑地撇撇嘴,说,就搓搓背,你怕什么?
对不起,你们自己搓吧。郭卫民说着,扭转身,准备走开。
瘦女孩张开双臂拦住了他。多给钱,行吗?她的语气变得温和了,仿佛在乞求。
郭卫民迟疑了一下,问道,多少钱?
一人一张“红鱼”,两人两张。瘦女孩的回答挺干脆。
郭卫民整个人僵在了那里,他像被一闷棍夯到了脑袋上。
义阳的市民习惯敬畏而又欢喜地把彤红的百元大钞叫做“红鱼”,在这里呆久了,郭卫民也学会了,亲切地把这个最大面额的中国货币称为“红鱼”。在这个世界上,人人都喜欢“红鱼”,忙来忙去,都是为“红鱼”忙活。普通搓一个背,只收六元钱,一百元,得搓多少个背啊?一般来说,即使是一个虎背熊腰的彪形大汉,完全搓一遍也就十来分钟。两个娇小的女孩,真搓起来还不是三下五去二?也许二十分钟都不要,两张“红鱼”到手。
瘦女孩知道这个老板被糖衣炮弹打中了,格格笑着推了他一把。别忘记了啊,老板。说着,她跑进了包房。
后来的事情,郭卫民仿佛都是在醉酒的状态下进行的,他似乎有些迷糊、麻木、沉醉、晕头涨脑,但是,他的动作依然熟练老到,干脆利落。他竭力不看女孩的脸,不看女孩的身体,只看自己搓背的手。他的手仿佛编入了程序的机器,精准,到位,节制有度,次序井然。前面,后面,上头,下头,方方面面,角角落落,沟沟汊汊。他极力控制着自己,不去想别的,只想那两张遍体通红的“红鱼”。
瘦女孩直率,大胆,当仁不让地躺在搓背的床上,劈手拉掉包裹着胴体的浴巾,暴露无遗。她的大方倒让郭卫民的工作又顺利又快捷。胖女孩却有些拘谨,难为情,动作迟缓,老想掩饰什么,到底又掩饰不住,不免也得彻头彻尾地摊开自己。给胖女孩搓背的时间就有些长了,郭卫民还憋出一头汗来。更要命的是,他不可抑制地冲动了,春光乍泄。他稍稍弯下腰来,企图遮蔽一下外泄的春光,但是他的努力宣告无效,他下面已经撑起了一个高高的帐篷。
瘦女孩正在冲洗,见这边搓完了,光着身子走到郭卫民面前,碰碰他的下面,飞了他一眼说,老板,放松放松吧。
郭卫民顿时觉得浑身所有的血液都往脑袋上冲过来,头大了许多,脸发烫。他结结巴巴地说,赶紧结账,我得走了。
结账?那我们也不跟你结啊,我们洗完了和吧台结。瘦女孩哈哈大笑着说。
别,别,那样不是害死我吗?郭卫民慌乱地说。
那我们也给你服务一下,双方都免单,谁也不欠谁,不是更好吗?瘦女孩依旧哈哈笑。
到底给不给?我该出去了。郭卫民的底气有些不足。
你还别不识好歹,我们平时就在火车站对面的金光宾馆工作,价位还没有低到今天这个份儿上,对你真是太优惠了。你还不领情。瘦女孩不依不饶。
郭卫民感觉透不过气来,他摇摇头,往门口走去,抓住了门把手。只要往左一拧保险扣,轻轻一拉,门就会打开了。
慢!他身后传来一声轻喝。
他缓缓回过头来,看见胖女孩严严实实地裹着浴巾,正在翻动一个手提包。她很快掏出两张大红的“红鱼”,跑过来,塞到他手上。
别介意,她喜欢开玩笑。胖女孩羞涩地笑笑。
郭卫民手里有了两张“红鱼”,如释重负。他快速把钱币团在手心里,捏了起来。他轻轻吁出一口气,稳定一下情绪,咔哒一声拧开了门上的保险扣。
6
刘美兰后来怎么也想不起来自己那天突然要见到郭卫民的原因了。也许是他的鬼鬼祟祟?也许是他的六神无主?反正那天他打五号包房搓完背出来后,有些异样。他如果像往常一样,给客人搓完背以后,眯着眼,叼着烟,哼着小曲,或者在吧台旁边坐一坐,或者到大厅里面去坐一坐,是没有人怀疑他的。尽管他很累,他的神情是悠闲的,是无拘无束的。但是,他那天坐在吧台旁边抽烟,却是一会儿抠抠脚,一会儿挠挠背,仿佛浑身不自在。那时候客人也不多,刘美兰也没有管他,自顾埋头在网上斗地主。她最后放了一个王炸,赢了,高兴得手舞足蹈。网上发牌的间隙,她发现郭卫民不见了。
她走出吧台,站在过道拐弯处,扭头朝两边看看。过道里什么都没有。她不能离开吧台,只好坐回去。网上牌已经发好,有网友抓了底牌,开始发牌。该她出牌了,她懒得出,兀自愣神。网友急眼了,老催她,快点儿吧,我等到花儿都谢了。她关了牌局,算她逃跑了,会扣好多积分的。平时她再急,也要把正打的那把牌打完的,这会儿她管不了那么多了。知夫莫若妻。她觉得今天郭卫民肯定有猫腻,他刚才都没有敢正眼看她。哪个包房有客,有什么客,客人需要什么服务,她比谁都清楚。包房里现有的男客都搓过背了,香琴在一个女客的包房服务,还有两个年轻的女客还没要服务。郭卫民现在没在吧台附近,他应该出现的唯一的地方,就是在大厅。
刘美兰正急眼呢,正好有个顾客掀开大厅厚厚的棉门帘,出来结账。她央求客人说,大哥,帮帮忙,进去喊一声,让郭老板出来一下。
客人热心地进去喊了,瞬间出来了,结账离开了。但是,郭卫民却没有出来。隔了一会儿,理发师老张出来了,他说老板没在外面?里面没有他啊。
刘美兰冷静地说,张师傅,三号、八号是女客,你别管,你到其他几个包房看看,他在不在里面。
老张迅速察看完了,如实说明了情况,两个空包房和五个有男客的包房都没有老板的影子。
你再到厕所里去看看。美兰说。
厕所里也空无一人。老张看过后,跑回来说。
算了,不找他了,张师傅忙你的去吧。美兰可不想在员工面前丢人,装得没事儿人一样。这几个地方都找遍了,都没有郭卫民,而他身上除了一个大裤头,所有衣物都在吧台里面放着呢。在这数九寒天,他不至于光着膀子出门了吧?不用头脑想,用脚趾头随便想一想,美兰都明白他到了什么地方。狗日的,也太无法无天啦!万一碰到派出所检查,发现这种情况,那真是黄泥巴掉进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了,那还能平平安安做生意吗?他口口声声替小澡堂的未来着想,就是这样着想的吗?等张师傅进去了,她动若脱兔,敲响了三号的门,让香琴抓紧过来替她照看吧台。
香琴匆忙服务完顾客,开门出来的时候,就看见美兰坐在了过道拐弯处。香琴去吧台了,美兰就凶巴巴地坐在了八号包房门口,仿佛那个守株待兔的宋国农夫。随着时间一点点流逝,美兰心头的怒火慢慢堆积起来,越积越厚。虽然她相信,他只有色心,没有色胆,他一定是财迷心窍,脑袋被门挤了,被驴踢了,才如此不顾廉耻不顾后果的,但是,只要想一想,他居然仅穿着裤头面对两个光着的年轻女人,她的身体就抑制不住地颤栗,心口就隐隐约约地作疼。她真想变作河东吼狮,一脚踢破八号包房的门,旋风般冲进去,揪住就打,不顾头不顾腚地打,朝死里打,打他个鼻青脸肿皮开肉绽,打他个死去活来灵魂出壳,打他个一佛出世二佛升天,但是,她忍住了。她不想把战火烧到包房里面,无论如何,里面两个小妖精是她的客人,是她的衣食父母,她做了十多年生意,这点基本常识她还是有的。她只能管教自己的男人,放这两个小骚蹄子一马。
郭卫民手心里团着两张“红鱼”,心花怒放地走出八号包房的时候,眼珠子一下子瞪得比牛蛋都大。他傻了一样站在门口。他最不希望出现的人出现在了她最不应该出现的地方。刘美兰手疾眼快,从他身后带上了包房的门,然后,劈手扇了郭卫民两个大嘴巴,恶狠狠地说,晚上没人了再收拾你!他一动不动,手臂伸得老长,手心摊开,两张“红鱼”怕冷似的紧紧抱在一起,卧在他宽大的手心里。纵然是傻子,也看得出来,那是多么美好的东西。美兰的两个指尖仿佛鱼鹰的长喙,叼起那团“红鱼”,衔着。
香琴听见两声啪啪的脆响,刚来得及把硕大的脑袋瓜子从拐弯处探出来,却什么西洋景也没有看到,只看见表姐意气风发地跟在呆若木鸡的姐夫后面,仿佛女警官押解着一个落网的犯人,凯旋而归。
美兰朝香琴扔过去一团东西,空中迅捷地划出一道红色的弧线,仿佛雨后彩虹,转瞬即逝。香琴没有接住,落在了她脚边。她弯腰捡起来,掰开纸团,两张完整的“红鱼”。她困惑地看着表姐。
美兰轻轻地说,如果你不嫌脏,这两张“红鱼”归你了。
脏?香琴嘀咕一声,钱有什么好脏的?她看看表姐,又看看姐夫,有些明白,又有些不明白,但她明白了最重要的一点,这两张表姐嫌脏的“红鱼”,真的是自己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