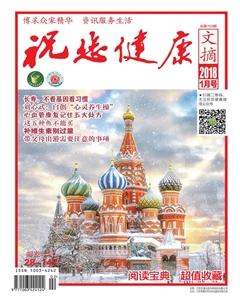在患癌的日子里
2010年5月20日,是我和先生结婚20年的纪念日。当年结婚结得潦草,我们原本盼着这个日子去补婚纱照,再补个只属于两个人的小仪式,可是世事难料,我们期盼的这个大日子,却是在病房度过的。转天上午,我就要做手术,作别乳腺上的“不速之客”——肿瘤君。
我至今也不太确定究竟是什么支撑着我那般平静而淡然地接受了肿瘤君的不期而至,好像并不突然,没有特别的惊异,更无自艾自怜。较之我生命过往遭遇的那些大沟小坎,我不觉得它有什么特别的,“尽人事听天命”,是我30岁后对待世事无常一以贯之的人生态度。
我唯一要做的,只有听医生的话,他们比我更熟悉肿瘤君的脾气秉性。不可否认,我是个“科学主义”者,我把自己交给医生的同时,把肿瘤君交给了当代医学。
先生面对肿瘤君,却是如临大敌,他甚至被吓哭,乱了阵脚,倒是我来安慰他,好像遭侵犯的不是我而是他似的。
术后留院期间,先生执意独自护理我,我们没有惊动任何亲戚朋友,也没请护工,他好像要把20年来我予他的所有照料一股脑地还给我,我欣然接受,内心无比幸福。一种满足感进一步冲淡了肿瘤君的威胁,我开始在脑海中冷静地整理自己的生命过往。
住院的7天,我作了两个重大决定:一是决定让儿子赴英留学;二是决定将我积累了20年的书稿整理付梓。
当时儿子正值中考,我们正于留学不留学间踌躇不决,面对肿瘤君的恐吓,我强烈地渴望儿子的内心要足够强大,要强大到足以支撑失去母亲陪伴的人生。
而我自己此生如果还有什么憾事,那就是太在乎小家的角色,从未在意自己事业的得失。
出院那日,我对先生说,你下周一就回去上班,我不希望你因为我生病改变生活轨迹,那样我会有压力。此外,我还请他帮我婉拒了所有亲朋的探视。我几乎断了一切外界联系,遵医嘱化疗放疗,按部就班。治疗之余,读书写作整理书稿。九月送走儿子,日子更显清静而简单了。
过往的7年,我如愿出版图书,逐步开启自己的事业。我竟对肿瘤君多了那么一丝的感激之情。因为它让我不再寄一切于明天和別处,教我珍视当下,活在此刻。
(雪松/文,摘自《健康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