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工登台
洪蔚琳
朱朱在深圳打工20年,但她现在同时是一名演员。在戏剧舞台上,她将自己真实的经历演了出来:辍学、流产、无休止的体力活。与她同台的女工们自导自演,在舞台是重现了自己的人生。
性别议题在她们的故事中反复出现。女工们曾因性别失去教育的机会,在婚姻中遭受暴力,在试图改变境况的时候为家庭责任所困。困境横亘在那里,但戏剧艺术让他们获得了表达的可能。说出这些问题,就是新的一步。
从流产手术台上下来,朱朱全身都在痛。她瘫倒在出租屋的床上,盯着天花板。小腹依然在痛,房间空无一人,天花板上一片空白。
钥匙转锁发出声响,下班的丈夫推门而入。
“做饭了吗?”他脱鞋、换衣裳,瞥一眼厨房。
“没呢。”
丈夫的语调又抬高几度:怎么衣服也没洗啊?
她说医生嘱咐不能碰冷水。
“要我洗啊,那我娶老婆回来干吗?”
朱朱从床上爬起来:“你不知道我刚做完流产手术回来,我不舒服吗?”
丈夫笑了:“不就流个产吗?又不是生小孩,怎么这么娇气啊。”
他穿上鞋,开门出去吃饭。“你一个人饿死算了。”
门“砰”地关上了。
两个女人在台上演了这场戏,剧本来自朱朱的真实经历。扮演丈夫的演员叫丁丽,是组织戏剧的公益机构的创始人。
上面这场对话演完,其他演员纷纷上前,一边往“妻子”和“丈夫”身上贴各色贴纸,一边念出纸上的句子:她是你老婆,不是你家保姆/要爱护好自己身体/男人也可以做家务/要尊重女性,男人也可以共同承担。
朱朱今年32岁,做过18年女工。头7年在流水线上,之后她做过酒店服务员、营业员、保险销售、幼儿园生活老师。丁丽16岁来深圳打工,后转做公益,2015年11月创办深圳唯一为女工服务的草根公益机构“绿色蔷薇”。她与朱朱相识十余年,去年9月邀请朱朱加入机构做社工。机构开办戏剧工作坊,丁丽组织七八个女工,自编自导自演戏剧《她们说》,让每个女工出演自己的真实故事。
一块红布
上海草台班的吴加闵担任戏剧指导,他和女工们共同构思,用一块红布穿起整部戏剧。演遗弃女婴时,红布被卷成一个襁褓;母亲逼婚的剧情里,演员被裹在红布里抬走,它成为束缚的象征。
工厂场景中,红布在舞台上摊开,铺成一条流水线。朱朱站到前面,讲述打工生涯:她13岁来深圳打工,进过磁带厂、玩具厂、塑胶厂、印刷厂、电子厂。她背过身,双手在红布上做出转磁带的动作,红布另一头的演员 演她的上司:“你,不要睡死了!”她转向观众笑笑:“真的好凶哦。”
“16岁,我在一家玩具厂做喷漆和装配。”演领导的演员又发话了:“提拔你做物料员吧,工资高还轻松呢。”朱朱喊:“我不干!”她嗓门大,声音劈裂。去年声带出了问题,她嫌50块一盒的药太贵,没有坚持吃,也没再去医院,至今没治好。
我问朱朱,说“我不干”是什么意思?升职你怎么还不干?朱朱哈哈笑几声:“因为我根本不想打工啊,我是被迫辍学的,我只想回去上学。”
朱朱小学五年级辍学,家里把上学的机会留给弟弟。来深圳一年后,她给家里打电话,要求用自己赚的钱回家上学,被拒绝了。她去上夜校,免费试听两晚电脑课,但她看不懂26个英文字母,跟不上,只好放弃。
流水线7年,她始终在做廉价劳动。21岁那年,她离开工厂去酒店,想通过接触不同的人改变命运,但她只认识了后来的丈夫。当儿子要上幼儿园,她又跑去幼儿园做生活老师,直到儿子毕业。
去年9月,她去“绿色蔷薇”活动室玩儿,被丁丽劝来加入。当时,丁丽的第一个搭档刚走,人手紧缺。朱朱没有更好的选择,觉得做社工至少比廉价劳动地位高、有价值。
朱朱和丁丽十几年前就认识,那时她们在同一家公益机构做义工。朱朱在康乐小组,负责搜索深圳什么地方好玩,组织踏青。而丁丽在文学小组,同时参与工人权益保护。
丁丽只在流水线上待过四年,18岁的时候,她进入公益机构工作,帮助工人保障权益。白天,义工们骑车到工业区普及劳动法,去医院了解工伤。有时晚上回到宿舍,十来个人在大阳台上打通铺,男男女女躺成一排,“聊的都是我们工人工作的理想。”夏天的夜里,凉风吹进阳台,困的人睡了,没困的人还在聊,地上满是啤酒瓶和卤味罐。
演员饭饭记得十年前,第一次在公益机构见到丁丽,她话不多,很腼腆,脸上有甘肃女孩特有的两片红。十年过去了,当我在活动室见到丁丽,她皮肤白皙,身材修长,穿着轻薄的绸裙,说话语速很快,声音清脆,耳坠随着讲话轻轻地晃。
采访中,她频繁和我谈权利:“你采访我,问题都是你决定的。我是跟着你的思路走,我没法说出我想表达的东西。”
她质疑媒体报道和文艺作品,把底层苦难放大成热点,在中产的圈子里传播,“是不是在消费工人?”
我问她,这些理念和想法从何而来。她说从书上,有些也来自她对打工经历的思考。她家的书架上,《美丽的权利》、《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一类的书摆了两排。她说,很早进入公益圈让她接触到大量资源,才有机会快速成长。“如果机会给了别人,她们也一样能做得很好。”
在戏台上,丁丽站在红布后面等待出场。她露出半个头,从布后面绕出来,弯腰做出拾掇麦子的动作。这是14岁的一天,她正在麦场上劳作,妈妈突然告诉她,家里不能供她念书了。
丁丽把红布卷成包裹,当作书包抱在怀里,她在台上自白:“每每看到穿着校服的同学,我心里有很多渴望和无奈。但我也只能回宿舍,默默写起了日记。”
辍学后,丁丽在打工的厂里發现了一个图书馆,晚上借着宿舍走廊的灯,通宵看书。她那时看《简·爱》,记住了里面的一句话:“我贫穷,卑微,不美丽,但当我们的灵魂穿过坟墓来到上帝面前时,我们都是平等的。”
围城内外
第一次上台时,朱朱不知道自己的眼睛该往哪儿看。社区的小会议厅里坐着近100位观众,她说着台词,眼神一会儿放在墙角,一会儿放在观众的头顶以上,最后定在没人坐的最后一排。
她演流产手术后争吵的戏,“心里没底”,担心“观众会不会鄙视我?”她曾对女工友讲起,对方用怪异的眼神看着她:“你这女人怎么这样?不都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嘛。”但当表演结束,掌声淹没了会议厅。女观众上台,因想起自己的相似经历而失声落泪;男观众上来冷静反思:“有老婆呢,才有这个家。爱老婆就等于爱这个家。”
朱朱最喜欢这个环节。“是压抑后的释放,释放了心里轻松很多。”
8年前,朱朱在产下第一胎六个月后再次怀孕。她不想生,怀胎三个月时去做流产手术。术后她常常腰痛,做体力活非常吃力。妇科病长期困扰着她,去年要做两个妇科手术,但她交不起住院费,手术最终没做成。
她21岁在酒店做客房服务员,认识了负责酒店物业的男同事,开始恋爱。朱朱说,家里催着结婚,长辈们让她找个有技术的男人。男同事会做招牌和电工,比工厂里的男性能养家。但婚前,对方因为她不买早点给了她一耳光。计划分手时,她发现怀了对方的孩子。
“总有一天给你打回来!”朱朱告诉我,她选择结婚,但从此和丈夫一有争执就动手。为了离婚,她和丈夫闹到法院。没离成,朱朱改变了策略:丈夫回江西老家,她一个人留在深圳,和离婚感觉差不多。
我向朱朱索要她丈夫的联系方式,被她拒绝了。“他不会理你,还会怨我。”她说丈夫从不愿接触她的工作和朋友圈。一次她把“绿色蔷薇”的微信推文发到婆家群里,丈夫问她:“你瞎发什么?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说起“单身生活”,她开心地在床上蹦:“她们都羡慕我,说你怎么活得这么潇洒呀!我就告诉她们,有什么想不开的?想开了就什么都好了!”
13岁来深圳,她看着其他女孩为赚快钱站街,染了一身病。夏夜里,工厂附近的草地上总有男女抱着翻滚。一切都让她把性和肮脏联系起来。“我不想糟蹋自己的身体。”
22岁,她和现在的丈夫发生关系后,认为这辈子不能再和其他男人做同样的事。“如果有的选,我不想结婚,不想谈恋爱,也不想发生那种事。”
流产落下妇科病后,她去医院看。医生问她有没有性生活,她羞于承认,但从此又把性和妇科病联系起来。
“没谈恋爱,没发生性关系之前,我身体都很好。”采访中,她向我说起现在没什么性生活,表现得如释重负,似乎没有是种解脱。
她声称自己从不想恋爱,却时常羡慕早恋的中学生。她读过琼瑶,追《流星花园》,《大鱼海棠》她也很喜欢,觉得男孩女孩跨越两个世界的爱隋太感人。我问她,你就是喜欢这种爱情故事啊?她脸红着低头笑。过一会儿又对我说,那都不是真的。
流产后的争吵戏演完了,朱朱退场,留下丁丽继续演自己生子的片段。她上前一步,站到舞台中心:“当小孩从我身体里出来,我觉得女人的身体太神奇了!”后面的一排演员张开双臂,跟着她重复:“太神奇了!”丁丽说:“她有手!”演员们纷纷挥着双手;“她有脚!”大家晃晃自己的脚。“她有眼睛!”大家指指自己的眼睛。
“可是神奇过后,她对我身体的限制也越来越多。”丁丽顿了顿:“我要上班。”一个演员扑上来,把她的肩膀压歪了;“我要做家务。”另一个把她的腰压塌了;“小孩生病了,我要带她去医院。”第三个压得她蹲下来;“小孩上学,要我上环。”最后一个把她扑倒在地板上。
几秒后,演员们一个个站起来,丁丽最后也站了起来。采访中,我向她问起这个情节。“这是表达我们共同的愿望,”丁丽说,“想从束缚中挣脱。”
丁丽对性的最初认知来自电线杆上的处女膜修复广告,上面教育她们保持贞操,婚后初夜必须见红,但她很快通过公益讲座了解到了正确的性知识。有一天淋浴,温热的水流滑过,她突然察觉到身体某种异样的感受。她很惊喜,开始探索身体,发现女性也可以取悦自己。她把性看作婚姻中重要的部分,一定要婚前测试是否合拍。
两年前,她注册“绿色蔷薇”,没和丈夫商量,之后为机构投入大量时间精力。丈夫既不满她为工作奔忙,也不理解她倡导的女权思想。婚后,丁丽同时负担工作和家务,丈夫很少帮忙,她觉得不公平,要求丈夫为她的家务劳动付费,洗一次碗至少20块,丈夫觉得匪夷所思。一次丈夫冲孩子发火,她担心丈夫打孩子,直接报警了,丈夫因为这事一个月没和她说话。初次采访一小时后,她就告诉我,由于价值观不合,她和丈夫离婚了。
土耳其家园
在戏剧结尾,演员们在台上拉起手,边跳边唱《我想》,第—句是“我想有个家”。
歌由她們集体创作,灵感来自一个女工的一组照片:她刚来深圳时,第一次去的每个地方,包括大海、莲花山……深圳给了她很多第一次,给了她憧憬,她想扎根在这里。观众被拉上台加入舞蹈,整个剧场回荡着“我想有个家”的大合唱。
丁丽回忆起自己的青春期,10年前,在公益机构下了班,她和同事们跑去横岗大厦唱歌,在一个投币KTV,一块钱唱一首。大家唱到深夜,出门走在横岗最繁华的大街上。她们穿过成片商品房,一个人突然喊了一句:“是我们劳动者创造了美好的大厦!”大家亢奋起来。另一个人对着高楼一指:“看我们劳动者勤劳的双手!”有人起了个调,大家开始边走边唱《国际歌》。唱完又唱《美丽的朝霞》,唱到“在这林立的高楼大厦,哪里是我的家”,眼前刚好又是一座高楼大厦,她们激动地在路上乱跑。
深圳给了朱朱一个在疯玩中度过的青春期。她跳出了同乡打工者的圈子,和“比较开放”的四川、湖南姑娘去歌厅蹦迪,去冰场学溜冰,一次摔得连班都上不了。一个call机99块,其他打工女孩舍不得买。朱朱每月攒几十块,两个月就去买了一台。有call机以后,她玩得更疯了,因为她随时能用call机找到玩伴。
“我在深圳比在老家还久,整个青春给了深圳。”我跟着朱朱坐车回老家时,她突然感慨:“现在年纪大了,没准儿哪天深圳一脚把我蹬走。”
流水线上的工作不招收30岁以上的女工,朱朱32岁了,觉得自己老了。她考虑过回老家生活,但回家路上,她一直嘟嘟囔囔:“还回家吗,要不别回家了。”
我让她给家里打个电话,告诉他们带我一起回家。
“不用打,没人管。”
我再三要求,她终于翻开手机通讯录。“哎,我怎么都没有我妈电活啊。”
朱朱的妈妈生了五个女儿,第六年生了儿子。家里父母各一个房间,弟弟一个房间,五姐妹共用一个房间。嫁出去的女儿哪个回来了,就临时住在这间小屋里。
屋里堆满全家的杂物,四处是灰。朱朱把床上的杂物搬下来,掀开席子,一只蟑螂仓皇逃窜。天气又闷又热,朱朱坐着扇蒲扇。家里只有父亲和弟弟的房间装了空调。爸爸早出晚归,兩天里,我只看到他的一个背影。
朱朱是家里第二个女孩,3岁还不会走路、说话,经常发烧,吃什么都吐,连累家里更穷更难。朱朱说,妈妈总冲她抱怨:我也不想过这么穷的生活,我也不想要这么穷的家庭。可你知不知道,生不出儿子,全村人都不给我好脸!当初真想把你丢了。要是把你送人了,我就不会是今天这副穷样子。
朱朱听了立刻反驳:那你为什么不把我丢了?你把我丢了,说不定我还能赶上个好人家。我就能上学了,也不用被你逼婚了,我就不是今天这副德行了!
房子正对着小卖部,门口一张麻将桌,一群男人围着桌子闲聊、打麻将,嘈杂声持续到凌晨三四点。
“我每次回来,只听到男人的声音,听不到女人的声音,女人都在下地干活。”我和朱朱躺在床上,朱朱热得睡不着,床板硌得她难受。她坐起来盯着天花板,屋子里除了杂物和床,只有高高的天花板和空墙壁。“你看,生活就是这么无聊。”
天还没亮,鸡鸣就此起彼伏。客厅的摆钟响过8下,朱朱骑上电动车,在晨雾中出发了。她带我穿过老家城区,一路给我指两边的房子。“这栋是我表哥的房。”骑出几百米又指着另一栋:“这是我姐的。”半小时车程,她指出了全家所有人买的房。她至今住在深圳城中村的出租屋里,月租600块。“只有我没房。”
2002年,深圳房子均价几百块。那时她16岁,看中一套5万块的小房子。她和家里商量,每年将近一万的工资,能不能不寄回家了?存下来就能买套房。家里拒绝了她,问她是不是太自私了。
现在她没家可回,觉得自己没有归宿。为参加公益活动,她去过北京、厦门,但她不喜欢这些城市,“那都不是给我这种平民百姓的。”
在幼儿园做生活老师时,她听一个家长说起去土耳其旅游的经历。听上去,土耳其很穷、很破,怎么努力都好不起来。“就像我一样。”她不知道土耳其在哪儿,只查了那里的经济状况。网上讲得不清楚,她办了护照,想去旅游看看。
我问她,中国也有穷的地方,为什么非要跑去土耳其?
“我想不出中国哪里穷。中国现在经济发展多快呀,哪里也不会比土耳其更穷。”她说土耳其应该是个原始世界,不像有钱人的世界,天天勾心斗角。“我觉得好累,我想看看土耳其是不是不用这样。”
她向我讲起老家总有人争土地,工厂里总有人为升职互相举报。她说自己思想简单,搞不定这些,只有土耳其这种原始社会适合她。但土耳其签证要求存款五万,她拿不出来,最终没有去成。
学不会的函数
朱朱是“绿色蔷薇”里除丁丽外唯一的正职人员。丁丽很忙,手指在键盘上飞舞,不时打电话对外联络。朱朱常常蹲在地上哄孩子,出门取文件,和城中村的街坊联络感情。总有人路过活动室,隔着很远就喊朱朱的名字,让她帮个小忙,比如复印文件。
丁丽现在代表新锐女性和伊能静同台做ted演讲,去北京和崔永元合作主持《打工春晚》,独力撑起一家公益机构,靠自己的事业在深圳安身立命。
但朱朱在“绿色蔷薇”工作一年了,觉得自己没有成长。她参观其他机构,发现新人都能独当一面,只有她停滞不前。她自称“没有职业操守,脑子里没这方面智慧”。她将“职业操守”解释为女性主义之类的理论框架。她用一种办公软件写东西,始终不太明白怎么用。做完文件保存了,第二天又找不到了。周末要办活动,她两天前才想起:还没外联通知大家。
朱朱意识到自己需要改变。去年,她在老家广西贵港的广播电视大学报了一个大专,学工商管理。作为成人教育的一种形式,电大以网络远程教育为主,周末开设函授课。她期待学到本领,毕业做文秘。
我和她一起去听了次课。从深圳到贵港,要坐4小时动车,中途在广州转车。她说回贵港学习比在深圳便宜3000块,可以分期付款,每月只须从3000块工资里拿出250块。
40多人的教室里,除了三四个男生,其余都是女性,从20到40多岁不等。一些妈妈带着孩子来上课,小孩在教室里四处乱跑,老师的讲话总被打断。
这是一节经济数学基础课,讲授函数和微积分,但老师一直在教大家把答案对应填入网上的作业提交系统。姑娘们盯着电脑屏幕抄答案,朱朱突然举手:我想知道那个函数到底怎么算出来的。
老师看了她一眼:“哦,这很复杂,这里面的问题太多了。”
另一个姑娘举手:“老师,你能不能真的教会一个人给我们看看。”
全班大笑。老师叹口气:“难道这里有人能学会吗?”教室里一阵沉默。
下了课,朱朱跑去加老师微信,以备请教实际工作中的数学问题。
老师年近40岁,扎着马尾,表情严肃。她瞥了朱朱一眼:“那我也未必知道。我们这个课,就是教你一个数学思维。”
“我知道是这个思维,但那个实际问题我也要会解决啊,像求导啊解析啊这些。”
“你打算用多长时间学函数?你知道我学了多久吗?”老师抬高声调:“我大学学了4年啊!学函数要有始有终,你这种学不会的。”
朱朱走出教室,跺了下脚,冲着楼道喊:“哼!我怎么就不能有始有终了?”
我问她,做文秘需要懂函数吗?
“可是既然学了,把它学会了不好吗!”
她反复向我强调,函数是她的爱好。她常在出租屋的阳台上写数学练习册。她学《西方经济学》也非常认真,教材上用不同颜色的荧光笔画满重点。课堂上,老师讲到“消费者均衡”这一节,书上写着均衡条件公式:
Px·Qx+Py·Qy=M
Mux/Px=MUy=Mum
她突然忘了P、Q、M和x、y分别代表什么,翻到前几页去找,看懂了就兴冲冲地给我讲一遍。
下午的课程包括管理学课和公共关系课,但因为发错教材和突然断网,都没上成。4点,无课可上的朱朱提前回家。她在路上感叹:“我总结自己的一生,就是学习的一生。”
“其实是因为没文化,什么都要从头学,没办法专门积累哪个方面。”她说,“这些年我就是在晃。”
她在戏里也说了这句话:“我一直都在瞎晃。”吴加闵说,这说明朱朱对过去的经历有判断,她不是傻呵呵地就这么过去了,她觉得一切都没意义。
眼下,朱朱很快又打起精神,期待明年3月的毕业证。
走到校门口,她笔直站好,表情严肃,让我退后一点儿,给她和破落的学校合张影。
谢幕之后
演出告一段落,一个上午,我和丁丽、曹昂凑在朱朱家。曹昂是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的博士后,关注性别议题,为课题长期跟踪机构活动。初见时她告诉我,戏剧的目的在于把个人经验上升为社会议题,但朱朱纠结于个人琐事,很难从社会角度看待两性不平等。她对婚姻不满,却把问题归于“没嫁好”,内心还是想有个男人可依靠。
在朱朱家,我问曹昂:现在戏是演完了,但女性在现实中能怎么挣脱?她们的生活,不就是困在个人琐事里吗?
“她一个人的力量肯定不行,要有更多机构支持她们。”曹昂站起来,在狭小的空间里来回走动:“信息上的,传播性知识和劳动法;情感上的,大家分享自己的经历,鼓励彼此要自立;物质上的,做社工至少比廉价劳动收入高吧。”
“个人意志也很重要。”丁丽说,“就算现实改变不了,至少我内心解放了,不是为别人活着了。”她骄傲地举例:她如果哪天累了不做家务,不会觉得是罪过。
三个人围着小桌激烈讨论,从女性主义理论谈到相关文献,仿佛在逼仄的出租屋里开学术研讨大会。朱朱把炒好的空心菜端上来,拎个板凳坐到阳台上,一言不发。
第一次见丁丽时,我们谈戏剧对女工的意义。“戏剧是—种自主发声的工具,发声是—种建构历史的方式。”她说,戏剧还可以让理念内化《她们说》讲述性别议题,演员们能从中认识到性别不平等的普遍性,爭取自我解放。
我问她,女工们能理解这些东西吗?
“不理解也没关系,至少她们觉得自己的故事有价值,自己这个人也有价值。”她举例:研究生、博士生来机构做调研,从前她们对学生是仰视,觉得文化人比自己高一等,现在能随口让学生帮她们带孩子。
“这不就是改变吗?”
那天,朱朱始终显得沉闷。下午,丁丽和曹昂告辞,朱朱接一个老乡来家里,我们又聊起朱朱的婚姻困局,老乡笑她看不惯老家男人大男子主义,找个外省的,结果也一样。
朱朱说:“能找个靠谱男人就好了。找到了就一起留深圳,或者我带他回老家。”
我鼓励她:再找要找个尊重女性的。
朱朱和老乡冲我苦笑:你觉得我们这个阶层,能找到这种男人吗?
朱朱说,她曾经很为自己打离婚官司而骄傲。“我是接触过公益的人了,我有维权意识了,至少要离婚带走儿子。”但她最终又放弃了,认为自己不可能离婚。她没房没存款没保险,离了没处养老;儿子跟着她,在深圳没法上学。
我走进朱朱的卧室,床上放着很多毛绒玩具:两只兔子、一只熊、一只猫和一只熊猫。她说一个人睡感觉床太空,放上它们会好得多。有时她在床上练习弹尤克里里,“它们都能当我的观众。”
床头墙上有一大片密密麻麻的心形贴纸,是她手写的短句子:我生病没有人照顾,高兴没有人分享/被雨洗后的春天,你知道我在想你吗?被风吹过的夏天,你知道我的爱吗?/我不是傻子,你不会爱我的。
边缘处的贴纸是英文的:I must leaveVOU.Forever now.Love cannot live withmistrust.我问她这条英文什么意思,她让我把贴纸翻过来,背面是对应的中文:我现在必须永远离开你了。没有信任是不会有爱的。她先想到这句中文,又去网上查了英文翻译,把英文那面冲外贴着。“因为不想让别人知道。”
墙上还贴着她儿子的大幅照片,旁边写着:依然想念儿子,宝贝,妈妈想你啦!她画了一个微信里嘟嘴亲亲的表情。儿子今年8岁,因为没有深圳户口,去年回老家上小学。此前的8年,朱朱一直把孩子带在身边,现在她每两个月跑一趟江西看孩子。在城中村的图书馆,她恳请馆长送她几本书:《论语》《孟子》和《庄子》,她要拿回去教育儿子。她曾告诉我,儿子的成长是她现在最看重的事。“不能再让他像我—样,晃了20年一事无成。”
她从不承认自己需要情感陪伴,但她在鼓浪屿只买了一样纪念品,是三个木头做的猫咪挂链,上面分别刻着她名字的三个字:朱、丽、琴。她发朋友圈晒挂链,配文“最美好的礼物”。有个朋友留言索要,朱朱回复:我特意买了三个,就想我、老公、小孩各一个,这是我送他们的礼物。
她一个人住,出租屋门口贴着自己写的春节对联。上联:张灯结彩迎新春;下联:欢天喜地度佳节。横批:家庭幸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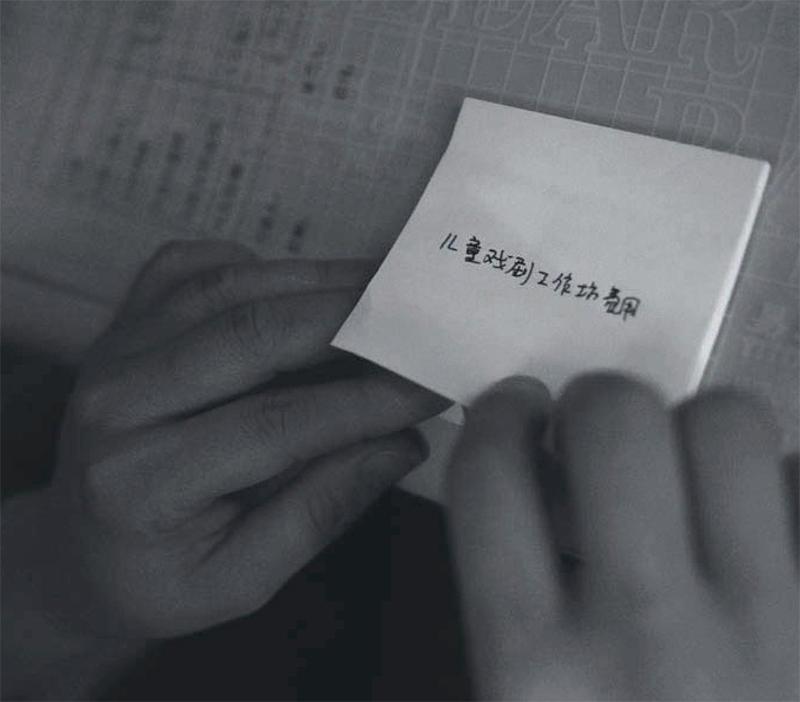

告别
见到朱朱的最后—天,我们去找戏剧的音乐指导黄小娜,路上经过朱朱打过工的厂子。工厂已倒闭多年,工人宿舍变成了派出所。旁边是她和丁丽十年前一起做过义工的公益机构,办公室变成了洗车厂。
黄小娜和丈夫董军同在重D音乐队,帮助女工做戏剧。我问他们作为观众的感想,董军说,他想到自己的伯母,一辈子没走出过村子,在厨房里打转儿。“我觉得好悲哀。”
“我不认同董军说的悲哀。”黄小娜带我走进里屋,把门关好:“女性做一辈子家务没价值吗?只有外面的世界精彩吗?康德一辈子都没走出过小镇,可人家写出了自己的哲学。”
关于这场争论,我后来去问朱朱的看法,她说她既向往外面的世界,也想顾好家,但她觉得自己哪样都没做到。
那天在小娜的排练室,朱朱告诉我们,她准备回江西,和老公一起过日子了。
我很惊愕:不是说要挣脱婚姻吗,怎么又要回去了?
朱朱说:儿子在老家等着我,我在深圳也没有一个志同道合的男人。
关于朱朱的这个决定,我离开深圳后多次联系她讨论。她一会儿說接触公益让她坚信女性要独立,只要内心有坚持,环境不会干扰她;一会儿又说回去了不知道会怎样,眼前一片茫然,不行就“入乡随俗”。最后她问我:“我为什么这么矛盾呢?”
我问:你会不会觉得,回去还是一种妥协?
她反问:那我还能怎么办呢?
我把这个问题抛给小娜,她沉默了一会儿,对我说:“也许是改变不了什么,但你不能说这个过程对她没有价值。”
小娜从政法大学毕业后,在工人公益机构做了十年社工。最近,他们回访当年帮助过的一批工友,发现十年过去了,工人们其实没什么变化。现实的问题复杂缠绕,远非一时的觉醒就能解决。当年社工灌输的种种理念,他们现在大部分都忘了。唯一记得的是,在打工的艰难岁月里,机构给了他们一个温暖的家。
我在深圳的最后一晚,姑娘们凑在一起,在城中村的一家大排档给演员饭饭过生日。再过几个月,饭饭也要离开深圳,和丈夫回老家定居。一出戏总有谢幕散场的时候,但饭饭说,那是“很重要的、美好的回忆”。
夜里饭局散了,大家三三两两走回家。我对丁丽说,我要走了,明天回北京。
走在前面的朱朱突然回过身,隔着很远冲我喊:“走啦?”
我点头。
路灯底下,她停了一会儿,举起一只手臂向我挥了两下,转身消失在夜色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