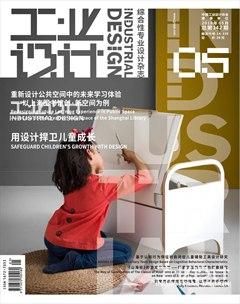浅析明代火器的发展对其形态造型设计的影响
冯峥
摘要:火药是我国的四大发明之一,而火器作为火药的主要载体,在我国的军事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应用火器的朝代中,明代是我国火器发展的巅峰时期,出现了大量结构巧妙、形态各异的火器。本文以有关火器的文献为切入点,找出目前对明代火器研究的不足,分析明代火器的发展对其形态造型设计的影响,体现出明代火器制作者丰富的想象力和当时人们对火器的敬畏之心,为明代火器相关的设计与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明代火器;形态造型设计;形态与功能
中图分类号:TB472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码:1672-7053(2018)05-0053-02
1 绪论
1.1 研究现状
关于明代火器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方面:
以明代火器的产生过程或管理过程为中心进行研究。如王兆春所著的《中国火器史》[1],记述了自唐代发明火药至清末,中国火器的发展历史,将火器的产生过程、发展与演变进行了总结,明代火器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做出了详细的叙述;如刘旭的《中国古代火药火器史》[2]和周绎的《中国兵器史》[3]则是将明代的火药热武器作为中国古代火器发展进化史的重要一部分,论述火器的产生过程;有的如李映发的《明代的火炮发展》[4],以具有代表性的明代火器的产生过程作为文章的主线,论述了明代火器的产生过程和其在当时的先进性。
以明代火器的制造技术与理论为中心进行研究。如王大文的《明清火器技术理论化研究》[5],详细研究了明代火器科学的材料加工技术、管体和配件的铸造技术等制造技术与理论。
以明代火器对军事部署调配及相关军事人员的分工安排为中心的研究。例如朱丽莉所写的《明代火器的发展及其对军事领域的影响》[6],论述了火器的发展对明代军事队伍的部署和军事力量结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2 本文的研究内容
目前对于中国明代的火器有了较为完整的研究,但大多数是对其生产制造、加工技艺理论及军事影响的研究。这些研究都很少关注到明代火器的发展对其形态造型设计的影响,以及其形态造型背后所传达出的思想。对此,本文对其进行了补充研究。
2 明代火器的发展
2.1 明代火器发展的初期
在我国的战争史上,火器的出现与应用是冷兵器向热兵器过渡的重要节点。早在唐代,我国就有使用火器的记载,不过仅仅是将火药作为助燃剂来使用,无法称之为真正的火器。此后的火器在功能和形态上都没有很大的变化,直到宋朝才有了质的突破,出现了以火药为燃料的火铳,但在宋代没有将火器广泛应用与战场,火器仅是强弩和刀枪的辅助武器,军事战术也没有因火器的出现而做出改变,还是沿用从前的战术,即在平原或草原遇到敌人时,先用强弩等远程武器打击,与敌人紧身作战时使用刀枪。
明代在宋代的基础上进行了火器的探索,为了增加火器的使用功能和应对更多的特殊环境,出现了大量形态造型各异的火器,这些火器具有很高的创新性,展现出当时的制作者正处于不断尝试的阶段,为了提高当时军队士兵对火器的认知,制作者采用了大量的仿生设计,有仿照自然生物的设计,也有仿照幻想生物的设计等等。从军事的角度来看,这些火器的杀伤力较小,但从设计的角度来看,其丰富的形态造型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和研究价值。
2.2 明代火器发展的成熟期
在初期探索的基础上不断进行提升的明代火器是中国火器史上的高峰时期。明代火器的材料制造工艺相较于之前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基础制造技艺的层面直接引领火器向更高的方向发展,并趋于成熟。如火器管体是火器制造最重要关键的环节,其主要作用是承受火药引燃后所产生的强烈气压,由此引导弹丸的运动,赋予弹丸一定的初速度,管体越直顺,同等长度的火器管体所能赋予弹丸的初速度越高,火器的精度和穿透力也就越高,简而言之,火器管体质量的好坏决定了火器的好坏。
这个时期,火器的功能更加丰富多样,形态造型也更符合功能性,对于应用的场合也做出了细分,并出现了火器大量在战场上应用。明朝军队为配合火器的使用,对原有的远程战术进行了改进,即在弩箭发射前先使用火器进行一轮远程打击,距离接近时再使用近身武器。随着明朝火器制造技术的发展和提升,火器的种类和用途有了更广泛的发展,军队使用火器的方法也更加灵活。
3 明代火器的形态造型设计分析
3.1 不同发展时期的形态造型设计
明代火爺发展迅速,其形态造型十分丰富,但不同的发展时期对其形态造型的影响不同,大致可分為两种类型。
3.1.1 以形象为主的形态造型设计
此类火器形态大多出现在明代火器发展的早期。因为火器在当时来看是新兴的事物,人们想要对其有更加直观的认识,当时的制造者将自己对自然的观察与想象赋予到火器的形态上,不仅以生活或想象的动物为灵感来源,而且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汲取灵感,虽然其作为武器的功能并没有其他火器出色,但其富有新意的尝试给后世的人们带来更多有关火器的探索空间。下面举例出三个在当时具有创新性的火器形态造型。
神火飞鸦:神火飞鸦是由多个装有火药的筒状助准器所捆绑而成形似飞鸦的火箭。其形态造型是用细竹子做成形似飞鸦的骨架,并在内部装入炸药后在整体框架上糊上一层薄纸,其双翅下各放置两个通过火药线引燃的提供助推力的火箭,火箭助推完成的的最后会引燃飞鸦内的炸药,引起剧烈的爆炸。从作为武器的功能角度来看,其功能符合了对敌军阵营造成破坏的军事打击目的,但对打击目标的精准度和效率并不理想。而从创新的角度来看,其形态是在对生活中飞鸦的借鉴与思考,并将其形态与功能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很好的结合。
火龙出水:其形态仿照古代传统龙的形象,视觉上具很强的冲击力,整体用竹条扎成龙的形态,并在其内部除了放入大量的炸药外还额外加入了两个火箭,在外部和两侧各捆绑二至四支火箭,根据预定目标的距离和方位,调整好其内部和外部火箭的发射角度,将各个火箭的火药引线聚拢成—股,最后固定在火器的尾部。从作为武器的功能角度来看,该火器与过去的火器相比创造性地加入了二级火箭这个设计,具有很大的突破。从设计角度看,其功能与形态有创造性的结合,其形态仿照龙进行设计,虽然龙的形态在制作上过于复杂,且可能会影响其飞行的精度,但该火器可以在空中长距离飞行的功能从当时士兵的视角来看完全符合对龙的形态的认知,所以当时火器的制作者利用了人们对龙的认知,来使士兵在使用这些未曾见过的火器时有很高的认知度。
太极总炮:从现在的视角来看,太极总炮是在炮体内安装引爆装置的地雷,又称太极火图。其形态参照中国传统的太极图,其外部材质多使用硬木或瓷器、熟铁来制造装爆炸物的密闭容器。太极总炮的结构分上中下三个部分,上部为盖,形似太极图,开有一个可以放入火药引线的孔。中部形似四象,每一象的部位安装有两个火铳,故又称八卦铳。下部装有大量火药,会产生很强的杀伤力。太极总炮适合防守战用,因其杀伤力很大,足以抵挡数百人,是防守的利器。古人将其埋在防守的关键位置,敌人一旦从埋有太极总炮地方的经过,就会触碰到引爆的机关,太极总炮就会立即爆炸。可见其功能与地雷类似。此炮不仅材质多样,而且其形态的设计理念人融了传统阴阳八卦的太极图案。
3.1.2 以功能为主的形态造型设计
此类火器形态大多出现在明代火器发展的成熟期。当时的人们对火器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和认识,因此其形态造型更符合使用功能。其中乌铳和将军炮是这个时期代表性的火器,其形态造型相较于早期的火器更加简洁明了,更符合我们传统意义上对火器形态造型的认识。
乌铳:乌铳是明代后期对火绳枪和燧发枪的统称,由铳管、瞄准装置、扳机、铳床、弯形铳托构成。乌铳的形态造型符合其功能:细长的铳身增加7弹道长度,这就使射击的精度更高,穿透力也更强,提高了士兵的射击柏度。将枪柄由插在铳尾部的直形木把改为托住铳管的曲形木托,增加了射击的平稳性。
将军炮:在众多火炮中,以将军炮最为著名。将军炮,又称大将军炮、神机大将军。因为大将军炮发射的是大量的散弹,目的是达到广泛的覆盖型打击。其威力在当时惊人,而且威力也为敌人所惧。大将军炮很重,须有炮车来承载,以便增加机动性与灵活性。
3.2 形态造型设计所传达出的敬畏思想
在明代,火器与冷兵器相比所具有的巨大杀伤力和震慑力被当时的人们所畏惧。又因其在当时制作精密,很少有人懂其原理,稍不注意可能引发爆炸,因此人们在使用或保管时小心翼翼,甚至将其供奉起来,并提出使用之人要戒淫欲,摒荤食素等要求。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将火器神秘化,表现出大多数的人对火器的敬畏之心。同时因看到火器惊人的杀伤力违背了中国传统的“仁义”思想,当时的人们尽量不使用火器。
正因火器其巨大的杀伤力和难以控制的特性,古人对其认识过程中充满了敬畏,并通过各种形态造型的设计使火器符合当时人们的认知水平,希望对火器有更加直观的认识,从而更好地运用它,进而满足军事上开疆拓土的需求。
4 结论
通过上文的分析进行总结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明代火器作为该时代下一个新兴且快速发展的事物,在明代火器发展的初期,当时的人们需要直观且形象地认识火器,通过对其形态造型的设计,将火器与当时已知的事物结合,出现了大批富有创意,形态各异的火器,这些火器的形态造型设计体现出制作者的豐富想象力和创新力,同时传达出当时人们对火器的敬畏之心。在明代火器发展的成熟期,当时的人们对火器的认识达到了一定的水平,火器形态造型设计更符合功能的需求,从而达到更好掌控并使用火器的目的。
本文通过对明代不同时期代表性的火器形态造型进行说明,分析了明代火器发展的前期和成熟期对其形态造型设计所产生的影响,并分析了明代火器形态造型设计中所体现出的敬畏思想,为以后的相关研究者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参考文献
[1]王兆春.中国火器史[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
[2]刘旭著.中国古代火药火器史[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01.
[3]周纬.中国兵器史[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04.
[4]李映发.明代的火炮发展[J].大自然探索,1990,04.
[5]王大文.明清火器技术理论化研究[D].苏州大学,2011.
[6]朱丽莉.明代火器的发展及其对军事领域的影响[J].学理论,2011 (20):163-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