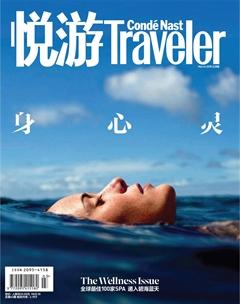遁入碧海蓝天
Rachel Howard



有些地方你向往已久,可真正到了那里却感到失望。
还好,阿英尔戈斯岛(Amorgos)不在此列。
我对这座偏远小岛的情愫始于年少时看的电影《碧海蓝天》(TheBig Blue)。我不仅期待着能潜入男主角让-马克·巴尔(Iean-Marc Barr)的“怀抱”中,更向往它既无邮轮停靠也无寿司吧的一面,阿莫尔戈斯岛仿佛是我消逝的希腊童年时光。哪怕在20世纪80年代末,阿莫尔戈斯岛也停留在一种更简单、纯粹的生活方式中——吕克·贝松选择此地拍摄了《碧海蓝天》的序幕,以黑白色调颂扬他挚爱的蓝。
去年夏天,我终于梦想成真。不得不说,阿莫尔戈斯岛可能是最童话的希腊岛屿。幸亏到达那里并不容易——从雅典搭乘近年刚开通的最快的渡轮也要六小时,所以没什么人愿意费这么大劲。在港口,一幅捕绘着阿莫尔戈斯岛海马形轮廓的地图上写着:“欢迎来到阿莫尔戈斯,到了这儿,再也没人能找到你。”如果是这样,我想我找对了地方——一间位于岩石海滩上的低调别墅,经过一段颠簸的土路才能抵达这个幽静之处。
别墅的主人是凯法利尼亚岛人,他在牌局中赢下了这块地皮,二十年后,才终于来到阿莫尔戈斯——虽然晚了,最后却证明是值得的,别墅的每个房间都有天空和大海景观。从我的房间看出去,Nikouria岛就与我隔着窄窄的海峡。附近有蜂农养殖蜜蜂,生产最美味的百里香蜜。在Langada村的养蜂场里,这位蜂农还会业余画点儿小画。
在这座岛屿上消失完全可能,你可以整天出没在大海里,对望着令人倍感舒缓的日落而惊叹。不过那样你会错过藏在山谷里的小村庄、牧羊人灿烂的笑容和飘在云上的小教堂。每个来到阿莫尔戈斯岛的人——无论潜水者、徒步者、孤独的人或朝圣者,都会拜访霍佐维奥蒂萨修道院(Monasteryof Hozoviotissa),这是一处建在海岸绝壁上的建筑奇迹——有八层楼高,进深却只有五米。300米高的悬崖与一千年前徒手建起它的坚韧顽强相比不值一提。
通往修道院的阶梯挟小得几乎要爬行通过。熏香萦绕在镀银的圣像旁;一扇笨重的大门通往锯齿形的阳台,阳台被漆上耀眼的白色,反衬着深蓝色的天空,遥远的天空下是两个小海湾,海水清澈见底,连海床上沙子的纹路和岩石都能看清。
在18世纪,这座修道院有一百位僧侣,如今只剩下三个。最年轻的狄奥菲洛(Theophilos,意为“上帝的朋友”)来岛上铺设光缆,然后留在了这里,完全过着“不插电”的生活。在点亮蜡烛后,他引我走进一个斯巴达式起居室,里面陈列着修道院院长们严肃的黑白照,简直是一面修道院的名人墙。随后我加入其他朝圣者,一起靠在长凳上将免费的Psimeni拉克酒(当地一种含有肉桂和糖的烈酒)一饮而尽,我察觉到修士不那么赞许的目光。很快,我掌握了品尝阿莫尔戈斯的拉克酒的门道——Psimeni拉克酒是为游客准备的,当地人则是喝纯的,他们通常会挤在希腊式咖啡馆——“Kafenio”(一处融合了咖啡馆、杂货店和工人俱乐部的场所)里。Kafenio曾经遍布希腊,现在近乎绝迹。
在阿莫尔戈斯,每个村子都有间Kafenio,比如在欢乐的主镇上有Parvas,它杂乱的后厨提供西葫芦炸鱼丸;在偏远的阿尔凯西尼(Arkesini)镇上有间Makis,手写菜单上的东西通通不超过一欧元,唯一的例外是Amstel啤酒——两欧元;在悠闲的卡塔波拉港(Katapola)的海边,Prekas也充当旅行社的角色,你可以一边吃着小鲱鱼,一边等待你的船靠岸;而在破败的托拉里亚(Tholaria),彩绘葫芦和葡萄酒罐悬挂在Kali Kardia小店的货架上,家传三代的女主人能做出爱琴海最好吃的肉丸子。他们从不大肆宣扬所用食材是应季或当地的,因为这根本不消说。不管你喝上多少拉克酒,在这些地方两个人的消费都很难到25欧以上。
“有一则当地谚语描述了当地人的好客”,英国探险家西奥多·本特(Theodore Bent)写道,他曾在19世纪80年代早期来基克拉迪群岛群岛(Cyclades Islands)壮游,“到了Brytzi却没饮醉的人就像朝圣者到了圣墓却没有朝拜一样。”本特住在这儿期间,当地人带来鸡蛋、葡萄酒、面包和小猪——“我们伸长脖子,看着它们被宰杀、去毛、烧烤……晚餐后,我们唱歌、跳舞,应和着古老的里拉琴的调子。第二天,当我离开时,主人不会收一分钱。”
小巧的Vroutsi——Brytzi今天的所在地,几乎在本特造访之后从未改变,要享用美味的猪排和欢歌笑语就去Georgalinis酒馆吧。我走在日光照耀的小路上,毛驴躲在墙根儿的阴凉里,一位牧师和他的妻子邀请我进去,他俩站在门廊下,仿佛来自远古的石化的树。女主人一瘸一拐地进屋帮我拿来冰水和一块有香蕉奶油夹心的金色巧克力,问我从哪儿来。“伦敦”此时像个遥不可及的地名。而当我再度回到炙烤的烈日中时,拐上了一条通往有着蓝色穹顶的Agios Ioannis教堂的小路。它立在山顶上,也是俯瞰整座岛屿的嘹望台——卡塔波拉的新月形港口、卡斯特里古老的卫城……岛上的徒步路线被称作“蓝色小径”,也许因为无论你往哪儿走都能看到大海。这些鼠尾草飘香的小路通往一片片隔绝的沙滩——Atomoudi、Mikri Glyfada、Hala、Plakes——都有光滑的岩石供你晒日光浴。
阿莫尔戈斯岛上总共只有四辆出租车,而且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柏油路才鋪到岛屿南部的Kato Meria。在这里就像身处20世纪50年代,当我开车经过孩子们时,他们会朝我挥手,毛发蓬乱的山羊在路边小憩;在简单的路边加油站,门廊外的碎花布桌子和几把塑料椅子就是一间小餐馆,祖母们拖着鞋到菜园里摘小番茄来做希腊沙拉;在StonPyrgo,古老的阿尔凯西尼塔旁有间井井有条得多的餐馆,玛利亚会用最好的鱼和Patatato招待你,Patatato是用嫩枝小火慢炖出的山羊肉和土豆。
最终,道路逐渐消失于卡洛塔里蒂萨(Kalotaritissa)完美的海湾里。破旧的渔船漂在平展的深蓝大海上。有人在浅海里学习潜水,有穿着“美人鱼会做得更好”字样T恤的女孩儿在沙滩上做侧手翻。我等待着去往Gramvoussa岛的下一班船,这时玛利亚·诺米科和她三个有着卷头发的漂亮女儿在那间木头餐厅里给我煎着芝士派。Gramvoussa是海岬旁的一座无人岛,那时船长去午睡了,因为那天他起了个大早,把朝圣者送去参加教堂节日。
在经历了十分钟兴致高昂的乘风破浪后,我来到Gramvoussa岛的金色沙滩。这儿的海是一片闪耀着的融化了的绿松石。同船的其他乘客只有一对希腊中年夫妇,他俩的手交缠在一起,他们的笑声融进了浪花里。在我们上岸时,女人禁不住唱起歌,跳了一小段肚皮舞。船开走时,剩下我们欣喜万分地留在沙滩上。船长向逐渐远离他的我们打着手势,问:“几点来接你们?”我伸出四根手指。
喜欢阿莫尔戈斯用不着当隐士。这儿多的是咖啡馆和酒吧,你可以兴高采烈地和陌生人玩在一起。在藏在霍拉镇上的Jazz-min,你可以玩西洋双陆棋、喝鸡尾酒;在总被浮云萦绕的兰加达村(Langada),你可以在Pergalidi来点儿草药饮品和奶酪煎蛋,背景音将是约翰·柯川的音乐和鱼贩子吹海螺招徕客人的声音混合成的超现实声响。在托利亚时髦的Seladi,不光有让人炫目的风景,还有一架观星望远镜。而最适合看日落的地方在Kamari,你要爬上Ano Potamos村数百级的台阶,当太阳隐去最后一点光芒时,遥远的岛屿和薄雾中的山峦会模糊地平线。
在这座人口数量不足两干的小岛,你总会一次又一次遇见熟悉的面孔,比如骑驴的船夫、弹奏布祖基琴(Bouzouki)的面包师、在Agios Georgios Valsamitis唱诗的希尔多费罗斯神父——这是一座16世纪的女修道院,艾琳修女和她的侍女住在一起。晨祷之后,信众们聚到葡萄藤阴凉下的走廊里,支起的桌子上摆满桃子、无花果、葡萄、自制的蛋糕和几罐咖啡。在荒凉的Asfondilitis村的早餐更让我大开眼界。村子在强风肆掠的岩石高地上,人们在贫瘠的土地上种出了小麦、小扁豆、大麦,甚至是棉花和烟草。有几个古蓄水池留存了下来,不过现在只是街道上的一堆石头。巨大的郁金香仙人掌如史前动物一样攀上墙头。
我爬了上去,在鬼魅般的清晨中看太阳从爱琴海上升起——在这片原始的大地前,我可以穿越回到黄铜时代。起初,村庄看似被遗弃了。不过有人正在挥舞希腊共产党的旗帜。那儿也有间朴素的小酒馆,但是强悍的主厨索菲亚今天没法做饭,风太大,根本没法点燃户外的炉子,而这里又没有电。
我顶着强风行走,一个牧羊人招呼我到他家去。屋子里十分幽暗,我不小心撞到了一个矮凳。逐渐,各种家什从黑暗中显形:—把生锈的镰刀、一副布满灰尘的潜水通气管、一堆山羊毛毯子。屋子的主人米凯利斯和他的七个兄弟姐妹就在这间屋子里长大。房子已有250年历史了,天花板是用石板瓦盖和木料搭起的精巧的迷宫,地板是裸露的水泥。
牧羊人强壮的邻居尼克斯也加入了我们,他戴着一顶漁夫帽,将衬衫系在腰上。这两个男人抽着烟,寂静偶尔被玩笑打破。我询问:“能拍张照片吗?”“拍吧。”尼克斯说,“我可是个像帕特农神庙一样的老古董了。”“也许你比我高,但我有颗大心脏。”米凯利斯咧嘴笑着,鼓起他的胸膛。
然后,他抓起一把刀消失了。等他回来,已经带了一袋子郁金香仙人掌。米凯利斯熟练地用手指给仙人掌去了皮,然后给我们倒上拉克酒,蓝眼睛在幽暗的光中闪耀着,举杯说道:“友谊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