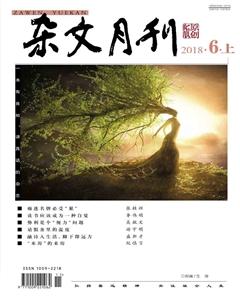杂文情怀
任蒙
记得前几年,有几个地县邀请我去讲散文创作,我说“写散文就是写自己”,就是写自己的情怀。一个作家情怀的高度和宽度,决定着他笔下散文境界的高度和宽度。其实,在杂文创作中起着决定作用的,仍然是作家的情怀。
杂文是个具有鲜明时代色彩的文体概念,在很多人看来,具有鲁迅杂文那种思辨功能和语言特点的社会批评,才是“正宗”的杂文。而对有些杂文选本收录的那些灯下随感或家长里短,尽管其中不乏好文字,仍被算作“杂烩”。
杂文是时代的产物。在社会转型期诸多矛盾凸显,社会普遍渴望加大反腐败力度的阶段,杂文便应运而繁荣起来。试想,当年某个偌大城市反腐倡廉大会隆重举行时,市委主要领导到会作重要讲话,市长和纪委书记也洋洋洒洒地讲了不少,会议材料合成印出来一大本,第二天市委机关报以头版位置对大会进行重头报道,而读者看到全市反腐败斗争最突出的任务,竟然只是抓“公车钓鱼”,大家该作何感想呢?整整一年过去之后,全市反腐倡廉大会又如此这般,报纸头版的大字标题,报道这年纪检工作的重点却是查处“公车娶亲”。某县纪委曾经规定干部送花圈,高度不得超过一米,等等。
这些都不是杜撰的故事,很多人都经历过。那个时代腐败之风甚嚣尘上,人们心急如焚却无能为力。
由此不难看出,党从十八大之后动真格反腐,为什么深得民心。
改革开放以来的这个时期,也是杂文丰收的季节。
浪漫出诗人,“愤怒”应该出杂文。
杂文作者骨子里必须有几分耿直,几分率真,几分正义,几分血性,他们笔下流淌的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只有那种责任,才能產生敏锐的感触和认知能力,才不会陷于麻木。
在看似尖利的冷嘲热讽之中,杂文传递的是对社会、对时代的善良与忠诚。
有评论家认为,李白主要受老庄哲学的影响,而杜甫则受儒家学说的影响很深,云云。其实,这是有意将后人的作品风骨去与前人寻求某种对应。杂文作者执笔为文,也不是因为此前出了个鲁迅,而是由于自己所处的时代使然。
浏览散文,你可以发现许多篇目写的是作者身边的某个人物,或者他们眼里的一花一草,一犬一牛,那些事物都与作者本人有着密切关联,大多就是他们自己的经历或家里的事情。而杂文则不然,杂文必须是超越这种“自我”的。
杂文写自己的情怀,但不是自我情感,它必须超越某些个人情感。
某年,本地高考的作文题目是《感情亲疏和对事物的认知》,多少年过去了,我仍然为当年的考生们感到不易。对于没有多少人生经历的孩子们来说,这个题目是不太浅显的。这个话题必须扣住“感情亲疏”四个字去展开,才能去论述两者之间的关系,才能说出感情亲近程度对认识能力的影响。萨达姆的女儿曾经评价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父亲”,某个身居高位的人物,其身边的人都对他感激涕零。然而,杂文不能以这种视角去观察社会。
杂文,写的是良知,更是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