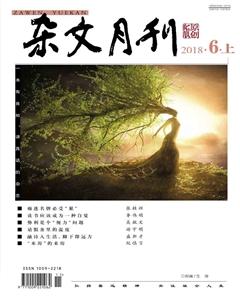司马迁的利义观
乐朋
利义之辨,即经济利益与礼义道德的关系问题,在春秋时期曾争论得很热闹。杨、墨(杨朱、墨翟)重利轻义,与之相左的孔、孟,则重义轻利。孔子有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又说,“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调门高亢,一下就占领了道德制高点,视杨、墨等派如粪土。而司马迁的老师董仲舒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宣扬“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标榜仁义、讳言财利,在西汉武帝朝发展为社会主流观点而风行于世。
对孔子、董仲舒,司马迁是尊重、推崇的;但“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司马迁,并不认同、拘泥于儒家的利义观。《史记》之《货殖列传》,便对逐利营商的富豪不吝赞美之辞。司马迁持非主流的利义观,与儒家拉开距离,凸显了史学家的独特与进步,达成一种历史的超越。司马迁批判侈谈仁义道德、不讲物质利益的荒谬观点,下面这段话十分有名:
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势益彰,失势则客无所之……”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这段话集中反映了司马迁的利义观。他从历史演进考察中得出结论:诗书礼乐、仁义道德,不能脱离现实社会的物质基础而存在;人生在世,生活欲望、想过好日子、追求物质财富,是与生俱来的普遍人性,君子小人,无一例外。譬之身体,利是骨肉,义为皮毛。我不愿穿越、拔高,说司马迁具备现代唯物史观,但其注重实利,把追求物质生活满足视同“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的自然规律,超越古人前贤,大有朴素唯物论的意味是可以定论的。
司马迁的可贵,犹在其一反汉儒“口不言利”的虚伪、愚昧,把追求财利、想过好日子作为普遍人性加以褒扬,认定为推动社会发展的物质力量。他将物质产品的生产和流通视作社会进步的根本,置于礼义道德之上,主张通过各行各业人们的各尽其才力,实现“上则富国,下则富家”的国家和社会治理目标。任何国家或民族,都不能指望单纯依靠意识形态、仁义道德求得兴旺发达;只有好好发展经济,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才能实现民富国强、长治久安。“礼仪之邦”的中国仁义道德唱了几千年,可人民却难求温饱,长期陷于饥饿,其精神道德面貌怎会“独步天下”?国家又岂能不积贫积弱?儒家张扬“仁义治天下”,实是舍本逐末、开错了治国理政的药方。把被儒家弄颠倒的利义观重新颠倒过来,以经济振兴助推精神道德建设,正是司马迁的一个历史贡献。
司马迁对刘汉王朝的世袭权贵是心存不满的,而对那些身无官阶爵禄,通过开发资源、经商牟利的新兴地主富商,则持欣赏态度。“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富商地主的兴起,打破宗法权贵对财富的世代垄断,标志着陈旧生产关系的衰败和社会的进步。司马迁鄙视官本位的世卿世禄者的先贵后富,赞美能力本位的新兴地主富商的先富后贵,无异于是对汉初实行分封制的沉重一击!叔孙通、公孙弘等汉儒讳言货利,标榜仁义道德,实际上只是充当权贵的帮闲,或帮凶,替统治者涂脂抹粉,愚弄、奴化民众,要他们永远“安贫乐道”。所以司马迁讽刺说,“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自己没有真隐士的高尚道德,长期贫贱而又满口仁义,鄙薄生产经商,难道不是令人羞耻之事吗?阳为君子、阴为小人的汉儒,有什么颜面奢谈礼义廉耻?司马迁对伪善的儒家利义观的批评,入木三分。
鲁迅说,中国人“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古今道德家的“仁政”“德治”高调总唱不完。但在我看,只消将道德家丢进柴房,饿上三天肚子,也许他们就再无兴趣去鼓噪仁义道德了。新时代的我们要从司马迁的利义观中汲取营養,就须紧紧扭住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不放松,下功夫做好“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这篇大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