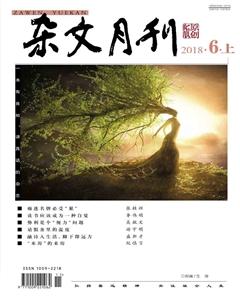我爱生活,并为使其美好而战斗
哈米
翻译讲究信、达、雅。信达不用说了。雅呐,什么叫雅?作为门外汉的我认为,雅,不仅忠实于原文的内涵,并且优于原文。行家说过,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有优于原文之处。据此观点,我多年来一直想表达如下的一个意见。这意见并无深奥之处,是很具体单一的。
我是尤利乌斯·伏契克的拥趸者,读过《绞刑架下的报告》好些不同译本,有刘辽逸据俄文转译的,陈敬容据法文转译的,蒋承俊、徐伟珠各自据捷克文直译的两个译本。他们译笔各有千秋。《报告》中一段最著名的话,刘辽逸是这样翻译的:
我爱生活,并且为它而战斗。我爱你们,人们,我爱你们,当你们也以同样的回答我的时候,我是幸福的。当你们不了解我的时候,我是难过的。我得罪了谁,那么请你原谅吧;我使谁快乐过,那么请你们不要为我而悲哀吧。让我的名字在任何人心里都不要唤起悲哀......如果眼泪能够帮助你洗掉心头的忧愁,那么你们就放声哭吧。但不要怜悯我,我为欢乐而生,为欢乐而死,在我的坟墓上安放悲哀的安琪儿是不公正的。
这段文字极为简洁,却堪称《绞刑架下的报告》的核心思想,极具感染力地传递出伏契克的人生价值观和巨大的人格魅力。这是一位英雄对亲人、战友和同志的遗言,但不是那种掷地有声的豪言壮语,而是极为亲切的、既庄严又柔情的挚友间促膝谈心似的言辞。说的是牺牲与死亡,可传递出来的,却是欢乐和明朗如春日的情愫———这不是用笔写出来的,而是源自与生俱来的磊落的天性!我不止一次说过,我之所以对其人其作品一见倾心而成为他的拥趸者,并不是由于他所信奉的主义,而是他这种天然自成的、无法效仿的性格魅力。
其实,远不止是我,许多七零后八零后乃至九零后读者,他们所处的时代已经没有人向他们宣传这位捷克英雄了。他们都是在自己的阅读中发现了这种魅力,被感染了而成为“伏粉”,成为我的同志的。
要说艺术性,这就是《绞刑架下的报告》艺术性(更确切地说是灵性)所产生的效果。不仅仅是上述所引这几句,整部《报告》都充满着这种既激越又温馨的语言。这使得这个作品在所有的监狱文学中独树一帜。
上述刘辽逸译文所以一下子打动了我,除了内涵之外,译文的美妙是个重要因素。我们都有体会,行文(不管用哪种语言)要有节奏感、音乐性。“我爱生活,并且为它而战斗”,干净利落,节节推进,毫无拖沓之感。
可到了陈敬容根据法文转译时,这句话译成了:“我爱生活,为了它的美好,我参加了斗争。”语气一下子松弛了,像刹那泄了气的皮球,没有了节奏。而且我觉得“斗争”没有“战斗”好。
蒋承俊根据捷克文直接翻译的也如此,而且重叠了两个“生活”,更显拖沓:“我爱生活,为了生活的美好,我投入了战斗。”
徐伟珠根据捷克文直译的也类似而且更加累赘:“我那样热爱生活,为了生活的美好,我投入了战斗。”
为什么说累赘,因为不仅重叠了“生活”,而且,在“爱”前面加了个“热”还不够,再叠上个“那样”,明显“蛇足”!
除刘译外,这种结构类似、却变动添加字眼的现象,我猜大体是后译者想区别于前译者译法各异的不得已之举。但有一点引起了我的注意:为什么后三位不同于刘译,在“我爱生活”后面有一句“为了生活的美好”呢?是否原文就是如此?如果是,那么后三位译法尽管缺乏节奏感,却是忠实于原作,是准确的。不懂捷克文,只好找来英译本对照参考,发现后三位与英译很吻合。但我仍然欣赏刘辽逸的中译。一位“伏粉”对我说,刘译只讲“我爱生活,并且为它而战斗”,没有说到“为了生活的美好”呀。我说“为它而战斗”,当然指为“美好的生活”,这是不言而喻的,总没有为了丑恶的生活而战的吧。
还有,刘译的最后一句“我为欢乐而生,为欢乐而死,在我的坟墓上安放悲哀的安琪儿是不公正的。”同样节奏明快,而且“悲哀的安琪儿”读来非常顺口,不像其他三位译成“悲悼天使”或“悲怆的天使”那样拗口又缺乏诗意。
因此,我每次写稿引用伏契克这段话,都是选定刘译的这几个句子,再根据其他译者译的个别字眼综合调整成最佳组合而用的。后来我又想,没有译出原文有的那“为了生活的美好”也不很恰当,能不能译得更好一些,既有“为了美好的生活”这层意思,又保持紧凑的节奏呢?我想了下,动手把它改“译”了一下———
我爱生活,并为使其美好而战斗。我愛你们,人们......
自觉最佳,不知大家认为怎样。这,算不算就是翻译之“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