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号公路和圣塔菲
洁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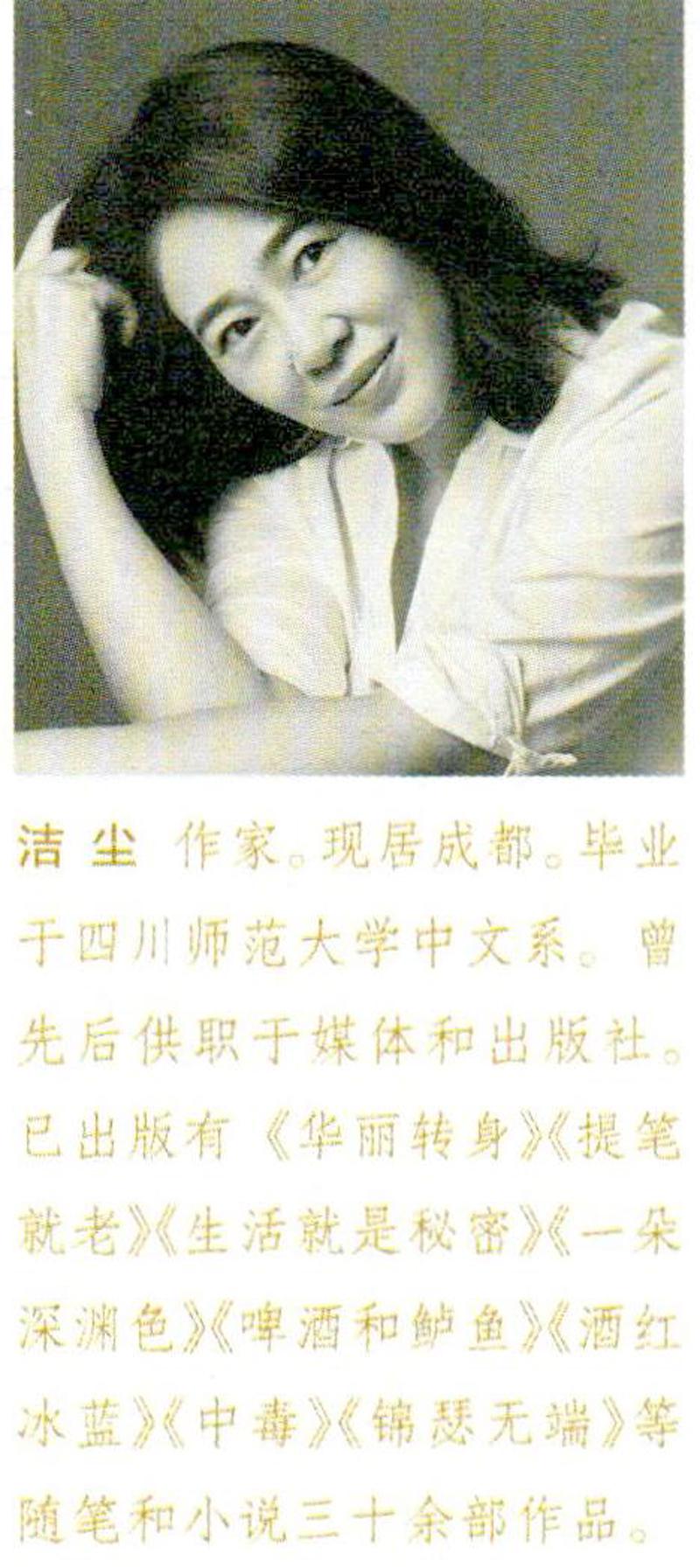
一
我们的环美自驾三人行之公路狂奔版,准确说是从加州的圣地亚哥开始的。我们这趟的出发地点是洛杉矶,但我们想先逛一下美墨边境上的墨西哥小城提华纳,就从洛杉矶附近的圣地亚哥出境,去那边兜了一天,然后返回。从圣地亚哥往西北开了一截后,我们的领队兼司机兼翻译、艺术家何工老师对我们说,上40号公路了哈。
这就开始有点激动了。也就是說,我们踏上了非常著名的66号公路。约翰·斯坦贝克在《愤怒的葡萄》里,把这条公路称作“母亲之路”。
66号公路始建于1926年,连接了芝加哥和洛杉矶,全长2448英里(约3939公里)。这条公路前前后后修了十几年,正式竣工是1938年。这段时间,正值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这个工程当时为数以万计的美国人提供了就业机会,被称为大萧条时期的救命稻草。公路建成后,贯通且促进了美国东西海岸之间的包括人员和物资的各种流通,对美国经济的飞跃发展居功甚伟。1984年,公路改建,原有的66号公路包含在40号州际公路之中,但沿途好些原址还保留着,成为美国公路文化的历史见证。
因为要赶路,66号公路两边穿插下去的好些景点我们都没有去,但在途经的很多加油站的商店里,66号的历史气息扑面而来:一进门,各种印有“Rotlte 66”字样的T恤、汽车牌挂得满满当当的,随时提醒旅人们:你们是在66号公路上哦。我买了一件这样的T恤。
我们走的是66号公路其中的一段,穿过了五个州,加利福尼亚、亚利桑那、德克萨斯、俄克拉荷马和堪萨斯。我们走的这一段,恰是以前在电影里看到的典型的美国西部景貌:白花花的烈日下,迎面而来除了延绵不绝的公路之外,就是延绵不绝的石山以及延绵不绝的戈壁.植被稀少。只有矮小零星的衰草和鬼魅一般的巨型仙人掌。在这样的景貌中,太阳也显得格外地严厉和凶险,白,惨烈的白。可以想象,这个时候,如果见到一匹马驮着一个挎枪的牛仔从远处而来,该是多么让人绝望的孤寂啊。我坐在副驾上,眼睛逐渐发愣,有亡命天涯不知所终的那种感觉,这个时候,好不容易遇到一辆超过我们的车或者迎面而来的车,我都想跟人家打个招呼。
66号公路在与太平洋铁路并行的那一段长长的区域里,在20世纪30年代,一直是美国劫匪活跃的地区,他们在这个区域内,上劫火车,下劫公路,那叫一个彪悍啊!
关于这段历史,美国很多电影都有呈现。我首先想到的,是我非常偏爱的一部电影,《虎豹小霸王》。如果仔细考察,《虎豹小霸王》的故事时间跟66号公路的时间其实并不太吻合,但发生区域是在这一块。对于一部虚构的电影,就不用那么严谨了吧。
1969年出品的《虎豹小霸王》是传统美国西部片的颠覆之作.当年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又叫好又叫座。片中两个劫匪主要是抢太平洋铁路上的货车。跟以往西部片里的那些僵直坚硬的英雄和坏蛋不一样的是,保罗·纽曼饰演的布奇和罗伯特·雷德饰演的日舞小子从质地上讲轻松了很多,他们显得弹性很大,跳出来的空间也很轻盈,他们是道德和文化上双重的规外人物,是彻底的个人主义者,是浪漫、温存、调皮、诙谐的坏人,有一套令人莞尔的混账逻辑和一种浑不吝的魅力。这两个角色的轻松,在于他们身上没有文化的印记,而又天资卓越、个性美好,这种人物让人有一种本能上的好感,或者说是生理意义上的好感。说起来《虎豹小霸王》是一部悲剧,两个歹徒的悲剧。但两人冲将出去万劫不复的那个定格的结尾,让人微笑。可以说.这是唯一的一部我愿意一而再再而三观赏的悲剧。这次奔行在66号公路上,我再一次回想那部迷人的电影,回忆他们的逃亡、斗嘴、调情和幻想,回忆他们的坏笑。片中女主角是女教师艾塔,一个天性生猛且浪漫的姑娘,跟着他们一路打家劫舍,到了最后,艾塔说,跟着你们很过瘾,但不要让我亲眼见你们死,那个场面恕我不奉陪了。
艾塔跑了,邦妮可是一路死磕到底。是的,著名的雌雄大盗邦妮和克莱德也是在这个区域里的德克萨斯境内出没、成名、发迹且最终毁灭的。那是66号公路正在修建的时期,20世纪30年代。
黑道鸳鸯的故事可以说是电影的一个母题。其中的经典就有改编自真人真事的《邦妮和克莱德》。这部片子成为经典有几个要素:第一,菲·唐纳薇饰演的邦妮和沃伦·比蒂饰演的克莱德都漂亮得耀眼.他们身上有一种诱人的邪气。第二,两个人之间无缘无故的爱和忠贞,十分突兀,但相当动人。第三,也是最奇怪的一点,这对黑道鸳鸯没有性生活,因为男方性无能。这也为大盗克莱德的疯狂行为提供了一个心理学上的佐证:他用对抗社会的方式来和自己心爱的女人做爱。《邦妮和克莱德》是1967年出品的,迄今还是黑道鸳鸯片的巅峰之作。结尾处两人被警察乱枪打死的镜头让人难忘,是近乎纪实片似的死法,那种残酷、真实和破灭,给人的冲击力,难以超越。
上了66号公路不久,停车小憩,我站在路边车前,摆了一个pose。这个时候,我想起了菲·唐纳薇演的邦妮。这部十分酷炫的电影,曾是我青春期的大麻。……电影一开头,24四岁的邦妮裸着身子对着镜子抹口红,听到有人在鼓捣汽车,便从窗口探出去,晨光里,她与那个正在偷她家汽车的俊俏男人一见钟情——全美国最著名的一对雌雄大盗从此结盟。……
二
有几个美国地名一直萦绕于我,不是纽约,也不是芝加哥、旧金山、洛杉矶。它们都太大了。萦绕于我的几个地名,小且柔美,其中有新墨西哥州的圣塔菲和圣塔菲旁边的小镇陶斯。圣塔菲和陶斯,是和乔治亚·欧姬芙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圣塔菲有欧姬芙博物馆,陶斯有她的故居。
2015年4月,我来到了圣塔菲。可惜的是,因为行程的关系,陶斯没有去成。
在此之前,我对于欧姬芙的阅读已经很久了。我喜欢她的画,巨大的特写视角的花卉和关于沙漠的风景,尤其喜欢她将风景、牛头骨和花卉组合在一起的画而,死亡和生机、短暂和永恒、硬朗和柔美,各种气质并置,化学方应后相当玄妙。我也喜欢她的容貌,长得特别清俊。至于说我是不是喜欢她的人,我说不好,她太酷了,完全无法走近,难以了解,我就是仰望她而已。
我和同行的朋友何工和周露苗是在4月20日傍晚进入圣塔菲的。我们的车子直接开到欧姬芙博物馆的门口。博物馆当然已经关门了。晚光璀璨,四下无人。已经进入初夏的圣塔菲,晚上还有春天的寒意,行道树也不知是什么树,没几片叶子的光秃秃的枝条朝天伸展,还是一副冬装的模样。博物馆外墙上悬挂着巨大的海报,“新墨西哥创造的现代主义艺术”(Modernism Made in New Mexico),一个群展,领衔者当然是欧姬芙,展期是1月30日至4月30日。我们正好赶在尾巴上。我们决定就在欧姬芙博物馆附近找家酒店,明天一早开馆就过来。
天光越来越暗,在很小的圣塔菲城里边找酒店边缓慢绕行。好美的小城!清一色的圣塔菲建筑风格的房子,浅棕色的泥土外墙随着光线的逐渐消失,也渐渐沉入深棕乃至于黑色之中,美丽的带有弧形的轮廓线与天边残存的血红落日并置于眼前,相当魅惑。顺便说点题外话,这一晚,我们入住了整个环美自驾行中的最奢华的酒店(原因是晚上看上去没什么人的圣塔菲已经有了很多外来的访客。经济型酒店全部客满了,我们只好咬牙入住能找到的大套间客房。),一个套房除两间大卧室之外,还带巨大的客厅和厨房,可惜对我们来说没什么用。这样的房间还定了两个,一个是我和苗苗的,一个是何工的,三人都啧啧摇头,太浪费了。
圣塔菲,建于1610年,在美国算是古城了。这个位于新墨西哥州的小城,以艺术和建筑闻名。建筑方面,全城的建筑统一风格,基本上都是拷贝印第安原住民普韦布洛人的砖坯房子,清一色的浅棕色泥土外墙(现在应该不是泥土外墙,是仿泥土的涂料)。这一特色让这个小城显得相当的精致和考究。艺术方面,圣塔菲更是大名鼎鼎,它是除纽约之外最大的艺术城市,从20世纪中期开始,很多艺术家陆续来到这里定居,小城里遍布小画廊、小美术馆以及艺术家工作室。
欧姬芙应该算是圣塔菲区域的艺术开拓者,她是1929年来到陶斯的。
欧姬芙1887年生于威斯康辛州。年轻时在纽约从事绘画期间,认识了摄影家史泰格列兹,与之结婚,并成为他的模特儿。史泰格列兹拍摄了关于欧姬芙大量的照片,包括肖像、裸照和手的特写。史泰格列兹曾经在纽约举办过以欧姬芙为模特对象的摄影展,因其中有很多裸照而轰动八方,也因此招致当时保守人士的攻击。在那个年代,这种事情对于女性来说是一种非常大的困扰,但对于欧姬芙来说,完全不以为意。她天生就是一个大女人。年轻时说脱就脱,面孔和胴体都美妙傲人。到了中年之后,她把自己遮得严严实实的,只穿黑白两色,一袭长袍拖曳在后半生的岁月里。她从不化妆,盯着镜头,几乎不笑,傲慢无比。
从欧姬芙的各种照片里能感受她的傲慢,这种傲慢不仅来自思想,来自才华,来自性格,还来自天生的美貌。天赋美貌,当然可以不在乎是否美,因为足够美。
好些曾经在各种画册里看过的出自史泰格列兹之手的欧姬芙的肖像,在第二天一早进入欧姬芙博物馆后又重温了一次。
欧姬芙博物馆是个普韦布洛建筑风格的小型博物馆,就欧姬芙作品的藏品来看,在我看来好像还没有芝加哥艺术馆多。我在芝加哥艺术馆看到了她大量的作品,在华盛顿的国家美术馆和纽约的Moma、大都会博物馆也看到了一些,芝加哥博物馆最多。但欧姬芙博物馆里收有欧姬芙遗留的各种物品,她的画桌、画笔、画架、调色板之类,这对于欧姬芙的仰慕者来说,也是一种安慰。当时我在现场看到这些东西,想到没有时间去陶斯她故居的现场,心里多少还是遗憾,安慰自己说,以后找机会再去吧。可是,以后是什么时候呢?真说不清楚。
欧姬芙在长达98岁的一生中,画材分阶段地有好些个,早年的星空系列,中年住在纽约时的高楼系列,后来定居新墨西哥州后的沙漠景色系列以及头骨系列,等等。她像很多卓有成就的画家一样,在一个阶段里通过反复地从数量和质量上丰富一个题材,待有所固定之后再加以转换,从而构成作为一个艺术家生平创作的丰富性和深厚品质。但欧姬芙跟好些画家不太一样的是,她还有一个贯穿了一生的题材,那就是她的标签:花卉。
她的花卉只有少量的普通视角,更多的花卉在她笔下是被放大了的,呈现的是一朵花甚至是一朵花的局部,以花蕊作为构图的焦点。这样的视角更像是一只蝴蝶或者说一只蜜蜂的视角,于是看出去的花,硕大无比,在感受花瓣质地非常细腻的同时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广袤的感觉。如果观众不想将自己带入昆虫的角色的话,那么,欧姬芙的花卉就只能用梦境中的人视角的变形来解释了。我第一次接触欧姬芙的花卉时,感觉它们作为格列佛游记中的巨人国的配图很合适,观者仿佛变形为一个小小的人儿,以花为荫,得到一种柔美的安抚。这种安抚是私密的,不能也不宜讲述的。
在一般的解读中,欧姬芙花卉作品一向暗指女阴,这一点,欧姬芙本人是不同意的,但也半推半就不做更多的解释;因此,作为一个美国最为著名的现代派女画家,欧姬芙以其本人大量的裸照以及其作品浓厚的性意识和女权气息出位。其实,在我的观感里,这些花卉中并没有太多女性由性出发产生的自恋情结,它们其实相当地单纯,是女性对于花朵这种天然的与自身的品质类似的对象所产生的某种通感。
曾经有一个心理学者说,欧姬芙的花卉画可作为心理治疗的视觉教材。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否合适,但在我看来,她笔下的那些花卉作品,《红罂粟》《黑蜀葵与蓝燕草》《黑色鸢尾》《紫色牵牛花》《红昙》等等,多用大块的纯色,局部写意,所描绘对象的整体轮廓被模糊甚至变形,这很有点可以催眠的效果。很巧的是,看欧姬芙的传记,发现她早年对心理学有着浓厚的兴趣。这一点,虽不敢断定和她的作品有什么直接的关联,但这其中某种暗合也是显而易见的。还有一个对比性质的暗合也是心理学意义上的:作品色彩绚丽强烈的欧姬芙,一辈子基本上只着黑白两色的服装。又是一个艳与寂这一高超的美学境界的范例。
虽然没有能够去陶斯,但陶斯的风景于我不算陌生。一来,欧姬芙以及新墨西哥州的艺术家画了很多的风景画,加上一些摄影作品,从视觉阅读的角度来讲,陶斯这种美国西部小镇以及周边风景,已经有了符号化的意义。再者,有一部2009年出品的欧姬芙的传记片就是在陶斯拍的,片名就叫作《Georgia0Keeffe》,中文译名为《乔冶亚·欧姬芙回忆录》。该片导演是鲍勃·巴拉班,他在2014年导演了颇受好评的《布达佩斯大饭店》。出演史泰格列兹的是杰瑞米·艾恩斯,出演欧姬芙的是托尼奖得主琼·艾伦。这部电影刚出来不久我就迫不及待找来看了,说实话,我挺失望的。故事结构和人物塑造都挺平庸的,琼·艾伦的表演除了尽力模仿欧姬芙外在的孤傲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内心的东西呈现出来,而且,她还没有欧姬芙本人美。在我看来,这部片子呈现的陶斯是最为动人的,荒漠、山丘、烈日、仙人掌,完美的孤寂气质。
曾经有人在我聊到欧姬芙的时候问我,欧姬芙和墨西哥女画家弗里达·卡洛是不是曾经是一对?我有点蒙,努力回忆我脑子里的资料:这两人倒都是传闻中的双性恋,不过,好像两人只在纽约欧姬芙的画展上见过一面,画展上弗里达对待欧姬芙非常热情,这种热情被当时的媒体形容为调情。一对?太玄乎的说法吧。
欧姬芙的孤傲是无人可以比肩的。一个证据是她隐居陶斯沙漠50年;另一个证据是她基本上不怎么读书的,也基本上不和同时代的文学艺术人士来往。据说最牛的事是她游历欧洲时,毕加索想认识一下她,被她拒绝。当然,也没见她对热情的弗里达有过什么评价。但她喜欢D.H.劳伦斯,甚至可以说崇拜他,基本上不读书的她把他的作品读了个遍。当她偶然听说劳伦斯也定居陶斯时,她相当激动,登门拜访。那是1930年。不巧当时劳伦斯夫妇出游欧洲了。欧姬芙在劳伦斯家门口逡巡良久,之后画下了她著名的作品《劳伦斯树》。这画是她在劳伦斯曾经居住的牧场,抬头仰望一棵树得到的灵感。她把这棵树命名为劳伦斯树。那幅《劳伦斯树》是仰视的角度,一棵老树虬结的枝丫以及深色的树冠,顺着粗大的枝干盘旋在目光之上,有晕眩之感,还有爱慕之意。
欧姬芙没有和劳伦斯见过面。错过了。那趟欧游,劳伦斯病逝于意大利,终年45岁。后来欧姬芙认识了捧着劳伦斯骨灰重回陶斯的劳伦斯夫人。仅仅是认识而已。
欧姬芙博物馆里,很多原作是可以拍照的。我拍下来了,而且还和好些作品合了影,留个纪念。纪念品商店里面好多衍生品我没有买,实物的证明没有要紧的,要緊的是我来过了。所谓旅行目的地,目的就在于此,到达现场,目睹原作。作品、建筑、风景,都是原作。到达了,目睹了,看似没有什么,但其实其气息已经进入身体之内,成为自身的一部分。这也是我近年来热衷旅行的一个重要原因。
那天,从博物馆出来,眼前一黑,旋即被炽烈的阳光所笼罩。圣塔菲的干爽、清冽、阳光、蓝天、建筑风格以及街面的各种光影,通透、简洁、色彩饱和度很高。我拍了不少照片,以后可以慢慢翻看。当时我想,不知道自己以后还会不会再来。现在,在书房里写这篇文字,我想,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再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