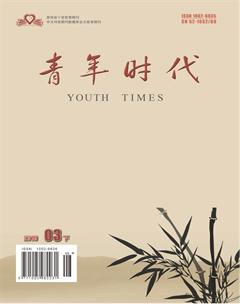看客之眼生命之思
张滢文
摘要:“看客”是鲁迅作品中常见的形象,普遍有着麻木、愚昧,品评他人悲欢离合的不良喜好。鲁迅在作品中尤其是小说中对这类看客通过各种方式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在揭露“看客”无聊荒谬行为的同时也寄予了自己对人该如何生存、生命理应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等哲学问题的思考。本文将主要从鲁迅几篇小说入手,分析其中“看客”形象的异同,并将“看客”分为三个层次,逐层分析鲁迅在讽刺“看客”时对生命存在方式的思考。
关键词:鲁迅;看客;生命存在方式
“看客”故名思议,是指从无论是否合乎道德法律的热闹的人事中尽可能地寻找能使自己感到愉悦有趣的细节,以冷眼旁观的态度挖掘其中低劣的趣味,并永远乐此不疲的人。早在上个世纪,鲁迅就对当时中国普遍存在的“看客”行为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并在他的许多作品,尤其是在小说中揭露“看客”的麻木无知、可悲可恨,以期唤起人们的自省。
从另一方面,鲁迅在对“看客”进行批判时也寄予了他对人生命存在方式的独特思考。不同的看客形象虽各有相似之处,但所体现出的鲁迅对生命存在方式的认识也有所不同。以下将对鲁迅有关“看客”的六篇文章进行三层分析,从不同的“看客”心理解读鲁迅对人生命存在方式的思考。
第一层次的看客,体现在《风波》和《示众》中。《风波》围绕七斤没有辫子展开矛盾冲突。七斤上了城被迫剪掉了辫子,周围的人对七斤赶上了时代剪了辫子有所称赞,但不久听赵七爷说“皇帝坐了龙庭”后就一个个态度大变,对他冷嘲热讽,认为他是犯了皇法,不值得同情,“村人们呆呆站着,心里计算,都觉得自己确乎抵不住张翼德,因此也决定七斤便要没有性命。七斤既然犯了皇法,想起他往常对人谈论城中的新闻的时候,就不该含着长烟管显出那般骄傲模样,所以对于七斤的犯法,也觉得有些畅快。”这里的“看客”是指七斤周围的村民,包括七斤嫂子和赵七爷,他们的关注点实则在于“皇帝是否又坐了龙庭”,而非是否剪辫子,在“看客”所惯有的冷嘲热讽地“看热闹”的心态中便少了几分彻骨的麻木与冷漠。
《示众》则是一篇赤裸裸直接描写“看客”的小说。里面的看客形形色色,有十一二岁的胖孩子、抱着孩子的老妈子、小学生、胖大汉、长子、秃头、卖包子的人,均为苦于奔波生计的社会底层。他们看巡警牵着犯人游街示众,为了挤到前排看的更清一点,在人墙中拥挤、穿梭,甚至后来在人墙外围经过的人力车夫摔倒时,也引起了别的看客们不小的注意,“什么地方忽悠几个人同声喝采。都知道该有什么事情起来了,一切头便全数回转去。连巡警和他牵着的犯人也有些摇动了。”鲁迅在文中没有详细描写“被看者”的状况,只是以肖像描写的方式详细地描绘了“看客”们的神态动作,只是“看”,看犯人,看热闹,因此,讽刺意味就不如《药》《孔乙己》《复仇》那样深刻。
将《风波》和《示众》里的“看客”归入第一层次,是对于其中“看客”们以虚无渺茫、懵懂无知、落后封闭的人生态度过日子的定位。鲁迅以《风波》和《示众》的“看客”来写生命存在方式的虚掷,写生命只是如蝼蚁般苟活于世,以警示后人不能在麻木不仁中沉沦,而要“向上走,不必理会冷笑和暗箭”(鲁迅《热风-四十一》)第二层次的看客,体现在《孔乙己》《阿Q正传》中。
《孔乙己》中的“看客”范围较广,几乎是除了孔乙己以外的所有成年人,孔乙己作为“被看者”孤立无援,酒馆里的掌柜、酒客、路人皆是看客。但鲁迅没有像《示众》里那样直接描写“看客”的形态,却从孔乙己间接的视角反观“看客”。当众人故意说孔乙己偷窃后,鲁迅将孔乙己的表情描述地生动形象,“孔乙己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争辩道,‘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接着便是难懂的话,什么‘君子固穷,什么‘者乎之类,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以镜面的视角反观“看客”的哄笑和快活,更加平静而深刻地表现看客的麻木。
《阿Q正传》里的“看客”与“被看者”的关系则较复杂,鲁迅通过二元对立又相互补充的方式全方位地展现看客,阿Q既是“被看者”,一定程度上也是看客。当阿Q被旁人戏弄时,阿Q是作为“被看者”的形象出现,面对比自己更弱小的小尼姑,阿Q转眼间便成了“看客”,甚至是施暴者,“阿Q走近伊身旁,突然伸出手去磨着伊新剃的头皮,呆笑着,说:‘秃儿!快回去,和尚等着你……酒店里的人大笑了。阿Q看见自己的勋业得了赏识,便愈加兴高采烈起来。”弱者面对更弱者非但没有产生同情,反而也成了“看客”,此处角色的转换从更深层次揭露了“看客”角色本身的虚伪与无意义。
对这第二层次的“看客”,鲁迅着力写出他们身上体现出的是生命存在的无价值和多余,是“零余者”的形象。不同于第一层次的“看客”,而第二层次的看客们已经完全融入了“看客”的角色,对于自己向他人身上施加的心理暴行浑然不知,陷于腐朽丑恶的习俗却不能自知,终会走向存在的虚无与毁灭。
在第二层和第三层“看客”之间,还有一个两者特点兼具的中间形态,那就是《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孤独者》中的魏连殳是一个介于“看”与“不看”之间具有反抗性的形象。他渴望通过自己的方式实现人生价值,以自己的初衷实现抱负,这是“入仕”的方式,不料却处处走投无路,最后只得当军阀杜师长的参谋来生活,这又是一种逃避理想,置身乱世之外的“看客”方式。他既“看”别人,又清楚地知道自己行為的危害,却无法改变自己成为别人“看客”的命运。文中以“我”的口吻写出了鲁迅对这种苟活的生命存在方式的质疑,魏连殳的死也暗示了最终革命理想破灭的现实,生命之存在,理当有着人生的大欢喜。
第三层次的“看客”,除了有着前两个层次“看客”对自己和他人权利与命运的麻木与无知,已上升到了对于家国危难的漠视和对封建恶势力的助纣为虐,而鲁迅也在《药》和《复仇》中将这一类看客写的入木三分,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
《药》中以“夏瑜”为中心,“看客——被看者”可以分为四组,几乎无处不在。第一组是“华老栓——夏瑜”,为了给小栓治痨病,老栓不惜重金蘸取革命烈士夏瑜的鲜血做人血馒头,此处的“看”与“被看”关系是温和的。第二组是“牢头——夏瑜”,夏瑜被捕入狱后在牢房内宣传“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却被代表旧思想旧势力的牢头暴打,形成“看”与“被看”之间更加激烈的冲突。第三组是“康大叔、茶馆的茶客——夏瑜”,对他因宣传革命道理而挨了牢头的打,非但不同情,反而报之以幸灾乐祸,说他“发了疯了”,是“贱骨头”,“看”与“被看”上升到拷问人性生命价值层次。第四组是“满脸横肉的刽子手——华老栓”,间接关系中的“看”与“被看”反映出整个社会已陷入“看客”的泥潭,每个人都身不由己地成为看与被看者。
而《复仇》的两个人物形象,则是从生命与信仰的形而上角度对“看客”进行抨击。路人“从四面奔来,而且拼命地伸长颈子,要赏鉴这拥抱或杀戮”,路人在看,手持利刃面对面的人在互相看,也在看路人,“以死人似的眼光,赏鉴这路人们干枯、无血的大戮,而永远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鲁迅在《复仇》中将看客已经提升到了生命哲学的高度,互相对视的两人的复仇不只是对“看客”的复仇,更是对虚无、无价值人生的复仇,更多的是对不如意的抗争,对嬉笑嘲弄者高贵的蔑视。
在对第三层次的“看客”的描写中,鲁迅为“生命应当以怎样的方式存在”提出了较明确的指向——要抗争,与封建旧势力抗争、与官僚主义抗争、与帝国主义抗争,与所有欺压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恶势力抗争,并且还要不屈服于周围众人的威压,生命中要始终存有希望。
三类“看客”是鲁迅向世人提出的对个人命运、生命价值、民族精神的拷问,层层递进,以期世人在生命的大悲壮与大欢喜中能透彻人生的真谛。对于青年人该如何做,如何使自己的生命更加厚重,鲁迅便在《热风-四十一》中写道:“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份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