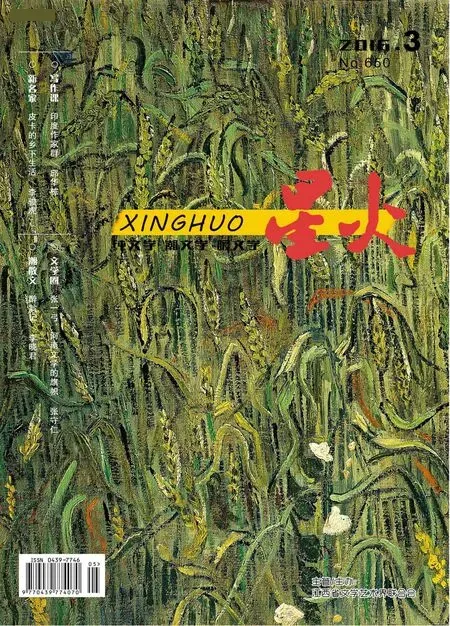我以为你知道
○田 宁

田宁,1975年生,江西上犹人,中学教师。在《滇池》等处发表过作品。江西省第五届青年作家改稿班学员。
庙里念经的声音响了一夜。
呼兰大妈直到后半夜才睡着。一开始,呼兰大妈耳边一直回响着念经的声音,后来窗外的蛙声又加了进来。到了半夜,有人从村庄里走过,村庄里又响起此起彼伏的狗叫声。几种声音夹杂在一起,呼兰大妈就再也没睡着了。
这时正是春夏之交,房间里空气溽湿,席子下面的稻草散发出一股潮乎乎的霉味儿。被子那么重,呼兰大妈觉得自己快要喘不过气来,胸口像是压着一块大石头,每吸一口气都要用尽全身的力气。到了后来,呼兰大妈终于忍受不住,用脚把被子踢开一道缝隙。一股凉气顿时从被子底下钻进来,呼兰大妈这才觉得舒服一些。
进入春天之后,天气逐渐变暖,呼兰大妈的梦也渐渐多起来。在梦里,各种场景走马灯似的换,人也走马灯似的换。有时候是丈夫,有时候是儿子,有时候是死去的父母,有时又换成别的一闪而过的面孔。每一次这些人都面目模糊,像是隐藏在一片灰蒙蒙的雾里。有时候呼兰大妈试着伸手去抓,一个都抓不住。有那么一次,她就要抓住丈夫的一片衣角了,却还是没能牵住丈夫,自己却差一点被脚下的一片杂草绊倒在地。那一次,呼兰大妈在梦里就哭了起来。好在每一次呼兰大妈从梦里醒来,梦境也就离她而去,除了稍微觉得有点头晕,梦里的人和事都只剩下一片淡淡的残影。很多个早晨,呼兰大妈都是躺在床上看着蚊帐顶,任由那片残影在眼前慢慢消失,然后才起床穿着洗漱,开始新的一天的生活。
这天夜里,杂乱的声音让呼兰大妈难以入睡,梦自然就迟迟没做,直到凌晨,呼兰大妈才终于在一片零碎的梦境中看见了儿子。几天没见,儿子的眼窝深深凹陷下去,在脸上形成两个小小的坑洞,显得更消瘦了;儿子左边的脸颊上有一块血污,无论怎么擦都擦不干净。梦里的儿子推着一辆独轮车,呼兰大妈紧跟在儿子身后。和过去的梦境一样,呼兰大妈用尽全力还是追不上儿子。一番费力的追逐之后,儿子忽然陷进了一处沼泽地。呼兰大妈眼看着泥水一点点漫过儿子的脖颈,漫过儿子脸上的血污,儿子的眼睛却一眨不眨。呼兰大妈急得一下子惊醒过来。就在这时,堂屋神龛上的老式座钟咚咚敲了六下。呼兰大妈睁开眼睛,看见灰亮的光线已经透过窗户射了进来。
呼兰大妈坐起身,披起挂在床头的衣服。这一次,梦里的情形没有像往常一样立刻消失,儿子脸上的血污以及沼泽吞没儿子的情形重新浮现在呼兰大妈的眼前。
“我的心肝肉!”
呼兰大妈听见自己在心里喊。她闭上眼睛靠在床头,直到儿子被沼泽吞没的幻象慢慢消散才重新睁开眼睛。呼兰大妈擦干净眼角的泪渍,掀开被子下了床,两只脚在床前一阵摸索,找到鞋子穿上,打开房门,来到厅堂。由于厅门紧闭,厅堂四面又没有另外安窗户,所以尽管在卧室里已经感觉到天亮,厅堂里却还是一片漆黑。呼兰大妈在漆黑里移动脚步穿过厅堂,摸索着取下门栓。呼兰大妈打开大门,一眼看见整个村庄笼罩在一片乳白色的浓雾里。这时庙里念经的声音已经停了,雾里的村庄响起一些别的声音:鸡叫,牛哞,猪哼唧;有人吱呀一声拉开大门,有人沉重地咳嗽。
鸡埘在篱笆和墙相连的地方,这会儿鸡正在疯狂地剥啄鸡埘上的木板。
“人都还没吃,你们吵什么?”
呼兰大妈嘴里骂着走到鸡埘边,抽出木板,几只羽毛灰暗的母鸡立即冲了出来,争先恐后奔向院子里的食槽,抢食那里前一天剩下的米糠。呼兰大妈拿起一根竹片,一边撵鸡,一边在食槽壁上刮了几下,还是刮下了一小撮米糠。只一会儿工夫,米糠就被母鸡们啄食干净。见没什么可吃的了,母鸡们便四面散开翻啄院子里的杂草。几天没有清理,院子里的杂草又长高了不少。
早饭是前一天留下的饭菜。谷雨过后,呼兰大妈就吃得很少,有时早上做好一锅饭菜能吃上一整天。现在又正是地里的瓜菜断帮的时候,菜做来做去都是那几样,四季豆,莴苣叶,四季豆,莴苣叶,看着就没有胃口。呼兰大妈将饭菜在锅里热了一下,将就着吃下。吃完早饭后,阳光透过雾气照过来,雾就开始慢慢散了。庙里念经的声音又响了起来。呼兰大妈把一张椅子拖到门口,坐着听念经的声音。有那么一会儿,呼兰大妈仿佛又进入了某个梦境,梦里人声鼎沸,呼兰大妈牵着儿子的手在人群里穿梭。醒来之后呼兰大妈恍惚想起这不是梦,很多年前,儿子还小的时候,为了买一样东西,她的确这样牵着儿子在集市上的人群里穿梭。呼兰大妈坐了一会儿,把椅子拖回屋里,进了卧室,打开衣柜底下的抽屉,取出一个纸包。纸包里面是一些零钱,呼兰大妈数了数,一百二十三块零七毛。呼兰大妈取出其中的一百二十块钱,把纸包重新包上放回抽屉。关上抽屉,想了想,又拉开抽屉,把纸包打开,把取出的钱放回去,把纸包整个儿装进衣服口袋里,回到堂屋,关上门出去。
村庄的轮廓渐渐从雾气中显现出来。一溜砖房静静矗立在村子东边,一个个门洞像一张张张开的嘴,黑乎乎的什么都看不见。当然啦,就算什么都看不见,呼兰大妈也知道哪个门洞里住着什么人。最东边那栋独门独院的一层楼高的砖房里住的是余婆和她瞎眼的丈夫,靠近余婆家的那栋两层楼高的砖房里住的是驼背的胡婆,接下来是松太公和瘫痪在床上的松太婆,然后是妻子死去多年的清源阿公……村子正中是一些高高低低的老房子,往西一带延伸到河边的是一片广阔的农田。从前这个时候,田里应该已经栽上了秧苗或其他庄稼,绿油油的看着就让人心里高兴,人们在田间地头高声说话;如今那里则是大片大片疯长的野草。
这时雾气已经散尽,阳光下的天空明净高远。一只老鹰出现在村子上空。呼兰大妈停下脚步,仰头看着老鹰在天宇下忽高忽低盘旋,忽然想起出门的时候没把母鸡关进鸡埘,不知道它们能否躲过老鹰的攻击。这时村庄里响起一阵敲打空竹筒的声音,看来是有人也发现了天上的老鹰,于是敲打竹筒发出警告。老鹰在空中盘旋了一会儿,忽然振翅朝北边飞去,然后消失在碧蓝的天空里。呼兰大妈用眼睛追着老鹰,直到老鹰变成一只黑点,才低下头接着移动脚步。
也许时间还早,通往庙里的路上除了呼兰大妈,没有别的人。不过就算时间再晚一点,路上也不会有什么人。这几年,年轻人纷纷离开村庄,村庄一天天变得荒凉冷落;村庄里能走动的老人已经不多,他们就是走动也只是就近在邻居家里坐一坐,而不会冒险走到大路上来。很久以前,这还是一条漂亮的柏油公路,从县城方向延伸过来,穿过村庄后一直通向遥远的北方。后来路面渐渐变得坑洼不平,每一次车从路面碾过都要扬起一阵尘土;再后来公路改道从河边绕过村子,这条路也就渐渐废弃了。路的两边长满了杂草,人们扫出的垃圾直接倾倒在路边。从前这条路有车经过的时候,村庄里还能听见司机们经过时按响的喇叭,尽管略嫌嘈杂,倒也是难得的动静。等到这条路荒弃之后,村子就彻底冷清了下来。
上了一小段坡路,呼兰大妈隔很远就看见了庙门口那几棵梧桐,心里忽然紧张起来。梧桐树浓密的树叶上面,隐约可见伸出的一角琉璃瓦飞檐。呼兰大妈转过身,回头看向村子,路上依旧不见一个人影,自己家那座用篱笆围起的老房子倒是突兀地出现在视野里。
庙里念经的声音一直响个不停。那声音听起来只有一个腔调,中间夹着木鱼不间断的敲击声,感觉像是由不得人喘息。呼兰大妈不觉加快了一点脚步。这样一来,呼兰大妈的脚步是加快了,但同时,喘气的声音也更加浊重。换做二十年前,两里多的路程根本不算什么,一杯茶的时间也就到了;但是现在,呼兰大妈走到庙门口,却几乎用了将近一顿饭的时间。好在一路上确实没有遇到什么人,但如果耽搁的时间再久一点,那就很难说。
庙门早就开了,安装在门上面一角的一只小广播里正源源不断地传出念经的声音。那种嗡嗡嗡的声音从广播里面传出来,如同千万根看不见的丝线穿进人脑的缝隙里;又像一条宽阔无边的河流,慢慢地将人从脚到头一点点淹没。
从昨天夜里开始,呼兰大妈就感觉自己像条鱼,顺着诱饵一直游到了这里。
“有人在吗?”呼兰大妈拍打着庙门,木质的庙门发出邦邦邦的声音。也许是广播里念经的声音盖住了拍门声,没有人回答。
“里面有没有人?”呼兰大妈把门拍重了一些,继续问。
“谁呀?”这一次,东边厢房里传出一个男人的声音。
“是我……”呼兰大妈回答。
“我就是问你是谁……”
呼兰大妈没有回答。
“是来给菩萨过生日上礼的吗?”
呼兰大妈还是没有回答。
“那麻烦你到佛堂等我一下,”男人没有等到回答,接着说道,“我马上就来。”
呼兰大妈站在庙门口看过去,正对庙门的是一溜十五六级的台阶,台阶上布满斑斑点点的暗红色血迹,那应该是远近进香的人们宰杀公鸡后留下来的鸡血。很多年以前,也就是丈夫生病那会儿,呼兰大妈也曾经和儿子提着公鸡来到这里杀鸡敬神,希望庙里的菩萨能够保佑丈夫挺过难关。那时候儿子的手一挥,刀子在公鸡的脖子上一抹,鸡血就飞溅出来。当时垂死的公鸡突然挣脱儿子的手在地上一阵扑腾,搞得鸡血四处飞溅。尽管呼兰大妈觉得自己和儿子对菩萨们表达了足够的敬意,丈夫终究还是没能挺过去,在那年秋天死去。从那以后,呼兰大妈再也没来过这里,现在看来,那么多年过去,庙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台阶的上面,就是男人说的佛堂。和过去相比,佛堂看起来高大了不少,左右厢房的位置,原来种满了密密麻麻的梧桐,现在只在东西两边各留下一棵,树根的部位被水泥围成花圃的样子。扩建的佛堂加上左右厢房,原先的小庙就变成了眼前这样一座大庙。早先呼兰大妈来敬神的时候,一进门就能看见庙里供着的神像,那时庙里的陈设也简单;现在庙门往下推出那么多,站在门口只能看见眼前的这十多级台阶,佛堂里的一切则隐藏在一片深幽的灰暗里。
“是你?”
呼兰大妈听见一个男人惊愕的声音,回过神来,看见一个男人正从东面厢房出来,两只手一边往上提裤子,一边扣裤腰上的皮带。
“是你……”呼兰大妈看清楚男人的样子,也吃了一惊。
“对,是我。”男人脸上的表情由惊愕变成惊喜,接着就有一丝慌乱。呼兰大妈看着男人,无数往事像放电影似的从脑袋里呼啸而过,一些往事突然变得清晰无比,眼前这个男人的形象夹杂在这些混乱无章的往事里,显得尖锐而突兀。呼兰大妈觉得心里一阵翻腾,差点站立不住,赶紧伸手扶住门框。但接着,往事又像潮水一样呼啦啦迅速退去,那些纷繁的影像顷刻之间又消失得无影无踪,只留下呼兰大妈站在庙门口,不知道是该进去,还是该转身往回走。
“你是来给菩萨上礼,还是来看我?”男人短暂的慌乱之后,恢复了镇定。
“你怎么在这里!”
“我在这里守庙。我没想到会是你,我刚才在拉屎。你快进来,到这儿来,让我看看你……你怎么站着不动?你不会是专门来看我的,你肯定以为我早就死了……这么多年,你是不是以为我死了……你是来给菩萨上礼的吧,那就快进来,站在门口怎么上礼?”
呼兰大妈转身看向来时走过的路,通往村子的那条路上依旧空无一人,道路两边的杂草肆意疯长;路边的一片荒田里,一头牛在低头扯着田里的嫩草;远处的村庄笼罩在一片明晃晃的阳光下,一些砖房外墙的马赛克瓷砖像是一些玻璃碎片,那些碎片正将阳光反射出来,一忽儿明亮,一忽儿又暗下去。念经的声音这会儿像是泛滥的河水,正漫过村庄和田地,漫过远处的山岭。呼兰大妈站着想了想,终于还是跟着男人上了台阶。
进入佛堂,呼兰大妈就看见佛堂正中一张铺着红布的神桌上摆放着菩萨的塑像,菩萨前面左右两只电蜡烛泛着红光,一盏油灯已经熄灭,几只红色的纸包并排放在菩萨面前的托盘里,两对铙钹放在桌角;神桌的前面是四只蒲团。男人看见熄灭的油灯,给油灯重新上油,点亮灯芯,呼兰大妈立刻就闻到了一股香腻的花生油的味道。
菩萨后面则是一字排开的众多神像,有的慈眉善目,有的面目凶恶,有的胖,有的瘦。在呼兰大妈每年都要来庙里敬神的那些年月,庙里的神像就是这样了。但更早一些时候,呼兰大妈也曾经亲眼看见庙里的神像在一夜之间被人砸成碎片,整座庙被拆成一堆瓦砾,有用的一些木料则被人们搬回了自己家里。有人为了抢夺庙里有用的东西还打了起来。那时尽管庙成了一片废墟,每逢年节还是有不少人就着废墟杀鸡,把香烛插在石头堆里,和之前一样敬神。
“我们多久没见了?有二十年?我们都老啦……不对,在我心里,你永远都是十四岁的样子,那时候我们在油菜花地里,你还记得吗……是我老了……我记得很清楚,最后一次见你的时候,你把头发盘在头顶,像极了庙里的菩萨……我现在在这里守庙,天天守着这些菩萨,就想起你的样子……你还好吗?”男人见呼兰大妈坐着一动不动,一边说话,一边给呼兰大妈倒来一杯茶,放在呼兰大妈面前的桌子上。呼兰大妈端起茶杯。几片茶叶的碎末在杯子里上下浮动,茶杯的杯缘上有一层暗黄色的茶垢。呼兰大妈凝视着茶杯看了一会儿,猛地把茶泼在地上。
“你这是做什么?”
“你的茶脏。”呼兰大妈说。
男人看着呼兰大妈,忽然笑了起来。“你生气了,哈哈,你生气了。”
“很好笑?你觉得很好笑?”
“当然好笑,我们那么久没见,一见面你就生气。你自从看见我,就一直板着脸,看都不看我一下,你一定是怪我这么久都没来找你,现在回来了,也没来看你,你为这个生气,我当然高兴。”男人慢慢收住笑声,接着叹了一口气,“你生气的样子真是一点都没变。”
“我变不变,都不关你的事。”呼兰大妈说。
“怎么不关我的事?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这辈子就只喜欢过一个女人,那就是你。”
“你除了一张嘴,没别的本事。”
“你承认了,哈哈,你承认我这辈子只喜欢你一个女人。你知不知道,”男人忽然停住笑,凝视着呼兰大妈,一字一句说道,“我做梦都想和你上床。”
“你做梦!”呼兰大妈站起身,往后退了一步,脚下差一点被一只蒲团绊倒。
“是,我是做梦,要不是那个婊子养的杂种先上了你的床,你看我是不是做梦!”
“他是我丈夫,不准你这样说他!”
“你还是向着他,你一辈子都向着他,自从那杂种上了你的床,你就替他说话,你就把我们说过的那些话全都给忘了,我们在油菜花地里发的誓你也忘了……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片油菜花,那时候我们紧紧抱在一起……那个婊子养的杂种,他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打骂你,可你还是向着他,”男人泄气地坐到凳子上,“你倒是说说看,论长相论本事,他哪样比得上我?”
“他比你更像个男人。”
“你是说在床上他更像个男人?我们只是亲过抱过,又没上过床,你没试过我床上的本事,怎么知道我比不上他?”男人看着呼兰大妈。
“你这样不害臊,我不跟你说了。”
“你不跟我说,那是因为你知道,我的确比他更有本事。那杂种仗着自己有几个钱,管着村里几个破仓库,就会勾引女人上床,除了这个,他没别的本事!”
“你有本事,我一个人没依没靠的时候,你在哪里?他们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把我的衣服撕下来的时候,你在哪里?我一个人哭得昏天黑地的时候,你在哪里?他对我很好,不会丢下我不管,他帮我埋掉父亲,赶走那些上门催债的人,还清父亲欠的那些钱,他就是个男人。父亲养了你十几年,事到临头你却像条狗一样夹起尾巴!父亲瞎了眼,我也瞎了眼!如果不是你到处对人说迟早要把我搞回你的床上,他哪里会喝醉酒,哪里会打我骂我?就算是这样,那年你被人捆起来吊在村头用棍子下死命抽,如果不是他帮你还清赌债,你都不知道怎么死。倒是你,拿了他给你的钱就不见了人影,和我需要你出现的时候一个样。现在你还有脸回来,你说,你有什么资格说他。”呼兰大妈看着男人,一口气说了下去。
“你变了,呼兰,你变了。”男人盯着呼兰大妈看了好一会儿,然后说道。
“你没变,和从前一样没种。”呼兰大妈干脆利落地回答,“要说你有什么变化,就是比从前更下流,更不害臊!”
“他有种,他不下流,他除了有几个臭钱,还有什么?有钱很了不起?”
“有钱没什么了不起。他有钱没钱,都是个男人。”
“如果有钱的是我,我也会这么做。”
“你什么意思?”
“他帮我还债,给我钱,就是要我离你远点,”男人说,“这狗娘养的,他骗不过我。”
“他救了你的命。”
“我的命不值钱。自从他上了你的床,我的命就不值钱。”
“你什么都好,就是没良心。”呼兰大妈看了男人一眼,伸手扶着桌子,慢慢又坐了下来。
男人看着呼兰大妈,忽然叹了一口气:“算了算了,事情都已经过去二十多年,说得再多也没用。你来这里肯定不是来看我的,那你来干什么?是给菩萨上礼?他现在怎么样?照说他想得到的东西他都得到了,应该活得好好的,没那么快死。”
呼兰大妈看着男人。
“你放心,我不会对他怎么样,我要是想对他怎么样,就不会只在这里守庙了。我如果要杀他,那天看见你们滚到一起的时候就已经宰了他,现在我对杀他没兴趣,最起码现在没有。”男人看见呼兰大妈脸上奇怪的表情,说。
“你就这么恨他?”
“我不恨他,我谁都不恨。”男人说,“要说恨谁,我这辈子只恨一个人,那就是我自己。他该有七十了吧?我记得他比我大十来岁。”
“我以为你知道。”呼兰大妈低下头看着地面。
“我知道什么?”
“他死了,你走后第三年,他就死了。”呼兰大妈抬头看了一眼菩萨。菩萨垂着眼睛坐在神桌上一动不动,镀着黄铜的塑像在照进佛堂门口的阳光的反光里流动着一层神秘的光影。“是肺癌。”呼兰大妈说。
“你怎么不告诉我这些?没人告诉我这些。”过了好一会儿,男人说。
“告诉你,又能怎么样?那时候,在我心里,你早就死了……有人说你去了广东,有人说你死在福建……没死又怎么样?你活着除了喝酒赌钱,还会干什么?你当年依靠不上,以后更依靠不上!”
“我为什么喝酒赌钱,难道你不清楚?”男人说。
“清楚不清楚,只有老天爷才知道。”呼兰大妈说,“清楚又怎么样?他死了,你还活得好好的,这就是命,我们都斗不过命。”
男人不说话。庙里突然变得安静下来。念经的声音像是被挡在了佛堂的外面,又或者这声音塞满了庙里的各个角落,反而听不到了。油灯里的灯芯发出细密的嗤嗤声,花生油的香味更浓烈地弥散在佛堂里。
“要我说,他死得好。”男人长长呼了一口气。
呼兰大妈看着男人,男人毫不示弱地看着呼兰大妈。“他毁了我这辈子,现在看起来,也毁了你这辈子,我犯不着为他的死难过。”男人说,“他死得越早,我越高兴。”
“你高兴?他就算死了,都比你强,他活着你斗不过他,死了你照样斗不过。”
“这老杂种!”
“你就一张嘴,除了这张嘴,你什么都没有,”呼兰大妈说,“可那时候,我还是希望你像个男人。”
“你真这么想?”男人看着呼兰大妈。
呼兰大妈却又不看男人了。一个女人的身影出现在台阶下的庙门口,呼兰大妈突然紧张起来。女人抬头向佛堂张望了一下,也许是没有看见光线灰暗的佛堂里的两个人,女人的身影又消失在庙门口,一眼看过去,从庙门口直到更远处的村庄,又什么人都看不见了。呼兰大妈的心慢慢又放下来。
“你真的希望我像个男人?”男人接着问。
“我希望又有什么用?你做不了男人,那时候,我们这种出身的人,能保命就是老天保佑了。你父亲死的时候把你托付给我父亲,我父亲把你养在家里,到死都没把你说出去。可我父亲还是受不了那些人的折磨,死了,死的时候,脚上连双鞋都没有,你又能怎么样?”呼兰大妈的声音渐渐低了下去,父亲光着脚死去的形象恍惚又出现在眼前。
“算啦,你说的那些事,我早就忘光了,”过了一会儿,男人挥了挥手,像是要赶走什么东西,“……他怎么死的?刚才你说是肺癌?”男人问道。
“是肺癌。他咳了好几个月,身上起了好些脓包,镇上的医生叫我找些草药敷在脓包上,可这几个消下去,另外一些又长出来。一开始我们都以为是梅毒。村里的人都知道,你也知道,他在冷水滩那边有个相好,我听说那个女人不止他一个相好,身上不干净……”
“是冷水滩姓胡的那骚货?”
“就是她。后来有人说是肺痨,因为咳出肺热,所以身上才长脓包。我们用了各种土方子,也来这里拜过菩萨。最后不行了,我和文武才推着他去了医院,检查出是肺癌……后来又拖了一年多,那一年霜降才死。”
“他在外面有相好,你还说他对你很好?”
“他有相好是一回事,对我好是另外一回事。我是个女人,我还能怎么样?最起码他活着的时候,每天晚上还能和我睡在同一张床上,在儿子面前,保住了我的脸面。我是女人,我只能要求这么多。他好这口,你又不是不知道。没有冷水滩姓胡的,还会有别的女人。”
“我没说错,他就是个杂种!”
“他得了这个病,家里先前存的钱不久就花光了。牛卖了,猪卖了,拖拉机也卖了,能卖的东西都卖得差不多了,换来的钱还是不够治他的病。去一趟医院要一两千,向亲戚借钱,那个时候,哪家都没钱,能借的都借了,不能借的厚着脸皮也借来一点,到他死,光借的钱就四五万。那时候,起一栋屋都不用一万呢,我们倒好,一下子就欠了四五万。那时孙子又刚出生,没什么吃的,饿得嗷嗷叫,苦了文武和他媳妇,文武那时候才刚满二十二岁呢,头上就已经见白了……”
呼兰大妈自顾自说下去。有那么一会儿,呼兰大妈仿佛觉得周围的一切都好像又不存在了,男人、香烛、菩萨、佛堂全都漂浮在一片茫然的虚空里;在这一片茫然的虚空里,念经的声音却像潮水一样一阵接一阵地扑过来,自己的声音则像一股轻烟,在扑面而来的潮水的拍打之下四面飘散,终于无迹可寻。多年来呼兰大妈不止一次说起丈夫,说起丈夫的病,说得多了,这些事情就好像和自己没什么关系了。刚开始那几年一说起丈夫,呼兰大妈的眼泪就止不住地流,后来慢慢地,眼泪就没有了,再后来,眼泪又为别的事情而流,留给丈夫的眼泪就彻底没有了。当然了,要说眼泪彻底没有了也不对,在那些迷迷糊糊的梦里,呼兰大妈还是流过好几次眼泪。但这一次却不一样,呼兰大妈分明觉得自己的眼泪好像已经到了鼻子那里,马上就要流下来。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眼前这个和自己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的男人?呼兰大妈说不上来。男人这个时候已经为呼兰大妈倒好另一杯茶。呼兰大妈看了男人一眼,把茶杯端起来握在手里,感觉茶的温热穿过玻璃一点一点透进掌心,呼兰大妈的心情也就慢慢平复下来。
从一开始看见男人,呼兰大妈想到的就是一张渔网,而她和男人就是网上相隔遥远,却用千万根丝线连在一起的两个结点。
呼兰大妈喝光杯子里的茶,把茶杯放回桌上。阳光慢慢偏离佛堂门口,转移到了台阶下面,佛堂里的光亮因此稍微暗下去一点。坐在呼兰大妈的位置,可以越过山门的顶端隐约看见通往村子的那条路。这个时候,大马路上偶尔会有一两辆车疾驰而过,到了通往村庄的路口,车子就调转车头拐向了河边新修的公路,一转眼就消失在路的尽头;通往村子的那条路上依旧没什么人影,只有阳光更热烈地铺洒下来。
“今天是菩萨的生日?”呼兰大妈问男人,“看样子没什么人来。”
“你是听到念经的声音了吧?昨天夜里开始念经,做法事,后天才是正日。”男人为呼兰大妈把茶倒满,“这几天先收礼,算人数,后天才摆酒席。”
“上礼……要多少钱?”
“不上席,五十;上席,一百;有事专门求菩萨保佑,就要两百。”男人说。
“两百……”呼兰大妈听见自己的声音一点一点低了下去。
“你有事求菩萨?我就说你一定是有事情才来这里,你怎么可能专门来看我,你根本不知道我回来了……那就两百。升官,发财,生儿子,求姻缘,保佑一家老少没病痛,都可以。”男人说,“你别看菩萨闭着眼睛,菩萨什么都看在眼里。”
“我丈夫得病的时候,我也来求过菩萨,可他最后还是死了。”呼兰大妈说。
“那肯定是你不虔心,心诚才灵。”男人说,“也可能这就是他的命。你说过,人斗不过命。”
“我们和别人一样杀了鸡,上了香,拜了菩萨,还要怎么才算虔心?”
“那你有没有捐香火钱?”男人想了想,说。
“什么香火钱?”呼兰大妈问道。
“就是你上香敬神的时候,有没有另外捐钱给庙里。”
“我连给他治病的钱都没有,哪里还有别的钱?”
“这就对了,”男人说,“没捐香火钱,菩萨怎么保佑你?你知道圩镇背后有户人家,每年来敬神都捐香火钱,不是一百就是两百,他家的儿子一年升一次官,现在官做大了,全家都搬到省里去啦。后天菩萨生日,他家人肯定要开车回来。”
“河对面有户人家,每年也给庙里捐钱,前年出了一场车祸,一家人一下死了三个。杨梅坳有户人家,每年千里迢迢来给庙里捐钱烧香,去年一场大火,全家烧个精光。我们这个村子,每年多少人给庙里捐钱,不也死的死老的老病的病……”
“我不和你争,”男人的脸红了,“我去年才回来,你说的那些事我根本不知道。有没有看到菩萨面前那些红色的纸包?里面装的都是已经捐了两百块香火钱的人的名字。那么多人信菩萨,总不会大家都是傻子。这几天做法事,这些名字沾了香火,菩萨就能保佑到他们了。”
“照你的意思,求菩萨保佑,就要花上两百块钱?”过了一会儿,呼兰大妈问男人。
“不是‘花’,是‘捐’,对菩萨不能说‘花钱’。”男人说。
“都是一回事。”
“你还是那么倔,呼兰。”
“现在我问你,要求菩萨保佑,是不是一定要两百?”呼兰大妈看着男人。
“两百块,一分不要多,一分也不能少。”男人说,“庙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查一次账,我们是老相好,但是钱的事情,必须明算账。”
“谁和你是老相好!”呼兰大妈说。
“那你求菩萨什么事?”看见呼兰大妈板下脸,男人笑了笑,“求菩萨让那杂种活过来?熬了这么多年,想男人了?”
“就算到死,你的狗嘴里都还是不说人话。”呼兰大妈站了起来。
“好啦好啦,别生气啦。”男人感觉到呼兰大妈是真的生气了,“你看来没什么事要求菩萨嘛,那杂种是死了,但那是好多年的事情了,现在你有儿子有孙子,好好在家里享福就是了,用不着在这里花这些钱。哪像我,孤老一个。”男人说,脸色突然黯淡了下去。
“你现在也是一个人?”呼兰大妈看着男人。
“可不是。那年我离开村子,东一个地方西一个地方,到处走。我去了福建挖煤,你知道的,很多人都去了福建挖煤,我也跟着去了,不过没死。再后来回到隔壁县,我不想回来,这个你知道……遇到一个寡妇,招了我,就住了下来。前些年,她死了,她儿子把我赶出门,我和她没有生养,孤老一个,也没别的地方可去,就转了回来,到这里做了庙佬。这也是命。呸,”男人朝地上吐了一口痰,“不说了,人这一辈子,怎么过不都是一辈子?咦,刚才你说我也是一个人,怎么,你现在也是一个人?”
“我以为你知道。”呼兰大妈说。
“我不知道。我知道什么?”男人说,“是文武不养你?这小杂种,那时看着都还好,现在这么坏吗?到底是那老王八的种……”
“他死了。”呼兰大妈打断男人的话。
“死了?你说你儿子,文武,也死了?”
“他也去了福建挖煤,煤窑塌下来,人就死了。”呼兰大妈说。
男人看着呼兰大妈。呼兰大妈却不看男人。呼兰大妈的眼光穿过佛堂门,越过庙门上面的琉璃瓦飞檐,看向更远的村庄。这时候的村庄在阳光下依旧一片静谧。太阳已经升到半空,地面上的水汽已经蒸腾殆尽,远处的村庄在碧蓝的天空下显示出更加清晰的轮廓。呼兰大妈的目光在村庄上空游移。“他爸治病欠下那么多钱,听说去福建挖煤赚钱快,他就跟着去了,没想到煤窑会塌下来,他又瘦,没跑出来,就死了。”
“这也是命。”过了好一阵子,男人叹了口气,说,“老板赔了多少?我记得应该有这个数。”男人伸出三根手指。
“25万。”呼兰大妈摇了摇头,“人都不在了,钱有什么用。”
“那总比没有好。”男人说。
“赔的钱还清家里欠的债,还剩下一些。新妇说孙子还小,将来上学读书、盖房子娶亲都得用钱,就把钱存了起来。再后来,新妇就带着钱和孙子走了。”
“走了?去了哪里?回她娘家去了?”男人瞪大眼睛。
“不知道。这样也好,新妇还年轻,总是要嫁人,有了这笔钱,孙子也饿不着。”
“你蠢啊,没钱,你一个人,怎么养活自己。”男人叫了起来。
“我不也活到了现在?”呼兰大妈说,“没有钱,我不也活到了现在?丈夫死了,我还有儿子;儿子死了,我还有孙子;孙子走了,我一个人,十几二十年,不也活到了现在?不也活得好好的?一个人,又怎么样,我照样能活。”呼兰大妈看了一眼男人,伸手扶着桌子慢慢坐了下来。男人看着呼兰大妈,突然笑了起来。
“好,好,没钱你照样能活,你是神,是仙,不吃饭也能活,行了吧?”男人说,“我还不知道你,你就是死鸡脖子硬。”
呼兰大妈不再说话,广播里一直响着的念经的声音不知什么时候也已经停止。男人见呼兰大妈不做声,也不再说话。庙里又安静了下来,整个佛堂里就只有油灯里的一根灯芯在咝咝作响。男人翻开一本账簿,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名字,男人一边对照着账簿拨打算盘,一边在账簿上做一些标记,整个佛堂里又只能听见算盘噼里啪啦的回响了。
男人对完一页账簿,抬头看了呼兰大妈一眼,见呼兰大妈还是端坐在凳子上,一只脚轻轻拨弄脚边的一只蒲团。这时一群麻雀呼啦啦从外面飞过,其中一只撞进了佛堂,在梁柱之间扑棱着飞来飞去,好一阵子找不到出口。男人的目光追着麻雀在梁柱间绕来绕去,直到麻雀终于找到出口,唧啾一声消失在门口,男人才调转目光,继续对照账簿拨打算盘。
“一定要两百?”呼兰大妈忽然开口问道。
“你要求菩萨保佑,那就是两百,一分都不能少。”男人停止拨打算盘,把账簿掉转过来朝向呼兰大妈,“你看,账目都在这里。”
“我不用看,也看不懂。”呼兰大妈说,“字是你写的,你想怎么写都行。”
“你不相信我?”
“我谁都不信。”
“那你信不信菩萨?”
呼兰大妈不说话。男人看了看呼兰大妈,忽然笑了起来。“我知道了,你没钱,你身上没有两百块钱。你想求菩萨保佑,你想让我把你的名字也装进纸包里,让菩萨保佑,可是你拿不出两百块钱,所以才这么说,被我说中了,对不对?”
呼兰大妈一动不动地看着男人,神色平静,脸上既没有悲伤,也没有男人意料中的羞愧。男人被呼兰大妈这样看着,倒觉得不好意思起来,讪讪地收起笑脸。“这年头,一个人再怎么样,身上两百块钱还是有的,对吧?赔了那么些钱,就算被你新妇全都卷走了,多少还剩下一些,对吧?你一个人又不花什么钱,两百块还是有的。”男人收回自己说的话。
“我没有。”呼兰大妈说。
“你有。”
“我没有。”
“你有,我说错了还不行吗?”男人焦躁起来。
“我没有。我没有两百块钱。”呼兰大妈从里面口袋里掏出纸包,“我只有一百二十几块钱,没有两百。”
男人看着呼兰大妈把纸包里的钱抽出来,不动声色地一张一张摆在桌面上,男人脸上的表情阴晴不定。
“你想怎么样?”最后还是男人忍不住开口问道。
“我有事求菩萨,你要把我的名字写进红纸包里,但我没有两百块钱。”呼兰大妈说。
“我办不了。没有两百块钱,我办不了。”男人的口气坚决起来,“我只负责守庙,做不了人情。”
“你做得了。”
“你真是倔得要命,呼兰呀呼兰,要怎么说你才明白?我……”男人提高了声音,看着呼兰大妈不动声色地坐着一动不动,男人心里一动,眼睛忽然迷离起来,“我……做得了……我做得了……可是我为什么要帮你?”
“我们是老……相识。”
“这可不够。”
“我丈夫曾经给过你一笔钱。”
“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我记不起来了。”男人的眼睛盯着呼兰大妈。
“你还说过,我是你喜欢过的唯一的女人。”
“那又怎么样?”
“这还不够?”
“不够……还不够……”男人目不转睛地看着呼兰大妈,嘴里喃喃自语。
呼兰大妈看了一眼男人,在男人的眼睛里,呼兰大妈看到了一片潮湿。呼兰大妈低下头。佛堂里静得只听见男人呼吸的声音。过了一会儿,呼兰大妈抬起头,转头看着菩萨,菩萨依旧眼皮低垂。“你说过,菩萨什么都看得见,你就不怕?”
“菩萨闭着眼睛,什么都看不见。”男人说。
呼兰大妈躺在男人的床上,从头到尾没有发出一点声音。无论是身上承受男人的重压的那一瞬,还是身体深处传来异样的感觉的时候。男人一开始还只是双手哆嗦着慢慢探索,但呼兰大妈的木然不动让男人的动作突然暴烈起来,男人开始奋力撕剥呼兰大妈的衣服。有那么一刻,男人面对呼兰大妈惨白的、一览无余的身体,浊重的呼吸突然停顿下来,眼睛里有一刻的茫然和退缩,但接着则是更猛烈的撞击。
在男人压上身体的一瞬间,呼兰大妈就仿佛掉进了一个辽远的梦里。在梦里,呼兰大妈的身体在短暂的、撕裂的疼痛之后就开始了漫无目的的漂游。二十年?还是五十年?呼兰大妈觉得时间陷入了一片混沌。母亲的笑容温暖而模糊,父亲僵直的身体冰冷却遥不可及;童年时采摘的一朵小花,分娩时儿子响亮的啼哭;丈夫终于死去时黑瘦而严肃的脸,少女时代第一次来月经时的羞涩与恐惧;一片耀眼的油菜花,一双痉挛的手……然后,呼兰大妈感觉身体突然迅速下坠,坠向一片更加深广无边的黑暗。在那里,村庄里活着或死去的人的浮肿的脸漂浮在虚空里,疾病时的痛、漫长的无人过问的孤苦、梦魇时的辗转反侧、屋梁上黑漆漆的棺材、深夜里突然响起的敲门声、潮湿而沉重的被褥、衰老的身体、日复一日的绝望……人一生中经历的痛苦如同一股来自地狱的飓风,将呼兰大妈卷向黑暗的更深处。忽然飓风停止,一缕喃喃的念经的声音在黑暗中响起,声音忽高忽低飘忽不定,但越来越响也越来越清晰。黑暗开始迅速退去。在喃喃的念经声中,呼兰大妈重新看见了丈夫和儿子。丈夫还是刚结婚时的老样子,嘴里叼着一根稻草,拎着一串钥匙行走在田间地头。儿子脸上的血污不见了,身上的宝蓝色衬衫在三月份的阳光下鲜亮夺目。更多死去的亲人的面孔浮现在眼前,他们排着长队,唱起一支模糊不清的老歌。歌声盘旋而上,与念经的声音缠绕在一起。缠绕在一起的声音一忽儿像春天里的低吟,一忽儿又像旷野里的喘息,声音散发出一股浓重的、似曾相识的甜腻的味道,而呼兰大妈的身体就漂浮在这股甜腻的气息里。正在呼兰大妈呼吸这股气息的时候,一阵更猛烈的撞击呼啸而来,呼兰大妈睁开眼睛,看见男人的身体突然绷直,然后颓然倒向旁边的床上。
呼兰大妈穿好衣服坐在床边。这是东厢房男人吃饭睡觉的地方,门窗窄小,房间里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两张独头凳,地上放着男人的鞋和烧水煮饭的用具,这会儿,刚才闻到的那股甜腻的气息弥漫在整个房间里。男人俯卧在床上,伸出一只左手搭在呼兰大妈的小腹上。
“拿开你的手。”呼兰大妈说,“别再碰我。”
“你这是干什么?”男人翻身坐了起来。
“没什么,你不能再碰我。”
“好好,不碰就不碰。还有你这种女人,床都上过了,还不让碰。”男人咕哝着,在呼兰大妈身后开始穿衣服。
“你别忘了答应我的事。”呼兰大妈从床边站了起来。
“你放心,我不会忘记的,”男人说,“我什么都不会忘记。”
呼兰大妈不再理男人,拨开门栓打开房门,一阵风立刻吹了进来。门外阳光刺眼,厢房外的梧桐树在风里唰唰作响,树下落满了的白色的桐花,已经被踩得七零八落。
“你还没告诉我你想求菩萨什么事呢。”男人在身后叫住呼兰大妈。
“我以为你知道。”
“我能知道什么?我又不是菩萨。”男人说,“你说清楚,你究竟求菩萨什么事。”
从昨天夜里听到第一声念经的声音开始,呼兰大妈就已经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她转过身,把阳光挡在门外。透过房间灰蒙蒙的光亮,呼兰大妈看见自己一生经历的时间像流水一样从眼前缓缓流过。人这一辈子,真是太奇怪了,认识的人越多,心里越孤单。她上了床,把蚊帐放下,躺在冰冷坚硬的床上,感觉自己好像已经躺在漆黑潮湿的棺材里。现在面对男人询问的目光,一瞬间,呼兰大妈觉得自己已经完全透明。她看着男人,回答说:
“让我脑子坏掉,不记得所有的人。”
“也包括你。”见男人愣得像木头,呼兰大妈又一字一句补上四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