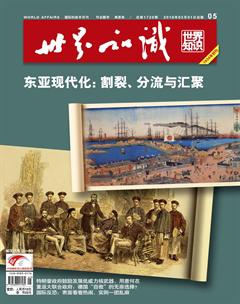中国经验对非洲发展的意义
王磊
2018年1月,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按惯例首访非洲,这种独特传统体现了中国一如既往的“真实亲诚”对非政策理念。2018年还有一件更令人期待的中非交往盛事——今年秋天将在北京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届时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中非将共话合作发展大计。
近年来,非洲大陆总体安全形势趋稳向好,国家间的战争、冲突处于历史较低水平,发展已经成为非洲的首要诉求,摆脱贫困、实现工业化、解决青年就业问题等则是具体的发展目标。同时,在发展道路的探索上,非洲国家独立自主意识增强,更重视结合自身国情,对西方不盲信、不盲从,普遍希望借鉴中国的后发经验。
非洲自主求索发展道路的意愿强烈
从经济领域看,非洲经济自1990年代中期开始提速,在近20年的时间里年均增长超过5%。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由于发达经济体不景气,新兴经济体发展普遍放缓,特别是2013年以来大宗商品价格低位运行,非洲经济在2014年至2017年年均增速降为3%。2017年非洲经济总量突破2万亿美元,但其产业单一的结构性难题并未消除,普遍面临由资源依赖型增长转向可持续增长的艰巨挑战。
具体观之,非洲各地区、各类型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趋势明显。从地区来看,东非长期领跑,埃塞俄比亚、卢旺达、肯尼亚、坦桑尼亚等国受益于政局长期稳定,发展目标明确,产业政策有效,受到外资青睐,经济增速常年在非洲保持领先,并跻身世界领跑行列。南部非洲、西部非洲分别受到南非和尼日利亚两个“巨头”的深度影响,这两国都属于资源富集国,但南非面临种族矛盾,产业老化、升级乏力,近年经济增速基本低于2%;尼日利亚过度依赖石油经济,多元化产业尚未建立,受油价波动影响较大。在中部非洲,中非共和国受内乱影响,经济重建缓慢,乍得、刚果(金)、喀麦隆等国仍主要依靠油气、矿产资源。北非一度深受“阿拉伯之春”影响,但近期埃及、突尼斯政局趋稳,经济发展回归正轨,2016年和2017年北非地区经济增速分别为2.6%和3.4%。从类型来看,埃塞俄比亚、塞内加尔、科特迪瓦等非资源富集国增速常年快于尼日利亚、安哥拉等资源富集国,反映出多经济部门、多元产业带来的增长动力明显更强。
一方面,支撑非洲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渐足,正面带动效果逐渐显现。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基础设施改善。据世界银行统计,近十余年非洲每年的基础设施开支约450亿美元,主要用于交通运输和能源供应领域。其二,“人口红利”逐渐显现。非洲是全球最年轻的大陆,据推算,2015年至2025年非洲将新增适龄工作人口2.1亿,占全球的42%,非洲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劳动力市场。联合国报告指出,未来30年非洲每年将获得“人口红利”约5000亿美元。其三,中产阶层扩大带动了内需。非洲开发银行研究报告显示,以每人每天收入在20美元以上为标准,非洲有约3.7亿人(约占非洲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进入中产阶层,消费市场可观。
另一方面,非洲经济发展仍面临一些严峻挑战:其一,新兴经济体增速放缓和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带来负面影响。前者是近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低位运行的主因之一,近期油价有所反弹但力度有限,尼日利亚等非洲石油出口国财政拮据情况短期内难有改观。同时,受到美国退出“量宽”、加息影响,全球资金回流美国,非洲亦受波及,莫桑比克等国债务高企,风险不容忽视。其二,部分非洲国家安全形势恶化,影响经济发展。2012年以来,非洲北部形成一条“暴恐动荡弧”,以“基地”组织北非分支、尼日利亚“博科圣地”和索马里“青年党”为主要代表,暴恐大案频发。南苏丹、马里等国持续内乱,刚果(金)等国因领导人谋求超期连任引发局势不稳,都是经济发展的隐忧。其三,非洲出口产品单一、对外依赖严重等结构性问题仍然存在。据世界银行统计,目前初级产品仍占非洲出口总量的四分之三左右,农业和制造业发展仍面临诸多阻碍。安哥拉、乍得、赤道几内亚、加蓬和尼日利亚等国出口外汇收入80%以上来自石油;博茨瓦纳、几内亚、毛里塔尼亚和塞拉利昂等国出口外汇收入50%以上依靠自然资源。
在政治领域,非洲在冷战结束后出现民主化浪潮,但由于忽视实际情况,转变过急过猛,普遍出现部族主义恶性膨胀、武装冲突、社会激烈动荡等严重问题,非洲国家因此对民主化浪潮进行了深层次反思。1990年代中期以后,多数非洲国家开始强调“不要外来方式的民主”、民主建设必须符合非洲实际。2008年金融危机后,欧美深陷各种危机,西方民主制度的光环进一步丧失,非洲更加重视自主求索符合自己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
目前,多数非洲国家仍停留在“形式民主”阶段,投票选举基本是最主要的表现方式,部分国家政治转型摇摆不定、屡遭挫折,西式民主和本土政治间的结构性矛盾也出现了固化、长期化的趋势。尼日利亚作为非洲人口和经济第一大国,1999年开启民主化进程后的四次选举都伴随着暴乱,2015年大选是唯一一次以比较和平的方式实现政权更迭,但固有的南北部族、教派矛盾时而因选举阵营的划分而激化。相比之下,乌干达、卢旺达、埃塞俄比亚等东非国家政府权威较高,反而政局稳定,经济持续高速发展。近年來,刚果(布)、卢旺达等国领导人成功修宪寻求连任,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众渴望稳定、厌恶“选举折腾”的意愿。鉴于非洲国家普遍积贫积弱的状况,其经济发展、安全稳定等要害问题仍受制于欧美,一些脱离“西方民主轨迹”、自主摸索政治发展道路的国家(如埃塞俄比亚)面临着巨大的外部挑战,政治转型有被外来干预中断的风险。总而言之,非洲政治道路探索注定充满曲折。
中国提供了“全新选择”

2016年12月20日,中国驻利比里亚维和警察防暴队到当地学校开展爱心助学活动,与师生们进行互动。
当前非洲的经济、政治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和历史节点,中国也进入了新时代,双方的意愿、能力、政策取向都有利于中非合作迸发出新的火花。结合非洲的迫切需求、双方的禀赋优势,中国的发展经验对非洲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脱贫经验的交流互鉴。减贫是非洲发展的重要目标和迫切诉求,据联合国报告,目前全球超过40%的极端贫困人口生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积累了丰富而有效的减贫经验,从减贫理念到措施方法对非洲都很有借鉴性,习近平主席的《摆脱贫困》一书受到非洲许多政商高层人士的喜欢,“弱鸟先飞”“扶贫先扶志”等理念在非洲产生强烈共鸣。
二是产业转移的历史机遇。发达国家的历史发展经验表明,制造业在经济中的比重随着经济增长呈倒U型变化。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制造业占GDP比重逐渐增大,一般在经济体迈入中等收入阶段时达到30%~40%的峰值,其后随着经济体不断富裕而逐渐减小。非洲制造业尚处于起步阶段,据麦肯锡公司数据,目前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整体制造业约占GDP的10%,中国则是接近峰值的38%。同时,国际机构一般认为,多数非洲国家制造业与中国存在梯次承继关系。成长为全球制造业主要基地的中国,有意向非洲转移部分制造业岗位,从而为非洲制造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非洲自身也有意愿,近年埃塞俄比亚等非洲国家以及非盟出台了系列重大发展规划文件,如《非洲基础设施发展规划宣言》(2013年发布)、《非洲2063愿景》(2013年发布)等,非洲希望通过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推动非洲工业化和经济一体化进程。
三是发展道路的“全新选择”。2008年金融危机后,西方面临经济增长乏力、政治极化、社会分裂等深层次问题,西方制度的弊端尽显,而中国经济稳步发展,社会稳定、凝聚力强。中国在主观上并不寻求“模式输出”,但客观上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东西方鲜明的对比促使非洲国家加强对西式发展模式的反思,“向东看”意愿明显增强。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非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