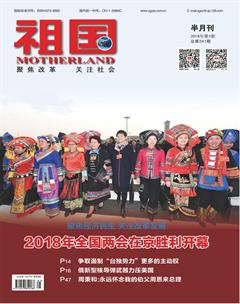浅议“规范性文件”在法律体系中的效力界定
陈孟
摘要:“规范性文件”虽未在法律体系之内,但却在法律实践中对公民的权利、义务产生重要影响。理论界也对“规范性文件”的法律效力,范围界定存在诸多分歧。为此,本文将着重就“规范性文件”的法律效力及界定问题展开探析。
关键词:规范性文件 法律界定 效力分析
我国《立法法》中对法律的规范,主要通过法律、法規和规章等进行说明,而对于“规范性文件”,由于其数量多,在法律实践中往往存在混乱现象。如在行政规范性文件中,多数法理学教材都将之等同于国务院通过的具有规范性的命令、决定,在法律效力上与相关行政法规等同;而对于权力机关发布的规范性文件,如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则都将之视为“法律”,与法律具有同等效力。事实上,在这些规范性文件中,学界并未形成一致性意见。为此,本文将就行政机关、权力机关、司法机关相关的规范性文件进行澄清,探析其效力。
一、“规范性文件”的广义用法与狭义化趋势
从法律领域来看,“规范性文件”主要指具有规范性的、适用于不同对象的各种文件。如2013年《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中,将共产党的一些纪律性文件设定为“规范性文件”。从法律实践中来看,对于“规范性文件”的内涵,并非仅限于法律之外。通过检索法律领域的“规范性文件”,多为地方性法规、规章及最高法司法解释,以及某些司法文件、行政机关的文件等,却未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或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中出现。如在1989年《行政诉讼法》第32条“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其他一些法律中如《行政处罚法》、《行政强制法》等也采用同样说法。2006年《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中,也规定了“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内容。此外,最高法、最高检在作出审判、检察工作中也应用了该解释。可见,“规范性文件”的广义用法已经存在在法律实践中。由此来看,“规范性文件”的狭义用法也相当普遍。
二、行政法规、规章的效力应高于相应立法主体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
行政法规、规章的制定主体具有差异性,不同立法主体的“规范性文件”,在法律效力上如何界定?在《宪法》中确定了国务院可以“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规,发布决定和命令”;同样,在一些地方人民政府,各省级、自治区、直辖市等也可以根据法律、法规要求制定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等地方性规章,决定、命令等。但这些行政法规、规章中的“规范性文件”,其法律效率与性质也存在相应区别。显然,我国法律体系中对“规范性文件”的解释并非一致。如《立法法》、《行政许可法》等对行政类法规和规章的制定,以及相关立法保留事项也进行了特殊的规定,但对于国务院和其他行政机关所制定的一般规范性文件,并未给予细化规定和说明。如在《行政复议法》中,针对“国务院部门的规定”的规章及内容,在进行行政复议时,也需要提出附带性审查,说明对于该类规章也是区别对待的。同样,在行政法规、规章与一般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效力界定上,行政法规在法律效力上只能称为“规定”、“条例”、“办法”等,而规章在法律效力上则只能称为“规定”、“办法”等。也就是说,对于一般性行政规范性文件,则主要称为“决议”、“决定”、“命令”、“公告”、“意见”等。由此可见,针对法律范畴内的所谓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地方性法规”,其效力关系也是较为明确的。不过,对于这些法律性文件并不等同于一般性“规范性文件”,两者的效力等级关系却显得模糊。如果行政法规、规章与相关的规范性文件具有同等效力,则《立法法》第83条中“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自治条例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新的规定与旧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于新的规定”,同样也应该适用于规范性文件之间的冲突。所以,行政法规的权威地位,应该高于国务院规范性文件的效力;规章的效力应该高于规章主体制定的一般规范性文件。
三、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性文件与规范性文件的效力界定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其规范性文件在法律与规范性文件之间的效力如何界定。尽管当前理论界和学界并未给予格外关注,但其适用性依然受到质疑。按照立法权限逻辑,立法权限机关也会制定一般规范性文件。但对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议、决定,没有法律性规范进行区别,虽然多数决议、决定称之为“法”,但事实上应该为“条例”、“办法”、“规定”、“通则”等。同时,从立法性文件本身,如果根据《立法法》规定,第23条、第41条中“由国家主席签署主席令予以公布”的规定,则应该化归于“法律”体系;否则,仅称为“规范性文件”。不过,我们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的“规范性文件”中,其在实际应用中却未进行严格划分,也未对其效力进行明确界定。如201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统计》将“1979年以来通过的法律”分为“宪法”、“宪法修正案”、“法律”、“法律解释”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由此可见,我们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立法规划室的做法中,对于立法性文件存在的“法律”与“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解释,也未将之置于“规范性文件”,仍被视为“通过的法律”。可见,全国人大常委会下属工作部门所制定的立法性文件,这些“规范性文件”在法律效力上并未进行严格区分。《立法法》所规定的法律程序,如果不符合《立法法》规定之程序则不能称为“法律”,只能视为“规范性文件”。
总的来说,由于“规范性文件”数量较多,对公民权利、义务的影响作用较大,在法律未明确规定的条件下,只有坚持法律体系的统一性原则,依据现有法律规定进行推论。当然,从法律实践来看,要想真正予以明确规定,还需要从宪法及宪法解释等方面,将之进行修订和完善,以明确其效力及地位。
参考文献:
[1]邓小兵,杨威.论内部规范性文件的法律性质及效力[J].求索,2013,(05).
[2]曹红.多方位强化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法治精神[J].改革与开放,2017,(10).
(作者单位: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