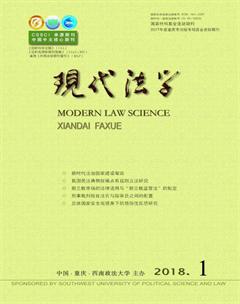论环境保护“三同时”义务的履行障碍与相对豁免
唐绍均 蒋云飞
摘要:高难度、高虚耗与低效率,是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履行环境保护“三同时”义务所面临的主要障碍。“改良论”与“废除论”是学界从制度存废角度展开的“路径选择”论争,但终究难为环境保护“三同时”义务履行障碍的破解提供可靠理论方案。从“义务相对豁免”角度切入与展开,允许企业以委托第三方治理或采用清洁生产工艺(设备)等方式有条件地获得环境保护“三同时”义务的豁免,符合激励理论、规模经济理论与“理性经济人”假设。希冀通过立法明确环境保护“三同时”义务相对豁免的适用条件、审定程序、政府监管与责任保障,构建环境保护“三同时”义务的相对豁免制度,以期促进“三同时”义务履行障碍的消释。
关键词:环境保护;“三同时”义务;履行障碍;相对豁免
中图分类号:DF468 文献标志码:A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80212
一、环境保护“三同时”义务履行障碍的现状检视
自1979年我国颁行《环境保护法(试行)》起1979年《环境保护法(试行)》第6条规定:“一切企业、事业单位的选址、设计、建设和生产,都必须充分注意防止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其中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的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环境保护“三同时”义务(以下简称“三同时”义务)被正式确立为企业
根据2014年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2017年新修订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新《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三同时”义务的主体应为企业单位、事业单位等一切对环境有影响的单位,考虑到“三同时”义务的主体主要是企业单位,为行文简洁,笔者将企业单位简称为企业。的一项法定义务。企业对此义务履行与否以及履行是否充分,均影响着“三同时”制度所承载的预防功能的实现。从近些年《全国环境统计公报》公布的数据看(参见图1),“三同时”执行合格率
根据《环境保护部建设项目“三同时”监督检查和竣工环保验收管理规程(试行)》第16条至第18条的规定,企业执行“同时设计与同时施工”后(部分建设项目需进行试生产),可向监管部门申请“三同时”验收,验收合格的视为已执行“三同时”制度。由此可见,《全国环境统计公报》中公布的“三同时”执行合格率大致等同于企业执行“同时设计与同时施工”的合格率,“同时投產使用”则未被考虑在内。平均高达96%,其中2011年至2015年分别为979%、973%、966%、967%、961%。单凭数据而言,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三同时”义务已经得到了企业的有效履行,“三同时”制度所承载的预防功能也理应得到了充分发挥。 “从理论上说,如果企业能够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那么超标排污或者发生重大污染事故的可能性就不大”[1],但现实图景却是,我国“环境质量总体向好但形势依然严峻”
前环保部部长陈吉宁在“2017年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上指出:“我国生态系统总体稳定,环境质量在全国范围和平均水平上总体向好,某些特征污染物和部分时段部分地区局部恶化,环境保护形势依然严峻。”(参见:曹红艳环保部部长陈吉宁:环境质量总体向好但形势依然严峻[EB/OL](2017-01-11)[2017-11-05] 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1701/11/t20170111_19549371shtml):环境污染事故频发、污染物排放量大面广
2016年11月24日,由国务院印发并实施的《“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指出,生态环境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突出短板,其主要体现为环境污染物排放量大面广、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频发等。、排污收费数额(主要为超标排污费)呈现逐年攀升态势
汪劲指出:“从1979年至2008年,全国累计征收排污费(主要由超标排污费构成)已达1419亿元,呈现出连年增加态势。”(参见:汪劲 环保法治三十年我们成功了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95-96)……为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虽然“三同时”执行合格率极高,但是“三同时”义务实际上并未得到企业的有效履行
“三同时”制度实际执行效果不彰,如下数据可佐证。山西省环保厅对全省11市63县293家企业的环境检查时发现:“‘三同时制度及环保试生产要求落实不到位,有202个项目违反‘三同时制度,占被检查企业总数的692%”;2014年环保部通报的数据显示:“违反环评及‘三同时制度仍是最主要的环境违法行为,占案件总量的5157%。”(分别参见:张隽波近七成项目违反“三同时”制度[N]山西日报,2006-10-18;张秋蕾环境保护部:违反环评及三同时制度问题突出[N]中国环境报,2014-09-24)。“三同时”义务未得到企业的有效履行,原因可能是多元的,但究其根源应该还在于企业履行“三同时”义务存在诸多阻碍或困境。这些阻碍或困境,笔者将其称为“三同时”义务的履行障碍
“履行障碍”渊源于德国债法上的“给付障碍”,所谓“给付障碍”是指债务人不依债之本旨履行债法上的义务,抑或指债务人在履行义务过程中面临的种种阻碍(参见:杜景林,卢谌德国新债法给付障碍体系重构[J]比较法研究,2004(1):79-84)。笔者借鉴德国债法对“履行障碍”的界定,将“三同时”义务履行过程中面临的种种困境或阻碍归结为“三同时”义务的履行障碍。。仔细考察“三同时”制度的立法与实践,我们不难发现,高难度、高虚耗与低效率是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履行环境保护“三同时”义务所面临的主要障碍。
(2016)》尚未公布,只能统计到2015年的数据;第二,《全国环境统计公报(2005-2010)》未公布当年“三同时”一次性执行合格项目数;第三,《全国环境统计公报(2010)》未公布2010年“三同时”执行合格率,故采用《2011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的数据。(参见:国家统计局,环境保护部 2011中国环境统计年鉴[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150)
(一)“三同时”义务履行的高难度
“三同时”义务由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三项义务构成。一般而言,同时设计义务与同时施工义务相对易于履行,即企业只需按照“经批准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要求”履行义务即可
2014年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第41条规定:“防治污染的设施应当符合经批准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要求,不得擅自拆除或者闲置。”根据这一条款,企业履行“三同时”义务必须以“经批准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为前提或基础。,但是,同时投产使用义务的履行却绝非易事。申言之,基于市场的瞬息万变,建设项目在投产使用后所排放的污染物存在较大“变数”,这个“变数”既包括污染物数量的“变数”,也包括污染物种类的“变数”,而企业按既定“计划”(即“经批准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建成的环保设施的处置能力却是“不变”的,导致这些环保设施往往难以有效处置存在较大“变数”的污染物。第一,若企业扩大产能,由此产生的“超计划数量”的污染物将超过环保设施原定“计划”的处置量;第二,若企业改变生产的产品种类或采用新的原材料,由此产生的“超计划种类”的污染物也将超出环保设施的原定“计划”处置能力。显而易见,按“计划”建成的环保设施往往无法处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较大“变数”的污染物,在此情形下,国家要求企业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并实现其所承载的预防功能,企业要“以不变应万变”的方式履行“三同时”义务毋容置疑会存在较高难度。
(二)“三同时”义务履行的高虚耗
所谓“三同时”义务履行的高虚耗,主要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按照“三同时”制度的要求所建设的配套环保设施可能造成的资金浪费或设备闲置。申言之,基于“开发区”
环保部印发的《关于加强开发区区域环境影响评价有关问题的通知》(环发〔2002〕174号)将“开发区”界定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保税区、国家旅游度假区、边境经济合作区,笔者采用此界定。集中治污模式的推广以及市场的瞬息万变,对于开发区内的企业而言,其更倾向于委托开发区内的集中治污企业作为第三方来治理污染物,而非选择自行履行“三同时”义务。当前,我国规划建设的开发区已普遍建有污水、固废等集中处置设施,且提供市场化和专业化服务,企业很可能基于“经济理性”
“经济理性”理论认为:“每一个参加公共选择的人都会依据自己的偏好和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进行活动,他们都是理性的、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经济人。”(参见:理查德
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M]蒋兆康,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25)將污染物交由开发区内的第三方企业集中治理。若选择第三方治理,企业无疑会闲置已建成的环保设施,因而造成建设资金的浪费。对于开发区外的企业而言,其也可能因市场变化(譬如减少产能)或者产业转型升级(譬如采用新的原材料)而闲置部分环保设施,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若开发区外的企业选择第三方治理,其也可能会闲置已建成的环保设施。由此足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三同时”义务的履行存在资金浪费或设备闲置的弊端。
(三)“三同时”义务履行的低效率
“三同时”制度要求企业设计、建设、运营与维护环保设施,其“实际上是一种分散的点源治理模式”[2]。这种分散的点源治理模式是实现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以及控制新污染源的可靠方式,但实践中极易造成“三同时”义务履行的低效率。概言之,造成“三同时”义务履行低效率的主要原因在于分散的点源治理模式不符合社会分工专业化的要求以及无法形成规模经济效应。第一,分散的点源治理模式不符合社会分工专业化的要求。亚当
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3]简言之,即“分工与效率明显呈现正相关关系,分工出效率,无分工则无效率”一些学者对“分工出效率”命题做了系统论述,其中叶生洪、彭星闾认为:“分工和专业化使得劳动生产者越来越将其生产活动集中于较少的操作上,能够较快地提高其生产的熟练程度,节约生产的人力资源,从而提高企业的管理效率。”(参见:叶生洪,彭星闾论规模经济的本质:结构经济[J]财贸研究,2003(1):17-23) 。于企业而言,“分工出效率”是指企业通过生产的专业化分工实现其生产效率的提高,而分散的点源治理模式要求企业在生产专业化的同时还须实现污染治理的专业化,则体现了“无分工则无效率”,这显然与社会分工专业化要求相悖,实践中很可能影响第三方治理的引入以及环境污染治理分工的专业化,因此企业通过分散的点源治理模式自行履行“三同时”义务难免呈现低效化态势。第二,分散的点源治理模式无法形成规模经济效应。西方经济学理论认为,企业的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呈U形,即“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平均成本逐渐向右下方倾斜,但超过一定点又会逐渐向右上方倾斜”[4],且“规模生产又可促进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提高了生产效率,节约了生产费用”[5]。概言之,在一定条件下,规模生产既可降低成本又能提高效率。但是,分散的点源治理模式却导致企业在治理环境污染时“各自为战”,与西方经济学理论所主张的规模生产与专业化分工要求相悖,无法有效降低污染治理成本,也无法提高污染治理的效率,因而无法形成环境污染治理的规模经济效应。基于此,企业通过分散的点源治理模式自行履行“三同时”义务不可避免会呈现低效化态势。
二、环境保护“三同时”义务履行障碍引发的“存废论争”
针对“三同时”义务的履行障碍,学界提出了两种应对方案:一是改良现行“三同时”制度,使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二是废除“三同时”制度。笔者将以上两种不同的理论争议概括为“三同时”制度的“存废论争”。[SS][S)]
“三同时”义务履行的“两高一低”障碍 “三同时”义务履行的“两高一低”障碍是笔者针对企业履行“三同时”义务过程中所面临的阻碍或困境的系统概括,而在此之前,一些学者对此问题也有零星论述。(参见:杨源市场经济下“三同时”制度的新思路[J]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6):37-38;胡静中国“三同时”环境法律制度需要改良[J]中国法律,2008(5):21-22;雷霆,王芳循环经济理论与“三同时”法律制度的融合[J]经济问题探索,2004(6):19-21;常纪文,杨朝霞环境法的新发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320-327)引起了部分学者的关注,他们对此问题也有零星论述。梳理这些文献,我们大致可以将其观点概括为“三同时”制度的“改良论”与“废除论”。
(一)“改良论”
“改良论”是从“三同时”制度“存”的角度提出的观点,其冀望透过温和、渐序改良的方式来提升制度的适应性,是目前学界的主流观点。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学者李乐修颇具前瞻性地指出:“‘三同时制度对部分区域性开发建设项目不太适应,与其他环境管理制度也不太协调,迫切需要加强其与污染集中控制制度的对接”
参见:李乐修完善“三同时”制度适应改革新发展[J]环境保护,1996(7):27-36,但究竟如何实现与集中治理制度的对接,其并未提出相应解决方案。进入21世纪之后,企业执行“三同时”制度所存在的不经济、不效益、不专业等弊端日渐凸显,引起了部分学者的关注。围绕如何革新“三同时”制度,以周珂、常纪文、杨朝霞、胡静、雷霆、王芳为代表的“改良论”学者提出了一些改良建议(参见表1)。概言之,这些改良建议大多聚焦于“三同时”的验收及审批程序的完善、开发区“三同时”制度的构建、“三同时”制度与集中治理制度及清洁生产制度的衔接、“三同时”制度的市场化设计等,冀望通过制度改良以提升“三同时”制度的适应性。
值得一提的是,部分“改良论”学者在深入研判“三同时”制度困境及其根由的基础上,提出了“分类执行‘三同时制度”“‘三同时制度适用例外”等的理论主张。其中,胡静认为:“‘三同时制度的分类执行思路有三条:第一是对特殊行业通过立法执行‘三同时;第二是环保部门在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或者发放排污许可证时对建设单位提出个别要求;第三是明确使用清洁生产设施、工艺的视为配备环境保护设施。”[6]常纪文与杨朝霞则对“分类执行‘三同时制度”的意义与内涵做了系统解读,他们认为:“对环境可能造成重大影响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建设项目必须严格执行‘三同时;对环境可能造成轻度影响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选择性地强制执行‘三同时,建设单位不进行‘三同时的,需提出委托专门从事环境治理的企业进行治理(如集中治理)的申请,是否许可,经审批该环境影响报告表的环保部门核查后做出决定;对环境影响很小不需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建设项目可自愿选择是否进行‘三同时,对于不进行‘三同时的也应采取相应措施(譬如开展清洁生产、综合利用、无害化处置等措施),以保证能满足同‘三同时制度验收标准同样的要求。”[2]有别于前述三位学者主张的“分类执行‘三同时制度”,周珂提出了“‘三同時制度适用例外”之观点,他认为:“如果企业采取清洁生产方式,污染少或无污染,当然可以‘少建或者不建环保设施”[7]。
(二)“废除论”
“废除论”是从“三同时”制度“废”的角度提出的观点,其主张者旗帜鲜明地倡导废除“三同时”制度。主要理由有三(参见表2):第一,“三同时”制度的实施会造成资源浪费。对企业而言,“三同时”制度要求其“花巨额资金去兴建一座座污染防治设施,却无力让这些污染防治设施发挥作用,实在是人、财、物的巨大浪费。”[11]对政府而言,则可能导致行政执法资源的浪费,有学者指出:“‘三同时监管相当于监管企业防止污染的‘过程,而对企业是否超标排污或者超出总量限制排污的监管相当于监管企业防止污染的‘结果,既然监管‘结果就足以实现环保目标,又何必浪费人力、物力去监管‘过程”①。第二,“三同时”制度与环评制度、集中治理制度的功能相重合,后两者可取前者而代之。正如汪劲所言:“在环评制度存在的前提下,‘三同时制度完全可以融合到环评制度之中;在污染物集中处理的前提下,‘三同时制度对于排污企业来说也是多余的”[1]。第三,“三同时”制度与循环经济理念相冲突。刘国涛指出:“‘三同时制度与循环经济所要求的少污染或不污染相冲突,按照循环经济的发展要求,污染治理设施可以少建或不建,如此方可消除污染。”[12]基于以上缘由,“废除论”学者明确呼吁废除“三同时”制度。
①为准确援引原作者的观点,表1中“改良论”的具体主张及理由大多为原文摘抄,其中少许观点经笔者适当提炼。
(三)对“存废论争”的评析
尽管“改良论”与“废除论”在理论主张上相左,但二者均洞见了“三同时”制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实施困境及变革需求。“改良论”注意到现行“三同时”制度在适用范围、验收程序、责任承担等方面的缺陷,冀望通过制度改良方式加以克服,无疑有助于革新现行“三同时”制度。值得一提的是,胡静、常纪文、杨朝霞等学者提出的“分类执行‘三同时制度”建议颇有理论创新价值,实践中亦有利于破解“三同时”义务的履行障碍,但遗憾的是,这三位学者并没有明确提出分类执行“三同时”制度的适用条件,因此该理论方案的可行性有待商榷。对比而言,周珂提出的“‘三同时制度适用例外”(即企业若采用清洁生产方式可少建或不建环保设施)之观点同样具有理论创新价值,该主张不仅有助于鼓励企业引入清洁生产工艺(设备)以贯彻绿色发展、循环经济等理念,还有助于激励企业主动执行“三同时”制度。
相较于“改良论”,“废除论”主张则稍显激进和超前,在缺乏有效替代方案的情况下,若废除“三同时”制度,结果极可能加剧环境污染防治形势的恶化。我们不妨假设:第一,“三同时”制度废除后,“经批准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中提出的环保措施该如何落实?按照现有的制度安排,“环评与‘三同时两个环节一前一后,相互衔接,构成了一个严密的整体。把握住这两个环节,就可以保证同步建设的顺利进行”[13]。据此而言,若缺少“三同时”环节,环评的预防功能将难以实现。第二,环评制度与集中治理制度能否取代“三同时”制度并发挥其所承载的污染防治功能?笔者以为,“三同时”制度实质上是一项“贯彻环境法综合防治原则的支柱性制度”[14],兼具“防”与“治”的双重功能,但环评制度仅具备形式意义上的“防”,集中治理制度只能对应部分环境污染的“治”,若以这两项制度替代“三同时”制度,将难以实现对环境污染的综合“防治”。总体而言,时下“三同时”制度尽管饱受学界诟病,但实践中仍具有不可替代的污染防治功能,故短期内不宜废除该制度。
三、环境保护“三同时”义务相对豁免的理论回应
基于以上判断,“改良论”“废除论”均为“三同时”义务履行障碍的破解提供了不少思想的火花,但尚未形成整套可靠的理论方案。笔者以為,破解“三同时”义务履行障碍的关键应在于:改变过去由企业自行履行“三同时”义务的单一做法,允许企业有条件地获得“三同时”义务的豁免,为“三同时”义务的履行提供多元选择。申言之,企业既可选择自
①为准确援引原作者的观点,表2中“废除论”的具体理由大多为原文摘抄,其中少许观点经笔者适当提炼。
行履行“三同时”义务,又可选择附条件免除此义务,这对破解“三同时”义务履行障碍以及实现“三同时”制度所承载的预防功能将大有裨益。
(一)“三同时”义务相对豁免的基本内涵
按照《牛津法律大辞典》的解释,“豁免”是指“不受某些法律后果约束或不适用某些法律规则的自由状态”[15]。从国际法律文件和一些国家法律规定看,法律上的豁免主要包含国家元首豁免、外交豁免、司法人员豁免、律师豁免、污点证人豁免、议员豁免等。在我国,法律规定的豁免除外交豁免与律师豁免外,还包括人大代表豁免、近亲属作证豁免、危险废物管理豁免、产品质量监督检查豁免(即产品免检)等。对于人大代表豁免,《宪法》第75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种会议上的发言和表决,不受法律追究。”对于近亲属作证豁免,《刑事诉讼法》第188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对于危险废物管理豁免,《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16)》第5条规定:“列入本名录附录《危险废物豁免管理清单》中的危险废物,在所列的豁免环节,且满足相应的豁免条件时,可以按照豁免内容的规定实行豁免管理。”对于产品质量监督检查豁免,《产品免于质量监督检查管理办法》第2条规定:“符合本办法规定的产品免于政府部门实施的质量监督检查。”
梳理以上法律规定,我们可以将豁免归纳为以下两类:一是具备“特定身份”的豁免,如人大代表豁免与近亲属作证豁免;二是具备“特定条件”的豁免,如危险废物管理豁免与产品质量监督检查豁免。其中,具备“特定条件”的豁免又可称作附条件豁免或相对豁免
依《辞海》对“相对”一词的定义,“相对”是指“有条件的、暂时的、有限的、特殊的”。(参见:夏征农,陈至立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2494)基于此,笔者主张的“相对豁免”亦指“附条件豁免”或“具备特定条件豁免”。,即惟有满足法律规定的“特定条件”时,才能豁免义务或责任。需要说明的是,“豁免”免除的是具备“特定身份”或具备“特定条件”的主体的法律义务(责任),其目的是保障行为主体履行职责、维系其身份关系或者提升其履行义务的效果之需要,若行为主体不再具备某“特定身份”或“特定条件”,则“沦为”普通义务(责任)主体,此时不再涉及义务或责任的“豁免”。譬如,夫妻关系解除之后,双方之间对彼此都负有法定的作证义务;又如,若某项产品不再满足《产品免于质量监督检查管理办法》规定的“免检条件”时,那么该产品应接受国家质量监督检查。
依此可见,法定义务并非绝对的、无条件的由义务人自行履行,当具备“特定身份”或“特定条件”时,义务主体完全可以被法律豁免该义务。基于同一原理,当企业具备某些“特定条件”时,同样可免于履行“三同时”义务,此即“三同时”义务的相对豁免。“三同时”义务相对豁免本质上是一种附“特定条件”的豁免,而非附“特定身份”的豁免。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三同时”义务相对豁免不是废除“三同时”义务,也不是否定“三同时”义务的价值,而是允许企业有条件地获得“三同时”义务履行的豁免,藉此鼓励企业选择更经济、更高效、更专业的方式来执行“三同时”制度,最终提升污染防治的效果。在“三同时”义务相对豁免命题之下,企业具有履行“三同时”义务的充分自主权,即既可选择自行履行“三同时”义务,也可选择附条件豁免“三同时”义务。若选择后者,企业必须满足豁免“三同时”义务的“特定条件”,若企业不再满足“特定条件”,其法定义务则不再被豁免,而应依法履行“三同时”义务。
(二)“三同时”义务相对豁免的理论诠释
1附条件豁免“三同时”义务,符合激励理论,有助于对企业实现“三同时”制度所承载的预防功能形成充分激励
“三同时”制度是一种典型的命令式管制,“以自上而下的‘命令—服从或‘权威—依附型制度为重心”[16],由于缺乏对守法者的充足激励,企业在执行“三同时”制度时常常消极应对,甚至采取拖延、隐瞒、阻扰等方式抗拒“三同时”监督管理。针对“三同时”制度激励不足问题,有学者曾指出,“‘三同时验收只能解决污染防治设施‘有和无、验收时期‘是否达标排放等问题,并不能解决其是否能长期稳定达标运行和设施运行成本导致的企业是否愿意长期运行等问题”[17],且“许多企业宁可交纳超标排污费,也不愿意开动工厂的污染治理设施”[18]。激励理论源于对命令式管制之激励不足的反思,该理论认为,“法律制度能否得到认真遵守和良好实施,在根本上取决于其产生的激励是否充足,能否使依法行动符合行动者的理性选择”[19],并提出“应重视经济手段和正激励的运用”[20]。从激励视角分析,现行“三同时”制度不加区分地要求企业履行“三同时”义务,明显是“管制有余而激励不足”,以至于现实中很难调动企业主动预防污染的积极性。而坚持“三同时”义务相对豁免,不仅为企业履行“三同时”义务提供了多元选择,且较之自行履行“三同时”义务更具成本、收益、效率等比较优势,可对企业防治污染形成充分激励。在具有多元选择的正向激励下,企业履行“三同时”义务的自主性势必得到有效提升,“三同时”制度所承载的预防功能也能得到较好实现。
2附条件豁免“三同时”义务,符合规模经济理论,是环保产业实现规模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
规模经济是社会化大生产与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以马歇尔(Marshall)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者认为:“大规模生产的主要利益,是技术的经济、机械的经济和原料的经济。”[21]彭星闾在反思古典经济学者观点的基础上指出:“规模经济的本质是通过结构优化而实现的经济,即根源于分工、专业化所带来的经济节约。”[22]Goldsby则对规模经济的形成机理做了系统分析,他认为:“任务成本的上升‘倒逼出分工战略,分工战略则可促进规模生产,最终实现收益的递增”[23]。综合以上学者论说,规模化生产可以有效节约成本与促进专业分工,进而实现规模经济,此即经济学上的“规模经济理论”。立足于该理论,环境污染治理的“规模化生产”将有助于促进污染治理分工的专业化,降低生产成本,并实现环保产业的规模经济。传统“三同时”制度固守“谁污染谁治理”模式,企业无论大小均需建设配套的环保设施,这既不利于污染治理的集约化,实践中也无法实现规模经济。而坚持“三同时”义务相对豁免,有助于引导企业由“谁污染谁治理”转向第三方治理,从而实现第三方治理产业乃至整个环保产业的规模经济。首先,第三方治理的推行有利于降低第三方治理成本,提升治理效率,进而实现第三方企业的内部规模经济;其次,第三方治理的推行还能有效促进环保产业的分工协作,减少环境污染治理的成本,最终实现外部规模经济。国外学者Yutian与Debapriya的研究亦佐证了上述推断,他们指出,“集约化生产或外包效率的增加,不仅可实现企业内部的规模经济,还能促进外包公司的研发激励以及实现整个社会成本的锐减”[24]。
3附条件豁免“三同时”义务,符合“理性经济人”逻辑,有助于企业选择成本最小化、收益最大化的方案
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理性经济人”假设不但是“解释人类行为的最普遍、最有效、最成功的工具”[25],也是其庞大经济学体系的重要支点。自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该理论假设逐渐被理查德
等法经济学者引入到对人类法律行为的分析。“理性经济人”假设认为,“每个人都能够通过成本—收益比较或趋利避害原则来对其所面临的一切机会和目标及实现目标的手段进行优化选择”[28],且“当遵守法律比不遵守法律似乎给他们带来更大好处或更小坏处时,他们才会愿意去遵守”[29]。借助于这一经典理论框架,若企业选择自行建设配套的环保设施,则付出的成本或代價可能较为高昂当然这也存在例外情况:若企业本身就具有专业治污技术、治污设备或管理人才等条件,则自行履行“三同时”义务的成本可能低于选择第三方治理的成本。;若企业以付费方式委托市场上专业的第三方企业治理污染,抑或是在建设项目设计之初就考虑采用清洁生产工艺或设备,那么从长远来看,企业选择满足上述“特定条件”以免除“三同时”义务的成本极可能小于其自行履行“三同时”义务的成本,所获收益也可能更大。在“两弊相衡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的心理驱动下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认为:“人具有趋利避害的本性,凡人断为有利的,他必不会等闲视之,除非希望获得更大的好处,或是出于害怕更大的祸患。”(参见: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M]温锡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215),作为“理性经济人”的企业有可能会优先选择更符合“成本—收益”原则的附条件豁免“三同时”义务,而非选择自行履行“三同时”义务。
[S(3][]四、环境保护“三同时”义务相对豁免的制度构建
[SS][S)]
如前所述,“三同时”义务的相对豁免为企业在自行履行“三同时”义务之外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构建“三同时”义务的相对豁免制度将有助于“三同时”义务履行障碍的破解。笔者认为,明确“三同时”义务相对豁免的适用条件、审定程序、政府监管与责任保障是该制度构建的基本内容。
(一)“三同时”义务相对豁免的适用条件
概言之,“三同时”义务相对豁免的实质就是企业可以选择满足“特定条件”以获得“三同时”义务的豁免。何谓“特定条件”,笔者认为,企业委托第三方治理或者企业采用清洁生产工艺或设备(以下简称“豁免条件”)均可分别作为“三同时”义务相对豁免的“特定条件”。
1企业委托第三方治理
申言之,排污企业与第三方企业签订协议,排污企业以付费方式委托第三方企业代为治理污染,且该污染治理义务存在被实际履行的可能性,此时可豁免排污企业的“三同时”义务。曾有学者提出:“若建设单位不进行‘三同时的,需提出委托专门从事环境治理的企业进行治理(如集中治理)的申请,是否许可,经审批该环境影响报告表的环保部门核查后作出决定”参见:常纪文,杨朝霞环境法的新发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329,该观点可为本文主张的“企业若委托第三方治理可豁免其‘三同时义务”观点提供思想的火花。之所以将“企业委托第三方治理”作为“三同时”义务相对豁免的适用条件,原因在于委托第三方治理可以实现甚至超过企业自行履行“三同时”义务所能达到的效果:首先,相较于企业自行履行“三同时”义务,第三方治理有降低治理成本的比较优势;其次,相较于企业自行履行“三同时”义务,第三方治理还具有专业与效率的比较优势,更符合“专业人干专业事”的理念。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企业委托第三方治理,实质是排污企业通过第三方企业代为治理其排放的污染物而获得“三同时”义务的豁免,而非第三方企业替代排污企业履行“三同时”义务。企业委托第三方治理关注的重点在于治理的“结果”而非治理的“过程”,即只要治理的“结果”达标,治理的“过程”则可以多元化。
2企业采用清洁生产工艺(设备)
相较于仅具备“治污”功能的环保设施,清洁生产工艺(设备)兼具“生产”与“治污”之双重功能,更有助于实现“少排放”甚至“零排放”目标,企业如果采用了清洁生产工艺(设备),则无再履行“三同时”义务的必要。曾有学者提出:“污染治理设施可以少建或者不建,但是应是有条件的:如果企业采取清洁生产方式,污染少或无污染,当然可以‘少建或者不建”[29],该观点可为本文主张的“企业若采用清洁生产工艺(设备)可豁免其‘三同时义务”观点提供思考的灵感。之所以将企业采用清洁生产工艺(设备)作为“三同时”义务相对豁免的适用条件,原因在于企业采用清洁生产工艺(设备)可以实现甚至超过企业通过配备环保设施自行履行“三同时”义务所能达到的效果:首先,企业采用清洁生产工艺(设备)可以从源头减少污染,有效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并减少污染物排放,促使企业由末端治理走向源头防控,这对预防环境污染与改善环境质量大有裨益;其次,较之单纯注重资金投入或者环境效益的环保设施建设,企业采用清洁生产工艺(设备)可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双赢,可为环境污染治理及治污设备的更新换代提供充足资金,客观上也有助于激励企业参与环境污染防控。此外,企业采用清洁生产工艺(设备)也是践行绿色发展、循环经济、清洁生产等理念的客观需要,符合社会发展趋势。
(二)“三同时”义务相对豁免的审定程序
若企业通过委托第三方治理或者采用清洁生产工艺(设备)的方式获得“三同时”义务的豁免,其无需再按照新《管理条例》第17条之规定进行“三同时”验收
新《管理条例》第17条规定:“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编制验收报告。”根据这一条款,“三同时”验收已由政府验收改由企业“自行验收”。,政府亦不再对建设项目环保设施设计、施工、投产、使用等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从行政管制的角度看,“三同时”义务相对豁免制度的实施客观上可能弱化政府对企业治理污染的直接管控,但为确保“三同时”义务相对豁免制度的严格实施,企业在选择附条件豁免“三同时”义务时,必须严格遵循“三同时”义务相对豁免的审定程序(参见图2)。具体而言,该审定程序主要分为如下两步:
1企业向环保部门提出豁免“三同时”义务的申请并提交支撑材料
首先,有意選择豁免“三同时”义务的企业需向环保部门提出申请(即坚持“豁免须依申请”原则),填写“三同时”义务相对豁免申请表。其次,企业应向环保部门提交申请豁免“三同时”义务的支撑材料,根据所选的不同“豁免条件”,这些支撑材料应有所区分:若企业选择委托第三方治理以豁免“三同时”义务,则需提交其与第三方企业签订的治理协议、第三方企业的资质等材料,其中治理协议应包含治理内容、治理目标、收费标准、双方责任等内容;若企业选择采用清洁生产工艺(设备)以豁免“三同时”义务,则需提交其所采用的清洁生产工艺(设备)的名称、种类、数量、投产使用时间等材料。此外,因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而需要履行新的“三同时”义务,若企业想继续获得“三同时”义务的豁免,则应当向环保部门提出新的豁免申请,并提交相应材料。
2环保部门对豁免“三同时”义务的申请予以审定,并向社会公告
具体而言,环保部门根据企业提交的材料进行书面审查,针对不符合“三同时”义务豁免条件的企业,若是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应当告知企业及时补全材料或者遵循法定形式,若仍不满足“三同时”义务的豁免条件,对企业申请做出不予批准的决定;针对符合豁免“三同时”义务条件的企业,应当做出书面的批准决定,及时通知申请企业并向社会公告。需要说明的是,企业获得“三同时”义务的豁免并无时间限制,即一旦获得“三同时”义务的豁免,企业可永久性地选择附条件免除“三同时”义务,但是,当企业不符合豁免“三同时”义务的条件时,其法定义务不再被豁免,而应依法履行“三同时”义务。
(三)“三同时”义务相对豁免的政府监管
企业获得“三同时”义务的豁免后,必须保证其申请豁免时所提出的“委托第三方治理或者采用清洁生产工艺(设备)”之条件的有效落实,但可以预见,并非所有企业都能够真正落实,譬如部分企业可能基于资金短缺而在落实“豁免条件”方面大打折扣。为避免出现此类情形以及规范“三同时”义务相对豁免制度的实施,作为监管者的政府应当通过强制力对企业的行为进行适当干预,确保其行动符合制度预期。
1开展“双随机”抽查,监督企业落实“豁免条件”
“双随机”抽查最早由《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广随机抽查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通知》(国办发〔2015〕58号)规定,是指监管部门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并及时公布查处结果,是政府监管创新的一项重要举措。由于实施成效显著,“双随机”抽查逐渐在浙江、湖南、四川等地被用于对建设项目环保设施建设以及定点污染源治理的监管。在“三同时”义务相对豁免制度的实施过程中,政府部门可运用“双随机”抽查进行监督,即随机抽取检查落实“豁免条件”的企业、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对企业委托第三方治理或者采取清洁生产工艺(设备)的落实情况展开监督,并将监督情况向社会公布,对企业形成强大震慑力。在开展“双随机”抽查时,应当严格限制监管部门的自由裁量权,即建立获得“三同时”义务豁免的企业名录库和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从上述名录库中随机抽取检查对象和选派执法检查人员,合理确定随机抽查的比例和频次。
2强化信息公开,督促企业落实“豁免条件”
“三同时”义务相对豁免的审定实质上是一种行政许可,因此做出豁免许可的监管部门可以按照《行政许可法》第61条的规定进行信息监管
《行政许可法》第61条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健全监督制度,通过核查反映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活动情况的有关材料,履行监督责任。行政机关依法对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的活动进行监督检查时,应当将监督检查的情况和处理结果予以记录,由监督检查人员签字后归档。公众有权查阅行政机关监督检查记录。 行政机关应当创造条件,实现与被许可人、其他有关行政机关的计算机档案系统互联,核查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活动情况。”,以督促企业有效委托第三方治理或者如实配备清洁生产工艺(设备)。信息公开的重点在于:第一,监管部门应抓紧建立统一的“三同时”监管信息平台,全面录入有关“三同时”义务相对豁免的申请、审查、决定、撤销等信息;第二,监管部门对企业委托第三方治理或者配备清洁生产工艺(设备)的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将监管检查情况与处理结果予以记录,由监督检查人员签字归档并全面录入“三同时”监管信息平台;第三,除按照国家规定需要保密的情形外,监管部门应当通过“三同时”监管信息平台或者其他便于公众知悉的方式,依法向社会公开企业落实“豁免条件”的具体情况,并及时反馈公众的质询。
3加强信用管理,规范企业落实“豁免条件”
所谓“信用管理”,是指“政府对各类经济组织履行各种经济承诺的能力,以及可信任程度的综合判断和评定”[30]。作为政府监管的另一制度创新,“信用管理”在新《管理条例》第20条第2款
新《管理条例》第20条第2款规定:“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建设项目有关环境违法信息记入社会诚信档案,及时向社会公开违法者名单。”和《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33号)中均得到了充分体现,其中后者更是明确提出建立信用信息公示机制、信用信息归集共享和使用机制、信用红黑名单制度、激励和惩戒措施清单制度、信用修复机制等,确保企业诚信自律。为提升政府监管的效果,监管部门完全可以将“信用管理”运用到“三同时”义务相对豁免的监管之中。申言之,监管部门可定期对排污企业在落实“豁免条件”中的表现以及治污企业在第三方治理中的表现做出信用评价,通过环保部门网站或其他便于公众知悉的方式向社会公布上述信用评价,同时也允许排污企业和第三方企业修复自身信用。此外,监管部门可根据信息评价制作信用红黑名单,并向社会公布。
(四)“三同时”义务相对豁免的责任保障
“三同时”义务的相对豁免制度本质上是一项行政法律制度,构建该制度的目的在于督促企業更好履行的“三同时”义务,因此在探讨“三同时”义务相对豁免的责任保障时,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并非笔者关注的重点,此节仅研究企业、监管部门、环境服务机构在“三同时”义务相对豁免中可能承担的行政法律责任。
法律责任作为法律运行的保障机制,是法治不可缺少的环节[31]。为确保“三同时”义务相对豁免制度的有效落实,须构建科学合理的法律责任追究机制。在“三同时”义务未被豁免的情况下,企业违反此义务的法律责任较为明确,即仅需按照新《管理条例》第23条的规定
新《管理条例》第23条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建设项目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或者在环境保护设施验收中弄虚作假的,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处10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重大环境污染或者生态破坏的,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或者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关闭。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单位未依法向社会公开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报告的,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公开,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予以公告。”,承担限期改正、罚款、停止生产或使用、关停、公开验收报告等法律责任。然而,在“三同时”义务被有条件豁免的情况下,若企业委托第三方治理或者采用清洁生产工艺(设备)未能达到预期目的,抑或存在弄虚作假的,此时由谁承担法律责任,以及如何承担法律责任是亟需回应的问题。
1厘清企业的法律责任
在“三同时”义务相对豁免制度的实施过程中,若企业委托第三方治理或采用清洁生产工艺(设备)未达预期目的、弄虚作假或未依法公开信息的,可比照新《管理条例》第23条规定的“环保设施未建成、未经验收、验收不合格、验收中弄虚作假、未依法公开验收报告”之责任规定,承担限期改正、罚款、停止生产或者使用、关停等法律责任。但需要注意的是:第一,企业承担罚款责任的前提是监管部门已经责令其限期改正而拒不改正,其他的责任形式如停止生产或者使用、关停等,则不以监管部门已经责令其限期改正而拒不改正为前提,如此安排意在鼓励或引导企业主动落实“豁免条件”;第二,对企业罚款时应采取“双罚制”,即不仅要处罚企业,还要处罚企业的负责人,这有利于降低企业负责人和其他责任人员参与、纵容企业在落实“豁免条件”时违法的可能性;第三,若责令限期改正、罚款仍不足以督促企业落实“豁免条件”的,相关监管部门可撤销企业的“三同时”义务豁免许可,责令其自行履行“三同时”义务;第四,若企业在落实“豁免条件”时造成重大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监管部门可直接责令企业停止生产或者使用,或者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关闭。
2明晰监管部门的法律责任
在“三同时”义务相对豁免的审查、决定以及后续监管过程中,若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但尚不构成犯罪的,相关监管部门应当根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495号)的相关规定,处以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等行政处分。譬如,监管部门的直接责任人滥用职权批准企业的“三同时”义务相对豁免申请但尚不构成犯罪的,有权进行监管的部门应根据违法情节处以警告、记过甚至开除等行政处分。
3界定环境服务机构的法律责任
在“三同时”义务相对豁免制度的实施过程中,若环境服务机构(如第三方治理企业、第三方验收机构)存在弄虚作假、乱收费等违法行为的,可比照新《管理条例》第25条之规定
新《管理条例》第23条规定:“从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单位,在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中弄虚作假的,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处所收费用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由县级以上环保部门处以罚款。此外,监管部门还可将服务能力弱、管理水平低、综合信用差的环境服务企业列入黑名单,定期向社会公布,并建立相应的奖惩机制,藉此更好地规范与鼓励环境服务企业参与第三方治理,充分发挥“三同时”义务相对豁免制度的作用。
参考文献:[1]汪劲环保法治三十年:我们成功了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88,155,154,154-155
[2]常纪文,杨朝霞环境法的新发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322,329,329-336
[3]亚当·斯密国富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1
[4] 邓启惠关于规模经济理论的几个问题[J]求索,1996(3):4-7
[5] 叶生洪规模经济新论[J]当代财经,2007(2):10-15
[6] 胡静中国“三同时”环境法律制度需要改良[J]中国法律,2008(5):21-22
[7]周珂,迟冠群我国循环经济立法必要性刍议[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9-14
[8]雷霆,王芳循环经济理论与“三同时”法律制度的融合[J]经济问题探索,2004 (6):19-21
[9]成虹燕论我国“三同时”制度的运行效益[J]法制与社会,2008(7):149-151
[10]范晓峰我国环境法基本制度的发展与完善[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4):62-66
[11]杨源市场经济下“三同时”制度的新思路[J]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 (6):37-38
[12]刘国涛循环经济·绿色产业·法制建设[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23
[13]曲格平中国的环境管理[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89:24
[14]黄明健环境法制度论[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4:185
[15]沃克牛津法律大辞典[M]李双元,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546
[16]刘超管制、互动与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2): 96-104
[17]陶娟娟,高志永,王凯军从技术视角看新《环境保护法》中的环境管理制度[J]环境保护,2016(4):64-66
[18]汪劲中外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比较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58
[19]巩固激励理论与环境法研究的实践转向[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4):20-23
[20]巩固守法激励视角中的《环境保护法》修订与适用[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4 (3):29-41
[21]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经济学原理[M]廉运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168
[22]彭星闾,叶生洪论规模经济的本质[J]当代财经,2003(2):5-9
[23] Goldsby, et al ask-switching costs promote the evolution of division of labor and shifts in individuality[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2, 109(34):13686-13691
[24]Yutian Chen, Debapriya Sen Outsourcing and downstream R&D; under economies of scale[J] BE Journal of heoretical Economics, 2012, 12(1):1-27
[25]张曙光制度·主体·行为[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64
[26]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M]蒋兆康,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18-26
[27]罗伯特·考特,托马斯·尤伦法和经济学[M]史晋川,等,译上海:格致出版社, 2010:14-16
[28]李树经济理性与法律效率——法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逻辑[J]南京社会科学,2010 (8):108-114
[29]霍布斯论公民[M]应星,冯克利,译贵阳:贵阳人民出版社,2003:53
[30]金代志,石春生,刘任重信誉管理理论的文献综述[J]商业研究,2007(4): 37-40
[31]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101
Abstract:Difficulty, high cost and ineffectiveness, are the main obstacles that enterprise faced when fulfill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ree simultaneous” obligations under market economy “Reform theory” and “abolish theory” are the “path choice” debate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abstraction, but it is difficult to provide the effective theoretical solution for breaking the performance obstacle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ree simultaneous” obligation Star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bligation relative immunity”, it is conforming to the “rational economic man” hypothesis, theory of scale economy and incentive regulation to allow enterprise selecting thirdparty governance or equipped with cleaner production process (equipment) to conditionally obtain the immunit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ree simultaneous” obligation It is suggested that legislation should be used to clarify the applicable conditions, review the decision process, government regulation and legal liability of relative immunit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ree simultaneous” obligation, and construct the “three simultaneous” obligation exemption system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n promoting the removal of performance obstacle of “three simultaneous” obligation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ree simultaneous” obligation; performance obstacle; relative immunity
本文責任编辑:周玉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