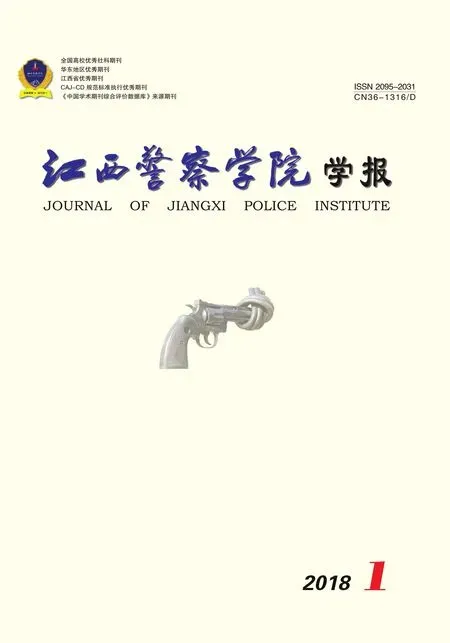“偷换二维码案”的法律定性
——新型三角诈骗理论之提倡
程 畅
(武汉大学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案情概览:被告人把商户的支付宝二维码换成自己的二维码,顾客付款时实际上将货款转给了被告人,直到遭受较大损失后商户才发现 (下文简称“偷换二维码案”)。虽然寥寥数语就可以说清这个案子的来龙去脉,但此案究竟应当如何定性却吸引了众多法学理论界、实务界专家学者的目光。
一、被害人认定
要给这类案件定性,必须先厘清一个问题:谁是被害人。一种观点认为,顾客是受害人。在顾客陷入认识错误向行为人的账户转账后,如果认为商户对顾客的债权仍未消失,商户可以继续向顾客要求支付价款,那么顾客成为了该案唯一的被害人。[1]还有观点认为应从民、刑不同角度认定被害人,在本案中应将刑法上的被害人认定为顾客,而将民法上的最终受损人认定为商户。[2]笔者不能认同以上两种观点。此案中被害人认定的问题确实涉及到民、刑交叉地带,下面笔者将从法经济学分析原理、民法理论和刑法理论三个方面,论证商户是本案唯一被害人。
首先,顾客在扫码付款后,商户对其债权已消失,不得再次主张。如此时商户仍可以向顾客主张债权,便是施加给顾客“扫码前确认二维码”的义务,然而一则,一些二维码上没有带有标识作用的头像,仅凭肉眼难以分辨;二则,商户与顾客之间本来仅存在一方给付商品、另一方给付货款的权利义务关系,如对顾客额外施加辨别二维码的义务,而并没有权利与之呼应,就会使双方的权利义务的天平大大失衡。根据法经济学分析原理,承担责任不是因为行为有过错,而是为了将事故的成本归于能够通过最低成本避免事故之人,通过个人的理性决策实现社会成本的最小化。[3]该案中,商户可以用最低的成本避免自己店中的二维码被更换,也最有能力和主观动力时时检查账户是否存在异常。与之相比,顾客要确认二维码的成本则要高上许多。总而言之,二维码的使用是为了提高收、付款效率,降低假币风险,便宜交易双方。但当商户因自身管理二维码有失时,如果将责任转嫁给顾客,则会导致顾客因付款前难以确保自己扫码后是向商户的账户付款,最终放弃使用扫码付款这一便捷的支付手段。如此决策违背了社会经济发展需要,打击了第三方支付手段的发展,拉低了经济活动效率,其缺陷显而易见。
其次,笔者认为该案被害人的认定,可以借鉴民法理论中“债务人对债权准占有人的清偿制度”。所谓债权准占有人是指虽非债权人,但是以自己的意思事实上行使债权,依照一般交易观念,足以使人相信其为债权人的人。[4]最先在立法上确立对债权准占有人清偿制度的是 《法国民法典》,该法第1240条规定:“向占有债权人所作的善意清偿,即使占有人的占有事后被他人追夺,亦为有效。”《日本民法典》也明文规定了这一制度。一般认为,债务人对债权准占有人的给付发生清偿效力,须符合如下三个条件:(1)受领人为债权准占有人;(2)债务人在主观上须为善意;(3)债务人已履行给付义务。一旦成立,债务人的给付即发生清偿的效力,债权人只能要求债权准占有人返还不当得利或者赔偿损害。[5]我国立法虽然没有明文规定这一制度,但其理论内核在“表见代理”等制度中有所体现。
在“偷换二维码案”中,根据一般交易习惯,商店中的二维码所有权属于该商户,顾客有理由相信扫码付款后就履行了对商户的债务。从另一个角度看,行为人更换二维码的行为使顾客误认为他就是债权人,顾客善意且履行支付义务,这一过程与债务人对债权准占有人进行清偿相似度极高。受到损失的商户只能要求行为人返还不当得利或者赔偿损失,但不能向顾客二次主张债权。所以,借鉴民法理论可以得出结论,“偷换二维码案”中的顾客没有受到损失。
最后,将刑事被害人与民事被害人分别认定是否合理?有学者认为,刑法上的被害人是因为犯罪行为导致财物直接受损的人,即本案中的顾客。[2]依前文所述,能够肯定商户无权继续向顾客主张债权,在该案中顾客客观上没有任何损失,那么根据该学者的思路,则会得出该案没有被害人的荒谬结论。既然已经确定是谁遭受到损失,下一步应该考察其损失后果可否归属于被告人的行为。[6]在该案中,需要追问的是,商户的损失与被告人的行为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归责可否成立?毫无疑问,不管根据何种因果关系学说,商户的损失都可以归责于行为人偷换二维码的行为。从刑法理论出发,也应当认定商户才是本案被害人。
二、对成立盗窃罪观点的批驳
根据通说理论,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公私财物的行为。[7]许多学者主张该案应成立盗窃罪,盗窃对象是商户的债权。笔者认同财产性利益也可以成为盗窃罪的对象,但由于本案中行为人的作案手法不能满足构成要件,所以不认同该案定性为盗窃罪,认为该案应当定性为盗窃罪且又分为成立直接盗窃和成立间接盗窃两种情节,笔者将在下文中分别进行分析。
“偷换二维码案”中,主张成立盗窃罪(直接正犯)的学者大多认为,被告人窃得了商家对顾客的债权,也有学者将其表述为“被告人窃得商户的债权人地位”。[1]程雁群学者借鉴了另一案例:王某窃取债权公司的欠条后向债务人主张结算贷款,造成债权公司重大损失(以下简称“盗窃欠条案”)。[8]陈兴良教授在点评该案时说,在本案中受到财产损失的是债权公司,由于王某窃取欠条并收取货款,使债权公司遭受了经济损失。这一经济损失应当归责于王某窃取欠条的行为,因此构成盗窃罪。在本案中,王某向债务公司实现债权的时候,确实存在一定的诈欺行为,但是债务公司的财产并没有因此受到损失,当然就不能把王某的行为认定为诈骗罪。程雁群学者认为该案与“偷换二维码案”本质相同,商户在案件里只是扮演着一个债权公司的形象,本身并没有被欺骗,只是自己的收款凭证被偷了而已,[9]同样应当认定为盗窃罪。
“盗窃欠条案”与“偷换二维码案”确有可以类比之处,但是笔者并不认同以上学者的观点。如果依上述思路进行分析,判定“偷换二维码案”中被告人犯盗窃罪,便是从被害人的认定反推行为符合何种构成要件,因顾客没有受到损失而不把被告人的欺诈行为在刑法上进行评价,并把顾客扫码付款的行为仅看作行为人为了实现盗窃目的而实施的手段。这样的案情概括与本案客观上的发展脉络不相符合,行为人偷换二维码使顾客陷入认识错误而付款,将这样的欺诈情节完全撇去不谈,直接根据被害人是店家而认定盗窃罪,笔者不能认同。刑法关注的核心应当是被告人的行为,被害人是依附于行为的发展轨迹而逐步揭晓的。先认定被害人,后依其结论反推行为定性,这是彻底本末倒置的做法。
其次,我国刑法理论通说认为,被窃财物要求为他人所占有。一个加之于财物之上的占有状态,通常由事实上的控制力以及规范层面上对控制的认可共同组成,两者之间互相补强。事实控制力是占有成立的基础,规范因素可以对占有进行评判。在判断占有的有无时,事实控制力为零时不可能成立占有,但判断控制力的有无,又需要以规范性视角作为观察工具。[10]“偷换二维码案”中,顾客基于认识错误直接将其对银行享有的债权转移到了被告人的账户上,商户自始至终没有对该债权施加事实上的控制力。根据一般社会观念和生活经验,可以说这个债权应当由商户占有,但是无论观念上如何补强,在事实控制力为零的前提下,占有便无从谈起。主张成立盗窃罪(直接正犯)的学者提出,该案中被告人的行为相当于“在商户的钱柜下面挖个洞,让所收款项掉到洞下被告人自己的袋子”(以下简称“钱袋案”)。但是应当看到,在“占有”这一关键点上,两者存在明显不同。在“钱袋案”中,尽管钱款进入商户的钱柜只是短短一瞬,但应考虑到,钱柜是商户施加强有力控制的特殊区域,即使掉落在钱柜下方,也应当承认商户对钱款有事实上的控制,这一点决定了“钱袋案”与“偷换二维码案”不可类比。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该案成立盗窃罪 (间接正犯),不知真相的顾客是被告人实施盗窃的工具。该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之处,成立盗窃罪间接正犯的场合,会出现与此案类似的三角结构,例如:甲闲逛时发现本市高速公路旁有一闲置的旧压路机,便假冒公司人员找到附近一废品收购站经营人乙,谎称该压路机已报废准备变卖,二人以6000元的价格成交。次日,在拆卸时被群众发现报警,甲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下文简称为“压路机案”)。[11]
在“压路机案”中,应当认定甲的直接目的是盗窃,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甲盗窃的对象并非压路机,因为甲想要非法占有的是压路机价值的财产性利益。甲利用欺诈手段使不知情的乙陷入错误认识,帮助甲实施犯罪。就压路机所有权人而言,甲的行为成立盗窃罪,就乙而言,甲的行为成立诈骗罪。因而,笔者认为该案应当认定为盗窃罪(间接正犯)与诈骗罪的想象竞合。至于针对同一法益能否成立两罪想象竞合的问题,与本文的论述重点无关,故不再此展开讨论。
“压路机案”中同样呈现三方结构,同样被告人只实施了一个行为,同样犯罪对象是财产性利益,但是该案与“偷换二维码案”存在明显差异:第一,虽然“压路机案”的被害人(压路机所有人)对压路机事实上的控制力较弱(案中所说“闲置”),但一般社会观念足以补强使其成立占有,毕竟压路机这种机械有自身特殊性;而“偷换二维码”案中的被害人(商户)对顾客的债权却从未占有过,占有不成立,则盗窃罪不成立。第二,根据间接正犯理论,盗窃罪中的间接正犯应当实施了客观上转移被害人财物的行为,“压路机案”中乙找来切割工和吊车拆卸压路机便是实施盗窃罪中“转移占有”。而“偷换二维码”案中,如果说顾客是被被告人利用的间接正犯,那么顾客是怎样转移被害人财物的呢?顾客在取得商品后扫码付款,转移了自己对银行的债权至被告人的账户,整个过程中顾客何时转移了被害人商户的财物呢?
综上所述,由于“占有”这一关键点的缺失,“偷换二维码案”不能成立盗窃罪。
三、对成立一般诈骗罪、“双向诈骗”观点的批驳
根据通说理论,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欺骗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12]主张二维码案应认定为诈骗罪的学者有三种思路:成立一般诈骗(诈骗对象是顾客)、成立“双向诈骗”以及成立特殊三角诈骗。
主张成立一般诈骗的学者认为,被告人偷换二维码是隐瞒真相,令顾客产生认识错误从而交付财物,且顾客是债权占有人,所以案情完全符合诈骗罪构造。[13]主张成立“双向诈骗”的学者主张,被告人的行为在使顾客基于认识错误处分银行债权的同时,也使商户“错误地”将商品处分给顾客,两者都受到了欺骗,而由于只有一个行为,最终认定为想象竞合。[6]
以上两种主张有一共同点,认为顾客受到了欺骗,即使把案件中的商户搁置一边,行为人的行为就足以构成诈骗罪。由此便引出另一关键问题,诈骗罪的成立是否以造成被害人财产上的损失为必要?认为本案成立一般诈骗罪或双向诈骗罪的观点,是以形式的个别财产减少说作为理论根基。形式的个别财产减少说认为,诈骗罪是相对于个别财产的犯罪,被害人转移或丧失了财物或财产性利益,这本身就是损害,即便行为人向对方提供了价值相当的补偿,也仍然不影响诈骗罪的成立。[14]该说为日本刑法理论通说,也有判例支持这一观点:对方如果知道不是具有特定公司商标的药品就不会购买,却在与真正药品的效用无异的药品上贴上伪造的商标而销售了的(大判昭 8·2·15 集 12·126),判例认为也成立诈骗罪。[15]25
笔者认为形式的个别财产减少说有两点疑问:
首先,诈骗罪的本质在于使用违反诚实信用的手段取得他人财产,[16]但是诚实信用自身并不是刑法保护的法益,而只是附随于财产法益的外部因素。日本刑法理论通说一面认为,诈骗罪终究是财产犯罪,当然应以某种财产上的损失为必要,但同时又将交付本身理解为损失,因而可以说,这实质上与财产性损失不要说并无不同。[17]这样一来明显扩大了诈骗罪的成立范围,把事实上没有侵害财产法益的欺诈行为与诈骗犯罪同等处罚,不符合刑法谦抑性原则。
其次,形式的个别财产减少说对数额的认定过于严苛。在被告人就部分财物具有正当权利,或者被告人为了达到欺骗目的向被害人支付了部分对价的场合,计算诈骗金额时,应当就被害人交付的全部财物成立诈骗罪,还是就扣除权利或对价后的部分成立诈骗罪呢?根据该说,在作为欺骗人的手段提供了代价时,也应当认为诈取额是不扣除代价所交付的全部财物。[15]254笔者认为,财产犯罪必须放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考察,财产的损失是以客观经济价值为衡量尺度的,在存在对价的场合,必须全面考虑权利人的得与失,最终确定是否有实质的经济上的损害以及损害数额的多少。基于以上两点原因,笔者不认同形式的个别财产减少说。
笔者认为,对于财产损失的认定问题,整体财产减少说更具有合理性。整体财产减少说认为,使用欺骗方法骗取财物,但同时作出补偿,使被害人财产的总体并未受到损害,此场合不成立诈骗罪。[18]必须说明的是,德国刑法将诈骗罪规定为对整体财产的犯罪,对于整体财产的得失情况需要适用个别化原则,根据被害人对财物的利用能力等状况作出客观评价。而且除了金钱价值外,还要根据案情考虑市场状况、个人资产状况等。[19]也就是说,整体财产减少说绝非片面比较金钱价值利益,而是要在被骗者交付的财物和收受的财物之间权衡比较,既要考虑财物的客观价值,又要考虑与被害人相关的各种情况。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认为,被害人发生下列三种困境时,即有财产损害:1.所得到的给付,与交易目的不完全相同,或无法可能的方式对其加以利用。2.因为承担义务,不得不采取减损财产的措施(例如,支付较高的利息向银行贷款)。3.由于承担这项义务,再也不能善加利用自己的资产。换言之,缔约之后,经济上的活动自由大受限制。此项判决后来得到了实务界的广泛认可。[20]
根据我国刑法通说理论,诈骗罪的成立要求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而被害人是否遭受数额较大的财产损失,应当是比较被告人行为前后,被害人的整体财产状况得出的结论。的确,诈骗罪是针对被害人个别财产的犯罪,但在许多情境下,被害人需要将个别财物与其他财物结合起来加以利用,个别财物对被害人的主观价值必须与其他财物联系起来才能判断。举例说明,被害人买的车必须适合自家车库的尺寸,因为被骗买到市场价值更高但无法开入自家车库的车,反而会使被害人因停车增加额外支出。因此仅凭“诈骗罪是针对被害人个别财产的犯罪”这一点,并不足以否定整体财产减少说理论。
值得一提的是,形式的个别财产减少说经过修正,引入“法益关系错误”概念,发展出实质的个别财产减少说,认为在诈骗罪中,财产是作为达成目的的手段而予以保护的,因此在“目的实现”这一点上有错误的,就能肯定存在有关法益的错误,进而肯定诈骗罪的成立。[21]313“在商品交易中,最重要的是,受骗者是否取得了他意欲取得的东西。”[21]314显而易见,这一理论将被害人交易目的的实现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张明楷教授认为日本的实质个别财产减少说与德国的整体财产减少说没有原则上的区别,因为实质的个别财产减少说主张从实质上判断被害人丧失财产是否形成财产损失,所以必须联系被害人的交易目的、财产对被害人的可利用性等因素判断,这一点与整体财产减少说相同。[22]笔者认为,实质的个别财产减少说由形式的个别财产减少说修正而来,确实是由形式判断走向了实质判断,更具合理性。但是,虽然两学说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处理结果相同,但本质上仍有区别:整体财产说中客观价值的考察优先于主观交易目的,而在实质的个别财产说中,客观价值的比较和交易目的的衡量不存在位阶性的关系。[23]因此有学者认为,整体财产减少说始终强调客观判断,虽然被质疑过于坚持客观主义,丧失了实质正义,这一“缺陷”反而是整体财产说的优势所在。[24]笔者赞同这一观点。财产在经济生活中的价值,是依据客观上被广泛认可的标准确定的,强调被害人的使用目的不利于坚持客观主义立场。在被告人支付部分对价的情况下,适用实质的个别财产减少说仍会使处罚结果过于严厉。司法实践中,刑法介入经济生活的边界常常难以把握,坚持整体财产减少说可使刑法谦抑性与实质正义并行不悖。
综上所述,由于反对形式的个别财产说,笔者认为“偷换二维码案”中顾客没有损失,不应认定其为被害人,所以本案既不能成立一般诈骗,也不能成立“双向诈骗”。笔者对本案的理解是:被告人偷换二维码的行为欺骗了商户,最终商户遭受损失,但是商户自始至终没有对银行债权进行处分;被告人偷换二维码也欺骗了顾客,顾客陷入错误认识处分了银行债权,但最终实现了交易目的,没有财产损失。所以无论是商户还是顾客,单独而言,两者与被告人之间的关系均不能满足诈骗罪的犯罪构成。
四、结论:成立新型三角诈骗
评价全案,笔者赞同张明楷教授提出的新类型的三角诈骗理论。[6]传统三角诈骗的行为模式是:被告人实施欺骗行为——受骗人基于认识错误处分财物——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通说认为受骗人需具有对被害人财物的处分权限。而在新型三角诈骗中,受骗人基于错误认识处分了自己的财物。利用这一新型三角结构可以使二维码案中当事三方都找到合适的位置,评价整个案件事实不重不漏,解决了传统理论均无法自圆其说的难题,在笔者看来是最合理的解释途径。
在笔者看来,新型三角诈骗理论对传统模式最大的颠覆在于,受骗人与被害人之间不再需要主观上紧密连接。诈骗犯罪从两方结构发展到三方结构,被告人的目标从单一被害人模式转变为受骗人+被害人模式。传统三角诈骗理论中,不管是阵营说、权限说、效果说或其他理论,都是想要说明,虽然客观上被告人的对面是两个人,但他们可以作为一个整体看待。而在新型三角诈骗理论中,受骗人无过错地处分了自己的财物,是否有处分权限的问题在这里已经不存在了,此时的受骗人与被害人之间只存在更为明了、客观的债权债务关系。笔者认为这样的理论创新并无不妥之处,既然传统理论无法满足解释现实案件的需要,发展完善则势在必行。
许多学者质疑该新型三角诈骗理论存在的必要性,虽然张明楷教授也承认是为了处理二维码案件提出了所谓新类型的三角诈骗,但是笔者相信,在第三方支付手段迅速普及、金融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这一理论模型定有更加广阔的适用前景。
[1]柏浪涛.论诈骗罪中的“处分意识”[J].东方法学,2017,(2):97-106.
[2]张庆立.偷换二维码取财的行为宜认定为诈骗罪[J].东方法学,2017,(2):123-131.
[3]冯珏.汉德公式的解读与反思[J].中外法学,2008,(4):512-532.
[4]史尚宽.债法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2000:734.
[5]其木提.论债务人对债权准占有人清偿的效社力[J].法学,2013,(3):87-95.
[6]张明楷.三角诈骗的类型[J].法学评论,2017,35(1):9-26.
[7]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504.
[8]陈兴良.盗窃罪与诈骗罪的界分[J].中国审判,2008,(10):78.
[9]程雁群.盗窃与诈骗——对二维码案的性质探讨[J].中国校外教育,2016,(33):159-161.
[10]车浩.占有概念的二重性:事实与规范[J].中外法学,2014,(5):1180-1229.
[11]陈洪兵.盗窃罪与诈骗罪的关系[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7(6):134-141.
[12]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1000.
[13]李勇.“掉包二维码案”别争了,定诈骗 [EB/OL].(2016-12-01) [2017-09-15].http://www.360doc.com/content/16/1201/23/37195862[611175523].shtml.
[14]刘明祥.论诈骗罪中的财产损害[J].湘潭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1):47-50.
[15][日]大塚仁.刑法概说(各论)[M].冯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16][日]大谷实.刑法讲义各论[M].黎宏,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234.
[17][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各论[M].王昭武,刘明祥,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212.
[18]陈兴良,周光权.刑法学的现代展开[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519.
[19]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596.
[20]林东茂.一个知识论上的刑法学思考[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150.
[21][日]山口厚.刑法各论[M].王昭武,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22]张明楷.论诈骗罪中的财产损失[J].中国法学,2005,(5):118-137.
[23]蔡桂生.论诈骗罪中财产损失的认定及排除——以捐助、补助诈骗案件为中心[J].政治与法律,2014,(9):48-59.
[24]史蔚.诈骗罪财产损失的类型化讨论[J].江西警察学院学报,2017,(2):1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