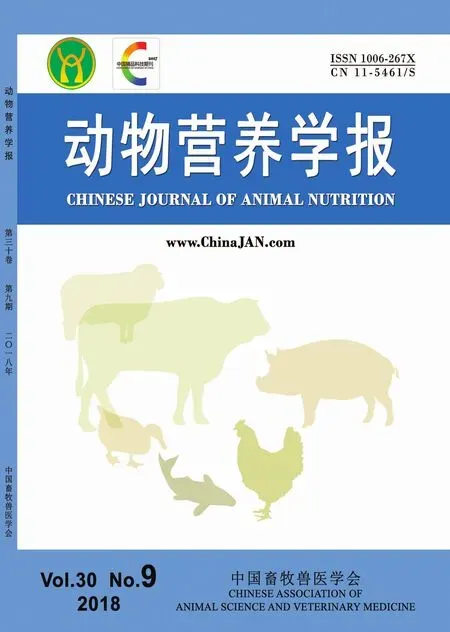宿主防御肽调节动物肠道屏障功能的研究进展
王 鑫 张萌萌 姜 宁 张爱忠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动物科技学院,大庆163319)
宿主防御肽(HDPs)也称为抗菌肽,是动物先天性免疫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具有广谱的抗革兰氏阴性细菌、革兰氏阳性细菌、真菌、病毒、原生动物甚至癌细胞的抗微生物活性,大多数HDPs在黏膜表面(包括胃肠道)均有表达。HDPs的主要种类有防御素、cathelicidins、S100家族、RNase A超家族、再生胰岛衍生Ⅲ(REGⅢ)C型凝集素和肽聚糖识别蛋白[1]。由于大多数HDPs带正电荷或具有两亲性,它们主要通过破坏细胞膜或与细胞内大分子相互作用来杀死细菌。通过静电相互作用,带正电荷的HDPs与细菌膜上带负电的磷脂基团结合。HDPs的两亲性使其易于插入靶细胞膜中,从而破坏细胞膜的完整性。在细胞内,某些HDPs也能够抑制蛋白质、DNA和RNA合成,或者与特异性靶标结合。除抗菌活性外,HDPs还参与调节固有免疫应答。譬如,3种鸡源cathelicidins(fowlicidin1、fowlicidin2和fowlicidin3)直接与细菌细胞壁外膜中的脂多糖(LPS)结合,具有中和LPS诱导巨噬细胞炎性细胞因子产生的能力[2]。3种牛源β牛防御素[牛中性粒细胞β-防御素3(BNBD3)、牛中性粒细胞β-防御素9(BNBD9)和牛肠源性防御素(EBD)]对未成熟的单核细胞来源的树突细胞具有趋化性[3]。猪源cathelicidin PR-39还能抑制吞噬细胞还原型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磷酸(NADPH)氧化酶活性,并通过阻断结合p47phox(一种NADPH氧化酶的胞质成分)而抑制酶复合物的合成来减弱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4]。因此,具有有效抗菌活性和调节固有免疫应答的HDPs被积极开发成新型抗生素。最近研究表明,HDPs能直接调节黏蛋白、紧密连接(TJ)蛋白的表达和微生物群落的组成,以增强黏膜屏障的通透性。HDPs在肠道屏障功能和肠道黏膜稳态中的新作用将作为本文的论述重点。
1 动物肠道屏障功能概述
胃肠道内的单层上皮细胞除可促进营养物质的消化和吸收外,还可作为微生物和毒素入侵的屏障,其是通过用黏液层涂覆上皮细胞并在上皮细胞之间形成选择渗透性屏障的手段来实现肠道屏障功能。黏液层主要由杯状细胞分泌的黏蛋白组成,其可作为肠腔内容物和宿主之间的物理屏障,并且还有助于营养物质的消化和吸收。改变黏蛋白的表达或糖基化通常与肠屏障功能障碍有关。例如,小鼠的黏蛋白2(MUC2)基因缺陷导致肠道上皮细胞渗透性增加、大出血、胃肠道炎症以及严重的生长迟缓[5]。黏蛋白1(MUC1)或MUC2基因缺陷型小鼠变得更容易感染空肠弯曲杆菌、幽门螺杆菌、鼠伤寒沙门氏菌以及鼠柠檬酸杆菌。此外,缺乏β-1,3-N-乙酰葡糖胺转移酶的小鼠表现出较薄的黏液层,增加了肠道细菌感染和葡聚糖硫酸钠(DSS)诱导的结肠炎的易感性[6]。
胃肠道的主要屏障功能表现在上皮细胞中,上皮细胞通过2种途径(即跨细胞和旁细胞途径)转运水、离子和大分子。跨细胞通路是指小分子主动或被动转运通过上皮细胞的运动,而旁细胞通路是指上皮细胞之间的水、大分子和免疫细胞的扩散。在完整的上皮细胞中,旁细胞通路决定了肠道的通透性并由上皮之间连接调节,被称为TJ。肠上皮是由几种不同类型的细胞组成的隐窝和绒毛。这些细胞包括肠上皮干细胞、肠上皮细胞和肠内分泌细胞,如潘氏细胞、杯状细胞和肠内分泌细胞[7]。肠上皮干细胞能分化出所有类型的上皮细胞,而肠上皮细胞主要在营养物质吸收中起作用,并具有合成和释放HDPs及黏蛋白的能力。潘氏细胞和杯状细胞分别是HDPs和黏蛋白的主要生产者,而肠内分泌细胞主要分泌许多激素,作为消化功能的调节剂[7]。通过形成3种主要类型的连接复合物,即TJ、黏附连接和桥粒,所有肠上皮细胞与侧膜连接[8]。总体而言,这些连接复合物形成了对细胞间隙几乎不可渗透的密封。除了屏障功能外,这些连接复合物通过将顶端与基底外侧膜分离来维持细胞极性[9]。TJ是位于侧膜最顶端的多蛋白复合物,由跨膜蛋白和胞质附着蛋白组成,这些蛋白直接与细胞骨架相互作用。在这3种主要的连接复合物中,只有TJ具有控制离子、水和小分子的选择性旁细胞通透性的能力[9]。因此,TJ是黏膜上皮渗透性的主要决定因素。
维持黏蛋白和TJ装配能确保营养物质、水、电解质的吸收和运输,同时使宿主免受病原体、毒素和肠道菌群的影响。同时,黏液层和TJ复合物的破坏会导致肠渗透性增加,随后细菌移位加剧,炎症加剧,并可能引起各种肠道和系统性疾病。在畜牧生产中,肠道屏障功能受损将影响动物健康,导致生产性能下降[10]。因此,了解HDPs如何维持和调节肠道屏障功能以实现最佳动物健康状态和生产性能将显得至关重要。
2 HDPs对肠道屏障功能的分子调节机制
2.1 HDPs诱导黏蛋白和TJ蛋白表达的细胞受体
许多细胞外和细胞内受体影响着人和小鼠中cathelicidin和防御素的一系列生理功能。人源抗菌肽LL-37和鼠源阳离子相关抗菌肽(CRAMP)是P2X嘌呤能受体7(P2X7)、甲酰肽受体样1/2、甘油醛-3-磷酸脱氢酶以及sequestosome-1/p62的配体,而几种人类和小鼠β-防御素与CC趋化因子受体2(CCR2)、CC趋化因子受体6(CCR6)、CXC趋化因子受体2(CXCR2)以及Toll样受体(TLR)1/2/4结合[11]。尽管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不是LL-37的直接受体,但LL-37诱导的肺上皮细胞中的气道黏液黏蛋白(MUC5AC)基因的表达似乎主要通过EGFR的反式激活介导[12]。最初,LL-37触发肿瘤坏死因子(TNF-α)转换酶的活化,依次切割TNF-α结合形式,但不切断肝素结合表皮生长因子(EGF);释放的TNF-α随后与EGFR相互作用并使其磷酸化,其通过激活多个信号转导途径来诱导MUC5AC基因的表达[12]。对于LL-37在人肠上皮细胞中诱导MUC2和黏蛋白3(MUC3)基因的表达,涉及EGFR和P2X7,但不涉及G蛋白偶联受体[13]。在人肠上皮细胞中HBD-2诱导的黏蛋白表达是通过CCR6部分介导的[14]。
2.2 HDPs调节肠道屏障的信号转导途径
促分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APK)途径是由细胞外调节蛋白激酶(ERK)、c-Jun N端激酶(JNK)和p38组成的3个典型信号级联[15]。S100A7能够激活这3个典型的信号级联。ERK在暴露于S100A7后2 min内迅速在人皮肤角质细胞中磷酸化,JNK和p38 MAPK也在30 min内被磷酸化。p38 MAPK参与调节人Caco-2细胞中MUC2产生的P2X7和EGFR活化[12]。抑制单个MAPK信号级联将显著降低跨表皮电阻(TEER),这意味着3个主要的MAPK途径都是必需的。抑制ERK途径增强了丁酸-腺苷酸环化酶激活剂(FSK)协同作用,而阻断JNK或p38途径显著降低了鸡巨噬细胞和空肠外植体对禽β-防御素9(AvBD9)的诱导[16]。丁酸钠激活了牛乳腺上皮细胞中TLR2/p38细胞转导通路,上调了气管抗菌肽(TAP)、牛中性粒细胞β-防御素5(BNBD5)、牛中性粒细胞β-防御素10(BNBD10)的表达,提高了抗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内化的能力并发挥抗炎作用[17]。丁酸钠诱导PK-15细胞中的猪β-防御素3(pBD3)、猪防御素EP2C(pEP2C)、猪β-防御素128(pBD128)、猪β-防御素123(pBD123)和猪β-防御素115(pBD115)表达上调,但没有发生炎症反应,同时,TLR2可被丁酸钠和肽聚糖激活,阻断TLR2表达,抑制了HDPs的诱导[18]。TJ蛋白的翻译后修饰和相关的肌动球蛋白环的状态对屏障渗透性会有很大的影响。许多因子通过某些TJ蛋白的磷酸化或通过肌球蛋白轻链激酶(MLCK)的激活来改变屏障功能,MLCK又使肌球蛋白轻链磷酸化并引起功能性肌动球蛋白环的收缩和细胞旁孔的开放。确定HDPs是否以及如何影响TJ蛋白的翻译后修饰以及MLCK的转录和活性将是后续研究热点之一。
2.3 HDPs调节肠道黏蛋白和TJ蛋白的合成
人β-防御素-2(HBD-2)上调人结肠上皮细胞HT-29中MUC2、MUC3 mRNA的表达,但不上调MUC1或MUC5ACmRNA的表达[13]。相对于HBD-2,人结肠上皮细胞Caco-2中MUC2 mRNA的表达也上调,而表达上调的MUC2又促进HBD-2 mRNA的表达,暗示MUC2与HBD-2之间存在正反馈调节机制[19]。LL-37在HT-29细胞中对MUC1、MUC2和MUC3 mRNA的表达均有增强作用,在Caco-2细胞中仅对MUC3 mRNA的表达有增强作用[13]。buforin Ⅱ是一种从亚洲蟾蜍的胃中分离出来的含21个氨基酸的HDPs,可改善受3种产肠毒素性大肠杆菌(ETEC)菌株攻击的断奶仔猪的肠道屏障功能[20]。口服给药buforin Ⅱ诱导受大肠杆菌攻击仔猪的空肠节段中claudin-1、occludin和ZO-1蛋白的表达增加。重要的是,buforin Ⅱ还可改善肠道形态和生长性能,并减少粪便拭子中的细菌脱落。此外,使用称为cathelicidin-BF的带状krait HDPs能诱导健康小鼠空肠中ZO-1蛋白的表达,并恢复LPS介导的ZO-1损伤和肠道屏障功能[21]。此外,pBD-2能恢复MUC1、MUC2 mRNA的表达,claudin-1、ZO-1和ZO-2蛋白的表达以及DSS处理小鼠结肠屏障的完整性[22]。
3 HDPs对肠道黏膜稳态的影响
肠上皮细胞的主要功能之一是作为抵抗微生物入侵的屏障。肠黏膜上有1 000多种微生物定植,其中大多数是共生细菌,通过这些细菌来改善消化、吸收和维生素合成的能力,从而有益于宿主,同时还能限制病原体繁殖。存在于人和小鼠肠道中的2种最主要的细菌是革兰氏阴性菌和革兰氏阳性菌,它们合计存在的细菌数占总细菌数的70%~80%。共生细菌对正常肠道形态和免疫系统的发育至关重要。尽管共生细菌在稳态条件下对宿主是有益的,但是在稳态失调或微生物群落失衡的状态下会导致炎症和上皮细胞动态平衡紊乱。
肠上皮通过模式识别受体(PRR)和微生物相关分子模式(MAMP)之间的相互作用持续监测定植微生物。激活PRR能刺激肠细胞中HDPs和黏蛋白的合成和释放。Paneth细胞和肠上皮细胞分泌的大量HDPs被保留在黏液层中,以形成强大的屏障抵抗细菌入侵。HDPs敲除和转基因小鼠的研究已经阐明了HDPs在肠内稳态和免疫防御中的作用。敲除小鼠cathelicidinCRAMP基因会引发小鼠结肠炎,并且在DSS诱导后疾病症状进一步恶化[23]。从野生型小鼠向CRAMP基因敲除小鼠转移骨髓细胞减轻了DSS诱导的结肠炎。携带人类防御素5(HD5)转基因的小鼠表现出增强抵御口服鼠伤寒沙门氏菌感染的能力。相反,产生生物活性肠道防御素的基质金属蛋白酶7(MMP7)基因敲除小鼠表现出清除肠道病原体的能力下降。与野生型小鼠相比,HD5转基因小鼠的硬壁菌菌数减少,类小杆菌菌数增加,而MMP7缺陷小鼠则相反[24]。此外,HD5在小鼠中的过度表达导致远端小肠中分节状细菌显著减少,固有层中T17细胞数也减少,这清楚地表明肠道HDPs代表了形成微生物群落的关键因素和消化道的炎症状态。
4 HDPs对动物生长性能和肠道形态的影响
多项研究强调了直接饲喂HDPs对猪生长、肠道形态和免疫状态的有益作用。饲喂重组家蚕HDPs天蚕素A/D明显提高了受ETEC侵袭的断奶仔猪的生长性能和饲料转化率,并减少了腹泻发生率,同时在6 d内对肠道形态和氮/能量利用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25]。饲粮中添加来源于牛乳铁蛋白的重组融合HDPs也提高了仔猪的生长性能,并在21 d内降低了受ETEC侵袭的仔猪的腹泻发生率[26]。在5个不同的农场中,饲喂4种重组HDPs的混合物,包括乳铁蛋白、天蚕素、防御素和菌丝霉素,可增强断奶仔猪的生长性能和饲料转化率,并减少了腹泻发生率[27]。与上述研究相似,在4周的试验中补充人工合成HDPs(AMP-A3或P5)改善了断奶仔猪的营养物质消化率、肠道形态和生长性能,但没有显著影响血清中免疫球蛋白A(IgA)、免疫球蛋白G(IgG)和免疫球蛋白M(IgM)的含量[28]。此外,AMP-A3和P5似乎降低了潜在有害梭菌的滴度以及回肠、盲肠和粪便中大肠菌群数量[29]。在受真菌毒素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的侵袭下,饲喂2种HDPs和1种益生菌酵母的组合物使仔猪的肠道形态和饲料转化率得到提升[30]。在上述大多数试验中,HDPs在促进猪群生长、提高饲料转化率和改善肠道形态方面与抗生素无差别。饲粮中补充AMP-A3增加了肉仔鸡的体重,提高了饲料转化率,这与饲粮中补充抗生素阿维菌素的肉仔鸡的生产性能相近[31]。通过增加小肠绒毛高度和绒毛高度隐窝深度比例,肉鸡的肠道形态也可得到改善。添加含重组天蚕素A/D的酵母肉汤提高了肉鸡的肠道形态和饲料转化率,在4周的试验中有提高肉鸡生长性能的趋势[32]。天蚕素A/D也降低了42日龄鸡的空肠和盲肠内容物的总需氧菌数量。总的来说,这些动物试验结果表明了HDPs饲喂动物的益处,证明了饲粮中补充HDPs作为促进动物生长和疾病控制的抗生素替代策略是合理的。
5 诱导HDPs合成的化合物
由于HDPs容易发生酶促降解并且合成或重组形式的生产成本高,因此在动物饲粮中直接补充HDPs可能不具有生物学有效性和经济效益。最近,已发现几类小分子化合物如丁酸盐可诱导HDPs合成,并增强动物体内的细菌清除率,而不引发炎症反应。饲粮补充这些简单的HDPs诱导化合物或其组合被证明是一种替代低成本动物常用抗生素的新方法。饲料补充0.1%丁酸显著增加鸡肠道HDPs的表达,同时减少盲肠中近10倍试验感染剂量的肠炎沙门氏菌的滴度[33]。在鸡HD11巨噬细胞和初级单核细胞中,诱导合成的HDPs与游离的脂肪烃链长度呈负相关,短链脂肪酸是最有效的,中链脂肪酸和长链脂肪酸效果较差[34]。3种短链脂肪酸,即乙酸盐、丙酸盐和丁酸盐,在鸡细胞中在增强HDPs基因表达方面发挥了强大的协同作用。与单独添加短链脂肪酸相比,将3种短链脂肪酸组合混合添加到饮水中能进一步减少鸡盲肠中的肠炎沙门氏菌感染。更重要的是,短链脂肪酸增强了HDPs基因的表达而不刺激促炎白细胞介素-1β的产生。丁酸盐缓解了大肠杆菌O157∶H7诱导的猪溶血性尿毒症的临床症状综合征(HUS)和部分炎症,并且通过乙酰化修饰作用来上调HDPs的表达[35]。乙酸、丙酸、丁酸和己酸均能减少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牛乳腺上皮细胞并上调TAP、BNBD5基因表达[36],但这些HDPs诱导化合物在促进动物生长、肠道健康和微生物群落平衡方面的功效尚需在反刍动物试验中进一步得到证实。
6 小 结
破坏肠道屏障会导致动物疾病并降低生产效率,因此了解肠道屏障功能及其调控机制对于确保畜牧业的可持续性发展至关重要。凭借强大的抗菌性和免疫调节能力,HDPs进一步表现出直接调节肠道屏障功能的新能力。HDPs异常合成通常导致肠道屏障功能障碍,屏障完整性受损的疾病通常与HDPs合成减少有关,这均显示出HDPs在增强肠道健康和动物表现方面的潜力。虽然已实现应用合成肽治疗人类疾病,但在畜牧业中应用成本还是非常高昂的。HDPs的诱导化合物或外源性重组HDPs已经成为动物疾病预防与治疗的有效策略,并且在未来可能替代畜牧生产中抗生素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