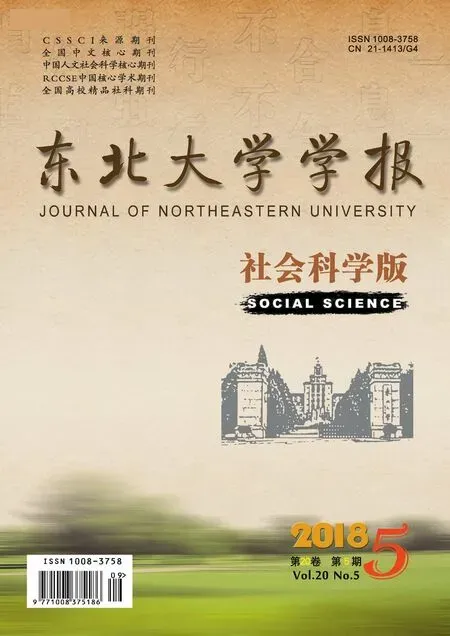论先秦儒家自然观对先秦儒家技术思想的“基础”作用
阚 迪, 吴 智
(1. 东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辽宁 沈阳 110169; 2. 沈阳建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辽宁 沈阳 110168; 3. 辽宁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辽宁 沈阳 110032)
纵观中国古代思想史及中国古代技术思想史,先秦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既是对夏商周以降先古思想的继承与总结,又开创性地为之后的古代传统思想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此意义上,对中国古代技术思想“源头”的先秦技术思想进行深入研究,显然是当代技术哲学领域的应有之义。然而,当下就思想谈思想地研究先秦(儒家)技术思想,往往存在着“内容缺失”和“视角缺失”的症结,即以某位思想家一家之言“以偏概全”地导出倾向性论断,或仅抓住先秦某家(儒家)涉及技术的言论就宣称获得整体性结论。于是,需要我们从技术思想所对应的自然观、历史性、社会性等方面多角度、多层次入手,方能共同揭示先秦技术思想的“真貌”。因此,以先秦儒家为例,深入剖析自然观与技术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论证先秦儒家自然观对先秦儒家技术思想的“基础”作用,既明晰了先秦儒家自然观为先秦儒家技术思想“内容”层面的科学构成,又将为先秦儒家技术思想提供“视角”层面的有益补充。
一、 先秦儒家自然观是先秦儒家技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础”
首先,在探究先秦儒家自然观与技术思想时,需要明确先秦儒家技术思想中的技术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技术,是搞‘技术工作’中的技术,是生产技术、工程技术、医疗技术,是针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技术”[1],即属于“狭义技术”范畴,而非“一切手段和方法总和”意义上的“广义技术”。那么,先秦儒家技术思想则是先秦儒家“以技术为对象的思考过程、思维意识产物及物化在技术产品中的人类意识的总和,包括所有对于技术本质的思考,技术经验和技术知识的总结,技术活动的感悟,技术后果的反思等”[2]。
其次,对于自然观,陈昌曙先生认为“是人们对自然界的总体性认识,是关于自然系统的性质、构成、发展规律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等方面的根本看法”[3]。张明国教授也认为:“自然观是人们关于自然界及其与人类关系的总的观点,它是人们认识和改造自然界的本体论基础和方法论前提。”[4]根据以上两位学者的总结,先秦儒家自然观应定位为“先秦儒家对自然界及其与人类关系的总的观点”。
最后,陈其荣先生提出技术哲学(思想)以技术为对象进行思考,“主要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工自然的角度研究技术的本质、结构和发展规律”[5],并进而确认技术哲学(技术思想)的研究“是以自然本体论为前提的”。据此,当先秦时期技术作为直接改造自然世界的手段和方法时,认识自然与改造自然两者紧密联系、互为表里的辩证统一关系就通过技术显现出来。于是,“如何认识自然”是研究“如何改造自然”的有益补充就顺理成章。当然,两者不仅局限于内容层面的有益补充,“怎样认识自然”还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怎样改造自然”并凸显出基础性作用。
因此,诚如乐爱国教授提出“中国古代的自然观是古代科技思想的组成部分,并且是其重要的思想基础”[6],我们可从三个层面入手,即通过怎样看待自然并确认自然是什么,通过人在自然界的定位确认人对自然界能够做什么,通过人应怎样对待自然并确认人与自然的关系,最终先秦儒家自然观对先秦儒家技术思想分别奠定了本体论、主体性、生态性的“基础”。
二、“天行有常”自然观为先秦儒家技术思想提供本体论“基础”
先秦时期并没有现代学术意义上的“自然观”概念,而先秦儒家最能够代表和涵盖“自然”概念的则对应着“天”。换言之,先秦儒家对“天”的认识则代表着对“自然”的认识。其中,孔子、孟子和荀子等儒家先贤就一脉相承地为我们诠释出“天”为何物。《论语》[注]下文引用孔子原文均出自此书,只标明篇名,不再作为参考文献一一标注。同样地,引用孟子和荀子原文也作类似处理。[7]论天,《阳货》: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述而》:天生德于予。《颜渊》:死生有命, 富贵在天。《宪问》:不怨天,不尤人; 下学而上达。知我者, 其天乎!《季氏》:畏天命。孔子在“天生”“怨天”“天命”和“在天”等命运、主宰、义理之天外,首次用“天何言哉”的自问自答正式提出与“四时”“万物”相对应的物质(自然)之天。《孟子》[8]论天,《梁惠王下》:吾之不遇鲁侯,天也。《万章上》: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 暴之于民而民受之;莫之为而为者, 天也。《告子上》:天之降大任于斯人也。《梁惠王上》: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浡然兴之矣。《离娄下》: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孟子在“天也”“天受之”和“天降大任”等命运、主宰、义理之天外,又明显增加了“天作云” “天高星远”的物质(自然)之天成分。《荀子》[9]论天,《儒效》:至高谓之天, 至下谓之地。《天论》: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夫是之谓天;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更加直接而坚定地从“至高天”到日月星辰客观运行规律中,得出“天行有常”的物质(自然)之天结论。
纵观孔子、孟子、荀子对“天”的认识,众多学术大家均有较一致的分类,冯友兰先生认为“‘天’概念有五种: 物质之天、主宰之天、运命之天、自然之天、义理之天”[10]。杨伯峻先生认为“天”包括:物质之天、主宰或命运之天、义理之天。然而,从先秦儒家技术思想的视角可进一步归为三类,一是物质之天和自然之天,可统称为物质之天即指向客观存在的自然界;二是主宰之天和命运之天,主要存于儒家先贤的情感抒发和感慨之中,并不意味先秦儒家是完全相信和服从于命运之天,否则哪会有儒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坚持;三是儒家的义理之天,通过人道和天道求仁的共同目标可推及天道即人道,人道可合乎天理并至天人合一。对此,我们需要整体地、历史地、客观地去重新厘清先秦儒家之“天”。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和正视先秦儒家对“天”的认识较夏商周有着整体性的变革和超越。随着先秦儒家对自然现象的不断经验性总结和对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物质之天(自然之天)逐渐走下先祖的宗教祭坛及神坛。可以说,先秦儒家自然观相较于前人最大的突破,正是极大增加了对物质之天的客观而科学的认识,并郑重宣告“天行有常”。其次,纵观人类科技史的进程,每一次对自然界的重大认识变革都需要通过时间的积累才能实现“螺旋式的上升”。于是,我们不必忌讳先秦儒家命运之天的残留,而应结合他们表述命运之天的具体语境,发现其中更多表达着一种基于人性的情感宣泄和人生感慨,例如孔子对子路发誓“予所否者, 天厌之!天厌之!”和孔子病中愤慨道“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其中不是对命运之天的妥协,而是口头语言的惯性语气。这也符合先秦儒家自然观“总体上是唯物主义但蕴含着唯心主义的因素”[4]的历史性特征,即命运之天并未否定先秦儒家对物质之天的科学认识及其先进性。最后,在《论语·八佾》“不然。获罪于天, 吾所祷也”中,先秦儒家的义理之天正是其道德之天,一方面这里的“天”已剥离愚昧化的神秘性,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神格天,为人们塑造和预设了一个完美的道德境界;另一方面它又蕴含着拟人化的道德属性,预示着人们通过道德修行,可达成“仁”的境界,即与天“合一”。于是,命运之天和神秘之天被拉下神坛,从而反向论证了“物质之天”的正确性。同时,更为自然界赋予“有机的”生命气息,清除了仅供谋算和索取的无生命的、机械的自然“外壳”。
至此,我们得以历史地、客观地、整体地去定位先秦儒家之“天”正是物质之天。先秦儒家“天行有常”的自然观肯定自然界整体上是唯物的、客观的、“有常的”,并且,“天行有常”正是沿着先秦儒家认识自然的历史脉络而成的。孔子之天“其主要意义已不是指主宰人类命运的神,而是指自然界生长发育的过程”[11]42;孟子之天“有着明显的神学成分,但这种神学观点不是殷周以来传统神学天道的继续”[12];荀子在孔孟基础上坚定地确立了“天行有常”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因此,无论是物质之天为先秦儒家自然观不断增加着科学、客观的成分,还是命运之天使朴素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仍残留唯心成分,甚至先秦儒家可以通过践行“仁”达到义理之天,从另一路径把命运之天拉下神坛。以上先秦儒家“三类天”整体呈现出“天行有常”的自然观,从而为人们(技术主体)认识客观自然提供了认识维度的“可知论基础”;又为人们(技术主体)通过技术实践来改造客观自然提供了实践维度的“对象性基础”,从而共同为其技术思想提供了本体论的基础。
三、“制天命而用之”自然观为先秦儒家技术思想提供主体性“基础”
先秦儒家物质之天的确立,夯实了“天”内含客观的、物质的自然属性,为人们挣脱神秘之天和宗教之天神格化、宗教化的统治,从而有尊严地面向自然“站”起来,奠定了认识维度的可知论基础和实践维度的对象性基础。然而,先秦儒家自然观绝未止步于本体论层面的基础作用,它还通过主体性的确立及技术主体能够通过技术实践生产并创造技术产品,彰显出技术主体的能动性和积极性。
先秦儒家先贤的重要创举之一正是提出并贯彻人类是独立于“神灵”和“禽兽”的族群,人因为德行和心性的强大而彰显主体的尊严。对此,有学者高度评价道:“如果说,孟子在中国思想史上最先树立了伟大的个体人格观念,那么,荀子便在中国思想史上最先树立了伟大的人的族类的整体气概”[13]。孔子在《论语·微子》正式提出:“鸟兽不可与同群”,道出人超越鸟兽之实。《论语·卫灵公篇》“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之“能”,坚决地展现出人的能动性和积极性。同时,儒家之道的达成并非坐井观天式的消极等待,而是“当仁不让于师”的主动践行。《论语·述而》更提出:“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这进一步彰显人们追求、修行“仁”这一儒家核心理念的主体能动性和自信力。《孟子·离娄下》:“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这表明人与禽兽等自然界其他生物的区别在于人可以“君子存之”,能够“明于庶物,察于人伦”,且“由仁义行”。那么,如何实现仁义,孟子通过“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表明人应通过主动地、积极地、自觉地反躬自省,弥补自身仁、智、敬等方面的差距,去实现爱、治、礼,进而“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于是,先秦儒家独有之积极、主动、自觉的主体性确立落实到其自然观层面,即“通过人这一德性主体的实践活动、创造活动而得以实现”[11]67,在人能认识自然的本体论基础上表现出人亦能改造自然的主体性“基础”。
同时,《孟子·尽心上》曰:“万物皆备于我, 反身而诚, 乐莫大焉”,又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此处的“万物”和“天”均属于先秦儒家自然观的“自然”范畴,那么,通过“反身而诚”和“尽心—知性—知天”的修行路径,表明“我”可承载世间万物,并反身求“诚”可至“大乐”。这种人从本性上与天道相通意味着人通过“求诚”“尽心”“知性”等自我努力,就能理解、认识甚至把握自然。这里即使“求诚”及“‘知天’的途径和方法有唯心意味, 但在人能够认识自然的问题上却毋庸置疑”[14]。《荀子·礼论》:“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对此,荀子通过人与水火、草木、禽兽之比,进一步明确了人在自然界的“贵”位即主体性地位。《荀子·天论》更是不再盲目歌颂自然界之伟大,而是从人能够通过技术实践改造自然出发,展现出“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的绝对自信和豪迈气概。至此,从“人能弘道”到“尽心—知性—知天”再到“制天命而用之”的自然观,为先秦儒家技术思想奏响“主体性基础”的“最强音”。
当然,这种主体性基础并非标榜人类的盲目自信和自我膨胀,而是基于先秦儒家对自然本体及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例如孔子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和孟子“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员”。“预善先利”的落实和“规矩成方圆”都表明,先秦儒家自然观中主体性的彰显绝非违背自然客观规律的恣意妄为,而是在客观认识自然基础上的理性确立。
四、“仁民而爱物”自然观为先秦儒家技术思想提供生态性“基础”
虽然,先秦儒家已经彰显出人作为技术主体的能动性和积极性,但这种主体性的彰显并非无限度的扩张和方向缺失的冒进,它始终受到先秦儒家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即“仁民而爱物”的自然观限制。《孟子·尽心上》:“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其中,即使有亲亲、仁民、爱物的层次性区分,但最终的落脚点都凝练在“仁民而爱物”中。仁爱万物将使得主体(技术主体)的实践合于人类从自然界中获得生活资料并守护自然的目的,而非无限度地向自然索取造成生态坏境的恶化。这种仁爱自然即仁惠自身的“有机的”和“整体性”的自然观,必然给技术思想赋予技术应符合人与自然和谐的“主旋律”。
《孟子·梁惠王上》提出:“不违农时,榖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荀子·礼论》也认为“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而百姓有余材也”。这里,孟子和荀子通过“时”的概念进一步诠释了“仁民而爱物”的自然观,即人们应该遵守“时”、维护“时”、顺应“时”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自然观。其中,先秦儒家之“时”应用到农业技术上,就指向农作物生长发育的自然客观规律;落实到林业或渔业技术上,则指向森林植被、鱼鳖水产等生长发育的自然客观规律。
人们若要使技术实践合于“不违时”“不失时”改造自然的目标,首先,需要认同人虽异于禽兽,但并非趾高气昂地凌驾于自然万物之上的观念。“君子”之所以贵,在于他们即使追求更多的生活资料,也不会放任自己向自然生态无节制、无限制地索取。其次,先秦儒家自然观明确了需顺应春夏秋冬不同时令来从事农林牧渔等方面的技术实践。这也与其认识维度的可知论基础密切相关,其技术实践是以科学、客观、合规律的认识为基础的。最后,先秦儒家通过对“时”的科学认识和顺“时”而“耕、耘、收、藏”,使得技术实践既合于“不违时”的目的性,又合于明“时”知天的规律性,从而保障人通过技术实践可以获得“余食”“余用”和“余材”,保障人工自然始终处于能够自我修复的承受范围内,保障人的技术实践都符合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主旋律。
可见,先秦儒家“仁民而爱物”的自然观规范着人们从事技术实践应顺“时”而为,并从儒家“王道之始”或“圣王之制”的高度,坚定地确认了其技术思想的生态性“基础”,即人通过技术实践向自然获取生活资料必须以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和谐为基础和前提。
五、结 语
当下,面对技术思想人文性和生态性缺失等原因造成的生态危机,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认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等方面的理论支撑和思想指南”[15]。然而,正如有机马克思主义代表柯布宣称的----“我相信,儒家和道家思想很有帮助”[16],我们还需充分认识到先秦儒家“天人合一自然观和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的相融性”[17],并从先秦儒家自然观中汲取弥补当代技术思想人文性和生态性缺失的有益养分。
其实,当我们剖析先秦儒家自然观为先秦儒家技术思想提供本体论、主体性和生态性“基础”时,先秦儒家自然观蕴含着有机的、动态的、整体的、和谐的生态理念就跨越历史,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中国化提供着有机论和整体论层面的“生态”价值启示。对此,从技术思想视角,这种“生态”价值也对应着前述先秦儒家自然观得以显现。一是先秦儒家“天行有常”的自然观,为人们能够认识自然并通过技术实践改造自然奠定了可知论及本体论的基础。这种基础中,先秦儒家义理之天指向“天人合一”所蕴含的拟人性、有机性、人与自然互通性,甚至命运之天对自然的敬畏性,都为消解人与自然疏离和技术异化,塑造出一个并非僵化的、机械的、与人对立的“活”的自然,即可由人道至天道的有机自然。二是先秦儒家“人能弘道”“尽心知天”到“制天命而用之”的自然观,宣告人们是可通过技术实践积极改造自然的行动者,彰显出人类作为技术主体的能动性基础。这种基础中,先秦儒家“万物皆备于我”的反躬自省和尽心而后知性、知性而后知天的修行理念,表明通过心灵的、德性的修行来保持精神的饱满、价值观的坚守和心境的自由,可以抵抗因技术异化造成人的物质化和自由的缺失。三是先秦儒家“仁民而爱物”的自然观倡导仁爱的范围要扩展到自然万物,人与自然应符合“王道之始”或“圣王之制”的规定:任何技术活动的开展和技术产品的应用都需要一种生态性的制约和基础。这种基础中,先秦儒家将人、技术与自然予以统一连接,约束着技术实践应符合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前提,技术对自然的改造应处于自然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范畴内,进而凸显出先秦儒家生生不息、万物一体的有机自然观,为拯救技术侵害自然导致生态危机提供了价值论层面的“和谐”理念。
因此,通过剖析和厘清先秦儒家自然观对先秦儒家技术思想的基础作用,既摆脱了就思想推演技术思想的研究局限,向先秦儒家技术思想“内容”层面深度挖掘、提炼出自身的重要组成部分,又为先秦儒家技术思想在“视角”层面,向外拓展出自然观层面的有益补充,更为丰富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切实推动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中国化,进而解决技术思想人文性和生态性缺失及生态危机,提供了浓厚的整体论和有机论的生态因子。
——由刖者三逃季羔论儒家的仁与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