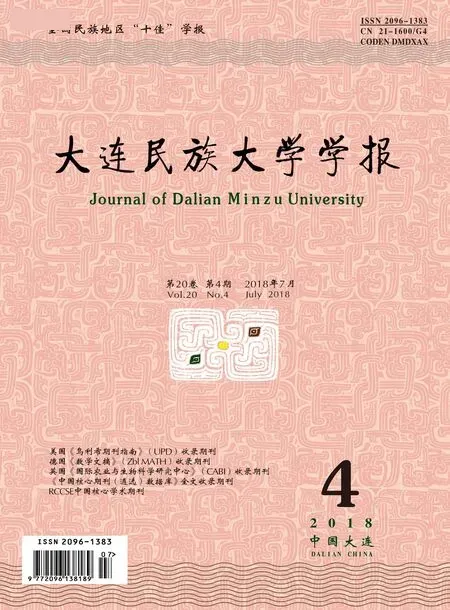蓝冰现代诗简论
李晓峰
(大连民族大学 文法学院,辽宁 大连 116605)
一
80至90年代,是20世纪中国诗坛最辉煌、最自豪的时代,是诗人、读者、编辑激情共同燃烧的时代。正是在那个时代,1950年代就诞生在大草原怀抱的《草原》文学月刊吸引了中国诗坛全部目光,那些一提到名字就让人热血沸腾的诗人们——北岛、顾城、杨炼、江河、海子、韩东、杨黎、昌耀、顾工、韩作荣、于坚、邹静之、张洪波、陈东东、叶延滨、潘洗尘尽数在《草原》“北中国诗卷”闪亮登场,“北中国诗卷”成为中国现代诗群的栖居之地。在“北中国诗卷”中同时栖居着另一个引人注目的诗歌群落,就是内蒙古高擎现代主义诗歌大旗的诗人们——雁北、默然、阿古拉泰、张天男、成子、博尔姬·塔娜、梁彬艳、方燕妮、蒙根高勒(采英)、白涛、杨挺、赵建华、蒙原、梁粱、赵飞、独桥木、李聪颖、伊勒特、袁凯军、齐俊峰、张钟涛、郭春浮、李岩、王忠范、王玉坤、殷杉、万方、尹树义、乌吉斯古冷、李天荣、张之静、黄锦卿、王维章、张改娟、冰峰等等。这一规模足够庞大的内蒙古本土现代主义诗群,以绝不亚于主流现代主义诗群的先锋意识,以绝不比主流现代主义诗群传统的现代诗艺,以迥异于主流现代主义诗群的对生命、死亡那些所谓终极哲学问题的极具北方色彩和草原气象的思想,卓然独立于中国诗坛。与此同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创刊的《诗选刊》在雁北、阿古拉泰的努力下,也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那时,我曾说过,如果没有北方草原现代主义诗群,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是不完整的。北方草原或现代主义诗群,是中国20世纪现代主义诗潮这部壮阔的交响乐章中不可缺失的乐章。
这一诗群中,就有蓝冰。他与雁北、张天南曾被誉为北国“诗坛三剑客”,在北方诗坛有很大的影响。著名诗人贾漫曾主持他们三个人的作品讨论会。
那一时期蓝冰的代表诗歌是组诗《阳台上的鸽子》和组诗《雪霁》等*本文所引用的蓝冰诗歌皆出自《蓝冰现代诗选》,民族出版社拟于2018年7月出版。。
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中期,蓝冰的现代主义诗歌,没有北岛们强烈的启蒙意识,没有江河、杨炼们压抑不住的重构历史的冲动,没有先锋诗人们对形式自恋式的痴迷,没有于坚、韩东们对崇高消解的口语游戏,他部分地接近于海子——在无数个雪花轻扬的午后和雪霁后的黎明,歌唱自己慈祥善良的母亲,怀念自己落后却纯朴的家乡,感恩贫瘠却又丰饶的土地,回忆村里历经沧桑的大榆树,还有山坡上庄稼和所有草木。他“重新考虑周围的事物”,但绝不象尼采那样发疯,理性的思考挡不住他对爱情的渴望和对自由的无边畅想。他把炽烈、率真、醇厚的情感,都浇注和投射在北方的村庄、北方的雪花、北方的大榆树、北方的土地、北方的土地庙等一切记忆和想象的北方,从而建构了他的“北方意象”。而这一点,也正是那些最优秀的现代主义诗人共有的特征。如,橡树、木棉、双桅船、航标灯之于舒婷;花手帕、阳光、瀑布、彩虹、橘红的灯之于顾城;麦子、土地、大海之于海子……。蓝冰属于北方,北方是蓝冰的北方,北方有蓝冰的家乡,那个有8000年历史积蕴和独特风俗的村庄。那历史如同日历在诗人的诗心中,一页页鲜活地展开,对家乡的无限思恋在春、夏、秋、冬的转换中绽放:“我热爱北方纯朴的村庄”“山坡上长满剑草”“我走过秋天的土地一一俯拾金黄的落叶”“在旷野的积雪下面,弱小的生命互相抚慰”“在积雪掩盖的屋子,是谁让一首歌谣去流浪”。在这些“北方意象”的诗歌中,蓝冰的浑厚深沉的诗情如同北方大原野上奔腾的马群和西拉沐沦湍急的波涛。他无意去打磨每一个诗句,无心雕琢每一个语词,而是任由这北方的诗情恣肆,北方的粗犷、北方的粗砺、北方的凝重色彩和生命力量,使他的诗迥异于西化的所谓“现代和先锋”而在“北中国诗群”中卓尔不群。
中国80年代的先锋诗人以及最早的现代主义诗人们,从不缺乏对生命、时代的体验和对真相、对真理、对历史、对人生的思考与思辨;从不缺乏哲学、社会、历史的思想资源。因此,追问、思索、重构、启蒙铸成的诗意的尖锐、目光的冷酷和对历史的洞穿力成为其共有的思想特征。蓝冰的《在一个名字古怪的影院看一场电影——至奥赫本》《哭泣的玛丽亚》《洛尔迦》《屈原》同样如此。而时空的跳宕、错置,知觉与体验的杂糅,意象的组合、意识的流动,意念的闪光、瞬间的直觉或感受的捕捉,以及暗喻、象征、隐语等现代主义诗歌的形式特征,也成为蓝冰现代主义诗歌的基本特点。例如《阳台上的鸽子》《没有云的黄昏》《山里人和帆船》《城市风光和雪》的“形式的意味”极其鲜明:“一只火轮船/从门前经过的时候/鸽子飞来驻留在/我的阳台上”(《阳台上的鸽子》) “火轮船”“鸽子”“我的阳台”由“经过”“驻留”所建构的动感情境,与“我的心最平静”,在动与静的强烈对比中,趋向平衡,在这一准星上,诗人锁定了“如此爱护自己”的人性黑洞。同样,“没有云的黄昏/你走在法国梧桐中/一群鸽子从你身边起飞/我从你的体内起飞/你将因此变得高尚”以及 “我怀抱一条疲惫的河流/在夜晚聆听海风狂喉,海妖啸叫/一万个章鱼在此刻爬上岸来/向你的窗口探视,监视你的梦境”这样的诗句,很容易让人想起舒婷的《路遇》《墙》、顾城的《弧线》《感觉》。在这些诗中,蓝冰保持着现代主义诗歌形式的唯美的高度和思想的哲学高度,而又与这些诗人个个不同。
在那个时代,蓝冰达到了自己现代主义诗歌的高点。
许多中国现代主义诗人,也都把自己的高点,永远定格在那个时代。
二
1998年秋天,蓝冰举家迁往辽东半岛的大连。中秋节,辽东半岛的最南端,一个诗人,一瓶北京二锅头,一盘炒鸡蛋,一支笔,一页素纸,一片大海,一怀愁绪,蓝冰开启了李白“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经典孤独模式,也开启了自己诗歌之旅的第二站,于是有《我站在海滨》《海的感怀》《眺望大海》《我要寄给你的》《故乡偶感》《海上的新娘》等“睹海思乡”等主题的系列诗作。
蓝冰与海仿佛有一种宿命。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蓝冰就写下过《蓝色女王》《我所期待的时刻蔚然降临》《是海,还是风?》等以大海为意象的现代诗。在这些诗中,海的意象承载着诗人对人生、现实、未来或深或浅,或明或暗的思考。海,是意念之海,思想之海,想象之海。在以海为核心,由海鸥、海舟、礁石等组成的整体意象中,诗人无限舒展自由的灵魂和思想,那纯净而灵动的诗句纷至沓来:“正午,阳光明亮/出海的渔舟划过我的胸脯/鸥鸟的双眼照耀我/我平静,我狂暴/放肆地伸展我的四肢/让每一个细胞感受阳光的分量”。在这里,诗人解放了自己的灵魂和身体,任由身体和灵魂释放自由的快意。在《蓝色女王》中,为了征服想象中的“蓝色女王”,诗人“安排茂盛的椰林”作“蓝色女王”的向导:让“所有的禽鸟作你的朋友”,当“蓝色女王”“离开我”时,“我的鲨鱼和海豚都将护卫你上岸”。这里,诗人是鲨鱼和海豚们的首领,而“蓝色女王”却是诗人的神明,诗人甘愿让自己小小的“心脏”成为“蓝色女王”手中“镀金的耳环”。该诗当然是多义的,你可以将之理解为他对爱情的誓言,也可以理解为1980年代中国青年共有的执着、热烈,一无所有却渴望献身的“时代精神”。但是,那种执着、智慧和坚定却不能不让人动容。在《我所期待的时刻蔚然降临》中,诗人写道:“我的渺小将永远为你伟大的上升而感动/为我沙哑的歌喉镀上你不朽的金色吧/我是早晨的出海者/你明亮的海水洗涮我的音符”,“鸥鸟永远不明白/它为什么依赖大海,相信大海,热爱大海/鸥鸟只是一千次一万次地扇动翅膀/它们看见,在每一片羽毛的末尾/天空都被撕开一道小缝,留下优美的弧线”。这种单纯的思想和热烈的情感,折射着此时蓝冰个体生命、情感的的屣迹,也同样倒映着一代人对爱情、生活信仰和理想的最终姿势。这姿势,正如诗人在《是海,还是风?》中所定格的那样:“唯有我,唯有我们/站在闪着金光的礁石上,向东方/向海洋之门,迎迓自由的鸥鸟/因为自由的名义是海的名义/自由的向往是海的向往”。值得一提的是,在上述诗歌中,例如“我小小心脏”甘愿做“蓝色女王”手中“镀金的耳环”,“我的渺小将永远为你伟大的上升而感动”等表现出来的诗人对自我的身份、价值的定位和深刻认知,决定了蓝冰永远是蓝冰,他不会成为海子、西川,也不会步北岛、江河、杨炼的后尘,当然也不会做伪装成平民的于坚。因此,蓝冰这一时期以海为意象的诗,与自己的其他具有探索意味的现代主义诗歌一样,在诗艺上从属于现代主义诗潮,在诗旨上,在与当时民主思想的觉醒和对社会政治强烈介入意识的社会思潮一脉相通的同时,又保持着特定的距离——不是他不想伫立潮头,而是他的诗心一直依偎着北方的大地和他热爱的生活。
但是,1998年后蓝冰的海意象诗却与上述诗歌完全不同。背井离乡面海而居固然是一种 “良禽择木而栖”的主体价值重建诉求驱动下的主动性选择,然而空间距离的骤然拉开,却反向造成了心与家乡的愈发扭紧,他的思乡之情也因为生存空间的位移而在“海”与“草原”之间展开。北方的村庄,扩展为北方草原,意念之海为现实之海取代,诗性思维空间对象的重组与置换,使二者之间在幻象和情感之维度进行了反复重合叠加:“我站在海滨,眼前是千顷波涛,可在我的心中她突然变成了牧草茫茫”(《我站在海滨》)。这里,诗人将喷涌而出的思乡之情,在幻觉与错觉同时在场、“草原”与“大海”的移形换位的空间蒙太奇效应导引下,回归草原深处,化作无间性的声声诉说:“我想念你荒凉的山岗/巍然挺立/就像衰老的父亲站在苍茫的北方”“我也怀恋那热烈的洒歌痛快酣畅”“我思恋苍凉辽远的北方/骏马的心,已紧紧系在拴马桩上”。在猎猎的海风中,在轰鸣的波涛中,在逐级推升的“想念”“怀恋”“思恋”中,让诗人凝重悲凉的思乡之情,因“你是我母亲居住的地方/我的祖辈,就安睡在你的衣襟上”的具象而得到无限的抚慰。于是,大海成为流动的草原,草原成为凝固的大海。《我站在海滨》是以思乡为情感媒介,将大海与草原进行情感与诗艺关联的经典之作。与该诗相似的还有《海的感怀》《眺望大海》《我要寄给你的》《故乡偶感》《海上的新娘》等,这些诗构成了蓝冰“海洋”的诗歌方阵,也标志着蓝冰现代诗创作对现实主义诗歌的回归。
三
且歌且行,为江山作传。这是近年来蓝冰关于自己诗歌创作意图说的最多的一句话,也是蓝冰对自己近年来现代诗歌创作转向和创作实践作出的总结。而我以为,“为江山作传”传达出来的更多的是一份文学责任,而“为山水立心”则彰显出蓝冰近年来诗学追求的又一次嬗变。
笔者曾在一篇谈论少数民族诗歌的文章中说过,50年代至70年代,由于政治文化环境乃至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制约,中国诗人们只能想象幅员辽阔的祖国,用诗脚走遍祖国的每一寸山河。而新世纪以后,不但政治文化环境为诗人创造了可以自由行走于祖国山水的社会环境,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为诗人提供了交通、资金方面的便利。诗人们终于可以用自己的双脚去丈量祖国的每一寸土地,用自己滚烫的诗心来触摸祖国的每一寸肌肤,他们对祖国的幅员辽阔的空间想象,转化成对每一寸土地、每一处历史遗迹、每一个民族和他们生命情态的真切体验。于是,他们不再重构神话,不再重述飞天,而是面对面地思考自然何其神奇,祖国何其辽阔,人民何其伟大,民族何其饱经沧桑,却巍然屹立[1]。这种概括同样适用于蓝冰近年来那些行走于祖国山山水水,勾绘自己诗歌地理版图的诗歌——从林海茫茫的阿尔山,到白雪皑皑的青藏高原,从西北之北,到彩云之南……近年来蓝冰且歌且行走遍了祖国大好河山的绝大部分,写下了数百首古体诗和现代诗(2013年他还出版了《且歌且行古体诗集》)。这东南西北万里江山仅仅是蓝冰诗歌地理的行踪坐标,而非其诗歌地理学的全部要义。直言之,蓝冰这些立意要“为江山作传”的诗,不同于时下流行的苦思竭想的“旅游诗”或“旅行诗”。他数百首诗歌中的大部,都属于不仅为江山作传,亦为山水“立心”之作。欲为其立心,必先参悟其心,能参悟其心者,要有山水之心,否则便难与山水息息想通,心心相印,其所立之传,必谬之千里。因之,蓝冰游走于山水之间,赏阅品鉴山水之美,体认感知山水之性灵,于山水之中探寻生命之本源,历史之足音,于山水间反观尘嚣,静观自我,而始终无意做山水景观的导游。因为“我们站立千年阅尽人世沧桑/只能接受空洞的瞩目和廉价的赞美”,所以 “我要指给你远天/远天中的鹰和飘荡的云”,从而为“兄弟松”的生命价值进行重新定义;因为罂粟“近亲名声不好”的知识和经验,所以当他面对“薄如蝉翼的罂粟花瓣/柔如绸缎的罂粟花瓣”“彼此相望的罂粟花/美丽无奈的罂粟花”时,欲以生命的名义为罂粟之生命的合法性正名;因为品味过太多世态炎凉,所以他对玫瑰峰千叮万嘱,语重心长:“玫瑰峰,玫瑰峰/你有亿万斯年的悲怆和坚强/放下的是包袱,挺起的是脊梁/泉水叮咚,溪流汤汤,远离恼人的尘嚣/心,就到达了很远很远的地方”,从而为玫瑰峰壮威;只因为知道了250多公斤黄金打造的世界上最大的玉石镶金弥勒佛——梵净山弥勒金佛,所以才有了超越无边佛法的“究竟要用多少黄金/才可以打造最虔诚的信念”的大胆诘问,从而在对功名利禄、贪嗔痴怒的痛悟的“泪流满面”中,在神圣的弥勒佛前,重新界定了梵净山弥勒金佛的警世意义。
这些为山水立心之作,虽有中国古代山水诗的谢风孟韵之余香,却不刻意于或空灵、或洒脱,或“欲辩已忘言”的曲径通幽,而是物我贯通,妙合无垠。在蓝冰的这类诗中,通常会出现有意设置的“我”“你”“它(他或她)”“谁”四个人称。如“柳兰,柳兰/是谁的深情让你来到乡间/落叶松做你的邻居,白桦做你的围栏/你坚守自己的承诺,你相信忠贞的期盼/不管是苦是甜,你总能等到一见钟情的爱恋”(《柳兰,柳兰》)“我要把这硕大的金块/捶打成一枚枚纽扣/扦在我的衣襟,缝在你的胸口/当我远离,当你告别/我们也会永远系住/阿尔山的山明水秀”(《油菜花——上帝的金子》)”“走不出你的森林/飞不出你的视线/忘不掉你的问讯/剪不断你的思念”(《阿尔山之恋》) “因为我们是兄弟肩并肩手挽手的兄弟/所以,我要指给你远天/远天中的鹰和飘荡的云”(《兄弟松》)“德令哈,德令哈/我不告诉别人你的秘密/你也不要让别人/打听到我的行踪”《与德令哈的约定》“啊,天山,天山/就算我生出翅膀/也飞不过你悠远辽阔的蓝天”(《天山之恋》)等等。在这些诗中,诗人不仅将山水生命化,对象主体化,也将自我山水化、对象化。从而,我非我,物非物,山非山,水非水,一切皆成“我”和“你”构成的互相倾诉的对象和主体营造的生命情境,而这一情境之外又有“谁”的在场而营造出的第二空间。于是,“我”“你”不仅在共享情境中可以彼此换位,同时也穿越于“你、我”的第一空间和由“谁”所拓展的第二空间之间。而当诗人“我”和“你”分开,“你”转换成“它”时,一直隐身的听众“它(他,她)”便会悄然出场:“急湍飞瀑的一咏三叹名叫三潭峡/春天时,我见过/它被无边的冰雪覆盖/巨大的河心石在雪被下沉睡/它们在等待匆匆赶来的恐龙妈妈”(《深秋三潭峡我看见一万只老虎》);“对谁的等候让你站在路边?/小路通向大路大路通向天边/这牵挂与爱恋的绳索/会把谁带到你面前”(《柳兰,柳兰》)。就这样,在与山水交互、对话、交流、呵护、启迪、宽慰、自我省察、反思、诉说的主体间性构拟中,自我山水化,山水主体化,诗人把自己的人生经验、生命冥思与人生的疑惑乃至神游畅想,统统交付山川万物,消弭了物象与心象的界限。这里,山川风物、人类遗迹都是时间撒落的历史碎片,自由、尊严、平等与爱的生命光辉,照亮了山水也照亮了自我,极大地拓展了诗歌精神和思想的维度,拓展了山水的生命时空,达至为山水立心之境界。本来易改之江山,无常之山水,在蓝冰的诗里获得了诗性之永恒。
四
蓝冰向来对板着教父面孔且启蒙欲望高涨的所谓精英知识分子敬而远之。几十年来古典文论的浸淫和“诗人”桂冠都始终无法改变他的平民知识分子的立场和情怀。他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特别同情、珍惜那些底层的、弱小的、边缘的生命,他深切地体察他们贫寒交加的生存状态,感知他们敏感而脆弱的心灵,发现他们生命微小的火花,把自己的人生经验和生命体验,传导给那些底层的、普通、弱小的、边缘的北方的农民、城市的拾荒者、山坡上知名和不知名的小花小草、村边任人砍伐的大树,用有温度的思想,有深度的精神,有宽度的情怀,温润他(它们)、鼓励他(它们)甚至彼此搀扶、慰藉、砥砺,这种人文精神和人文情怀是蓝冰诗歌的灵魂表征。这一点,从早期《阳台上的鸽子》中他惊讶于阳台上那只无限爱惜自己羽毛的鸽子,《大地的四季》中对北方村庄和山坡上那些伟大的植物与无名的小草的温情体认中就已露出端倪,几十年来这一思想和特征日渐清晰、日益成熟和稳定。他在《春:欣悦的暖流》中构建了他和自然界动植物的关系:“睁开眼睛吧,我熟悉的植物们/我用鞭声和犁铧惊醒你们的睡眠/睁开眼睛吧,我热爱的动物们/我们一起到欢快的河边去洗洗衣裳//我用欣悦的暖流呵痒大地的皮肤/我以我歌唱的理由命名我熟知的事物/春天春天让我在你的怀抱里/安放我小小的家园”而在《冬:一场大雪宣告冬天的消息》中这种关系进一步深化:“我和冬天的树木一起拒绝死亡/只让百草去装点冬天的寒冷/在旷野的积雪下面弱小的生命互相抚慰/携手渡过漫长的冬天”。 这是多么令人悲恸的生命图景。并非他幻想自然生命的永恒,而是他对超越死亡的永恒的价值充满了自信。珍视弱小的生命,比讴歌伟大的事物更具有人性的深度,因而更让人敬佩。而把自己的高度降低到冬天的树木和积雪下的小草,与他们一起互相取暖、相互抚慰,携手共度漫长的冬天,这本身就是对生命意义的生动阐释。在此,蓝冰的慈悲与温情是及物的,直抵人类生命的深处。因此,他面对“毒之花”的罂粟,才会发出“它们的前生结了什么孽缘/它们的今生要做怎样的回转”(《野罂粟》)的叹惋和抗辩。
《草的四季,草的忧伤》无疑是近年来蓝冰写得较为用力的长诗。这里积蕴着蓝冰太多的个体生存体验和人生经验,也包蕴着蓝冰对中国知识分子身份和价值的独立思考。诗中,诗人建构了自己的“草民”身份,他以一个平民知识分子的身份和立场与小草窃窃私语、相互凝视、彼此体贴。诗人悲痛地发现,《一场大雪宣告冬天的消息》中那些“携手渡过漫长的冬天”的小草们,所以要自信地要活下去,并不是为自己而生,而是“缘于六畜和昆虫们生的渴望”,“我见过那些冬天里饥饿的牛羊/雪原上,它们用滴血的蹄子刨开坚硬的雪/哭着喊着去寻找一棵草一片草”,正是为了些渴望生命的牛羊:“一棵探出头,另一棵也跟着探出头”,“春天就在它们的身后了/一棵走向远方/另一棵也走向远方/这样,秋天就跑在它们的前头了”,这一让人心灵颤动的悲壮场景,表达了诗人对生命与生命关系的深度思考,将诗歌的意义推升到“超越死亡的永恒价值”的高度,提出了具有本源性的问题:人为谁而生?又为谁而死?在此,不能不提及与这些诗异曲同工的《父亲——一个乡村行脚大夫的赞歌》《一棵树和它的全部生活》。在这两首诗中,“树”与“父亲”在“全部生活”的历史叙事时空中构成互文关系,在诗艺上构成一种隐喻关系,在诗旨上构成互补关系。如果说《父亲》中有太多太重的对父亲这位普普通通的“乡村行脚大夫”的“折断一片记忆却很难”的追忆和爱,那么《一棵树和它的全部生活》中对“站立是一种宿命,站立是一种宗教”生命姿态的赞美,同样倾注了诗人的全部情感。树的一生,仿佛就是行走在朴素、平凡故乡土地上的行脚大夫的“父亲”的隐喻。只不过,《父亲》中对平凡伟大的父亲的赞美,变成《一棵树和它的全部生活》中对承受着一切可抗与不可抗力的冲击,隐忍坚毅、傲然挺立的卑微生命的悲悯与感叹。类似的诗歌还有“满怀热望有又表情木然”的 “拾荒女人”(《拾荒女人》)。在此,我们不由想起惠特曼那句著名的诗句“哪里有土,哪里有水,哪里就长着草”。
蓝冰在诗中说:“通过农业的泥土和养料,我的思想抵达今天”,这就严格地区分了他和那些高喊“土地”“小麦”“粮食”的所谓乡土诗歌和底层诗歌。评价蓝冰在这些诗歌写作中呈现出来的人文精神和人文思想的价值并不难。强者当然需要歌颂而且从不缺少尾随的歌者,而弱者往往相反。正因如此,才有了能够彪炳历史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涅克拉索夫、哈里特·比彻·斯托、鲁迅……人类文学史的主流也是人类生存史的主流。如果将蓝冰投放在中国当代诗潮,或许很容易将其归入“底层写作”或者“底层诗歌”甚至更早期的现代主义诗潮,但又不能这样做,因为,他几乎没有刻意追随任何一个“现代”“先锋”“底层”潮流。如果一定要用“底层”的主流诗评话语来描述他近年来部分类似诗作,他的“底层写作”应该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例如,1991年蓝冰完成的《大地的四季》是在“歌颂正在消失的朴素的农业文明”,但是“我爱你们这些泥土一样父母般的农民呀”却将他的平民情怀暴露无遗。蓝冰的这一部分诗歌或者说他在这一部分诗歌中表现出了可贵的真正的知识分子情怀。张清华在谈到底层写作时曾说:“尽管我一直认为,诗歌只与心灵有关而与职业无关,但是在我们的时代,职业却连着命运,而命运正是诗歌的母体。历史上一切不朽和感人的写作,都与命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我们的时代尤其如此。当我们读到了太多无聊而充满自恋的、为‘中产阶层趣味’所复制出来的分行文字的时候,这种感觉就愈加强烈。”[2]如此说来,从“北中国诗群”中的蓝冰,到如今为江山立传、为山水立心、为草木请命、为普通和平凡立言的蓝冰,一直是中国当代波澜壮阔诗潮之中黑格尔所说的“这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