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动物
☉[英]埃罗尔·富勒 著 何兵 译
象牙嘴啄木鸟
象牙嘴啄木鸟是一种极其美丽的黑白色鸟,雄鸟头部后面有鲜红的羽冠。对啄木鸟而言,它非常之大,象牙嘴啄木鸟体长约50厘米(20英寸),是目前已知全世界第二大的啄木鸟。最大的是墨西哥的帝啄木鸟,而它同样也已灭绝。

象牙嘴啄木鸟与J.J.库恩在玩耍
象牙嘴啄木鸟在欧洲文明开始入侵美国东南部时开始衰减。在整个19世纪,一直到20世纪头几十年,其数量都在持续减少。尽管看似适宜的森林和沼泽栖息地至今仍然存在,但鸟儿们似乎无法抵挡人类的干扰(或者入侵)。
我们对象牙嘴啄木鸟的大部分了解,都来自于詹姆斯·T.坦纳的工作。他在20世纪30年代找到象牙嘴啄木鸟,此时已是这个物种行将消失之际,种群数量少得屈指可数。
1938年3月6日,他将一只幼鸟临时从巢中取出,给它佩戴环志,就在这个时候,一些精彩的照片诞生了,是那只年轻的象牙嘴啄木鸟和坦纳的同事J.J.库恩玩耍时拍的照片。这组照片提供了人类和这一灭绝鸟类互相交流的最后动人瞬间。
尽管坦纳能找到它们,并且提出了保护它们的建议,但象牙嘴啄木鸟还是在他的研究之后不久就消失了——彻底地消失。
他对这个物种的生存寄望于以路易斯安那州一片叫做“胜家之地”(Singer Tract)的大约80000英亩(约324平方千米)的森林为中心的区域。由于伐木活动正在严重地侵蚀这片森林,美国国家奥杜邦协会为了保护森林而作了不懈的斗争,时任美国总统的富兰克林·D·罗斯福也于1943年对伐木活动加以干预。但也许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带给他更为紧迫的挑战,他在这里失败了,砍伐继续进行。有趣的是,砍伐主要是德国战俘干的,大量木料用于制作茶叶盒子,以使英国士兵能在前线喝到他们喜欢的饮品。
尽管非常不情愿,詹姆斯·坦纳最终接受了象牙嘴啄木鸟消失的事实,而且为它写下了充满诗意的证言:

象牙嘴啄木鸟
(它)常被描述为幽暗沼泽的行者,与淤泥与阴沉相联,被唤做忧郁的鸟,但它绝非如此——它是树顶和阳光的行者,它活在太阳之下……活在和它羽毛一样明艳照人的世界里。
那么,关于象牙嘴啄木鸟还剩下些什么呢?除了剥制标本,还有些老照片。甚至还有一张古老的硝酸电影胶片(由于极易燃烧的特性,大部分照片已于20世纪60年代在康奈尔大学烧毁了),以及一些真实叫声的录音。
袋狼
袋狼是全世界最著名的神秘动物之一。它们是否依然还在塔斯马尼亚的偏远之地生存着,或是像学术记录的那样——最后一只已经在1936年9月7日死于霍巴特的博马里斯动物园,真相可能隐藏在二者之间。一小群被孤立的袋狼,可能在那只“最后”的袋狼死在动物园后,仍然还在塔斯马尼亚的荒野中游荡了数年。最大的可能性是,在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的某一天,真正最后一只袋狼孤独地死在了海岸边、森林中或者山坡上。
袋狼又常被称为“塔斯马尼亚虎”,它完美地适应了生存的环境。但名字里带有“虎”字是个严重的误导。这么叫它,只是简单地因为它是食肉动物,而且身上有条纹。其实,袋狼看起来更像是有条纹的大狗或者狼,但当你得知犬科家族和袋狼并没有近亲关系时,一定会特别惊讶。确实,在动物学领域,二者之间有个巨大的鸿沟。虽然长得像狗,但袋狼属于有袋类动物,与袋鼠、考拉是同类。但当你仔细观察一个袋狼头骨和狼头骨时,会发现它们有着惊人的相似性。除了齿列的某些特征,很难一下子就指出它们的区别。
袋狼曾广泛分布在澳大利亚大陆(以及新几内亚岛),但大多数动物学家都相信,当欧洲人到来时,它们只局限在塔斯马尼亚岛。它们无法抵御来自澳大利亚野狗(由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带来的)的竞争,然后逐渐退缩到偏远地区,直到最后完全从澳大利亚大陆消亡。
塔斯马尼亚作为欧洲殖民地,一开始是罪犯流放之地,后来成为农业发达的地方。而当地大部分的本土物种也都被消灭殆尽。最先消失的是塔斯马尼亚鸸鹋,随后就轮到了土著人。一位名叫楚格尼尼的老年妇女于1876年5月去世,她也被认为是其种族的最后一个人——当然也可能不准确。
作为一种大型食肉动物,袋狼对牧羊人的利益构成了潜在的危险,因此它们一直面临着生存的威胁。它们也的确遭受了威胁。19世纪期间,来自公司、政府或私人资助的赏金被投入到猎杀袋狼的行动当中。
金额各不相同。曾有一个时期,打死一只成年袋狼的赏金是1英镑,而一只幼崽则减半。每一个有枪的人都成为袋狼的敌人,袋狼的数量锐减。而数量减少的速度又因为某种未知的疾病而加快。到1900年时,袋狼已经非常稀少,但赏金依然如故。直到1936年,才有法律禁止猎杀袋狼,而这也是袋狼灭绝的年份,真是个神奇的巧合。

本杰明·谢帕德于1928年1月24日拍摄于霍巴特博马里斯动物园的照片。这通常被认为是最后一只圈养袋狼,但事实并不是那么回事。这只看起来特别绝望的动物在拍照之后第二天就死了,死于一种传染性疾病。这可能也是导致该动物园另外至少7只袋狼死亡的原因

1910年1月摄于博马里斯的四只袋狼
19世纪下半叶直至20世纪,动物园对袋狼的需求非常大。比如伦敦动物园,从185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几乎一直有袋狼的展出。死了一只,又再买一只。因此,给它拍照的机会非常多。甚至还有一些精彩的视频,现在也能轻易在网上看到。最好的照片,可能来自与该物种关系最紧密的动物园,塔斯马尼亚州霍巴特的博马里斯动物园。最具象征性的照片,是由本杰明·谢帕德于1928年拍摄,那是一只即将死去的袋狼,孤独而绝望地望向圈舍之外。
而一张时常被引用的照片,里面有四只袋狼,1910年拍摄于博马里斯动物园,不清楚摄影师是谁。另外一张来自博马里斯的照片,展示了相同的四只,拍摄时间大约在一到两个月之前。
最近有人建议从博物馆标本中提取DNA,然后再造袋狼。公众关注集中在悉尼澳大利亚博物馆中一只保存在酒精里的年轻袋狼标本上。这项任务最终能否行得通,还有待观察,不过就目前的知识和技术而言,显然还不太可行。
至于袋狼依然幸存的可能性,大多数的目光都很自然地投向了塔斯马尼亚岛。但最好的证据,是一只木乃伊化的干尸标本,是1966年在靠近南澳大利亚州和西澳大利亚州边界的蒙德拉比拉车站附近的一个山洞里发现的。根据碳同位素测定,其死亡年代大约在4500年前。然而,它却始终笼罩着神秘的光环。1990年,阿索尔·道格拉斯撰写了一篇极具说服力的文章,其中详细阐述了碳定年法过程可能存在的纰漏及其理由,并提出当人们发现这具尸体时,它死亡的时间不过只有几个月。但到目前为止,没有科学家对此给予足够的关注,重新检验标本,并重新审查证据。
白鳍豚
在中国历史上,白鳍豚一直备受关注,它时常出现在诗歌、故事、传说和学术文稿中。“白鳍”意为“白色的豚”,而西方科学界却始终不知道它的存在。直到1914年,一位名叫查尔斯·霍伊的17岁美国人在城陵矶附近射杀了一只。霍伊和同伴们吃了些它的肉,并给动物尸体拍了张照片。
霍伊把这只白鳍豚的头骨和部分脊椎骨清理干净,然后带回了美国,这些残骸最终被送到史密森学会。在那里,人们认识到,这些骨头属于一个科学界未知的物种。1918年,它被正式命名,而它也成为最后被科学界描述的大型动物之一。
但这个发现却并没有给霍伊带来什么好处。他在长江上感染了由一种寄生扁虫传播的血吸虫病。这种病会损伤肝脏和肠道。1922年霍伊去世了。
白鳍豚仅仅分布在扬子江以及一些附属的湖泊中。对白鳍豚而言,极为不幸的是,这条江的冲积区域是地球上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是全世界10%以上人口的家园。
长江流域大规模的建坝工程开始实施,这使白鳍豚的种群片段化,许多地方的种群不得不与其他地方的同类隔离开来。白鳍豚主食的鱼类种群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整个长江的生态系统就这样被彻底改变了。其他的物种也遭受了与白鳍豚同样的命运,比如一种巨大的鱼——白鲟。环境巨变造成的后果之一,就是白鳍豚种群数量急剧下降。与此同时,其他的问题也逐渐凸显。越来越多的大型船只在长江上航行,它们制造的“白色噪音”封堵了白鳍豚的听觉,它们用以捕猎和导航的回声定位系统变得越来越低效。许多白鳍豚直接撞向了轮船的螺旋桨,或者因为听觉混乱而搁浅。大规模的污染和新式的捕鱼方法——包括炸鱼和电鱼——宣告了这个物种最后的末日。
关于这个物种的大多数照片,都来自同一只个体,它于1980年被捕捉,而后取名为“淇淇”。在同类们逐渐消失之时,淇淇成为了明星。人们时常把它从水里拉出来,拍照片,以及带着近乎绝望的努力,不断刺激它,以期能产生有活力的精液。1986年,另外两只白鳍豚——一只雄性和一只雌性(后者被取名为“珍珍”)——被捕捉,但几星期后,那只雄性白鳍豚就死了,尽管它的同伴始终不离不弃地将它往水面上推,好让它能继续呼吸。在它死后,珍珍就与淇淇养在一起,但珍珍似乎还没有性成熟。而在活到性成熟的年龄之前,“她”也不幸地死了。

淇淇,摄于武汉的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查尔斯·霍伊和他杀死的白鳍豚
最终,2002年时,淇淇也死了,死因可能是因为糖尿病和年龄太大。它在人们的养育下活了22年之久,死后人们为它举办了一场隆重的葬礼,中央电视台都对此进行了报道。
其后,野外个体的目击仍然时有报道,但反复的调查显示,该物种事实上已经灭绝。
斑驴
斑驴有着如此与众不同的特征,这使它成为代表灭绝物种的象征之一。但最近的研究却揭示,它很可能不是一个完整的物种,而只是现存物种草原斑马的一个种群(亚种),DNA分析的结果确认了这个结论。但斑驴仍然毫无疑问地保留了这个标志性的地位,它戏剧性的历史和辨识度极高的外表确保了其地位的延续。
虽然斑驴的外型很像其他斑马,但色型却完全不同。它们只在头部、颈部和身体的前半部分有条纹,而在典型的斑马身上是白色的地方,在斑驴身上大部分是棕色,只有腿和腹部是白色。
人们对斑驴分类地位的争论,从许多方面来看都反映了对“物种”这一概念如何界定的问题,到底什么是一个完整的物种,而什么又不是?虽然对于“物种”这个概念本身有着明确的定义,但最终的解读仍然是开放性的。比如,没人会认为狮子和老虎是同一个物种,但亚洲狮和非洲狮到底是不是呢?这就很难判断,大多数科学家都认为它们的确属于同一个物种,但有些科学家却不赞同。

这是仅存的五张斑驴照片之一,由弗雷德里克·约克摄于1870年夏天,是伦敦动物园那只雌性斑驴照片中最好的一张
斑马也是同样的问题。
18世纪至19世纪,斑驴是非洲南部干旱草原非常常见的“居民”。和其他斑马一样,斑驴也不太容易被驯服。而且由于被当作是与黄牛和绵羊争夺牧场的害兽,它们经常遭到猎杀,以获取肉和皮张。狩猎愈演愈烈,最后终于被禁止。禁令始于1886年,但一切都已太晚——最后一只斑驴已经死了,三年之前,它在阿姆斯特丹动物园寿终正寝。而最后一只野生斑驴也大概在19世纪70年代被枪杀。
斑驴仅有5张照片存世,拍摄的都是同一只动物——来自伦敦动物园的一只雌性斑驴。“她”在动物园里生活了21年,于1872年7月15日去世。“她”的尸体被转移到一个名为杰拉兹的动物剥制师和骨骼学家公司,制作成了斑驴皮张和骨骼标本。骨骼以10英镑的价格卖给了美国著名恐龙猎人奥思尼尔·C·马什。该标本如今收藏在耶鲁大学皮博迪博物馆。而皮张剥制标本则最终卖给了爱丁堡的苏格兰皇家博物馆。
在斑驴的研究史上,也许最重要的一位人物当属南非博物学家莱因霍尔德·劳(1932-2006)。劳从博物馆剥制标本中提取了斑驴的组织样品。在一个制作不那么好的标本上,他提取到了斑驴的肌肉和组织,而通常情况下,在处理皮张的过程中,剥制师会将这些东西完全清除干净。正是对这些样品的分析结果,使他确信斑驴并非是一个单独的物种,而仅仅是草原斑马的一个亚种。在检查了所有证据之后,他产生了“再造”斑驴的想法。带着这个想法,他开创性地提出了一个称之为“斑驴项目”的行动计划。到最近几年,选择性繁殖已经开始取得劳所期待的成果。
熊氏鹿

一只圈养的熊氏鹿,1911年摄于柏林的一家动物园
尽管曾经相当常见,但熊氏鹿却是一种神秘的动物。全世界所有的博物馆中似乎只保存了一个标本,这就是位于巴黎的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收藏的熊氏鹿剥制标本。同样的,全世界似乎也只有一张熊氏鹿的照片,1911年拍摄于柏林的一家动物园。事实上,动物园里圈养的熊氏鹿非常少,在欧洲总共不超过7只,而北美一只也没有。也没有一个欧洲人曾在泰国——熊氏鹿的大本营——或者东南亚其他地方的野外看见活的熊氏鹿。尽管如此,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却保存了400对之多的熊氏鹿角,而这些角也曾在中医药贸易中大量出现。那些活得最好的熊氏鹿为我们展示了其精巧绝伦的鹿角分支,它们能长出令人惊讶的分支数量。
这个物种于1863年首次被科学描述,并以时任英国驻曼谷领事罗伯特·熊伯克爵士的名字命名。熊氏鹿栖息在生长着竹子和长草的沼泽平原——主要分布在泰国,但可能也出现在周边国家。它们通常会避开植被特别稠密的地区。在其喜欢的环境里,数量又往往很丰富。站立时,熊氏鹿的肩高约1米,体色为巧克力棕色,并有着一对壮观的鹿角,这使它们成为猎人的目标。每当洪水泛滥时,小群生活的熊氏鹿被迫聚集到较高的地方,而这些高地常常成为“孤岛”,很容易就被围捕。
随后,大屠杀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但这可能还并不是它们灭绝的真正原因。不断增长的大规模水稻种植,导致熊氏鹿的栖息地被蚕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熊氏鹿就已经变得十分稀少。
据目前所知,到20世纪30年代早期,熊氏鹿就已在野外灭绝。有一只熊氏鹿——或许是最后一只——被当作宠物养育在泰国龙仔厝府的一个寺院里,它一直活到了1938年。有个故事说,它是在那年被当地一个醉汉杀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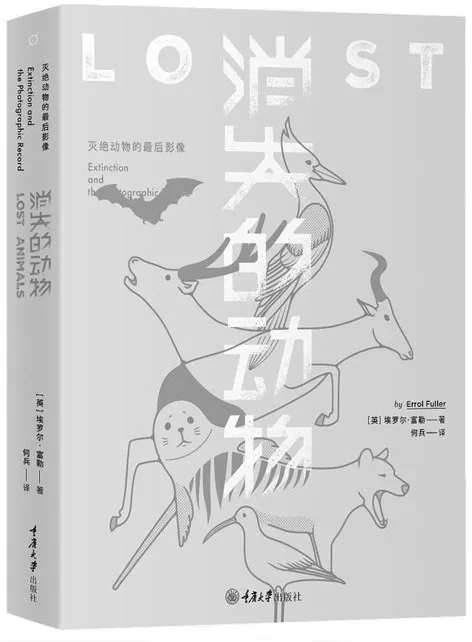
然而,这其实并非最后一只熊氏鹿。1991年2月,一对鹿角被人在老挝一家中药店里发现并拍了照片。这些药店通常有许多天然动植物,最显著的要数虎骨和碾碎的犀牛角,也常常会有鹿角。据称,这对鹿角来自附近一只前一年刚死亡的鹿,而这只鹿是熊氏鹿。假如果真如此,那么熊氏鹿显然直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还依然存活着——但是,仅靠中药店里的一对鹿角照片而鉴定出来的结果,真的能完全令人信服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