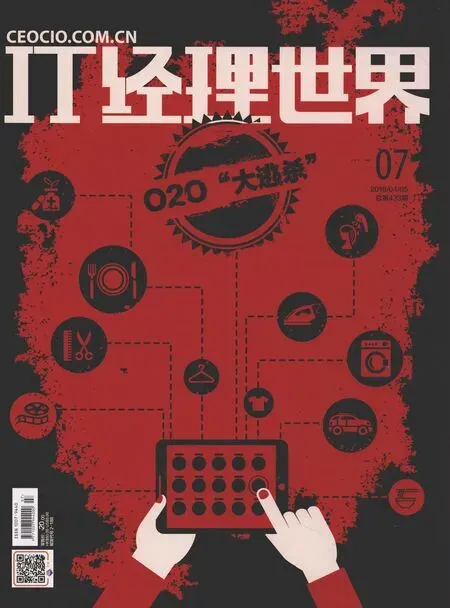那些关于“全民基本收入”的事儿
托马斯·史班达
如果有那么一种收入,沃伦·巴菲特可以得到,泰勒·斯威夫特可以得到,吸毒成瘾者和罪犯也可以得到,那些为自己的爱犬创建Instagram标签的人同样可以得到……那会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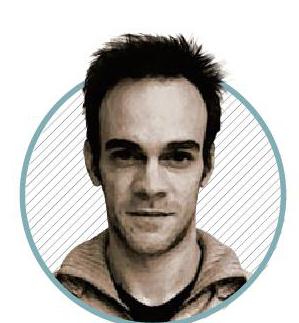
没错,那就是“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 简称UBI)——国家无条件对每个人给予的现金支付,不论他们从事怎样的工作或者想怎么花这笔钱。
今年2月份,英國维珍集团创始人理查德·布兰森公开表示,支持UBI这一做法。“现代社会中,每个人都应有机会工作和自我发展;而现在大多数国家都有能力通过发放UBI而确保国民在生活中基本需求的满足……这种做法值得进一步探索并成为现实,”布兰森说。
他本人曾与诸多全球领袖级人物如科菲·安南、德斯蒙德·图图和吉米·卡特等专门探讨过UBI议题。他说,“我本人从这些交流中获得的感受是,普遍的基本收入能帮助那些为了生存而挣扎的人们建立自尊感,让他们站起来,成为具有创新意识和创业精神的人。”
UBI并非新鲜事,却仍然尚未被洞悉
从历史上看,UBI的概念源起于人们的“乌托邦梦想”。就如同作家托马斯·莫在1516年出版的书中所描述,“一个没有犯罪的社会,正是因为它可以为每个人都提供基本的生活资料、从而没有人会有想成为一个小偷的必要……”而在1796年,美国政治理论家托马斯·潘恩年在其著书中也主张,建立一个国家基金,“让每个公民——无论富有或贫穷——在年满21岁时都可获得15英镑收入、此后每年亦有10英镑收入”。
而在最近几年,UBI被重新推上热议,核心的原因莫过于如美国在内的经济社会面临严重的收入不平等、脆弱的医疗体系、以及科技与智能自动化潜在带来的巨量失业可能性……这些都促使人们再次探讨起UBI的意义与如何变得更可操作。在美国硅谷,马克·扎克伯格(Facebook创始人)、斯图尔特·巴特菲尔德(Slack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特斯拉创始人)、山姆·奥特曼(Y Combinator 公司老板)等商界大佬也都是UBI政策的忠实拥趸。
但回顾在上世纪中叶起美国曾短暂实施过UBI的历程而言,早期的试验并未让人们有机会“透彻地洞察UBI的究竟”。
例如,1968年1月,约翰逊总统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专门研究当时美国福利制度的替代方案。该委员会最终推荐了一项“基本收入支持计划”,这也成为1969年尼克松总统提出的一项新法案的基石(尽管该法案并未获得通过)。在尼克松提出的“家庭援助计划”中,就提到了基本收入形式的一种,被称为“负所得税”。之后,美国有若干城市和州将UBI作法投入了小范围实操层面,其中最大的发生在丹佛——从1971年持续到1982年,涉及4800多户家庭;各地的试验还测试并记录了低收入家庭对不同的税收与福利水平的行为反应等。
但这些早期试验的结论解读有很大一部分存在着谬误。例如,有研究认为UBI的实施导致离婚率直线上升,而后来这个论点被证明不成立。还有持异议者认为,UBI的享有人把这笔额外得到的财富花费在了酒精或毒品上,不过在之后很多年的报告中,显示这与事实不符。
另外,从行为反应层面上,不少年轻人的工作时间减少了,主要是因为获得了基本收入之后不少人选择重返校园;在花费去向上,相当一部分额外支出依然投向了生活必需品,但并没有把人们从贫困中解救出来、或者说使其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随着罗纳德·里根总统任期内寻求削减(而非扩展)联邦福利的政策方向到来时,UBI的试验也自然而然在美国各地无疾而终了。
如今,多地区重新加入试验场
时光的大幕迅速闪回到21世纪10年代。出于上文提到的现实原因,从美国夏威夷、奥克兰,到荷兰、意大利、瑞典、加拿大和芬兰……欧美各有不少地方又重新投入UBI的试验或者可行性调研阶段。
其中尤以芬兰的试验作法备受关注。在2015年举行的一个全国性民调中,芬兰民众表达了对UBI政策的支持,并且每月发放1000欧元被认为是最合适的UBI金额(约合于芬兰最低退休养老金的1.5倍)。自2017年1月开始,一个为期两年的UBI实施计划在芬兰正式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