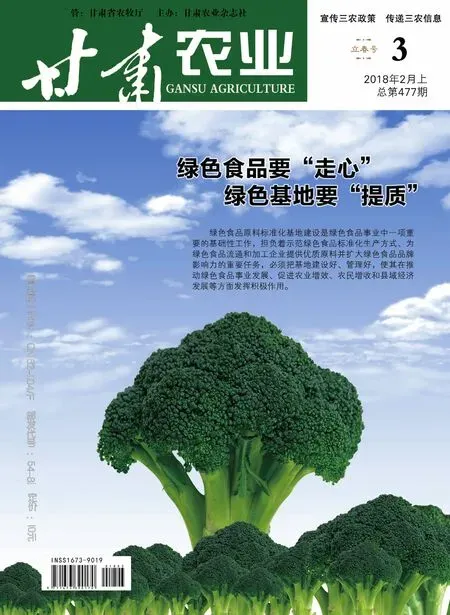古代陇上移民与屯田
■袁维和

翻开尘封的史册,查看历朝历代演变中甘肃大地的人物变迁,会使我们感慨万千。自秦汉以来,甘肃农业经济的发展,始终伴随着移民、屯田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几乎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远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王朝时期,大将军霍去病曾两次带兵远征,千里迢迢的从陕西出兵甘肃河西和内蒙古的西部,经过武力征讨,迫使匈奴浑邪王投降,西汉王朝正式将河西走廊并入大汉的版图。但是,大漠深处的匈奴右部势力,并没有遭受毁灭性的打击,他们退居甘肃河西走廊以北的蒙古高原大漠中,窥探祁连山下的河西走廊,企图重整势力,卷土重来。汉武帝雄才大略,审时度势,采纳张骞提出的“断匈奴右臂”的方案,决定在河西设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并决定通过将内地汉族大量迁徙边关,解决这里汉人人口稀少的矛盾。利用河西的土地肥沃,雪山雪水充足的优势自然资源。组织移民分片分块屯田,大力开发农业。靠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去长期戍守边关,控制东方到西方的丝绸之路商贸咽喉通道。
西汉王朝从公元前120年开始,分四次组织内地大规模的人口迁徙,移民甘肃。当时动用了大量的国库资金、粮食以及军队,朝廷派专人组织护送。从公元前120年至公元前111年,短短九年,从山东陕西河南等地,把近百万人口迁移到甘肃境内。
试想,从黄河中下游的大地上要将这么多的移民迁移过来,一路山高路远,酷暑严寒,的确是件十分艰难的事情。那些大队人马迁徙靠的是双脚,走的是秦汉古道。全家老少扶老携幼,白天行走在群山古道或大漠戈壁中,晚上赶往驿站、村落或荒郊野岭里歇息,那是一个多么悲壮伤感的场面啊。当时在迁徙的移民中,主要是日子贫穷难过,生活无着落的穷人,还有所谓犯了重刑罪犯的家属子女以及其他一些刑事犯人。
朝廷将这些移民迁徙安置到地广人稀,水草丰美的农业生产富饶土地上。这些内地移民的到来并定居,改变了匈奴统治时期的游牧生活方式,把自己与土地牢牢结合在了一起。他们都有一定的农业生产经验,当看到了广阔无垠且还未被开垦的肥美处女地时,当看到了祁连山皑皑白雪化成的河流从眼前流淌时,他们的心都醉了,宛若走进了另一个梦幻的世界,看到了希望,憧憬到了美好的未来。活着是最重要的,吃饭是第一要务,说干就干,他们在朝廷的统一组织下,凿石、挖渠、开道路,大量的开垦荒漠土地,在希望的土地上洒下了金色的种子,引来高山雪水灌溉农田,使荒漠变绿洲。他们每年打下的堆积如山的粮食,不仅自己享用,还支援了戍守边关的军人,巩固了边防,保证了大汉王朝在丝绸之路要道上的绝对统治地位。
据史料文献记载,除了移民屯田外,汉王朝还实行军屯,将士兵几十万大军组织集中在河西走廊的战略要塞之地,亦军亦农,平日垦荒种地,一有战事就操戈迎击来犯者。另外,朝廷还组织服遥役者来甘肃屯田尽义务,安心种田,一年一换,期满后送归故里。军队屯田所获军粮全部用于自己开支,剩余的由朝廷统一调配使用。
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方式,使甘肃地区迎来了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百姓丰衣足食,休养生息的好时代。
汉代过后的几百年,进入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内地中原战乱不断,民不聊生,百姓遭受了巨大的苦难,可是相对而言,甘肃特别是河西走廊远离战火纷扰,由于农业生产发展较快,特别是先进农耕耧犁和灌溉技术的应用,使农业生产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人们享受到了安逸舒适的生活。今天,当我们走进嘉峪关市的魏晋墓道内,从完好留存的砖画中就可看到当时这里富裕安逸的生活场面。这些古墓是当时的官吏豪门大户人家死了后厚葬于地下的陵墓,古墓砖画中除了战马、军队外,更多的是当时现实生活场面真实的再现,有老妇酿酒图,屠夫宰猪图,少妇梳妆打扮图,驿使骑马送信图,众人盛宴图,士兵屯田图等等,真实再现出当时这里的农耕文化,屯田生产使边关经济发生了很大变化。
历史的脚步走到了明代,甘肃又迎来了一次大规模的移民屯田的高潮。之前,由于元朝末年残酷的统治,无休止的战乱杀戮,已使国家元气大伤,特别是山东、中原大地的战乱和兵祸,造成了许多地方百里无炊烟,白骨露于野的悲惨景象,而山西山高水长的特殊地理位置却几乎没有遭受多大损失,于是,大量的逃难逃灾的难民涌入了山西,短时间内致使山西人口大增。明朝皇帝执政后,决定减少山西人口稠密的现状,通过移民的措施减轻山西人口的压力。于是,在山西洪洞县设局驻员,集中办理移民手续。从洪武初年至永乐十五年的将近50年内,明朝皇帝在山西就组织了18次大规模的移民。
“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这是一首至今流传在甘肃等地的民谣。明朝统治者当时在山西洪洞城北的广济寺专门设立了移民局,集中办理移民手续。广济寺门前有一棵汉代挺拔参天的大槐树,据民间传说,为了确保迅速移民,当时的朝廷统治者设了一个骗局,向人口稠密的山西三晋各地颁布公告,不愿迁徙者到洪洞大槐树下集合,限三天之内赶到;愿迁徙者可在家等候。公告消息传出后,众多家庭携儿带女长途跋涉而来,于是三天内,大槐树下一时间簇拥集结了十多万人。此时,早已埋伏准备好的明朝官兵呼啦啦蜂拥而至,把十多万百姓包围起来,长官高声宣布:大明皇帝圣曰,今日凡来大槐树下者,一律迁往外地。说完,官兵们便将身强力壮的青壮年者戴铐上枷,强行登记,发给凭证。被迁着按一家一户为单位,将手臂全部绳子相栓。十万百姓在强令喝训刀逼威胁下,哭天喊地的离开故乡,踏上了漫漫迁徙之路。故土难离,移民们在悲痛欲绝中伤感的回头望去,只能看到渐行渐远的大槐树。这种迁徙时心灵上造成的悲哀和创伤,通过民谣方式流传了下来。明代将近50年间的人口大迁徙中,很大一部分就迁往甘肃各地落户生根了。
当时除了从山西移民以外,明朝统治者还把水乡江南的江苏、安徽一带人口也组织迁往甘肃中部地区,原因是推翻元朝统治后,明王朝感到甘肃兰州、岷洮地区及青海湟水河流域的边防力量薄弱,为了巩固地方政权,防御少数民族进犯,统治者在临夏、甘南一带设立卫所。一卫军制上配备5600人,甘肃设立众多卫所,便增加了众多军队。军队及移民的人从哪里来?从洪武五年开始,南京周围的豪门大户和汴京17个姓氏的居民便被强行迁往甘肃中部。还从江南征集了士兵派往甘肃。
传说今天在甘肃临潭、临洮等地百姓中还传唱者一首民谣:“问我家乡何处有,南京城内竹子巷?”民间传说朱元璋皇帝,有一次在正月十五元宵佳节夜晚,兴致大发,外出看花灯。他与皇后装扮成平民百姓,在深夜出门观赏,一路观灯,来到城里竹子巷后发现花灯高悬,奇美无比,但赏灯的游人很少。忽然,一阵夜风吹来,撩拨呈现出皇后裙下的一双大脚。当时,因社会上女人以裹小脚,成“三寸金莲”为美。一位游灯平民看到后讥笑并窃窃私语,这便引起了皇上和皇后夫人的愤怒,朱元璋回宫后,认为是竹子巷的平民,嘲笑了大明皇后的大双脚,一怒之下,第二天便传下圣旨,将竹子巷的平民百姓全部发配往当时甘、青两省的河湟地区充军戍边,也就是今天的甘南、临夏、定西及青海湟水河一带。于是,江南鱼米之乡的部分百姓离乡背井,举家扶老携幼,拖儿带女,千里跋涉到了甘肃青海一带。
以上种种,是洪洞大槐树和南京竹子巷武力强制移民的民间传说,不一定十分准确,因为明王朝组织发动了多次大规模移民,有自愿的,有强制的,还有服遥役性质的,但足以说明当时平民离乡背井的悲伤心情。从今天甘肃百姓中流传下来的风俗习惯来看,当年移民确有其事,甘肃人把上厕所称为解手,就是流放迁移途中手被绳子捆绑,想方便只能喊解手。久而久之,这里人把方便称为解手了。在甘肃岷县、临潭是不产南方的茉莉花的,可当地民谣中传唱着:“你从哪里来?我从南京来;你带的什么花儿来?我带的茉莉花儿来。”这说明他们的祖辈是江南水乡人。从现在这一带流传的方言、民间故事、民间服饰以及生活风俗习惯等看,也多多少少带有江南水乡的特点。
甘肃历朝历代移民屯田,全都是一种政府的行为,因为强力推行运作,因而成效巨大。如在大清王朝顺治元年,清政府颁布告示,动员全国的老百姓开荒种地,大力发展农业,特别是对边关驻军屯田者,按士兵人数划拨给土地,由当地政府提供牛马犁等生产工具和各种农作物籽种。像甘肃河西许多地方,在清王朝代替明朝统治后,把明朝的军户改为屯丁,采取就地免除军人的军藉和改变身份属性的办法,使明朝的军人及随军家属变成了当地的农户及农民。这样既解除了清军内心的担忧,防止明军私下组织武装暴动,反清复明,又免除了支付给这些人的额外经济负担,把他们化整为零,通过开垦种植土地农作物,自给自足,实现了当地的长治久安和安定团结。
走进甘肃河西的一些偏僻且人迹罕至的地方,仍然能见到类似古堡古城的遗址,我感到十分的好奇,按照我省河东的习惯,古代土筑的古堡一般都建在悬崖绝壁之上,是一个村庄的百姓,用来防止土匪抢劫自卫的。而这里的土筑城堡建在平地上,内部还保存着土院墙、石磨、马槽,甚至佛龛等平民生活遗物,一问才知道这是明、清时代的军屯的屯庄或屯堡。当时朝廷多次运兵大西北,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从内地征粮草难,运输更难,几千里的后勤补给线难以为继。于是,将戍边军人变军屯,打仗时出击,平日种田,就地解决军需补给。同时,清政府“造福于民”,鼓励内地人口迁往河西,给愿意迁徙的百姓特发给足够的国库钱币,给足沿途行走时的口粮及皮衣盘费。他们到了河西后,当地政府又提供农具及种子,划出地皮建房,提供多年的免征赋税等优惠政策。开荒种地,随之而来的是水的问题,引雪山之水灌溉戈壁荒地必须有水渠,于是,移民们大规模地开展了农田水利建设。在河西走廊,按照从东到西的石羊河、黑河、疏勒河等河流沿途修渠引水;在甘肃中部黄河沿岸,则通过修建大量的水车用来提水灌溉,通过这些措施,确保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如今,我们已经走进了21世纪信息化的时代,陇原大地的山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型的机械化、信息化生产以及环境保护、生态维护等新措施,影响着今天的农业生产,人们走进了一个全新的农业经济发展新时代。但是,抚今追昔,昨天这里所发生的一切似乎距离我们并不遥远。群山深处,大漠戈壁,当年祖辈们移民迁徙、屯田、筑城堡、戍边的遗址仍然偶然相见,它们似乎在无言的诉说着往事。每天在晨曦或夕阳映照中的军屯土堡,古宅土墙的断垣残壁,以及散落破败的各种遗址,似乎成了一位历史的长者,无声地见证着昨天的往事,似乎在告诉我们今天的幸福与辉煌,源自于昨天他们的艰辛甚至牺牲,对此,我们应该不要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