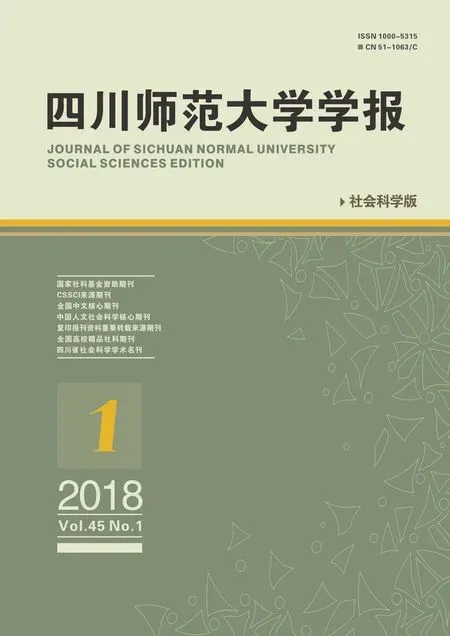论阐释学视野下顾炎武的“鉴往训今”
曾留香,2,谢 谦
(1.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成都 610065;2.成都师范学院 图书馆,成都 611130)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评价顾炎武:“论清学开山之祖,舍亭林没有第二个人。”[1]68顾炎武经世致用、训诂明道的思想,一洗明代“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2]399的空疏学风。其在音韵文字训诂方面的实证研究方法,开启了清代朴学研究之风。顾炎武作为一位学术大家,长久以来,其经学、小学、史学思想在学界已有不少讨论,但对于其文学思想、阐释方法论,学界似乎还关注不够,呈现“重学术而轻文学”[3]的局面。这一方面是由于顾炎武本身不以文人自居,另一方面,对于顾炎武在音韵学、训诂学方面取得的成就,学界更多是从语言学层面而非哲学、文学的层面来讨论。故笔者拟从阐释学的视角来探讨顾炎武的意义。
顾炎武对经学和文学的阐释,呈现出“鉴往训今”的特点,即根植于文本本身的阐释,以求回归传统经典,从而通明圣道。顾炎武通过对古今学术史的回顾,总结其中的规律,使其成为有据可依、符合当下语境并服务于社会现实的阐释。当然,这种“训今”的阐释不是随意性的主观阐发,完全不同于明代流行的借杯浇臆、师心自用的主观性笺注评点之学,而是根植于“鉴往”,即通过对经典文本的回归,对作品一字一句的训释,对音韵文字的实证性考究,来探寻作者本意。顾炎武在《答徐甥公萧书》中写道:“夫史书之作,鉴往所以训今。”[4]138实际上,纵观顾炎武之学,无不贯通着“鉴往训今”的阐释学思想。蒋寅先生指出:“(顾炎武)在推源考究中重新阐释诗学传统的价值和意义,从而树立起与时代要求相适应的诗歌理念。……这种理论方式是很有特点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决定了清代诗学突出学术性的基本倾向。”[5]这种“鉴往训今”的阐释的出现,与明清易代之际的时代思潮以及知识分子对于文化救亡的呼声一脉相承,也与顾炎武本身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密不可分。
一 “鉴往训今”的背景:“明道救世”
顾炎武在《与潘次耕札》一文中云:“君子之为学也,非利己而已也,有明道淑人之心,有拨乱反正之事,知天下之势之何以流极而至于此,则思起而有以救之。”[4]166其《与人书二十五》又云:“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4]98顾炎武表明了阐释的目的是“明道淑人”、“明道救世”,把治学上升到了“拨乱反正”的文化救亡的高度。明末清初,处在改朝换代之际的知识分子无不思考着明代覆亡的原因,顾炎武把它归咎于文化的衰落,他希望通过对传统儒家经典的重新阐释,而“知天下之势之何以流极而至于此”,以达到“思起而有以救之”的目的。
宋明心学、禅学的流行,导致阐释中的评点注释之学与主观心解、师心臆测之风兴盛。在这种文化语境下,阐释成为了可以依据个人主观感受随意发挥的臆测之学,诗无达诂成为为无稽之谈做辩护的借口。阐释失去了一个可以进行验证的有效标准,变成了无根据可言的虚妄空疏之学。永乐年间,治学之风衰颓,明成祖诏令众儒编写《四书五经大全》,作为科举考试用书,然而诸儒却“取已成之书抄誊一过,上欺朝廷,下诳士子”[2]1043,顾炎武因此感叹:“经学之废,实自此始。”[2]1043儒家经典的肆意篡改使得学风沦丧,重新阐释儒家经典本身已不单是文学问题,更是关系重建社会秩序、挽救民族危机的社会问题。只有恢复儒家经典的本来面貌,以穷经为指归,才能扭转颓丧的社会风气。
在此基础上,顾炎武发出了“文须有益于天下”的强烈呼声:
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剧袭之说,谀俊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2]1079
“有益于天下”,不仅是顾炎武作文的出发点,也是其一切学术的出发点,阐释的目的也在于此,即在古今之间寻找桥梁,回归和借鉴古之话语,从中获得启发,来为当下社会现实服务。其对经典的重新阐释是被放在“明道救世”的背景之下的。“鉴往”的目的是“训今”,而“训今”又以“鉴往”为前提。顾炎武对经典文本的阐释,无不饱含着他对古今之变、天下兴亡的强烈关注和忧国思民的淑世情怀,阐释活动被上升到扭转社会风气,进行文化救亡的高度。
二 “鉴往训今”的阐释学依据:“知人知言”
“鉴往训今”的阐释能够成立的条件是,在“往”与“今”之间是可以沟通的,即读者可以通过阐释活动,获得作者之志。作者之志是可知的。这与明代出现的把作者之志看作水月镜花、茫然不可求的“反诠释”倾向截然不同。在这样的条件下,儒家古老的“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的阐释原则又重新焕发了生命力,成为探求作者本意,达到这一阐释者的同一性理想的有效途径。
顾炎武相信,作者之志是可求的,言辞最终不能掩盖作者真实情感的流露。他在《文辞歁人》中说:“世有知言者出焉,则其人之真伪即以其言辨之,而卒莫能逃也。”[2]1095其《凡易之情》又说:“情伪相感,人心之至变也。于何知之?以其辞知之。”[2]44也就是说,人的情感虽然千变万化,但人心终究会通过其言辞表现出来。因此,在阐释活动中,透过言辞,读者能够探求作者本意。
既然须透过言辞而达“作者之志”,那么辨别言辞真伪的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如果不辨言辞真伪,就无法准确获取作者本意。顾炎武举例道:
《黍离》之大夫,始而摇摇,中而如噎,既而如醉,无可奈何,而付之苍天者,真也。汨罗之宗臣,言之重,辞之复,心烦意乱,而其词不能以次者,真也。栗里之征士,淡然若忘于世,而感愤之怀有时不能自止而微见其情者,真也。其汲汲于自表暴而为言者,伪也。《易》曰:“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失其守者其辞屈。”《诗》曰:“盗言孔甘,乱是用餤。”夫镜情伪,屏盗言,君子之道,兴王之事,莫先乎此。[2]1095
顾炎武认为,《诗经》的《黍离》篇中的“始而摇摇,中而如噎”正是作者当时充满故国之思、无可奈何的情感表现;屈原的“言之重,辞之复”也符合他当时谗而见疏、忠而被谤,被迫流放异乡时的心情;陶渊明淡然与世无争,有时也有如“猛志固常在”怒目金刚的一面,其“感愤之怀”不能自已。这些都是作者真情实感的流露。而那些急于表现自己,故意为言者,则很有可能是虚情假意、故弄玄虚之人。
顾炎武把分辨言辞真伪的问题,放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他认为言辞不仅可以反映作者情感真实与否,还能反映作者道德人品的高下。因此,辨别言辞真伪,真正做到“知言”“知人”,从而穷经,不仅是阐释活动建立的根基,还是“训今”的现实指归。“镜情伪,屏盗言”,已不单是阅读阐释文学作品的态度,更是治理家国天下者的首要之事。如若听信虚伪动听的谗言,就会“乱是用餤”,导致社会的混乱。在顾炎武所处的明清易代之际,不少名臣宿儒在面临身份选择的问题时摇摆不定,巧言令色,在这样的现实语境下,顾炎武自然对“知人”与“知言”有更高的要求。
顾炎武说:“听其言,观其眸子,人焉廋焉。”[2]44这与孔子所说的“听其言而观其行”[6]44有相通之处。换言之,顾炎武回到了由孔孟开创的“知人”与“知言”的阐释传统上来。即作者之志是可以探求的,要知其言需观其人,而观其人也才能更好地知其言。这也就是周裕锴先生指出的阐释上“理解的循环”[7]51。
三 “鉴往训今”的具体做法
(一)推源溯流
从阐释学的角度讲,宋明流行的禅学、心学与顾炎武奠基的清代朴学,其阐释的终极目标都是通圣人之道,但所走的路径却完全不同。陆九渊讲述自己读书的方法是“沉涵熟复,切己致思”[8]407,强调自我内心的反复思考与琢磨。禅学称:“不立文字,教外别传”[9]293下,以心传心的方式来传习心法。诚然,阐释活动需要读者与作者的共同参与,但忽略经典文本本身,仅依靠读者自身的主观心解,抛弃语言文字,不仅很难正确地探求、理解作者原意,甚至从根本上消解了阐释的意义。宋明理学所标榜的“明道”实则是“六经注我”,用古代先哲的经典或语录为自己创造的新理论做辩护。这样的“明道”出现的结果,很有可能是作者之“志”被阐释者的主观意图所解构、扭曲。
与之相反,顾炎武奠基的清代朴学,则是回归经典文本本身,通过推源溯流,对经典作一字一句的训释,得以“通经”,从而“明道”。
推源溯流,就是回到文本的源头,从根本上将事实分辨清楚。这种对正本清源的关注可以追溯到孔子的“祖述尧舜,宪章文武”[10]1459与其“述而不作”[6]65的写作态度,“其核心即强调文化生命历史连续性的文化阐释原则”[11]。如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对儒家传统诗教观的阐释:
《诗》之为教,虽主于温柔敦厚,然亦有直斥其人而不讳者。如曰“赫赫师尹,不平谓何”。如曰“赫赫宗周,褒姒灭之”,如曰“皇父卿士,番维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聚子内史,蹶维趣马,楀维师氏,艳妻煽方处”,如曰“伊谁云从,维暴之云”,则皆直斥其官族名字,古人不以为嫌也。《楚辞·离骚》:“余以兰为可恃兮,羌无实而容长。”王逸《章句》谓“怀王少弟司马子兰”;“椒专佞以慢慆兮”,《章句》谓“楚大夫子椒”,洪兴祖《补注》:“《古今人表》有令尹子椒。”如杜甫《丽人行》“赐名大国虢与秦,慎莫近前丞相嗔”,近于《十月之交》诗人之义矣。[2]1085-1086
中国古典诗歌“温柔敦厚”的诗教观受到了质疑,《毛诗》中“主文而谲谏”[12]13的阐释原则似不适用于所有情形。顾炎武从诗的源头找到证据,举出《诗经·小雅》中的不少篇章如《节南山》、《节南山之什》、《十月之交》、《何人斯》中都有直斥官族名字的例子,《楚辞》中也有不避名讳的情况出现,杜甫的《丽人行》更是直接斥责杨国忠兄妹权势显赫。顾炎武认为,只要是反映作者真情实感的诗句,直接显露地表达也未尝不可,这也是符合传统诗教的。中国传统诗歌的阐释不应该局限在“中和”“含蓄”这一狭隘的视域里。这样通过厘清事实,从源头上追溯诗歌传统,顾炎武对“温柔敦厚”的传统诗教观作出了自己的阐释和补充。
再如论“作诗之旨”:
舜曰“诗言志”,此诗之本也;《王制》“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此诗之用也;《荀子》论《小雅》曰:“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声有哀焉。”此诗之情也。故诗者,王者之迹也。建安以下,洎乎齐梁,所谓“辞人之赋丽以淫”,而于作诗之旨失之远矣。[2]1167
顾炎武用《尚书》、《礼记》、《荀子》中的话语,将诗之本、诗之用、诗之情作了界定,最后落足点回到“故诗者,王者之迹也”。这是回归经典文本,通过诗歌认识的历史构建来阐述自己的诗学观点。他又赞扬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精神,最后以葛洪《抱朴子》中的“古诗刺过失,故有益而贵。今诗纯虚誉,故有损而贱”作结[2]1168,顾炎武的观点已在古今对比和学术史的回顾中呈现。“鉴往”故而知诗始为“王者之迹也”,“训今”故而今人作诗也应立足现实,指刺过失,才能有益于社会,发挥其应有的价值。
那么,如何回到源头,即经典文本的本身?顾炎武的方法是:辨别真经而非伪经,并且全面地理解经典的含义。
顾炎武在《与友人论学书》中就通过推源溯流,将古今对“危微精一”说的不同理解进行比较,阐释了宋明理学所讲的“危微精一”实则是“六经注我”,并非经典本义:
窃叹夫百余年以来之为学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命与仁,夫子之所罕言也;性与天道,子贡之所未得闻也。性命之理,著之易传,未尝数以语人。其答问士也,则曰“行己有耻”;其为学,则曰“好古敏求”;其与门弟子言,举尧、舜相传所谓危微精一之说一切不道,而但曰:“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呜呼!圣人之所以为学者,何其平易而可循也,……今之君子则不然,聚宾客门人之学者数十百人,“譬诸草木,区以别矣”,而一皆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是必其道之高于夫子,而其门弟子之贤于子贡,祧东鲁而直接二帝之心传者也。我弗敢知也。[4]40
顾炎武通过考证,将古之学者与今之学者作对比,推溯到《论语》中记载孔子与门人所言,《论语·尧曰》有云:“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6]205尧勉励舜要随时胸怀四海百姓,如果他们陷于穷困,上天赐予的禄位就要终止。《论语》记载的孔子平日所言仅限于此,并未提及尧舜二帝曾有“危微精一”之说。“危微精一”即“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的简称。“今之学者”却将尧舜二帝未曾说过的“危微精一”之说奉为至宝,甚至认为是“直接二帝之心传者也”。顾炎武从儒家经典的原文出发,指出了心学所谓“危微精一”之说的漏洞,对这个被宋明理学家尊为“十六字真言”的“传心之要”提出了质疑。后来清代朴学家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更是通过严密的考证,证实了记载“危微精一”说的《大禹谟》实则为伪古文尚书。可见,宋明诸儒所崇尚的“传心之要”实则是伪经而非真经,根据伪经来寻求圣人之道,自然是缘木求鱼,无法真正获得经典的本义了。
事实上,“信古阙疑”一直是顾炎武返经汲古的态度。他说:“《五经》得于秦火之余,其中故不能无错误,学者不幸而生乎二千余载之后,信古而阙疑,乃其分也。”[2]123对于古今《尚书》之争,顾炎武也提出了自己的思考,认为“《泰誓》别得之民间,且非今之《泰誓》”[2]114,又说“孟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于今日而益验之矣”[2]115。后来清代朴学家广泛地搜集文献,考证辨伪,尤其是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一出,其详实严密的考证几使伪古文尚书成为公论,不得不说受了顾炎武的有益影响。
除了辨别经典的真伪之外,顾炎武还注意到,理解经典文本要返回其原始版本,而不是后儒的“语录”。顾炎武批评“近世喜言心学,舍全章本旨而独论人心、道心”[2]1048的现象,他们不是根据经典的文本来探求圣人之道和作者本旨,而是单独取其中之言来为我所用。他又抨击“今之理学”,“不取之五经而但资之语录”[4]58,舍本逐末,以后儒的语录来断章取义,而非回归五经的原始文本,“而问以本经,犹茫然不知为何语”[4]47。明永乐年间士子所奉行的《四书五经大全》,实际上是“取已成之书抄誊一过”[2]1043。这种拘泥于个别篇章字句、背诵“语录”而置完整的经典文本于不顾的做法,无异于以文害辞、以辞害志,因而远离了圣人之道。
综上,顾炎武的推源溯流、返经汲古一方面注重辨别经典的真伪,另一方面致力于返回未经篡改的经典的原始文本。这也是后来清代朴学家共同努力的方向。
(二)知音考文
对顾炎武而言,“鉴往训今”的阐释就是要在“往”与“今”之间,搭建一座沟通古今的桥梁。即解决文本与阐释者之间“时间距离”①的问题,以达到视野融合。对此,顾炎武提出了“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4]73的方法,这就包含着一条重要的阐释学原则——“知音考文”,后被乾嘉学者发扬光大。这与宋明理学、禅学空谈心性、心印证悟的阐释方法有根本区别。清代朴学家尤其注重对文字音韵的考究,讲求无征不信、实事求是的考证,顾炎武起了示范作用。
顾炎武倡导的“知音考文”的阐释原则即是由文字音韵入手,通过对经典的语言文字音韵进行训诂、考证来探求义理,进而通经,通过穷经以明道,明道以救世。在顾炎武眼中,通经的关键是要明白承载经典的语言,而通晓语言则须研究记录语言的文字和音韵。这种阐释的路径,就是由文字(声音)→语言→作者之志。
为此,顾炎武一再强调小学在阐释上的重要作用,如果不通古音、不识文字,则无法准确理解古书之义:
古之教人,必先小学,小学之书,声音文字是也。[2]257
学者读圣人之经与古人之作,而不能通其音,不知今人之音不同乎古也,而改古人之文以就之,可不谓之大惑乎?[4]69
三代六经之音,失其传也久矣,其文之存于后世者,多后人所不能通,以其不能通,而辄以今世之音改之,于是乎有改经之病。[4]69
顾炎武痛斥当时不识古音而妄加修改的弊病,如此“通经”,必然造成“大惑”。李清良先生在《中国阐释学》中说:“(要使理解能够有效)意义承担者必须能够像在原有的阐释语境中一样呈现其意义,也就是说,理解者的阐释语境要素没有破坏意义承担者原有的语境要素。”[13]284今人的随意改音破坏了经典文本的阐释环境原有的语境要素,因而背离了经典本身,也就离作者本意愈来愈远了。“以今世之音改之”,无异于用古人之经为自己的理论立说。正如顾炎武批判的“王夷甫之清谈,王介甫之新说,王伯安之良知”[2]1061,都是“六经注我”阐释方法的代表。“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百有余年之久者”[2]1061这种毫无根据的阐释,不仅败坏学风,甚至会造成整个社会风气的沦丧。
有鉴于此,顾炎武潜心钻研,考辨古音,终成《音学五书》一书,希望“审音学之源流也”[4]25,“举今日之音而还之淳古者”[4]25。他认为子孙后代学习《诗经》,辨明《诗经》的含义也应该从“知音”开始,“惧子侄之学《诗》不知古音也”[4]69。这不仅是准确理解古代经典含义的阐释途径,更是达“圣人之道”,进而改良今日社会风气、经世致用的法门。
在考究文字方面,顾炎武对许慎的《说文解字》非常推崇,并指出了以考究文字探求先儒诠释的路径。他说:“经学自有源流,自汉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考究,而后及于近儒之所著,然后可以知其异同离合之指。如论字者必本于《说文》,未有据隶楷而论古文者也。”[4]91同时,他不盲目迷信《说文》,在《日知录》中也指出了《说文》考证的不足之处。后来清代有关《说文解字》的研究蔚为大观,如出现了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王筠的《说文释例》和《说文句读》等研究专著。清初顾炎武对《说文》的推崇起到了推动作用。
要而言之,语言是一切阐释的基础。伽达默尔说:“一切人类生活共同体的形式都是语言共同体的形式,甚至可以说:它构成了语言。”[14]570也正如周裕锴先生所言:“人的存在归根结底是一种语言的存在,所以,一切所谓‘本质还原’和‘存在还原’的阐释,最终必须体现为一种‘语言的还原’。”[15]其实,顾炎武不过是将这条阐释学最基本的原则付诸实践,使阐释由“不立文字”转到“知音考文”的科学轨道上来,从而建立起阐释活动有效验证的根基。
(三)综核名实与明义例
顾炎武不仅将阐释活动建立在确实可靠、有根可循的语言文字基础上,而且通过大量的考证,综核名实来阐发义理,“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而后笔之于书”[16]1029。他不仅以诗自身的“本证”证之,还综合“采之他书”的“旁证”佐之②,力求名实相符,“要当以旁证以求其是,不必曲为立说”[2]1530。如《日知录》卷四“穀梁日误作曰”条[2]270,顾炎武不仅以《穀梁传》为证,还综合《尚书》《周易》《诗经》的例子,表明古人“日”与“曰”字同一书法,容易混淆,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将可疑处以音别之,具有合理性。顾炎武的《诗本音》《唐韵正》《易音》中,也常列上百条证据证明字的读音。
不仅如此,顾炎武还将金石文献与书籍相互对照,以“阐幽表微,补阙正误”[4]28,综核名实。如顾炎武对“《春秋》时月并书”的考证:
《春秋》时、月并书,于古未之见。考之《尚书》,如《泰誓》“十有三年春,大会于孟津”,《金縢》“秋,大熟,未获”,言时则不言月;《伊训》“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太甲中》“惟三祀十有二月朔”,《武成》“惟一月壬辰”,《康诰》“惟三月哉生魄”,《召诰》“三月惟丙午”,《多士》“惟三月”,《多方》“惟五月丁亥”,《顾命》“惟四月哉生魄”,《毕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言月则不言时。其它钟鼎古文多如此。《春秋》独并举时月者,以其为编年之史,有时、有月、有日,多是义例所存,不容于阙一也。[2]191
当他发现“《春秋》时、月并书,于古未之见”的问题,先求证《尚书》,或“言时则不言月”,或“言月则不言时”。他又进一步观察钟鼎文字,以金石材料与史书互证,发现“其他钟鼎古文多如此”,与史书记载是同一情况,只有《春秋》将时与月并举,并非史书误载。
在这一段话中,顾炎武还提出了一个关键词“义例”,又自注:
或疑夫子特笔,是不然。旧史既以“春秋”为名,自当书时。且如隐公三年“春,公会戎于潜”,不容二年书“春”,元年乃不书“春”。是知谓以时冠月出于夫子者,非也。[2]191
顾炎武指出了《春秋》写作的“义例”——时与月并举。“以其为编年之史,有时、有月、有日,多是义例所存,不容于阙一也”。“义例”即古书的一种写作惯例,是逐渐形成的一种典范书写。义例不仅是史书撰写的重要方法,也是阅读和阐释古书、进行文学研究的重要法则。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对同类事物用同种方式进行记载,有意无意形成了某种写作惯例,贯穿于文本之中,“其义例之见于文辞,圣人有戒心焉”[17]7。每一部古书都有自己的“义例”,即自身的写作惯例和书写样式,读者如若能发现义例,就能更好地了解和掌握作者的思维方式,发掘其背后隐藏的深意,从而更加有效地阐释文本。
因此,在阅读古书和阐释文本的过程中,读者须“明义例”,有“义例思维”,只有了解和掌握阐释文本的义例,才能更加准确地理解文本本义与作者本意,否则容易产生误读和曲解。顾炎武指出,如果没有理解《春秋》作为编年体史书的义例,就有可能误解经典本义,以为是“夫子特笔”,有特殊含义。读者若能由义例入手,阐释分析文本,发现其中一以贯之的写作规律,就能使文本“义理”的阐释有章可循、有据可依,从而达到“以意逆志”的目的。
此外,顾炎武更是亲自考察,以一手资料与史书记载相证。如《日知录》中对风俗制度的考察等,其门生潘耒在序言中说:“先生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有一疑义,反复参考,必归于至当;有一独见,援古证今,必畅其说而后止。”[2]《潘耒原序》,1梁启超将其归纳为“博证法”,称:“盖炎武研学之要诀在是,论一事必举证,尤不以孤证自足,必取之甚博,证备然后自表其所信。……此所用者,皆近世科学的研究法。乾嘉以还,学者固所共习,在当时则固炎武所自创也。”[18]16-17顾炎武通过大量的文本考证分析,综以“本证”“旁证”,且对照金石文献,并实地考察,多角度地对阐释的有效性做出验证。这也开启了后来乾嘉学者以严密考证为阐释方法的先河。
需要注意的是,顾炎武对文本本身的关注,推源溯流、知音考文、综核名实和明义例的方法,并非是排斥阐释的多元化。事实上,由于语言文本本身就具有开放性、未定性,阐释的多元化是不可避免的。他还在与友人的书信中称赞了在编纂《四书五经大全》之前世存多家传注的情况:“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胡氏、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犹不限于一家。”[4]41并批判了“欲道术之归于一”、“而通经之路愈来愈狭矣”的僵化做法[4]42。正如张隆溪在《道与逻各斯》一书中所言:“作者、文本、读者都以自己的要求和方式影响着意义的形成。对文学的深刻理解只能来自所有这些要求的综合、所有这些力量的暂时的平衡和协调一致。”[19]292顾炎武的意义在于,指出了多元化的阐释也需以合理的客观依据作支撑,绝非仅靠主观“切己致思”而信口开河。正如张伯伟所言:“即使是解释者的‘见仁见智’,所导致的也不是对作者诗心的必然的否定,而是必然的认识。”[20]189那些与文本本身无关的阐释,因为找不到一条验证有效性的道路,其结果发展到极端就可能堕入师心臆说的泥淖。因而,阐释活动具有客观性,它有一定的科学方法,而非主观的随意发挥。
四 对“鉴往训今”阐释的评价
顾炎武“鉴往训今”的阐释带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和现实倾向,是明清之际知识分子道德取向的代表。这种在“明道救世”背景下充满时代精神的阐释,与儒家兼济天下的入世观相通,将阐释经典上升到挽救时代危机、改良社会的高度。从某种意义上讲,顾炎武的阐释完成了其与儒家先哲之间的对话。这种阐释回到了由孔孟开创的“知人”与“知言”的阐释循环上来。可以说,顾炎武“鉴往训今”的阐释,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儒家“言以足志,文以足言”[21]1024的意图论阐释传统的回归,颠覆了明代以来“尚情”“尚趣”的阐释风气。
首先,这种阐释带有显著的学术性,遂成有清一代治学方式之大势。蒋寅先生指出:“他(顾炎武)不是将自己对诗歌的认识作为理论来演绎,而是以学术史的方式来呈现,即通过对诗学传统的重新解释使它成为有历史依据的、有成功经验支持的理论话语。”[5]推源溯流使阐释成为有学术背景支撑的可靠话语,知音考文使小学文字音韵为阐释理论背书,再通过综核名实和明义例,发现其中一以贯之的规律。这些方法非有广博学识和深厚学术功底者不能为,后成为乾嘉学者治学门径。在其观念引导之下,钱大昕仿效《日知录》体例撰《十驾斋养新录》,赵翼作《廿二史札记》,考证尤为精细,并说“或以比顾亭林《日知录》”[22]《廿二史札记小引》,1。乾嘉学者“一字之证,博及万卷”[23]93,这种综核名实的考证方法与顾炎武不无关系。此后清代的文学、经学、史学的阐释都带有学术化倾向。
其次,在阐释中对文字音韵倍加重视,顾炎武可谓有发轫之功。他强调通过一字一句的训释“知音考文”来通明圣道。如不能通小学,则不能准确理解文本本义,阐释也就变得毫无意义。这其实是对阐释的基础——语言的回归。自此开始,清代的文学和经学阐释尤其注重语言文字的考究,顾炎武开启了乾嘉学者“由文字、声音、训诂而得义理之真”[24]390的阐释路线。如惠栋说:“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25]21;戴震主张:“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26]192;王念孙称:“窃以诂训之旨,本于声音”[27]《自序》,2。顾炎武影响了有清一代的阐释方式。正如钱穆先生所言:“故治音韵为通经之钥,而通经为明道之资。明道即所以救世,亭林之意如是。乾嘉考证学,即本此推衍,以考文知音之工夫治经,即以治经工夫为明道,诚可谓得亭林宗传。”[28]148
再次,顾炎武“鉴往训今”的阐释突破了宋明以来心印证悟的阐释方式,使阐释活动由印象式、模糊性转向实证性、精确性。顾炎武通过推源溯流、知音考文、综核名实和明义例等方法,使阐释的有效性验证原则变得切实可行。因而宋明以来的“心解”“臆说”的阐释让位于对文字音韵训诂的严密考证,标志着阐释由明末借杯浇臆的主观性阐发转向了客观性的科学实证的方向。梁启超曾言:“亭林学术的特色在于反对向内的——主观的学问,而提倡向外的——客观的学问。”[1]72虽是针对亭林学术的总体而言,但若用来评价其在阐释学上的贡献也同样适用。
另外,“鉴往训今”的阐释所形成的无征不信、综核名实的一代学术风气,也影响到清代的文学阐释。顾炎武指出的“义例”,不仅可作为一种阐释方法,更可上升为一种抽象的理论思维。“实际上,‘明义例’之路途,一直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条隐线”[29]。广泛搜集、发现和了解阐释对象的义例,再加之实事求是的考证,从而使阐释变成有实证支撑的理论话语。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清代产生了许多对前代诗人诗集作注的经典作品,如杨伦《杜诗镜铨》、仇兆鳌《杜诗详注》、浦起龙《读杜心解》、査慎行《苏诗补注》、沈钦韩《王荆公文集注》《范石湖诗集注》、冯应榴《苏文忠公诗合注》、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等。
应该说,顾炎武的“鉴往训今”建立在有客观文本作支撑的有效性基础之上,是明末阐释学“心解”“臆说”的一大反动,具有纠正时弊的重要作用。但其在具体的阐释过程中,也存在矫枉过正,只为“经世致用”立说,牵强附会的问题。他说:“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4]91又说:“以格物为‘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则末矣。知者无不知也,当务之为急。”[2]377顾炎武把基于文学性的“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格物看作是低级的,而“当务之为急”的格物才是高级的。格物致知,就是推究事物的原理来获取知识,本是人研究和认识外物的基本方法,并无高低之分。而顾炎武在阐释时却已预设了一个为自己“经世致用”说立论的目的。可见有时顾炎武自己也陷入了“赋诗言志”的泥淖,与自身提倡的从客观理性的文本出发的阐释原则相矛盾。另外,顾炎武的“鉴往训今”有时过分拘泥于“鉴往”,一切为古是尊,把古人(尤其是汉人)的阐释看作是唯一正确的,甚至说:“著书不如抄书。凡今人之学,必不及古人,今人所见之书之博,必不及古人”[4]29,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消解了阐释在时间维度上的多元化。
事实上,由于文本的多义性、开放性,以及读者的主观参与,阐释的多元化是不可避免的。然而,诗无达诂并非是师心臆说的借口。还原作者之志,探寻作者本意,仍是阐释活动最重要的目标。顾炎武以其明道救世之志,通过“鉴往训今”的方式,使阐释一方面根植于客观文本本身,另一方面为当下的社会现实服务。在古往今来阐释者们追求作者本意的尝试中,顾炎武“鉴往训今”的阐释,为阐释者提供了一条获取文本本义最直接有效的途径,使得阐释者对作者本意的追求不再是一个幻想。阐释在建立起有效验证的根基后,其意义和价值也随之呈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讲,顾炎武在中国阐释学的发展史上具有独特意义。
注释:
①关于“时间距离”的概念,可参见:〔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373页。
②《音论》卷中“古诗无叶音”条有云:“稍为考据,列本证、旁证二条。本证者,诗自相证也;旁证者,采之他书也。”参见:顾炎武《音学五书》,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5页。
[1]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2]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3]孙雪霄.二十世纪顾炎武诗文研究评述[J].山东社会科学,2010,(5).
[4]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M].华忱之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
[5]蒋寅.顾炎武的诗学史意义[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1).
[6]论语译注[M].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
[7]周裕锴.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8]陆九渊.陆九渊集[M].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0.
[9]慧开.无门关[G]//大正藏:第48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
[10]礼记正义[G].郑玄注,孔颖达疏//李学勤.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1]李景林.孔子述作之义的文化继承性[J].天津社会科学,2002,(6).
[12]毛诗正义[G].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李学勤.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3]李清良.中国阐释学[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14]〔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15]周裕锴.语言还原法——乾嘉学派的阐释学思想之一[J].河北学刊,2004,(5).
[16]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7]章学诚.文史通义[M].上海:上海书店,1988.
[18]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北京:中华书局,2010.
[19]张隆溪.道与逻各斯[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20]张伯伟.中国诗学研究[M].沈阳:辽海出版社,2000.
[21]春秋左传正义[G].左丘明传,杜预注,孔颖达正义//李学勤.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2]赵翼(著),王树民(校正).廿二史札记校正[M].北京:中华书局,1984.
[23]阮元.揅经室续集[G]//丛书集成初编.新1版.北京:中华书局,1985.
[24]钱大昕.潜研堂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25]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6]戴震.戴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27]王念孙.广雅疏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8]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9]唐元,张静.文道关系与文辞义例——《文史通义·诗教》意旨辨[J].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