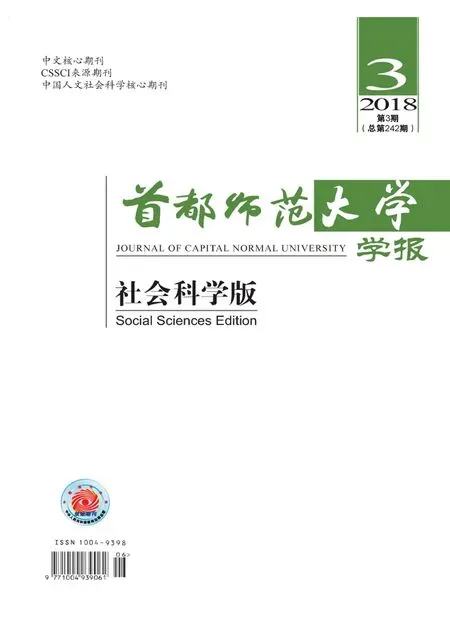宋代条例考论
李云龙
条例是中国古代法律形式之一,也是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条例一词在汉代就已出现,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被运用于法律领域。宋代是条例得到广泛运用的时期,在形式、内容、效力等方面都有很大改观,且渐趋完善,为后世条例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到明清时期,条例更是成为与律典并行的基本法律形式。目前学界对条例的研究多集中在明清时期,对于明清以前特别是宋代条例的研究虽已取得不少成果,但仍存在一些不足;对于宋代条例,现有研究仅限于一般性介绍和说明,更为深入的阐释尚有待展开。①关于宋代条例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吕志兴:《宋代法律体系与中华法系》,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杨一凡、刘笃才:《历代例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本人不揣浅陋,对宋代条例的含义、特点、编修、运用,及其与明代条例的异同等问题进行了初步考察,以求教于方家。不妥之处,敬祈指正。
一、宋代条例的含义与特点
条例一词在史籍中出现较早,对此刘笃才先生在《历代例考》一书中曾作过梳理。*参见杨一凡、刘笃才:《历代例考》,第7-8页。但早期的条例主要用于经学和史学研究,与法律领域无涉,关于这方面的条例,《后汉书》中有不少记载。随着条例的进一步发展,其适用范围也不再限于这两个较为专业的领域,而是逐渐作为一般的、条理化的规则的代称,被推向了更广泛的领域。在魏晋隋唐时期,条例的适用范围十分广泛,基本上涵盖了行政领域的各个方面,如礼仪制度、官员任用、地方监察、经济管理、选举制度等。在选举领域还出现了臣僚拟定的成文化的条例,如开元十七年(729),洋州刺史赵匡在议论举选的奏折后附有举人条例十三条、选人条例十条,对举人和选人的具体程序和内容作了说明。但此处的条例只是出于官员的自发愿望,尚不具备法律效力,不是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
需要指出的是,在魏晋隋唐时期,条例在多数情况下只是一般规则的代称,泛指意味强烈。这方面的例子有很多,如北魏时延尉少卿杨钧云:“又详恐喝条注:尊长与之已决,恐喝幼贱求之。然恐喝体同,而不受恐喝之罪者,以尊长与之已决故也。而张回本买婢于羊皮,乃真卖于定之。准此条例,得先有由。推之因缘,理颇相类。即状准条,处流为允。”*(北齐)魏收:《魏书》卷111《刑罚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881页。又如《隋书》载:“律令不一,实难去弊。杀伤有法,昏墨有刑,此盖常科,易为条例。”*(唐)魏徵、令狐德棻:《隋书》卷25《刑法志》,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697页。《唐律疏议》中的条例亦为此意:“里悝首制《法经》,而有杂法之目。递相祖习,多历年所。然至后周,更名《杂犯律》。隋又去犯,还为《杂律》。诸篇罪名,各有条例。”*(唐)长孙无忌等:《唐律疏议》卷26《杂律》,刘俊文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79页。
总的来看,宋代以前的条例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泛指一般规则和作为法律代称的意味强烈,专门制定的条例尚属少数;第二,多运用于行政事务的处理,司法审判活动中的条例并不多见;第三,涉及的具体事务内容丰富,范围广泛;第四,规范程度和效力层级较低,难以与律令格式等法律形式比肩。可以看到,条例在魏晋至隋唐时期逐渐步入正轨,运用日趋频繁和广泛。作为处理行政事务的具体明确规则的条例,在这一时期已经有了雏形,为宋代条例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
(一)宋代条例的含义
条例在宋代文献中主要有五个含义:
一是法律的泛指和代称。如太宗雍熙二年(985)九月乙未,诏:“岭南诸州民嫁娶、丧葬、衣服制度,委所在长吏渐加诫厉,俾遵条例。其杀人祭鬼,病不求医,僧置妻孥等事,深宜化导,使之悛革。无或峻法,以致烦扰。”*(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26,雍熙二年九月乙未,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599页。这里的条例即是法度的代称,延续了宋代以前对于条例的用法。
二是指某一具体的、以条例为名的法律。如太祖乾德二年(964)八月癸未,权知贡举卢多逊言:“诸州所荐士数益多,乃约周显德之制,定发解条例及殿罚之式,以惩滥进,诏颁行之。”*《长编》卷5,乾德二年八月癸未,第132页。其中提到了发解条例。又如真宗咸平五年(1002)二月甲午,审刑院上秦州私贩马条例:“自今一疋杖一百,十疋徒一年,二十疋加一等,三十疋奏裁,其马纳官,以半价给告事人。”*《长编》卷51,咸平五年二月甲午,第1117页。其中提到了秦州私贩马条例。
三是指零散的事例,有学者指出,“由于古人往往把各种形式具有‘条举事例’特征的例都泛称为条例”,*杨一凡、刘笃才:《历代例考》,第8页。因而不少史料中提到的条例,实际上并非指明确和规范的立法,而是指事例。如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五月癸卯,臣僚言:“大抵条例戒于妄开,今日行之,它日遂为故事,若有司因循,渐致堕紊。”*《长编》卷211,熙宁三年五月癸卯,第5126页。又如《宋史·高宗纪八》载:“(绍兴二十六年九月)戊辰,命吏、刑二部修条例为成法。”*(元)脱脱等:《宋史》卷31《高宗纪八》,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586页。这里提到的条例亦属零散事例的范畴。*有关这一史料的详细说明,参见拙作《宋代断例再析》,载(台湾)《法制史研究》第26期(2014年12月)。
四是指条与例的合称。如《宋史·徐处仁传》中载:“乞诏自今尚书、侍郎不得辄以事诿上,有条以条决之,有例以例决之,无条例者酌情裁决;不能决,乃申尚书省。”*《宋史》卷371《徐处仁传》,第11520页。又如绍兴四年(1134)八月,权吏部侍郎胡交修等奏:“契勘近降细务指挥内一项,六曹长贰以其事治,有条者以条决之,无条者以例决之,无条例者酌情裁决。”*(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帝系》11之2,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214页。条与例分别指称不同的法律形式,条例在这里用作二者的合称。
五是有“条分例举”之意,指有条理地加以说明。如太宗至道二年(996)五月壬子,就李继迁寇灵州事,臣僚张洎奏称:“灵武郡城,介在河上,馈运艰阻,臣请备陈始末,一二条例以言之。”*《长编》卷39,至道二年五月壬子,第835页。又如真宗咸平五年(1002)正月乙丑,真宗在与臣僚讨论防秋策略时称:“今已复春时,汲汲经营,至将来犹虑不及。中书、枢密院可各述所见,且今岁防边宜如何制置,条例以闻。”*《长编》卷51,咸平五年正月乙丑,第1112页。可见并非指名词意义上的条例。
(二)宋代条例的特点
通过对宋代基本史料中有关条例内容的梳理,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条例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主要适用于行政和经济事务。与明清时条例主要作为“律的补充和辅助的刑事法规”,*苏亦工:《明清律典与条例》,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2页。但苏亦工先生也指出,明清时期条例的刑事性质也不是绝对的,比如“乾隆间颁行的《钦颁磨勘简明条例》、光绪二十一年颁行的《钦定武场条例》等虽名为条例,却是有关行政方面的规定”,第44页。广泛适用于司法活动不同,宋代条例适用范围与唐代大体一致,主要用于具体的行政和经济事务。以《宋会要辑稿》为例,“条例”一词在《宋会要辑稿》中共出现了540次之多。其中在职官中出现了206次,食货中出现了154次。职官部分和食货部分是条例运用最多的,条例大量被运用的领域有两个:一是官员管理领域,二是经济生活领域。其最为直接和主要的原因,自然是王安石执政时期力推的、以“均通天下财利”为中心任务的制置三司条例司的设置,但条例相较于成文法所具有的简便易行的特点,也是条例能够在这两个领域发挥作用的原因。
第二,规范化程度相对较低,脱胎于具体事例的痕迹明显。虽然从研究的角度来看,宋代的条例已经具备了法律形式的特征,也在实际事务中发挥了类似的作用,但在时人眼中,条例尚不能与律、令、格、式、敕等传统法律形式相提并论。仁宗庆历四年(1044)八月辛卯,范仲淹奏称:“今中书,古天官冢宰也。枢密院,古夏官司马也。四官散于群有司,无三公兼领之重,而二府惟进擢差除循资级,议赏罚检用条例而已。”*《长编》卷151,庆历四年八月辛卯,第3673页。范仲淹认为当时的官制名实不符、事权分散,中书门下和枢密院作为主管政务和军事的两大核心机构,却只是负责一些简单低级的工作。神宗熙宁二年(1069),陈升之也认为:“条例者有司事尔,非宰相之职,宜罢之”,*《宋史》卷161《职官志一》,第3792页。“宰相无所不统,所领职事,岂可称司”。*《宋史》卷312《陈升之传》,第10238页。。
第三,涉及的范围包括部门内部和地方机构。通过对宋代史料的梳理和统计,可以发现存在众多以部门和地方为名的条例。不少部门内部都编有条例,以为日常运作过程中处理事务的依据。如咸平六年(1003)六月:“以吏部侍郎陈恕为尚书左丞、知开封府。恕在三司,前后逾十数年,究其利病,条例多所改创。”*《长编》卷55,咸平六年六月丙戌,第1205页。可见陈恕在三司任职时,改变和创制了不少在三司内部行用的条例。当面对类似事件,朝廷的处理方式前后有别时,也需要翻检前后的不同规定,重新编修相对统一的条例,如治平三年(1066)正月十八日,枢密院言:“使臣差出勾当许乘递马体例不一,欲检会前后条例,就差本院编例官重行删定。”*《宋会要辑稿·兵》24之17,第7187页。以地方为名的条例亦不在少数,如京东路条例、邕州条例、陕西等路条例、平夏城灵平寨条例、开封府界条例、京城条例等。与机构之间相互参照类似,这些条例也多为地方在处理具体事务时形成的,一经朝廷确定,便可为其它地方所效仿。
二、宋代条例的编修:原因、来源与原则
(一)宋代条例的编修原因
在中国传统社会,皇帝对于诸多事务拥有最终的决定权,宋代也不例外。但一方面事务繁多,皇帝不可能事无巨细地过问每一件事;另一方面,对于类似的事件和情形,由于时机和场合的不同,皇帝的处理也不可能完全一致。为了避免事务管理的混乱和处理结果的差异,以维持有效统治,制度性措施就显得十分必要。而律令格式等相对固化的法律形式往往内容有限、更新迟缓,因此律令格式以外的其他法律形式就有了发挥作用的空间。条例以其灵活便捷的特点,在宋代行政事务处理中得到了广泛运用,时人云:“素有令式者归有司,未有令式者立条例。”*《长编》卷257,熙宁七年十月庚辰,第6277页。
中国古代的皇帝虽然反对法律制度凌驾于自身权威之上,但只要不是昏庸和愚昧之至,往往并不反对将一些具体性的事务纳入制度的范围,所谓“不立制度,则未之前闻”。*《唐律疏议》卷1《名例律》,第1页。特别是对于格外注重守成的宋代皇帝来说,通过确立最终需获得其认可的制度规范,一方面可以防止部门和地方的长官获得过多的决定权和裁量权,另一方面也可以树立自己遵守法度的良好形象。从臣僚的角度来看,将部门内部和地方具体事务加以整理和编排乃至立法,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皇帝赏罚不均、任免无序等行为,也可以避免出现胥吏利用零散、繁复的不成文事例谋取非法利益的情况。
如大中祥符五年(1012)十二月丙寅,诏:“诸司使副任缘边部署、知州、钤辖、巡检等,入辞日,求补荫子侄,远近之际,恩典不均,宜令枢密院差定条例。”*《长编》卷79,大中祥符五年十二月丙寅,第1807页。庆历四年(1044)二月丁巳,针对审官院、三班院、铨曹这三个机构内部条例极为繁杂的情况,范仲淹奏称:
臣窃见审官、三班院并铨曹,自祖宗以来,条贯极多,逐旋冲改,久不删定。主判臣僚,卒难详悉,官员使臣,莫知涯涘,故司属高下,颇害至公。欲乞特降指挥,选差臣僚,就审官、三班院并铨曹,取索前后条例,与主判官员,同共看详,重行删定,画一闻奏。付中书、枢密院,参酌进呈。别降敕命,各令编成例策施行。*《长编》卷146,庆历四年二月丁巳,第3550页。
由于负责选官的机构内部行用的条例极为繁多,即便是部门官员对此都难以知悉,侵害到选任制度的公正性。所以范仲淹希望将审官院、三班院、铨曹这三个机构内部的条例,重新加以删定和纂修,以期处理方式协调划一。可见部门内部有不少零散的条例,这些零散条例积累多了以后难免会前后抵牾,有必要加以整理。熙宁四年(1071)四月,中书言:“选人磨勘并酬奖、致仕、改官,前后条例不一。”*《长编》卷222,熙宁四年四月壬午,第5412页。因而制定了新的规则,对不同级别官员的考选次数及相应的改官级别作出了具体规定。又如元丰元年(1078)六月二十一日,诏:“司农寺见行条例繁复,致州县未能通晓,引用差误。昨令编修,已经岁时,未见修成。令丞吴雍、孙路、主簿阎令权罢其余职事,专一删修,限半年,仍月以所修成条例上中书。”*《宋会要辑稿·刑法》1之11,第6467页。司农寺行用的条例,也是出于类似原因被要求进行删修。
(二)宋代条例的编修来源
条例的形成有两个主要途径:一是自发生成的途径,即零散的、不成文的事例经过长期行用而形成;二是正式编修的途径。后者又具体分为两种情况:其一为对自发生成的条例进一步明确和规范而形成,如中书条例;其二为对诏敕加以删修后形成的体系化的成文规则,如吏部条例。因而从广义的角度来看,条例编修的来源既包括事例,也包括诏敕,但是二者并不完全相同,后者由于出自政权中枢而规范性更强。关于事例的问题笔者已有专文加以论述,*参见拙作《宋代行政例刍议——以事例为中心的考察》,《求索》,2015年第9期。对于条例与诏敕的关系问题则鲜有学者涉足,因此下文以源于诏敕的条例为中心,对宋代条例的编修来源问题进行探讨。
在宋代正式编修的条例中,有不少源于皇帝发布的诏敕,这一点可以从不少史料中看出来。如《长编》载,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四月癸卯,“令礼部贡院取前后诏敕经久可行者,编为条例”。*《长编》卷77,大中祥符五年四月癸卯,第1761页。要求将经久可行的前后诏敕编纂为条例。又如熙宁五年(1072)二月甲寅:“大宗正司上编修条例六卷。先是,嘉祐六年正月,诏魏王宫教授李田编次本司先降宣敕,成六卷,以田辄删改元旨,仍改命大宗正丞张稚圭李德刍、馆阁校勘朱初平陈侗林希同编修,至是上之。”*《长编》卷230,熙宁五年二月甲寅,第5589页。史料中提到,原编修官李田在编修大宗正司条例时,因为随意删改作为原始材料的诏旨而被更换,说明条例编修的来源是皇帝的诏敕。哲宗元祐元年(1086)四月乙未,门下、中书外省在修成元丰尚书、户部、度支、金部、仓部敕令格式时称:
取到户部左右曹、度支、仓部官制条例,并诸处关到及旧三司续降并奉行官制后案卷、宣敕,共一万五千六百余件。除海行敕令所该载者已行删去,他司置局见编修者各牒送外,其事理未便顺,并系属别曹合归有司者,皆厘析改正,删除重复,补缀阙遗。*《长编》卷374,元祐元年四月乙未,第9079页。
虽未直接指出户部左右曹、度支、仓部官制条例的来源,但能够与续降(指挥)、宣敕等一同编修,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几类的内容是大体一致的。另外,从这则史料也能够看出条例内容的繁多冗杂,如果说这里的一万五千六百余件,还难以确定哪些属于官制条例,那么在另一条史料中,条例的繁杂体现得更为明显。绍兴二十八年(1158)九月辛巳,臣僚言:“被旨修吏部条例,本所取会到续降指挥计五千件,而删定官止五员,恐难办集。望于大理寺权暂差官五员,不妨本职,同共删修。”*(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0,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458页。
因此,正式编修的条例与编敕在来源上具有一致性,即皆为散敕。宋代的编敕编修频繁,内容庞杂,既包括海行敕,也包括一司一务敕。*有关宋代的编敕,参见戴建国:《宋代刑法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2-90页。经过删修的散敕,大部分且优先成为了更为规范的编敕。如神宗熙宁元年(1068)二月六日,诏:“近年诸司奏辟官员,就本司编录条例簿书文字,颇为烦冗。今后应系条贯体例,仰本司官依《编敕》分门逐时抄录入册,不得积留,别差辟官。如续降宣敕岁久数多,合行删修,即依祖宗朝故事,奏朝廷差官修定。”*《宋会要辑稿·刑法》1之6至7,第6464-6465页。可见删修编敕在层次上要高于编录条例。但条例的生成途径更为多样,适用范围更为具体,层次也更低(多为部门内部和地方事务),也更具有针对性(官员管理和经济活动),所以并不能被编敕完全取代,亦有其独特价值。
(三)宋代条例的编修原则
有关条例在编修时所应遵循的原则,在史料中能够见到的描述比较少。这一方面是由于大部分的条例并不是经由正式编修的途径,而是随着实践的长期运用逐渐形成。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条例的编修层次往往较低,多存在于部门或地方内部,较少由朝廷主导。此外,以诏敕为来源的正式编修的条例,其方式与编敕较为接近,并无太多特别之处。
因此下面主要围绕中书条例来进行探讨,如上文所言,中书条例并非是以诏敕为基础编修的,而是对自发生成的条例进一步规范后形成的。其本身实属部门内部的条例,但却因神宗致力于变法和改革的特殊背景,而得到了大力推动,这为我们了解此类条例的编修原则提供了难得的材料。北宋中期神宗即位后,希望革除积弊,“谓中书政事之本,首开制置中书条例司,设五房检正官,以清中书之务”。*《宋会要辑稿·职官》1之74,第2366页。对于中书编修条例十分重视,熙宁三年(1070)五月戊戌,针对中书编修条例的问题,神宗曾有过原则性的指示和说明:
中书所修条例,宜令简约有理,长久可施行遵守。仍先令次第编排,方可删定取舍。今中书编条例,闻已千余册,遇事如何省阅,虽吏人亦恐不能悉究。可令先分出合为中书每行一司条例为三等,仍别见行、已革、重复者,例或分明,与条无异,止录其已施行者。或自有正条违之以为例者。或不必著例自可为条者。或条不能该,必须例为比者,使各自为处,然后中书日以三五件参定存去修创之。朕所见大概当如此,卿等宜更审度,恐尚有不尽事理。近见閤门编仪制,取索文字费力,盖吏人不喜条例分明,亦须量立赏罚,以防漏落。*《长编》卷211,熙宁三年五月戊戌,第5121-5122页。
可见要求中书所编条例在总体上应该“简约有理,长久可施行遵守”,在方法上须“先令次第编排,方可删定取舍”,并且要“别见行、已革、重复者”。具体分为四种情况:第一,“例或分明,与条无异,止录其已施行者”。如果条例十分明确,且与律条没有冲突,只收录已经施行的。第二,“自有正条违之以为例者”。本身已有相关律条,但却违背其规定制定了条例,这样的自然不在收录之列。第三,“不必著例自可为条者”。不需要著为条例,而可以定为律条的,则要定为律条。第四,“条不能该,必须例为比者”。不应载于律条,需要著为条例以为比照和参考的,则著为条例。原来中书所编的条例有千余册之多,这些为数众多的条例或者只经过简单的整理编排,或者只是单纯的各种行政事例的积累和记录,在检索和使用过程中十分困难,为胥吏上下其手、谋取私利创造了条件。神宗深谙其弊,因而颇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编修时的基本原则和注意事项,希望对中书省内部的条例进行系统清理。
三、宋代条例的运用:检详、颁行与功能
(一)宋代条例的检详
无论是自发形成的条例,还是正式制定的条例,在运用过程中首先遇到的就是条例的检详,或称检用。宋代的条例规模庞大,零散的、未经编修的条例自不待言,即使是经过一定编修乃至正式制定的条例,其数量也十分可观。因而不少机构内部都有专门人员负责检用条例,如枢密院检详官。枢密院检详官,始置于神宗熙宁四年(1071),其职掌为“检阅、审核枢密院诸房条例与行遣文字,及起草机要文书,并按月将诸房所管外路兵官赏罚事送进奏院等”。*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09页。可见检详枢密院内部行用的条例是其重要职责之一。为使检用条例更加专业化,在熙宁五年(1072)二月到四月间,还曾短暂设置过枢密院检用条例官,《长编》载:
光禄寺丞杜纯为枢密院宣敕库检用条例官。先是,诏可专差官一员检用条例,其逐房所呈判检文字,并先送宣敕库贴写条例呈覆,故用纯为之。*《长编》卷230,熙宁五年二月丁卯,第5602页。
罢枢密院检用官杜纯归编敕所。先是,诸房条例即检详官检用,及都承旨李评建议,始别置检用官专主之,而每用例则亦取之诸房,徒使移报往复,益为迂滞,故罢之。*《长编》卷232,熙宁五年四月丙子,第5640页。
虽然这一职位由于不符合原有的检例机制、徒增事端而被取消,但却表明检用条例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了广泛认可。除枢密院外,其它机构在日常行政事务处理中也需要检用条例,如熙宁三年(1070)八月己卯,诏:“中书,应大卿监以下陈乞恩泽,并检条例进拟,不须面奏。”*《长编》卷214,熙宁三年八月己卯,第5219页。指出职位在大卿监以下的,只需要检具条例奏上,不需要上殿面奏。又如元丰五年(1082)六月癸亥,诏:“尚书省六曹事应取旨者,皆尚书省检具条例,上中书省。”*《长编》卷327,元丰五年六月癸亥,第7877页。尚书省下六部如果有事需要奏请,须由尚书省先检具相关条例,再上中书省。并且强调:“官司如辖下有申请,并须明具合用条例行下,不可泛言依条例施行。”*《宋会要辑稿·刑法》2之36,第6513页。在奏请的时候须列明相关的条例,不能泛泛地称所奏事项是有条例可依的。
(二)宋代条例的颁行
宋代的条例可以指称诸多效力层次的规则,从最低级的零散的事例,到相对规范、经过初步编排的规则,再到经过正式的编修逐渐成文化和规范化的条例,最高级的则是公开颁行的、接近于成法的条例。宋代正式颁行的条例比较少,如康定元年(1040)四月壬子:“李淑等上新修《閤门仪制》十二卷、《客省条例》七卷、《四方馆条例》一卷。”*《长编》卷127,康定元年四月壬子,第3009页。提到了《客省条例》和《四方馆条例》。熙宁八年(1075)二月己丑:“看详编修中书条例李承之等上《礼房条例》十三卷并《目录》十九册,诏行之。”*《长编》卷260熙宁八年二月己丑,第6348页。提到了《礼房条例》。又如政和七年(1117)十二月,枢密院言:
修成《高丽敕令格式例》二百四十册,《仪范坐图》一百五十八卷,《酒食例》九十册,《目录》七十四册,《看详》卷三百七十册,《颁降官司》五百六十六册,总一千四百九十八册,以《高丽国入贡接送馆伴条例》为目,缮写上进。*《宋会要辑稿·刑法》1之30,第6476页。
有的条例被明确要求予以颁行或颁示,政和七年(1117)四月十六日,详定一司敕令所奏:“修成《吏部侍郎左右选条例》,诏令颁行。”*《宋会要辑稿·刑法》1之29,第6476页。南宋高宗绍兴年间,叶颙“除吏部侍郎,复权尚书。时七司弊事未去,上疏言选部所以为弊,乃与郎官编七司条例为一书,上嘉之,令刻板颁示”。*《宋史》卷384《叶颙传》,第11820页。甚至有将条例雕版印卖的记录,靖康元年(1126),“诏吏部四选将逐曹条例编集成册,镂板印卖,从尚书莫俦之请也”。*《宋会要辑稿·选举》23之12,第4615页。建炎四年(1130),臣僚言:“望下省部诸司,各令合干人吏将所省记条例攒类成册,奏闻施行。内吏部铨注条例,乞颁下越州雕印出卖。”*《宋会要辑稿·刑法》1之34,第6478页。
(三)宋代条例的功能
条例在宋代的政治生活和法律体系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功能,具体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认识:
第一,促使朝廷处理方式相对一致。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社会带有强烈的人治特征,宋代也是如此。特别是从北宋开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有日益加强之趋势,诸多事务的决定权都掌握在以皇帝为中心的朝廷手中。但需要处理的事情千头万绪,如果缺乏制度性的措施,就很难保证类似事务得到类似处理。一方面为了防止可能得到的利益的损失,另一方面也便于提高处理类似事务的效率,用条例将皇帝的处理方式固定下来就显得尤为必要。如乾德二年(964)八月癸未,“权知贡举卢多逊言诸州所荐士数益多,乃约周显德之制,定发解条例及殿罚之式,以惩滥进,诏颁行之”。*《长编》卷5,乾德二年八月癸未,第132页。为了对诸州荐举的人数进行约束,防止滥进,于是制定发解条例予以规范。
又如熙宁九年(1076)正月乙亥,中书言:“中书主事以下,三年一次,许与试刑法官,同试刑法。第一等升一资,第二等升四名,第三等两名,无名可升者,候有正官,比附减半磨勘,余并比附试刑法官条例。”*《长编》卷272,熙宁九年正月乙亥,第6661页。对于中书主事以下官员试刑法的问题,除特别加以规定的外,其他事项参照试刑法官条例。在南宋时,发挥着这样作用的条例也很常见,如:“诏中书、门下省检正官,岁举官如左、右司条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6,第611页。“观文殿学士、醴泉观使、兼侍读秦桧为枢密使。应干恩数,并依见任宰相条例施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8,第2036页。
第二,促使部门具体事务有据可循。不断膨胀的皇权总是希望将更多事务的决定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但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实现的,皇帝的意志必然需要通过具体的部门和机构才能落实。而部门制度的完善与中央集权的加强,也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矛盾,实际上部门内部运行越规范,就越能防止部门长官拥有较多的事务决定权,也就越容易为皇帝所掌控。在部门具体事务的处理中,条例无疑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庆历三年(1043)十月己未,范仲淹奏称:
臣窃见京朝官、使臣选人等进状,或理会劳绩,或诉雪过犯,或陈乞差遣,其事理分明可行可罢者,则朝廷便有指挥。内有中书、枢密院未见根原文字,及恐审官、三班院、流内铨别有条例难便与夺者,多批送逐司。其逐司为见批送文字,别无与夺,便不施行,号为送煞。*《长编》卷144,庆历三年十月己未,第3484页。
如果遇到朝廷对这几类事件没有明确指挥的情况,中书省和枢密院“多批送逐司”,可见审官院、三班院、流内铨如果有内部行用的条例,在此时是能够发挥作用的,因而中书、枢密院也难以擅自决断。为防止因此造成的事务积滞,范仲淹希望以后遇到这类情况时“仰逐司主判子细看详。如内有合施行者,即与勘会,具条例情理定夺进呈,送中书、枢密院再行相度,别取进止。如不可施行,即仰逐司告谕本人知悉”。建议虽无相关规定但部门官员认为可以施行的,亦应“具条例情理定夺进呈”。
元祐元年(1086)闰二月甲申,司马光在议论元丰改制后,三司财政权被不同机构分夺时提到:“祖宗之制,天下钱谷,自非常平仓隶司农寺外,其条皆总于三司,一文一勺以上,悉申帐籍,非条例有定数者,不敢擅支。”*《长编》卷368,元祐元年闰二月甲午,第8871页。可见三司的支给是有定数的,须依条例所规定的执行。此外,从反面来看,如果相关条例缺失,则会极大阻碍事务的运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绍兴四年(1134)四月丙戍,
大理少卿张礿请自今朝廷降指挥,应特旨处死,情法两不相当,许本寺奏审。从之。去冬,都督府获奸细董宝以闻,下寺核治,无他情状,礿用案问,徒三年,诏从军法。礿欲奏谳,而以法寺未有执奏条例,弗敢言,至是乃上此奏*《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75,第1429页。。
在之前董宝川案的处理中,大理少卿张礿本欲奏请,但因为大理寺没有相关情形下可以执奏的条例规定,所以不果行,条例在部门事务处理中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第三,促使地方管理逐渐规范有序。除了在朝廷和中央部门发挥作用外,条例在地方事务管理中更是功不可没。目前从史料中看到的以地方及地方机构为名的条例,有相当多都是涉及地方事务的管理。如州学教授条例:“欲望依西外宗正司见行旧法,置敦宗院教授一员。庶几教导宗子,不致失学,请给人从乞依州学教授条例施行。”*《宋会要辑稿·职官》20之38,第2839页。如文州条例:“照得叙州年额买马专委知、通主管,内通判从本司依文州条例奏举,其本州所买马十元一二堪充起纲。”*《宋会要辑稿·职官》43之107,第3327页。
类似的条例《宋会要辑稿》中还有不少,虽然史料中往往对这些条例的内容一笔带过,未列明具体内容,但其用法与朝廷及部门机构的用法相当接近,亦是不同地方及其机构之间事务处理方式的相互借鉴,藉此加强对地方的管理和约束。条例的这一作用,在王安石与文彦博的一次对话中也有所反映,《长编》熙宁四年(1071)四月壬戌载:
安石又以为诸军宜各与钱作银楪子之类劝奖习艺,然宜为立条例,使诸路一体,不然,则诸路各务为厚以相倾,而无艺极。文彦博曰:“付与州郡公使,当听其自使。向时,曾令公使置例册,端午,知州送粽子若干个,亦上例册,人以其削弱为笑。”安石曰:“周公制礼,笾豆贵贱皆有数。笾豆之实,菹醢果蔬,皆有常物,周公当太平之时,财物最多,岂可制礼务为削弱可笑。盖用财多少,人心难一,故须王者事为之制,则财用得以均节,而厚薄当于人心也。”*《长编》卷222,熙宁四年四月壬戌,第5401页。
王安石认为诸军可以制作银楪子之类以劝奖习艺,但应制定条例,使各地大致相同,防止各路一味追求厚赏,而失立赏之本意。文彦博则不以为然,认为可以任由地方处置。王安石认为财物虽小,却事关制度大体,不应等闲视之。我们从中能够感受到宋廷对于地方管控的细密和强化。
四、宋代条例与明代条例的比较
宋代条例的运用非常频繁,元代的条例则较为少见,如《元史》中的军籍条例、税粮条例、户籍科差条例、御史台条例,及《新元史》中的赃罪条例、采访遗书条例等。到了明代,条例又受到极大重视,重新在法律体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为更好地认识宋代的条例,并对宋代以后条例的发展状况有所阐述,下面就对宋明条例之间的差异与相同之处进行探讨。
(一)宋明条例的差异之处
第一,内容范围不同。宋代的条例主要适用于行政领域,如在《宋会要辑稿》中,职官部分和食货部分是条例出现最多的,条例被大量运用的领域主要有两个:一是官员管理领域,二是经济生活领域。在王安石变法时期,条例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变法和改革的法律工具。虽然在司法领域中偶有泛称条例的用法,但并无专门制定的以条例为名的法律文件。那宋代的断例是否接近于明代的条例呢?二者也不相同,宋代的断例与明代的条例都是作为成法的补充而存在,但宋代的断例是以具有参考价值的案例的形式发挥作用。*关于宋代断例的相关问题,参见拙作《宋代断例再析》,载(台湾)《法制史研究》第26期(2014年12月)。明代条例的内容则是抽象的条文,而非案例,如万历《问刑条例》名例律《犯罪自首条例》:
凡强盗,系亲属首告到官,审其聚众不及十人及止行劫一次者,依律免罪减等等项,拟断发落。若聚众至十人及行劫累次者,系大功以上亲属告,发附近;小功以下亲属告,发边卫,各充军。其亲属本身被劫,因而告诉到官者,径依亲属相盗律科罪,不在此例。*《大明律》,怀效锋点校,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57页。
此外,明代的条例既涉及司法领域,也涉及行政领域,其适用范围已不再像宋代那样仅限于行政事务中。尤其是明代司法条例即《问刑条例》的崛起,格外引人关注,这无疑是魏晋隋唐以来条例在法律运用过程的重大转变,将条例的运用上升到一个新高度。
第二,规范程度不同。宋明条例的第二个区别体现在规范程度上,宋代的条例脱胎于具体事例的痕迹明显,在结构上相对简单,编修程序也不像编敕、断例等法律形式的修纂那样严格。
而明代的条例,无论是内容结构还是制定程序,相对于宋代条例都更为完善。苏亦工先生在论及《问刑条例》的编修程序时指出:“明代《问刑条例》的修定与现代的立法活动有近似之处,须要经过一定的程序,并非由皇帝随心所欲地制定的。修例的每个步骤都有一定的权限分工和合作,譬如第一步由主管司法的各机关共同提出草案,第二步由更广泛的国家机关参与审议和讨论。每一个步骤的进展都必须经过并围绕皇帝的指示进行。”*苏亦工:《明清律典与条例》,第193页。除了《问刑条例》,明代不少行政条例的编修也较为规范,而且受到皇帝的重视,如《责任条例》的制定,史载:“高皇帝惩吏职之弗称,亲制《责任条例》一篇,颁行各司府州县,令刻而悬之,永为遵守,务使上下相司,以稽成效。”*(明)申时行:《大明会典》卷12《吏部一一》,明万历内府刻本。
第三,效力层次不同。宋代条例的效力层次比较低,虽然在处理部门内部事务和地方事务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宋人眼中,条例始终要比成法低一等。即便是在王安石变法期间,通过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主导相关事务,仍不能改变人们的看法。史载:“安石尝置中书条例司,马光讥之曰:‘宰相以道佐主,苟事皆检例而行之,胥吏可为宰相,何择也?’”*(宋)吕中:《大事记讲义》卷6《真宗皇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陈升之也言:“条例者有司事尔,非宰相之职。”*《宋史》卷161《职官志一》,第3792页。
而明代条例在效力上要高的多,从司法条例来看,《问刑条例》与律并行达140余年,与律文一起在司法审判中发挥作用。万历《问刑条例》还实现了与律条的合编,《明史·刑法志》载:“万历时,给事中乌昇请续增条例。至十三年,刑部尚书舒化等乃辑嘉靖三十四年以后诏令及宗藩军政条例、捕盗条格、漕运议单与刑名相关者,律为正文,例为附注,共三百八十二条。”*(清)张廷玉等:《明史》卷93《刑法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287页。从行政条例来看,虽然明代行政例的效力状况并不完全一致,但其中的常法类条例“内容更为系统和规范,在明代例的体系中居于最高层的地位,有长期稳定的法律效力”。*杨一凡、刘笃才:《历代例考》,第168页。
(二)宋明条例的相同之处
宋明条例之间的相同之处体现为两点:
第一,运用上都具有广泛性。无论是宋代的条例还是明代的条例,在运用上都具有相当的广泛性。就宋代条例而言,无论是机构内部,还是地方事务,都能够看到条例发挥作用,而且从宋代条例所规制的内容来看,基本涵盖了行政管理的各个方面。如中书户房条例、六曹寺监条例、宗正寺条例、枢密院诸房条例、国子监太学条例、御书院条例、外官条例、太一宫真仪库官条例、发运司属官条例、诸仓界监官条例、发运司属官条例、保甲司勾当官条例、诸司押纲使臣条例等。而明代条例既有司法条例,也有行政条例,条例运用的领域更为广泛。具体来看,明代的《问刑条例》按照律典的篇章结构加以编排,涵盖的内容相当全面。而像《责任条例》、《吏部条例》、《宪纲条例》、《军政条例》、《宗藩条例》等官修条例,也覆盖了行政事务的诸多方面。
第二,功能上都具有补充性。宋代条例和明代条例在功能上都具有补充性,均作为律条的补充性角色存在。宋代的条例多是行政例,传统律典则具有强烈的刑法色彩,在部门和地方具体事务的处理过程中往往鞭长莫及、力有未逮,所以宋代的条例与其他行政例一起,起到了很好的补充作用。*宋代的其他行政例如则例、格例,亦在部门和地方具体事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参见拙作《宋代则例初探》,(韩国)《中国学报》第72辑(2015年5月);《宋代格例新探》,(韩国)《中国学报》第76辑(2016年5月)。而明代的条例,无论是司法条例还是行政条例,同样也具有补充性。《问刑条例》的编修,就在于弥补不能更改的《大明律》所带来的僵化和保守等不足,如臣僚言:
刑书所载有限,天下之情无穷。故有情轻罪重,亦有情重罪轻,往往取自上裁,斟酌损益,著为事例。盖比例行于在京法司者多,而行于在外者少,故在外问刑多至轻重失宜。宜选属官汇萃前后奏准事例,分类编集,会官裁定成编,通行内外,与《大明律》并用。庶事例有定,情罪无遗。*(明)徐学聚:《国朝典汇》卷181《刑部》,明天启四年徐与参刻本。
杨一凡先生认为:“通过制定和修订《问刑条例》,及时对《大明律》过时的条款予以修正,又针对当时出现的社会问题适时补充了新的规定。这种做法,既保持了明律的权威性和稳定性,又利于法律的有效实施。”*杨一凡、刘笃才:《历代例考》,第167页。此外,明代的各类行政条例也在相关事务的处理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这里不再赘述。
结语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宋代以前条例的运用虽渐入正轨,但尚不成熟。泛指一般规则和作为法律代称的意味强烈,专门制定的条例尚属少数。内容丰富广泛,但规范程度和效力层级较低。第二,宋代的条例具有五个方面的含义,可以指称不同效力层级的规则。从特点上来看,条例在宋代主要适用于行政和经济事务,脱胎于具体事例的痕迹明显,涉及的范围包括部门内部和地方机构。第三,条例以其灵活便捷的特点,在宋代行政事务的处理中得到广泛运用。条例的编修来源十分广泛,既包括事例也包括诏敕,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编修原则。第四,宋代的条例规模庞大,有的条例还被公开颁行。条例在宋代政治运作和事务管理中发挥着重要功能,主要体现在促使朝廷处理方式相对一致、部门具体事务有据可循及地方管理逐渐规范有序三个方面。第五,宋代条例与明代条例既有差异之处,又有相同之处,二者在内容范围、规范程度、效力层次上存在很大差异,但在运用和功能上又具有一定相似性。
条例从早期主要运用于经学和史学研究,到南北朝时期开始进入法律领域,直至唐宋时期成为行政事务处理的重要法律形式,这期间经历了漫长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在宋代,无论是条例的形式、内容,还是其编修、运用,都与前朝有了很大的改观,规范性、活跃性及重要性大为提高。而宋代以后,条例的发展并未就此止步,最终在明清时期成为与律典并行的核心法律形式之一,其主要适用领域也从行政事务转向司法审判,这一过程耐人寻味,值得深究。条例在中国古代的演进轨迹也是中国传统法律体系发展的一个缩影,折射出法律形式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一种法律形式的产生、运用与消亡并非偶然,而是与其所依托的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因素息息相关。如何更好地厘清二者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式、进路与机理,将是笔者今后的研究课题。
——《李叔同—弘一大师年谱长编》评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