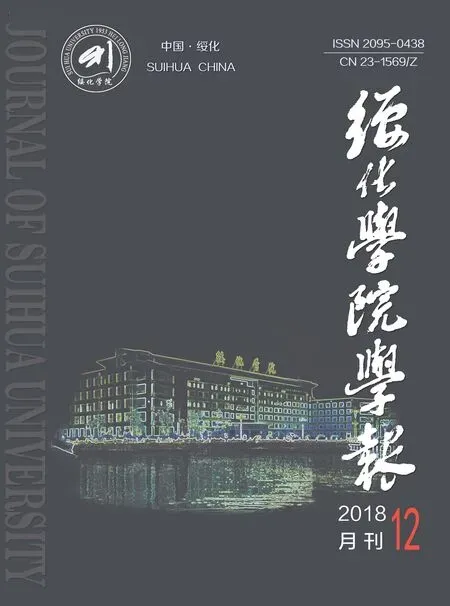符号化的“他者”
——《人间天堂》中男性视域下的“新女性”脸谱
王 潇 许庆红
(安徽大学外语学院 安徽合肥 230601)
《人间天堂》(1920)是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美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以严肃的笔调描写大学生生活的作品。小说记录了男主人公阿莫瑞·布莱恩从出生到30岁之前的人生经历,通过和五位女性的恋爱经历,生动形象地描绘出“喧嚣的二十年代”的社会历史画面,展现出年轻一代的心路历程。本文从女性主义的视角重新审视菲茨杰拉德的《人间天堂》中的“新女性”,发现小说中充斥着对这些“新女性”的偏见,男性视域下的女性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歪曲和误解。她们是父权社会双重评价标准下的“第二性”,被符号化——被塑造成外表美丽,但内心自私冷漠、拜金主义、行为放荡轻浮、道德观念薄弱的形象。她们被认为是衡量男性是否成功的符码,是男性借以向上流社会攀爬的工具,以及男性为满足虚荣心而挣逐追求的猎物;有些“新女性”则被呈现为“他者中的他者”,被认为是直接或间接导致了男性迷惘与幻灭、乃至人生悲剧的罪魁祸首。
一、双重评价标准下的“第二性”
菲茨杰拉德绝大多数作品设置的背景都是美国20世纪20年代的“金元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动摇了美国人的传统信仰和价值观念,女权主义运动也获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女性取得了选举权,在思想上更加开放,体现在衣着打扮和言行举止方面更加自由大胆,这样的“新女性”对男性权威构成了一定的挑战和颠覆。然而,“爵士时代”的美国,仍然是菲勒斯中心主义占据主宰。“新女性”们终究无法逃脱父权社会的价值判断。作品中充斥着对这些“新女性”的歪曲与贬斥,传达着对“新女性”的不满与怨怼。
父权社会的产生固然有其两性生理差异、自然环境条件和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等多方面必然性,但人们始终忽视的一点是,父权社会的严明秩序并不那么中性,在它那慈祥、平和、有几分聪慧和勤奋的面孔背后,另有青面獠牙、残暴狰狞的一面,这便是仅仅朝向女性的那张脸孔。[1](P2)父权社会结构体制下面对男女两性不同的两张面孔,突出表现在双重道德评价标准上,严苛的伦理规约仅仅针对女性。《人间天堂》中,比阿特丽斯被赋予了拜金主义者和没有道德意识的形象,她是个优雅的贵族女性,从小受显赫世家的淑女教育,曾与贫寒的达西陷入爱河,后来考虑到财力问题在怀有身孕的情况下嫁给了阿莫瑞的父亲。比阿特丽斯的真爱是阿莫瑞的生父达西,而非比阿特丽斯的丈夫。虽然小说有意抬高了比阿特丽斯的形象,贬低了阿莫瑞的父亲,然而,还是透露出比阿特丽斯是那种可以因为金钱而抛弃真爱,甚至是为了给自己的孩子找个有钱的爹才匆匆嫁给了一个自己不爱的男人。
小说开篇便点明阿莫瑞的父亲由于继承巨额遗产,家财颇丰,他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妻子像是个迷,暗示比阿特丽斯不爱自己的丈夫,是在和家世背景差距过大的达西恋爱未果后伤心憔悴才匆匆下嫁了阿莫瑞的父亲。这其中暗含着对比阿特丽斯的批判。然而,为什么达西没有受到任何批判而比阿特丽斯却要受到批判呢?这归根结底源自菲勒斯中心主义支配下的社会意识形态对男女两性的双重评价标准。在父权社会,男人生来就是人,是自由、合理、正确的,而女人不是生就的,是逐渐形成的,是被女性化的。[2](P309)同样的事情发生在男人身上是理所当然的,发生在女人身上就要被贴上“自私冷漠”“道德败坏”的标签,受到父权社会的指责和批判。弗吉尼亚·伍尔夫和波伏娃都曾强调女性独立经济地位的重要性,而当时的女性鲜少经济独立,在这方面男性具有明显的优越性,他们因此牢固了自己是世界的主人的地位,周围的一切都在告诉少女,变成他们的仆从是她最高的利益。[2](P379)在女性只能靠依附于男性才能获得物质条件的社会里,作者对于社会的不公、男女的不平等只字不提,对于比阿特丽斯出于在爱情和面包之间不得不放弃真爱的悲剧没有一丝同情怜悯却只有暗含的批评态度。
小说还有意质疑女性的道德准则,抹黑和贬低女性的自然身体欲望——在婚前与众多异性的接吻行为。当时美国流行“青年男女的亲吻晚会”,阿莫瑞和几位“新女性”都参加过。然而,受到质疑与谴责的只是女性。其中一位是休斯敦太太的女儿,她是个受欢迎的姑娘。可是,小说却借老一辈的休斯敦太太之口说道,“恐怕任何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妈妈……她们怎么也想象不到,自己的女儿对异性的亲吻有多随意、多习惯。女仆才是那样的。”[3](P82)休斯敦太太一直给女儿灌输加尔默罗修会(修女)的思想。同时,阿莫瑞作为一个这项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却又以高高在上的口吻来质疑、谴责现代女性的“道德准则”,并将其污名化:“周旋在十六到二十二个男孩之间……每场约会的间隙,她还会和P.D先生什么的在月光下、火炉旁或是黑夜里上演伤感的终情之吻。曾经的‘美女’已经变成了‘调情高手’,‘调情高手’又已经成为‘娃娃荡妇’。”[3](P82)在男女两性天差地别的双重评价标准下,男性的婚前性行为被社会普遍认可,然而女性的婚前牵手、亲吻、约会、性行为却被评价为道德堕落的“娃娃荡妇”。可见,在菲勒斯中心主义的认识论当中,“道德准则”只是针对女性,尤其是“新女性”。在主流男权社会的暴力规约下,女性的欲望、身体和语言都被紧紧地束缚和压抑着,男性是主体,女性是客体,是从属,是相对于男性第一性的第二性。[4](P186)
二、被符号化的女性
女性主义往往谈论性、质询性:什么样的性观念支持着人们的性行为,又是什么力量热衷于性管制,性在父权话语秩序中是如何被安排与理解的,女性的性魅力是如何被定义的,这些问题在《人间天堂》中都有清晰的反映。
在男性话语体系中,女性的“性”往往是被管制的。迈拉·圣·布莱尔被描写成一个随意轻浮、被男性征服随之又被厌恶的女性。迈拉是阿莫瑞的同学、13岁时的初吻对象,富裕家庭出身,这点从她家里拥有一位男管家,而在整个明尼阿波利斯只有三个男管家中可以看出。阿莫瑞应邀参加迈拉主办的舞会,他故意迟到以示自己与众不同,在到迈拉家门口前阿莫瑞反复练习见到迈拉的母亲时自己的说辞“尊敬的圣·布莱尔太太,很抱歉我来晚了,但是我的仆人......”[3](P14)其实阿莫瑞并没有仆人。随后俩人乘马车去和朋友们汇合,车上阿莫瑞不停地向迈拉示爱,然而,在阿莫瑞吻到了迈拉之后,他却“突然感到一阵恶心,他突然对整个事情都感到憎恶。不可遏制地,他想夺路而逃,永远不要再见到迈拉”[3](P21),在阿莫瑞实现了对年轻富有的迈拉的征服、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和征服欲之后,迈拉便立刻被弃如敝屣。迈拉在此只是证明阿莫瑞具有男性魅力和征服力的象征,是男性满足虚荣心的符号。
在否定女性之“性”的男权中心主义文化中,女性之“性”往往被看成负面的、消极的存在。《人间天堂》中,伊莎贝拉则被塑造成一位放荡不羁的女性。在男性叙事者的口中,伊莎贝拉在与无数男性的周旋中变得老于世故,年纪轻轻就结过婚,还又来参加这种舞会,对她言行举止的描写也是充满了男性偏见,是男主人公眼中矫揉造作、装作纯真的浪荡形象,阿莫瑞认为自己只不过是她的又一个爱情游戏对象。试想,如果男性认真的对待一位女性,怎么可能刚开始接触就能断定女性是游戏自己呢?对于女性的擅长社交为什么不是其知事明理而是任性放荡的结果呢?阿莫瑞与伊莎贝拉初见分别之后,一直保持书信往来,之后阿莫瑞邀请伊莎贝拉参加普林斯顿的晚会,阿莫瑞因为年轻貌美的伊莎贝拉的出现而名噪一时,受到瞩目,男主人公阿莫瑞借助女性使自己的名声和人气得到抬高之后,便与伊莎贝拉分道扬镳,末了还将罪责安在女性身上,哀叹到伊莎贝拉毁了他这一年。同样,阿莫瑞的最后一位女友埃莉诺·萨维奇在男性的叙事中也是一副颠覆传统的女性形象,她仅仅因为自己的突发奇想和骑着马突然冲向悬崖的一次过激行为而导致了阿莫瑞的厌烦。
罗莎林德则被歪曲为一个自私无情的拜金主义者。罗莎琳德是阿莫瑞大学同学亚力克的妹妹,年轻貌美,出身富裕,是菲茨杰拉德笔下典型的“美丽的巫女”,最能满足阿莫瑞虚荣心的对象。阿莫瑞和罗莎琳德陷入爱河无法自拔之时,罗莎琳德则考虑到阿莫瑞身无分无,而另一个自己的追求者道森·瑞德却是个富家子弟,于是果断地斩断了阿莫瑞的情思,嫁给了道森。然而,小说极力渲染阿莫瑞对她的爱恋之深,被罗莎林德抛弃后情伤难愈,这在一定程度上误导读者谴责罗莎林德的拜金和无情,转而站在男性这边同情阿莫瑞。可是从女性接受的视角来看,罗莎琳德的恋爱婚姻选择才是深思熟虑之后的明智之举,是长痛不如短痛的理智抉择。阿莫瑞口口声声谴责新女性的极度自私,实则他自己才是最自私的人,比起这些“新女性”他更爱的是自己,在他深深的潜意识里这些富贵貌美的“新女性”只是他满足虚荣心和实现自我的符号,是他迅速跻身上流社会的阶梯。如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言,在父权社会,父亲对少女拥有支配她的各种权力。如果她结婚,父亲会把权力全部转交给她的丈夫。妻子和役畜或一份动产一样也是男人的财产。[2](P94)凯特·米利特在《性政治》中揭示了男女两性的关系,从历史上到现在都是男性支配女性的权力结构关系,是一种支配与丛属的关系。[5](P33)《人间天堂》中的男主人公同样一直都试图在通过追逐、占有和支配出身显赫、年轻美貌的女性,而获得心理和生理上的满足,达到增加自身财富、提高阶级地位的欲望,因为在父权社会男性的潜意识中家庭生活与家庭关系的实质是男性对女性的性压迫、性束缚与性剥削。[6](P8)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露西·伊利格瑞更加尖锐的指出女性在社会传统中一直代表着男性的使用价值,是男性之间的交换价值。女性被先后被自己的父亲、丈夫等定价,决定着女性在性交易中的价值。[7](P37)《人间天堂》这部小说中作者却给男性的欲求披上爱情的美丽外衣,来掩盖强加给女性的符号化象征意义。
从这几位“新女性”与阿莫瑞的关系变化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些“新女性”被描写成衡量男性是否成功的符号、男性借以向上流社会攀爬的工具以及男性为满足虚荣心而挣逐追求的猎物。小说对她们的形象描写、情感态度与道德判断流露出了一些匪夷所思的厌恶、鄙视、质疑与谴责。
三、“他者”中的“他者”
菲茨杰拉德擅长描写现代“新女性”,她们大多年轻貌美、家世显赫、富贵多金。然而,小说中也不乏来自其他社会阶层、不同年龄段、相貌平平甚至有些丑陋的女性。这些次要的女性人物更加饱受偏见,成为菲茨杰拉德笔下“他者”中的“他者”。
不具备美貌的年轻女子,在男主人公心里就是“愚笨的”,尽管男性并没来得及真正了解女孩的内在和性格。对她们的外貌描写亦流露出男性的厌恶和鄙夷,在男性眼中相貌一般或丑陋的女性就是“可怜的”“从来没被注意过”,即使有异性对其展开示爱攻势,这也是“愚蠢的”,面对如此愚蠢的示爱,对从没被注意过的女孩却是难得的,她开心的“咯咯直笑”,而在男主人公看来,这场可笑的滑稽剧只不过是“不错的消遣”而已。由此可见,对于男性来说,女性姣好的相貌才是评判女性的依据,是虚荣、自私、无爱的男性满足自我的条件。面对这样的女性,男主人公似乎根本不愿意搞清楚她的其他状况就被直接全盘否定。相貌不出众的女性在肤浅男性的眼光中是“他者”中的“他者”,成了被双重边缘化与抹黑的对象。
克拉拉是阿莫瑞的表姐,早年丧夫、独自带着两个孩子。阿莫瑞被她的人格魅力——年轻美丽、大方得体、善良温柔深深吸引,想要跟她结婚。然而克拉拉经济状况不佳,出身亦非豪门,这些都无法满足阿莫瑞的虚荣心和人生理想,因此他才会因为梦见和克拉拉结婚的场面而被吓醒。阿莫瑞的潜意识里根本不愿意跟克拉拉结婚,即便她大方懂事、道德高尚,一个没财产没地位又寡居的拖油瓶对于男性来说作为女性的价值就一落千丈,对于这样的女性即使男性本能的欣赏和喜欢,考虑到对于自己没有价值也不会与其结百年之好。
在男权社会的男性视角下,女性一直占据一席留给罪人的位置,她们事事有罪,处处有罪:因为有欲望和没有欲望而负罪;因为太冷淡和太“热烈”而负罪;因为既不冷淡又不“热烈”而负罪;因为太过分的母性和不足够的母性而负罪;因为生孩子和不生孩子而负罪;因为抚养孩子和不抚养孩子而负罪……[8](P194)条件优渥的女性占据着罪人之席,因为在男性看来她们自私、拜金、感情不忠,而被写成直接或间接导致男性迷惘与幻灭乃至人生悲剧的罪魁祸首。相貌丑陋的少女、闪耀着人性光辉却贫穷丧偶的少妇与芳华已逝的中老年妇女在男性视域下更是稳坐罪人一席,是罪人中的罪人。在这种强烈的偏见下,进一步证明了波伏娃的女性主义观点,即女人的地位不是生来就是如此的,是男人、社会使她成为“第二性”。社会把第一性给予了男人,男人是主要者,女人是次要者。[4](P186)小说彰显的是在各种社会关系中建立的男性权力,忽视女性的社会性,将女性排斥在社会历史之外。[9](P146)在男人眼中,那些不漂亮、没有家世和财产、年老色衰的中老年妇女是被加倍边缘化、他者化、甚至妖魔化的,作品通过对她们的贬抑突出了男性对女性尊严的践踏及对女性权力的消解,然而贬斥的背后潜藏着这类女性对男性而言自身使用价值的贬值。毫无疑问她们是男性视域下“他者”中的“他者”。
结语
女性主义重启了女性身体的自由与解放问题,关心女性的性权利与性权力,解构男性作家作品中对女性之“性”的贬抑。尽管《人间天堂》几乎成了人们认识“喧嚣的二十年代”的权威典籍,成了年轻读者解读人生的生活指南。[10](P137)然而其对众多女性形象的歪曲与贬斥,仍然逃脱不了菲勒斯中心主义的影响,摆脱不掉被以作者为代表的男性群体符号化、他者化,是相对于男性的“第二性”。即使作者对当时的美国社会观察入微、认识超前,也依旧无法摆脱主流意识形态和男性视角的局限性,对以“新女性”为主的女性做出客观公正的刻画。女性主义认为,女性在社会、政治、心理等诸多领域受到了来自菲勒斯中心主义的压迫,《人间天堂》中的女性形象是对这一观点的有力证明。揭开作者盖在小说上的层层面纱,有助于我们从女性主义视角与女性读者接受的角度去理解该作品,加深对小说主题和人物形象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