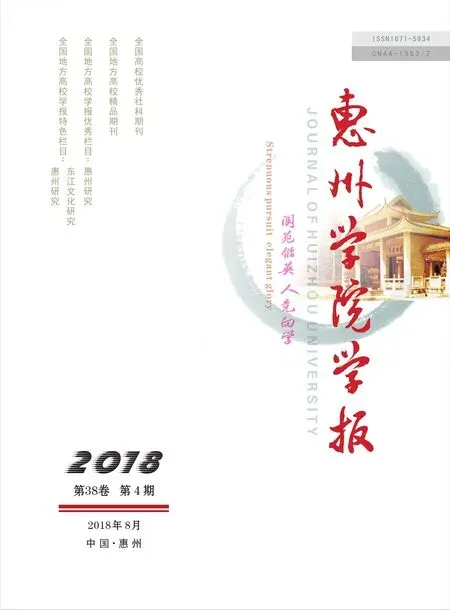熟悉的陌生人:网络人际交往的“失落”现象刍议1
唐珍
(安徽大学 社会与政治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藉由网络为媒介的社交,个体可以和陌生人建立熟悉的关系,是一种身体缺席的特殊交往形态,其交往空间的虚拟性和交往手段的多样性,不仅增加了交往主体间的新鲜感和吸引力,也让交往主体可以自由选择交往时间,随意更换自己的角色以满足不同的环境需要,并从中获得一种补偿性快乐。这种陌生人间的网络“虚拟”人际交往看似让处于疲惫、压抑、规训的现实社会成员寻得了自我满足的意义,释放了自由的天性,其实质上得到的是虚拟狂欢后的情感失落、人情淡化以及反抗现实生活的情绪。在网络交往的影响方面,S.Kiesler等人认为:“网络人际关系是肤浅、不真实的,网络不能建立起真诚和稳定的人际关系[1]”。B.Cornwell等研究者认为:“通过网络发展起来的浪漫关系较少涉及严肃性话题,并且不会真实地呈现自己[2]”。在浅层化、试探性的交往心态引领下,网络人际交往中的情感投入不足,难以形成类似现实社会的人际交往的强关系。而网络人际交往造就的身体与内心的非同步表达势必造成“网我”(网络中的我)与“真我”(现实中的我)的非对称性情感支持,进而产生来了社交失落。
一、熟悉的陌生人与网络人际交往的特殊性
网络人际交往突破了现实社会尤其是熟人社会交往的藩篱,将交往关系指向陌生人,使得看似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得以建立人际关系,进而形成了一种新型的人际交往方式。
(一)熟悉的陌生人
陌生人有两种,一种是毫无关系的陌生人,一种是与他人发生接触,却又保留离去自由的陌生人,后者不从属于任何群体、富有高度移动性的特点,他们之间常常会主动吐露的真相与私密[3]。该文所研究的对象是后者。韦尔曼提出:“网络环境扩展了传统意义上的人际交往,使交往对象大幅涵盖了弱联系和陌生人,同时还指出网络中的陌生人关系,不像都市街头擦身而过那样毫无关系,而是一种似近实远、又似远实近的社会关系[4]”。社会学意义上的“陌生人”概念最早是由德国社会学家西美尔提出来的,指出陌生人并不是过去意义上第一天来了第二天就要走的人,而是第一天来了之后会留下来的那种人[5]。它蕴含着近在眼前的人其实远在天涯,远在天涯的人也许近在眼前,是一种若远若近的关系。文章中将这种具有若远若近关系的陌生人称为“熟悉的陌生人”。
网络社会使得本来毫无关系的两个人甚至一群人得以接触和交往,但是,这种接触和交往不同于现实社会交往中人的肢体和感官接触,却也不是毫无关系。网络社会交往中,人借助电脑、手机等网络终端进入一个属于自己的虚拟交往空间,并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心仪的交往对象和交流内容。交往主体一旦对交往对象以及交往内容产生厌恶或者失去兴趣就会下线,且无碍于交往主体的现实生活。此外,在网络社会可以和任何人建立交往关系,但是又不会和任何人建立有机的交往关系,因为人与人在网络社会交往对象是随机的,时间也是不确定的,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上线,也不知道自己今天交往的对象明天会在不在。这种陌生人之间的交往互动是一种线上熟悉,线下陌生的人际关系,其实质是一种若远弱近的熟悉的陌生人。
(二)网络人际交往的特殊性
1.交往空间的开放性
网络社会将所有的信息转化为数字“0,1”,实现了信息形态的数字化,塑造了一个崭新的社会形态,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新的交往空间—Cyberspace(赛博空间)[6]。在这个空间里交往主体可以和任何人在任何时间发生交往关系,而这种交往行为仅仅发生在几秒之内并且超越了时间限制,让人际交往形态更具开放性。美国天体物理学家拉里·斯马尔说:“虚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沟通方式的变革是自古滕堡以来所发生的最根本的变化,这种相互连接的网络基本上是时空的破坏者,把距离和时间缩小到零[7]”。
2.交往关系确立的随机性
网络交往关系很强的偶然性和随机性。首先,交往的他者来源是不确定的,可能来自微信中的“摇一摇”,也可能来自QQ空间的“漂流瓶”,甚至可以是因为使用手机扫了某个商店的二维码,而认识了该商店的主人等。其次,选择交往时间的随机性。交往主体会在上班的闲暇时刻,下班的途中,也可能是在夜不能寐的时候。最后,交往关系的开始和结束具有随机性。因为交往关系的开始和结束时间均由交往主体自己所掌控,并依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互动话题或者交际对象。总而言之,整个交往过程都具有极大的随机性。
3.角色的虚拟性
现实社会人际交往是人与人在生产、生活中建立的一种社会关系,如亲人关系、债权关系、领导关系等。人在所属的社会关系中扮演着自己的角色,有着所属的身份和固定的标签。依据身份和标签的人际交往会受到年龄、性别、相貌、背景等因素的限制。然而,在网络人际交往空间本身所具有的连接和区隔的特性下,交往主体通过电子化的文字和符号等相关要素来呈现自己的身份和角色,而真实的显性身份则隐匿在网络架构的身后,以虚拟的方式进行选择性的角色建构,进而呈现最大化的理想型自我,获得补偿性快乐。交往主体可以根据交往需要随意对自己的性别、年龄等身份要素进行更换。例如,高龄老头儿将微博、微信等通信工具的头像设置成妙龄少女。
4.交往的去社会性
差序格局是对传统熟人社会关系的一种描述,并潜移默化的影响现实社会的人际交往。然而,网络社会交往是以网络为载体,借助电子文本或符号进行互动,没有主控中心、身份地位的差别、文化程度的高低等,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中心。主体可以根据交往的需要随心所欲地塑造自己的性别、身份、相貌等以更好寻求符合自己想象的交往对象。交往双方摒弃了来自现实社会的身份、地位等要素,进行平等而又轻松的交流,避免了现实社会人际交往的社会约束和压力。
二、网络人际交往的“失落”
网络人际关系使得主体获得了更多的倾诉对象并且加速了其社会角色的转换,却也造成了一系列的社交“失落”现象。
(一)人际感情趋向疏淡
每个交往主体都生活在现实社会中都必须遵循现实社会交往规则,而网络社会的开放性使得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交往的中心,且没有明确的交往规则。此外,交往关系的建立也是随机的,人们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在网络社会中结交自己喜欢的朋友,也可以瞬间解散这种朋友关系,并找到更多的替代者。这毕竟只是借助网络媒介以电子文本化的言语进行的浅层化的部分人格接触,任何交往关系的终结并不具有可预见性,故而感情关系显得疏淡和脆弱。
黄少华指出:“一种崭新的平面而无深度的感觉,正是后现代文明第一个,也是最明显的特征。说穿了这种全新的表面感,也就给人那样的感觉—表面、缺乏内涵、无深度,这几乎可说是后现代主义文化形式的最基本特征[8]”。由于交往主体卸除了来自现实社会的身份和标签,重塑了新的网络社会身份,隐匿了人的情感、价值、特征等,淡化了交往规则,最终导致交往主体间关系的疏远、感情的疏淡。正如网友所言:“对于网络交际不会只局限于一个人,而是像撒网式的寻求聊天对象,一下线也不会有接触的机会,甚至再次上线也可能遇不到,所以根本不需要顾忌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
(二)人际信任的弱化
信任的原始基础是熟悉的特征和过去的记录[9],是稳定社会关系的基本因素,人际信任则是维系人际交往关系的基本因素。现实社会的人际交往是面对面的交往,人可以根据交往主体的身份、姿态等判断其言语的真实性。同时,由于受到现实社会的道德伦理、交友原则等影响,个人必须保证其言语的真实性以更好的构建自己的亲友圈。对于主体而言,信任度越高,建立情感关系也越稳定。
在网络社会,交往主体可以最大限度地跨越性别、年龄、职业等限制构建所属符合交往需要的虚拟性角色,仅以电子符号化的文字呈现,因而难以判别交往对象的真实身份。同时,主体没有了现实社会的人情世故、伦理道德等约束,一旦在交往的过程中发生不愉快的情况,可以立即撤退或者更换交往对象,致使人际交往中信任缺失等问题产生,进而难以建立稳定的交往关系。此外,诸如“爱心筹”等公益募捐平台出现的虚假募捐消息骗取网民的同情和信任,以获取金钱收益。诸如此类,信任不断被弱化,最终泛化到现实生活中,影响现实人际关系的发展。
(三)反抗现实情绪的萌生
网络人际交往的独特性吸引了众多的社会群体,并趋向潮流化。一方面,网络人际交往的普遍性和多样性使得交往主体容易陷入角色扮演。另一方面,在网络社会,主体可以挣脱来自现实社会的身份、地位等束缚,将自己塑造成自己所期待的理想型角色并以最大化的方式呈现自己的完美人格。介于屏幕之隔,陌生交往主体间的交流常借助文字和符号夸夸其谈以隐匿面对面交流时的慌张、尴尬等心理,迎合了交往主体的情感需求,但又常常陷入角色扮演而无法自拔。
无论在网络社会扮演何种角色,最后依旧要回到现实生活中。在回归现实生活中,一部分人由于过度的角色扮演,沉浸在虚拟世界的快乐之中导致在现实社会中找不到属于自己的位置,产生了角色回归现实的落差感。这种落差感容易消解交往主体的线下交际能力,滋生沉溺网络社交的心理。如此,主体更愿意回归到虚拟社会寻求归属感,影响了其现实社会人际关系的构建。例如,电影《勇敢者游戏:决战丛林》中,现实中瘦小而羞涩的斯宾塞在游戏中变成了一名高大威武的硬汉冒险家,在游戏中充当着主要战斗角色并且遇到了心仪的女子,当游戏结束,斯宾塞却不愿意回到现实中,想要继续生活在游戏的虚拟世界享受着自己完美的身材和爱情。
三、网络社交“失落”的原因分析
网络社会交往的规则淡化、信任弱化以及角色失真带来的一系列社交“失落”,给个体带来了困扰,不利于人际交往的健康发展,亟需深度探寻“失落”背后的原因。
(一)角色失真下的感情回馈不足
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提出了“前台、后台”理论,即社会是一个大舞台,社会成员作为这个大舞台上的表演者都十分关心自己如何在众多的观众面前塑造能被人接受的形象。人们为了表演,可能会区分出前台和后台。前台是让观众看到并从中获得特定意义的表演场合,人们呈现的是能被他人和社会所接受的形象。后台是相对于前台而言的,是为前台表演做准备,掩饰在前台不能表演的东西的场合,人们会把他人和社会不能或难以接受的形象隐匿在后台[10]。依据戈夫曼的“拟剧论”,网络社会人际交往场域的“缺场性”使得交往主体由“前台”转向“后台”,把网络社会视为一个前台,现实社会当作一个后台。
通过选择性地开放自我信息来适应环境、通过给他人留下期望印象,来积极影响他人[11]。在“前台”,交往主体借助文字和符号包装自己并极力表演以获得最大化的自我呈现,隐匿“后台”真实的行为举止、面部表情都转换成了电子化的数字符号。各种各样的电子化符号不仅构成了人际交往的必不可少的中介,而且构成了人际交往的对象,主体与陌生人之间的交往成为电子符号间的输入、输出,仅仅依靠由电子符号拼凑成的碎片化信息致使人际交往中的情感、特征等丧失,消解了交往中的主体性,最终导致交往情感的淡漠。正如戈夫曼所说,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就是在表演自己,但并非表现真实的自己,而是表现伪装的自己,好像戴上了一个面具隐匿真实的自己。一旦下线,交往双方各自回到“后台”,对于“前台”并没有过多的情感。
(二)网际失信成本的降低
现实社会的人际交往由于人情面子、伦理道德、社会舆论等顾虑,以及“惩诫性权力”对身体造成的伤害[12],因此,在人际交往会遵循社会道德规范、恪守自己应有的权利和义务并诚信待人,尽可能的保持其言语的真实性以维持稳定的交往关系,一旦失信于人或者逾越社会规范,必然会破坏交往关系,甚至会让交往主体无法立足现有的社会地位以及付出更加严重的社会代价。
“多亏可以随时改换的假名,人们可以玩面具游戏,玩不同身份的游戏了,人们可以不必亲自来到而又能到场,能看到而又不会被看到,能假扮成另一个人走入未知世界,而又不冒任何危险[13]”。现实社会中的行为和道德规范在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虚拟化网络交往空间中的约束力大大弱化,交往主体可以无所顾忌的表达自我,根本不用担忧任何语言等带来的惩戒。此外,当一次交往关系结束,双方回归到各自所属的现实社会,并不会影响现实社会人际交往。当主体再次回到网络社会,原来的交往对象也不一定遇到,即便遇到了是否建立交往关系也由自己决定,将网络社会的人际交往当作是陌生人之间的一场游戏活动,难以建立信任关系。
(三)角色扮演下补偿性获得感的上升
现实社会的人际交往多以血缘、地缘关系为基础建立的交往关系,交往主体之间对彼此的身份和角色都有一定的了解,每种角色和身份所蕴含的权利和义务也是明确的。主体建立人际交往关系时也会恪守所属的身份和地位等标签,遵守自己的权利和义务。这些极大地束缚了个体的内心,限制了人际交往。因此,每个人心中存着自己的向往的角色,尽可能的尝试着扮演在生活中无法实现的角色,补偿自己无法实现的内心期待。
然而,这些熟悉的特征、所属的身份地位等在网络社会中消失殆尽,呈现在主体面前的五花八门的文字符号和经过刻意包装的信息,隔离了交往双方的真实的身份角色。同时,没有了社会约束和现实性的惩罚,个体更加自由尝试扮演与现实社会中不同的角色,甚至是一直都想尝试的但是却被压抑的角色,以补偿和体验个体在现实社会中失去的,寻求心里上的满足感和归属感,获得一种补偿性的快乐和成功。例如,在网络社会交往中,某些男子以美丽女子作为自己的头像,并热衷于探讨关于女性的话题,以满足对于女性身份的期待和对于美好事物的渴求,从而获得一种补偿性的满足和快乐。
四、构建良性网络社交关系的路径
倡导道德文明的网络人际交往,探索多维度的健康交往范式,以规避虚拟社交带来的个体失落问题,是构建良性社交关系过程中待需解决的重要议题。
(一)社会层面
个体嵌构于整体之中,个体的行为也应与社会整体的良性运行相协调,两者之间的调适不仅需要道德等维度的软约束,而且还需要法律等维度的硬规训。由于网络“虚拟”社交中的感情淡漠、角色失真、失信等现象导致的交往主体失落心态待需社会之力进行修复。在网络交往中的道德建构层面上,增强社会协同与舆论软引导的有机统一,倡导网络交往文明化、真实化。通过各种社交载体以生活化、具体化的社交案例进行网络交往中的道德宣传教育,促使网络交往主体认识到去道德化的人际交往行为的风险以及危害,进而建构出能够引起社交主体情感共鸣的网络道德范式。
在网络社交规训层面上,明确网络交往规范,着力健全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虚拟网络社交法规以及运作机制以引导网络交往主体进行良性社交活动,净化网络交往环境。具体而言,可加强诸如微博、微信等网络社交平台网络的监管。因为该类社交平台的社交主体准入门槛较低,且缺乏具体的实名制认证、注册等约定,导致该类社交平台的交往主体角色建构随意性和虚拟性较大,交往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因素相对难以管控。倡导网络社交实名制,制定网络交往文明公约以及相关法律法规,方能让网络行为有法可依,从网络社交规训层面上营造一个健康的网络环境。
(二)个体层面
培育网络社交过程中的缺场信任意识,树立正确社交价值导向。真诚友好是网络社交主体进行交往的基本态度,也是弘扬社会主义主旋律的基本要求。网络交往场域中有关陌生人之间的人际互动之所以存在信任缺失等现象,是因为匿名的网络环境中交往主体的身体与身份分离造成的真实意识根基不稳,网络社交主体间的交流缺少了现实社会社交中的相关确定性要素,导致网络中的社交具有先天性的信任劣势,加之网络社交欺骗现象层次不穷,进一步消解了交往主体间的信任度。所以,每个交往主体建构缺场性的信任意识以及正确的社交观,方能治愈交往主体的失落心理。
拓展线下社交空间,规避网络失信。网络社交主体要注重现实交往场域,拓展现实人际关系,开展面对面性质的身体在场性交往。在现实场域中的人际互动主要基于血缘、地缘、业缘等要素下展开的交际活动,去除了网络场域的交往媒介,其真实性能够通过个体在交往过程中多种感官的感知获得,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主体间的虚假呈现,获得真诚情感交流的机会以及情感支持的可能性大大增加。由于网络社交中人际关系的虚拟属性,导致交往主体间的真实身份有待证明,而交往主体的人格呈现也极具选择性,难以做到人格的全部坦露,导致互动双方信任淡化。交往个体要主动规避网络社交中的失信惯习以及交往过程中虚拟与现实的心理落差对现实交往范式的影响,淡化网络社交中的人际关系的依赖,逐渐回归到现实社会交往场域。
五、结语
相对于现实社会,网络社会的交往空间更具开放性、交往对象和过程更具随机性以及交往的去社会性,使得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主控中心。个体摆脱来自现实社会的角色身份和交往规则的束缚,以便获得及时性快乐和补偿性的成就感。这种陌生人间的浅层化互动所呈现出的狂欢式的假面舞会,其背后却蕴含了诸如信任弱化、感情疏淡等社交“失落”问题,致使交往主体间难以维持长久稳定的深度交往关系。化解陌生人范畴下的网络虚拟人际交往中涌现出的社交失落危机,要有别于现实社会人际交往问题的解决范式。对于网络虚拟社交失落等问题的规范既要需要社会层面的支持,又要需要个体层面的落实,既要道德等维度的软约束,还需要法律等维度的硬规训,以更好的规避网络人际交往的“失落”,共同构建和谐有序的网络交往生态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