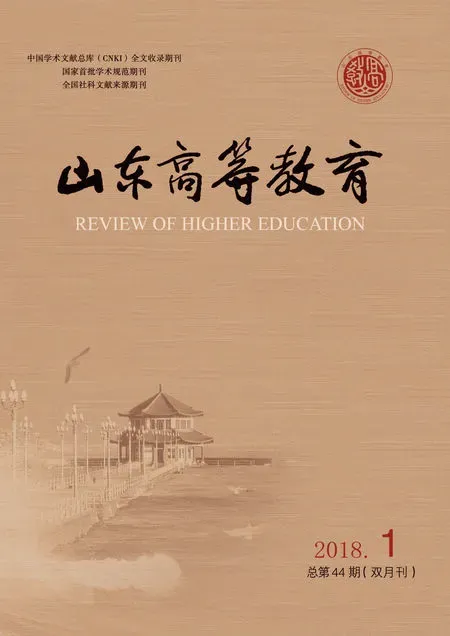史实之真 史识之新
——评《蔡元培与民国青岛教育研究》的学术特色
马斗成
新时期以来,蔡元培研究伴随着“民国诸子热”可谓风生水起,其中确有值得推崇的学术佳作,但也存在着“繁荣中的贫乏”现象,有筋骨、有温度的精品力作不多。为纪念蔡元培先生诞辰150周年,回应读者期待,青岛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翟广顺新近推出的《蔡元培与民国青岛教育研究》,以求真与致用为宗,挣脱名人范式的定性规约,别开蔡元培研究之生面,为阐释蔡元培的教育思想提供了一个立体多维的真实图像。
其一,转换蔡元培研究范式,于会通和合中唤起名人研究的地方记忆。
翟著《蔡元培与民国青岛教育研究》之所以引起读者的兴趣,即在于将天下、国家、民族之宏观话语,与青岛区域教育的微型景观“耦合”起来,大大扩充和延伸了蔡元培教育思想的空间。在凸显蔡元培对青岛高等教育的贡献时,翟著下沉了研究视线,发现了蔡氏高教思想之外的许多值得挖掘和深研的领域。例如:蔡元培对青岛银行家姚仲拔“移教就蒙”法的推介,其实包含着深刻的义务教育思想;蔡元培在胶济铁路中学的演讲,尤其是关于中学课程的分类,集中地反映了课程建设思想;蔡元培对青岛李村师范班未成行的访问和日记中的“只有工具,不能成器,必须自寻条件,自出花样”的演讲提纲,是对乡村简易师范教育最真切的期望。此外,蔡元培对青岛农林生产技术教育、民众教育与乡村建设,以及对青岛学校美育、海洋科普教育、图书文博事业,都有具体的指导意见。正是这一有别于名人写作规约的区域视角,让读者发现了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蔡元培。
翟著的研究范式有助于诠释“人与城市”和“城市与教育”的互动规律。人与环境作为一个相互影响的统一体,是任何版本的教育学绕不过去的问题,而真正将这一原理充分运用到教育科学研究领域,则非易事。事实上,北京大学的蔡元培与南京大学院时期的蔡元培相去甚远,旅寓青岛的蔡元培也绝不是晚年偏居香港的蔡元培。作为“蔡总长”的蔡元培,抑或作为“蔡校长”的蔡元培,或者作为“蔡院长”的蔡元培,都不是那个众所周知的“先生蔡”。当蔡元培从激荡的政治生活中退却下来,晚年蔡元培确有从中心向边缘、从经典向世俗的转变。早有论者指出:国内蔡元培研究对早年握有权柄的蔡元培写得多,而对晚年昌明学术的蔡元培着墨不够,学界热衷的往往是被定义为“教育家之教育家”的蔡元培,是那轮高悬于中国近现代教育史天幕上的明月,名人范式的定性规约固化乃至僵化了蔡元培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说,翟著的研究范式不仅是蔡元培研究的再出发,而且为“民国诸子”的重写带来了曙色熹微。
其二,丰富蔡元培研究思路,在区域历史库藏中深探名人文化足迹。
史贵求真,这个治史的基本原则成为读者指摘有关蔡元培研究论而不周、述而不全的把柄。名人研究往往容易遮蔽史实。透彻而确当地呈现一个历史人物,尤其像蔡元培这种无人不知的民国名人,史料的丰厚和真实是征服读者的关键。翟著首先在文献上下了深工夫,这使一些既往的定论得到了修正。例如:蔡元培力挺国立青岛大学的建立并非初衷之意,而是在“大学区”试验失败、国立和省立大学规划碰壁、大学院改组教育部、蔡元培在“权力真空”下的擘画。蔡元培通过吴稚晖为国立青岛大学争取经费的意图,正中蒋介石要蔡元培舍弃教育、改任监察院长的图谋,蔡元培虽保持了一介知识精英的骨气,却造成青岛大学顶着国立之名实则夹缝中生存的后患,杨振声、赵太侔两任校长先后辞职,经费拮据是主因。翟著不是将结论前置于史料,而是通过呈现某一现象发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真相,将其中盘根错节的各种事件加以系统、客观地研究,让读者寻求答案。事实上,蔡元培声冠士林的大名和对中国教育的杰出贡献,不是他以先知的面貌站在历史高点发号施令,而是主动适应社会实际、主动调整思路后的积极作为。
翟著之所以给蔡元培研究以青岛视角,不是出于单纯的主观愿望,而是基于丰赡的文献考证,源于作者对蔡元培著作、文章、日记、书信、演讲及媒体关于蔡元培的报道、谈话的淘洗,独具慧眼地发现了蔡元培留驻青岛的足迹。或许是出于岛城本土学者的学术自觉,作者对青岛的教育史籍烂熟于心,不仅包括已经刊布的史料,而且大量的非正式出版物和历史档案,作者都进行了必要的搜罗、鉴别和取舍,从精神渊源、历史选择、实践蕴化等层面,富有说服力地阐释了蔡元培包括大学思想、义务教育、师范教育、海洋科普教育等思想生成的根据。翟著考证精详,所呈现的千余条征引出自几百部(册)相关著述,字里行间投射出对蔡元培著作及蔡元培研究史料的搜集、鉴别、整理之功。
其三,增进读者的阅读快感,赋新思于旧事中促进名人研究深接地气。
许多研究成果不被满意,是因为读者没有阅读的获得感。当“泰斗”和“楷模”被奉为评价蔡元培的圭臬,研究者往往从先验的认识出发,免不了从概念到概念的写作路径,可读性受到影响。读者对《蔡元培与民国青岛教育研究》的好感,乃因为翟著用力对蔡元培的教育思想作出了富有历史厚度、思想深度和实践力度的展现。细读翟著,其中确有跌宕起伏的历史风云和大起大落的人生悲喜,如蔡元培在青岛探望抱病养疾的汪精卫,蔡元培为营救范文澜从青岛发给蒋介石的电文;但更多的是平淡无奇的历史写真,如蔡元培为浮山“朝阳庵”道士曾明本题写的楹联,曾明本在蔡元培逝世前不久发来的“月前仰观天象,见恶星虽仍猖獗,但东亚已现曙光,亟应恢复和平”的信函;包括蔡夫人在青岛的作画和蔡元培的题诗,以及沈鸿烈与蔡元培一家的欢宴、蔡元培由袁荣叟及如夫人陪同的崂山之游,都成为展示蔡元培君子风度的有效史料。作者善于对日常维度中琐屑平淡事物的着力关注,书中所引征和呈现的历史事件多不是蔡元培研究的热点和学界的兴趣点,看似信手拈来的故事,却在温情与敬意中既致力于人物思想的提纯与升华,又展示了教育史生动鲜活的学科特点。
这很能使人联想到作者近几年连续出版的几部青岛历史文化名人系列论著,旅寓青岛的作家群和学者群体是以群像的体例再现地方名人的魅力,而此前的《卫礼贤与近代青岛新式学校教育研究》及本书,则以鸿篇巨制分别昭示了两位大家独立的名人精神和学术个性,作者的贡献不仅是名人传记创作的新收获,也为地方教育史乘拓宽了时代视角。正如美国蔡元培研究专家W.J.戴维斯所言,社会变化是通过在保存那些过去的价值观念的同时,逐渐适应新思想来实现的。《蔡元培与民国青岛教育研究》及翟著的名人系列丛书,绝不是无关时代痛痒的缅怀之作,因为蔡元培的教育思想惠及当今而远未过时,对于蔡元培留下深深足迹的青岛来说,同样需要蔡元培教育思想的再引领。历史研究是一条艰辛之路、智慧之路,靠的不仅是常人难以体察的艰辛劳作,更重要的是坚持以历史分析为起点,在此基础上建立逻辑分析的理路,展示历史和思想本身的连续性。读者往往赞佩翟著的淘洗与锤炼之功,作者的话题资源往往通过个体丰富的人生阅历,培植出宽阔的学术视野,体现出一种难得的精心与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