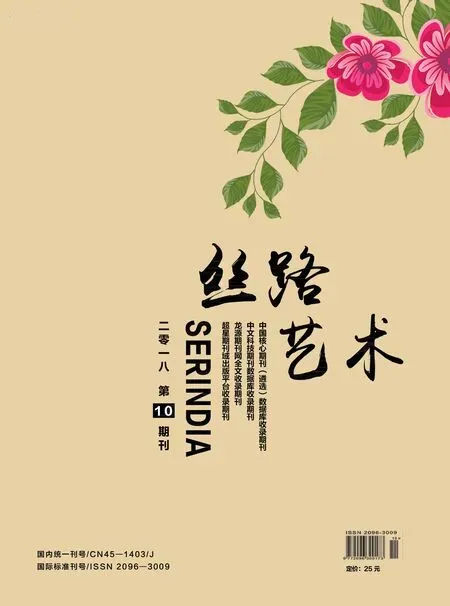浅析道家思想对霍去病墓石刻艺术风格形成的影响
史秀海(苏州大学艺术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0)
相较于造型逼真、手法写实的秦兵马俑,霍去病墓石刻在造型特点上有其独到之处:第一,寻石而刻,多利用原石自然形象,采取细部雕琢,以少胜多的手段进行创作;第二,多采用圆雕、浮雕和线刻的雕刻方法,力求简约、朴拙;第三,都以动物为题材,多以动物寓意,不仅还原了霍去病生前活动的祁连山一带的自然环境,还通过借用动物形象来象征将士及其戍边战斗的生活。这就使得霍去病墓石刻呈现出一种大气简练、浑然天成、充满了浪漫主义特色的大写意风格。
许多学者都认为霍去病墓石刻之所以形成这样一种独特的造型艺术特点和大写意的风格,是因为当时生产工具的落后造成,且霍去病墓石刻所用的石材都是较硬的花岗岩,所以无法做出秦兵马俑一样的写实作品。
对于这种观点,笔者认为是存在疑问的。首先,霍去病墓石刻中有两块石刻题记:“左司空”及“平原乐陵宿伯牙霍巨益”。据考证,“左司空”是当时皇家御用的雕刻专门机构,而后者极有可能是制作这批石刻的工匠署名。而且,西汉上层官僚有斥巨资吸纳社会上拥有特殊技艺的手工艺人,为己专用的现象,可想而知,“左司空”所吸纳的石刻工匠,其工艺水平在当时应是上乘。而且,隆丧厚葬,是西汉帝王的经国大事,霍去病是汉武帝的宠臣,是出击匈奴有功的大将,按照西汉流行的厚葬风俗,皇家的墓葬要求加上技艺精湛的匠师,不该出现不够写实的“粗制滥造”现象的。而就生产工具落后这一说法,笔者认为也是不够充分的:西汉时期,“百炼钢”的锻造技术兴起,使钢的质量大为提高;汉武帝时期,盐铁收归官办,也使得冶铁业空前发展。炼钢冶铁技术的进步也必然会促进雕刻所用的刀、斧、凿、锤等工具的发展。
所以笔者认为,霍去病墓石刻大写意的风格并非是受工具等因素限制不得已而形成,相反,我认为,这是由汉代的社会的审美意识所决定的,是汉人的艺术追求乃至是精神追求。而这一论据的立足点,便是道家思想的影响。
从反抗暴秦到楚汉争霸,多年的战争使得西汉刚建立的时候不得不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而道家学派的“无为而治”思想正好适合当时的社会,所以,黄老之学在汉初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从这批石刻自身来说,从选材便是按照道家思想中的“道法自然”,取材于自然形成的花岗岩,循道而行,顺其自然;而其制作过程亦遵循道家思想——“天人合一”,这也是霍去病墓石刻最可贵之处,即注重借意于石材的原貌,尽量少用人工雕凿,采用细部雕琢,以少胜多的手段;通过圆雕、浮雕、线刻手法,对自然物进行描摹,但这并不是对自然的专意摹求,而是对自然的尊重,力求简约、拙朴,这正是道家思想中所提倡的“自然无为”,是自然与人和谐的哲学思想观的体现。
汉武帝时期霍去病墓的石刻与陵墓环境的设置有着独到之处。石刻立马、卧马、跃马、卧虎等作品的设置,以及以陵为山的造型,使陵墓环境中营造出一种人与自然融合的艺术气氛,成为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的具体体现。这种哲学思想正是道家学派的观点。
而根据苏州大学博士生导师张朋川教授的研究发现,这批石刻中的“马踏匈奴”和“跃马”两件作品,是放置在墓冢前,而“卧马”却单独放置在墓冢正后方。这样独特的位置设计有其特殊的目的和含义,张朋川教授给出的解释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所谓的“南山”,即霍去病生前活动过的祁连山,这种称谓在汉代早已流行,见于班固所撰写的《汉书·西域传》:“西域南北有大山,其南山东出金城,与汉南山属。”霍去病率领汉军在祁连山大破匈奴,使得匈奴不再敢进犯漠南,使得汉王朝取得了长久的安宁,为了彰显霍去病这一伟大功绩,所以将“马踏匈奴”和“跃马”两件作品放置在其墓冢前。而汉王朝对匈奴的连年征战也造成了国家疲敝,府库空竭,百事废弛,统治者和百姓都渴望尽早结束战事,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故而将“卧马”单独放置在墓冢正后方。可见,道家的“无为而治”,在霍去病大破匈奴之后再次受到统治者关注,休养生息,成为当时最为重要的社会状态。
所以说,从西汉刚建立时的“无为而治”,休养生息,到后来的文景之治,以及汉武帝初期,黄老之学一直是西汉王朝的正统思想。汉代人所推崇的黄老之学,主张无为而治的哲学思想,使得西汉的艺术也体现出一种简约、质朴、自然、古拙的审美观,这对霍去病墓石刻独特的造型特点、质朴的风格特征形成起到至关重要的内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