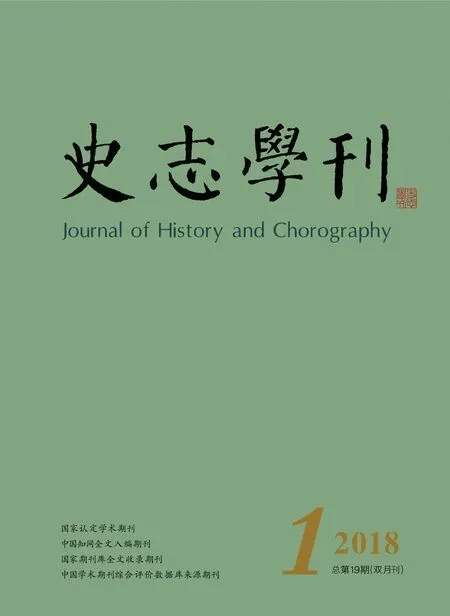“修志问道”与方志编纂思维更新
吉 祥
(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南京210004)
2017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地方志第一次被正式列入国家重大文化国策之中。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近年也先后对地方志作了两次重要批示,在2014年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的批示中,称“地方志是传承中华文明、发掘历史智慧的重要载体”,提出“修志问道,以启未来”。2015年在对全国地方志系统先进模范座谈会的批示中,提出了“直笔著信史,彰善引风气,为当代提供资政辅治之参考,为后世留下堪存堪鉴之记述”的要求。这两次重要批示传递了很多重要的新理念,“发掘历史智慧”“修志问道”“彰善引风气”“堪存堪鉴”等提法,较之以往地方志功能“资政、教化、存史”的表述有明显的不同,更加强调了地方志“文以载道”,掌握社会的发展规律,总结历史经验智慧,引领社会风气的作用。与这样的理念对照,现有的地方志存在明显的差距。30多年来,在“横排竖写”“述而不作”等体例规范下所形成的志书,更多的是外在体例形式上像志书,注重科学分类,而在内容上则显得相对平庸,没有体现出足够的独到价值;志书贯彻了“述而不作”的资料性文献要求,表象事实罗列有余,深度历史分析缺乏,只看到表象性的“是什么”,看不到历史发生的“为什么”,无法给人以真正的思想启迪;志书记载了组织机构及工作开展和制度的变化,而很少看到人的创造、人的思想、人的价值,基本看不出志书直接传递的历史智慧;“生不立传”带来创造当代历史的当代人在志书中很难见到踪影,而已故人物的活动以及传递的精神与当代精神风尚形成一定脱节;很多志书真正用心探寻和反映地方发展之道明显不足。
目前,地方志系统所开展的地方志资源开发利用,是对已出版的地方志(志书、年鉴)进行二次资源化开发利用。这种事后的以功能开发为首位的资源开发利用固然重要,但也提醒我们,为什么不能将“问道”的意识和方志利用的观念直接前置植入地方志的编纂过程中?因此,地方志编纂有必要随着新理念而作相应的改变。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和书写方式并不是单一的,有什么样的编纂思维就会有什么样的书写方式,也就会呈现什么样的功能价值。“述而不作”是志书的一种编纂模式,“问道”式的地方志同样也会是一种新的编纂思维形式。这一切取决于我们自身对地方志书新的功用定位和体例规定,新的范式就有可能从理念变为现实。
一、“修志问道”需要以地情研究为前提
过去的地方志工作把编修一部省、市、县三级志书作为主体。2015年9月3日国务院办公厅颁发《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中最新提出了六个基本原则(坚持正确方向、坚持依法治志、坚持全面发展、坚持改革创新、坚持质量第一、坚持修志为用)和11项主要任务,首次提出地方志工作要修用并举,并在“提高地方志资源开发利用水平”中还专门提出要“培育地方历史记忆”,进行地域研究(或地情研究、地方发展研究)的内容。过去一直只是把地方志看作为资政决策、社科研究、新闻写作、文学影视创作等提供基本资料素材,而没有意识到地方志工作者自身所直接进行的“问道”式的地方发展研究或地情研究。
从各地的编修实践尤其是二轮修志实践来看,由于地方志编修走的是通过政府行政手段众手成志而不是专家修志的方式,资料征集和初稿工作基本是在承编志书的基层和各职能部门进行,地方志专业部门并没有直接参与第一手资料的征集,所以方志部门所掌握的基本是经过基层承编单位非专业处理后的二手资料,专业地方志工作者所做的基本是体例和行文规范方面的技术性生产,而不是内容生产。地方志专业工作部门担负的是编辑角色,而没有承担第一手资料征集和研究的职能,这导致了专业方志工作者对地情研究的弱化。
地方志的编修过程本质上是“现实(地方发展或地情)—文本(方志编纂)—现实(方志利用和服务于现实)”或“地方(发展)—地方志—地方(发展)”的过程。地方志其实是对地方发展的文本记录和投射,是记录历史的人对创造历史的人的记录。地方志要强化“问道”功能,就必须从“地方志”研究回到“地方”研究的本体上去。地方志应该是建立在地方如何发展的地情研究基础上的自然产物,而不是相反。恰恰是由于目前地方志系统把重心停留在“编辑”上的定位问题,导致了地方志部门对“问道”地方发展的功能较差。所以,地方志要加强对地方发展决策咨询作用,必须要把工作重心从基于他人二手资料基础上的“编辑”,向前延伸到对地方发展基础资料的把握和地方发展路径的研究上来,应当要把志书看作是整个地方志工作的中端而不是终端。
目前,地方志部门强调的地方志理论研究,更多的是方志界业内关于编纂记述的技术性研究,而不是社会层面对地方志所期待的地方研究。方志工作者相当多的是将自己定位为方志行业内的“编修者”而不是社会角色意义上的地情研究者或使用者。相对于地方研究,地方志编纂研究在社会看来实在是微不足道和缺乏意义的。
方志界有人提出,地方志不仅要成为“知库”还要成为“智库”[1]洪民荣.地方志:既是“知库”,也应成为“智库”.解放日报,2017-07-18.。这个愿景很美好,但客观地说,很多方志工作者由于没有对地情进行过深入的研究,自身缺乏提出现实发展对策的能力,自然也就谈不上贡献什么“智”。在这方面,淮安市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荀德麟,对地情是有深入研究的,同样他从地情研究中生发出淮安地方发展的战略,先后提出了“三淮一体”和“运河之都”名片打造地方发展的战略,像他这样打铁还须自身硬的人,在地方志系统其实是不多的。如果我们用放大一些的社会眼光来看大方志,其实每个地方都应该有一批研究地情、参与地方志编纂并能提出地方发展之道的智者(智囊)。
二、地方志“问道”的重心是揭示地方发展之道
地方是一个相对于国家和中央而言的概念范畴。地方志不是国志、国史,而是地方的历史文献记录。而从改革开放的实践来看,很多探索是从地方发起的,地方志要把从本地实际出发所进行的新发展、新创造、新探索、新路径重点进行记述,尤其是地方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更是与地方发展之道息息相关。这样编纂的志书,才真正对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有启发借鉴意义。
我们以对应二轮修志断限的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为例,以往的表述基本上是一场由执政党和中央政府所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改什么、如何改由中央政府说了算,任何下级政府及企业、个人如果没有获得上级政府的授权,是不能自发进行制度创新的[1]杨瑞龙.昆山带给我们的启示.中国改革,2002,(7).。由于原先计划经济体制的特征是权力高度集中于上层,要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则意味着自我革命,事实上要突破自我的局限性往往是很困难的,因此,改革开放的最初历史发生路径往往并不是自上而下式的,而恰恰是呈现为从体制外部冲击体制内部(或是以对外开放拉动对内改革)、体制内部地方和民间底层的“以下犯上”和“自下而上”的制度突破。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就是一个改革开放“自下而上”成功突破的典型案例[2]吉祥,徐秋明.书写可理解的历史:历史发生与指数编纂的理念——以昆山经济开发区及指数为样本的案例分析.第二届中国地方志学术年会“第二轮市县志编纂及其理论问题”会议材料,2012.。1984年,邓小平视察南方三个特区,国务院增设特区办公室,全国出现第一批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央扩大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决策,为昆山的决策者们打开了思路。昆山人大着胆子仿照沿海开放城市创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做法,自费开发建立工业新区(1988年6月更名为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在自费开发过程中,他们突破开发区一没上级批准、二没资金来源、三没有任何优惠政策,白手起家的重重困难,发扬率先创业、率先开放、率先改革、率先发展的精神,大胆闯、大胆试、大胆干,勇于实践、敢为人先,在全国、全省创造了众多第一,昆山开发区的综合经济实力位居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前列。昆山建设自费开发区是改革开放中一个比较突出的自下而上实现制度突破的案例,成为向全国推广建立开发区的一个重要模式,对全国的外向型经济发展之路提供了一个样本。
再以《中国名镇志文化工程》为例,这套丛书的定位不应该只是各名镇的名片性质的社会普及性宣传书,还应当承担这些名镇在中国农村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发展方式、发展模式的示范启迪作用。以这套丛书中的《周庄镇志》[3]中国名镇志文化工程·周庄镇志.方志出版社,2016.为例,我们反复思索周庄镇在全国历史文化名镇以及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何在,为此在《周庄镇志》中设置了周庄古镇保护模式、周庄旅游开发模式,把周庄放在江南水乡的地域背景下横向考察,揭示周庄模式的发生路径、特点特征以及所产生的全国性、全球性的示范推广意义及其价值所在。再以这套丛书的《巴城镇志》为例,我们同样设置了专题调研报告《巴城:现代农业模式的新型城镇化样本》,我在该报告中,总结了该镇农村空间布局中的新型社区化、农村经济管理模式中的新型集体化、产业化经营的现代都市农业模式等特征,将巴城镇放在昆山市基本现代化的整体布局中,揭示巴城镇融生态、生活、生产的现代化“三生农业”在基本现代化中的位置,指出其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的结合对未来中国农村发展的路径所具有的重要启发意义。志书中这种对地方发展之道的探索,就是典型和直接的“修志问道”。
三、从“述而不作”到分析性记述
要发挥志书“问道”的功用,必须要改变“述而不作”的历史编纂书写方式,加强深层化“分析性记述”的方法运用。所谓分析性记述,并不是空发议论,而是基于历史事实、历史数据,对事实发生的源头起因、动因做客观的记述,对社会现象作结构性的分析,并将产生的后续影响作关联性的记述。对历史记述要赋予历史的洞察力、思辨力,客观合理地分析。这样书写的历史才是可理解的历史。
从首轮新方志编修开始,“述而不作”就是地方志编修的一条基本原则。“述而不作”出自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言说,其本义是遵循圣人之道而不改创,这种著述理念源于古人原道、征圣、宗经思想[1]郭明浩,万敥.“述而不作”与中国阐述学建构.云南社会科学,2012,(6).。清代章学诚对“述而不作”思想进行阐发时曾经说道:“文士撰文,唯恐不自己出;史家之文,唯恐出之于己,其大本先不同也。史体述而不造,史文而出于己,是为言之无征,无征且不信于后也。”[2]章学诚.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联系到章学诚的“志乃信史”“文人不可与修志”的言论,可以看出,章学诚对“述而不作”的理解主要表现在学术撰著与文学创作的区别上,史志撰著中的“述”必须都应该有历史依据而不能凭空改创。与撰史相反,文学创作则不能守旧僵化,蹈袭前人,而应提倡创新。作为方志学的鼻祖,章学诚的这种理论并没有错,但是“述而不作”的学术原则到了新方志编纂过程中则被广泛解释为志书只需要客观记述而不加以分析评论。这种对“述而不作”的阐释相当程度上已经背离了这句话的本初意义。
历史事实是不可以凭空杜撰的,不论是中国还是西方,一直都有以叙述事实为主的史书范式和风格。从文化观念史的角度考察,“述而不作”的传统在中国社会有着特定的背景。中国的传统政治生态环境是一种中央高度集权的政治专制制度,它所生成的是维护统治者的专制文化思想,专制思想对社会个体独立精神的扼杀,使整个社会的思想精神出现萎顿状态。因此独立精神人格的史家在记载历史真相时需要冒着生命风险。早期的史家出现了司马迁受宫刑及史官被杀的情形,后来进而演化出大多数文人的精神自宫,这种状况在清代文字狱发生后尤为明显。由于志书记述内容的当代性,加上修志是一项政府行为,需要体现政府的意志,保持与统治者的思想精神的一致性,这些局限性导致了志书对当代的隐讳,社会的潜规则很多时候是可以做而不可以说,或者是需要婉转、隐晦地说而不能直截了当、开门见山地说,凡是“当代”性质的史书只写事实不作分析评论的比比皆是,因此“述而不作”其实并不只是修志的一个准则或文化现象,而是整个传统史学的一个共同文化现象。
与中国的考据史学传统相近,西方近代史上也曾经存在德国兰克学派。兰克学派的史学基本思想是追求纯粹客观的历史,认为史学写作的目的在于复原历史,要达此目的,最重要的是找到原始资料,用史料说话,不偏不倚、如实客观地再现历史的真实性,因此这个学派极其重视原始资料的利用和考辨。但是这种史学思想由于过分注重对事实的描述,排斥了概括、解释和理论,忽视历史学家主体意识的作用,后来受到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的现代史学的批判和抛弃,新的史学不再是纯粹的客观叙述,而是出现了分析性的史学范式,历史学要求必须体现对历史的阐释能力。
而在中国,史书也从来就不只是“述而不作”的客观事实叙述,同时也存在着对历史的认知。翻检中国历史上的旧方志,也从来就不是只有记“是什么”和“不作”的单一记述模式,同样也有分析评论的志书,很多方志学着司马迁《史记》“太史公曰”的笔法书写对历史的见解。
回过头来看首轮修志的实践,我们可以观察到,由于“述而不作”编纂思想所赋予的秉性,志书呈现了两种特征,一个特征是“述”的浅层化、表象化,只写了“是什么”,根本看不出“为什么”,人们所看到的志书几乎是没有思想生气的,只有“冷冰冰”的板着面孔书写的机械的事实,而看不到地方志丰富“正史”所应该具有的丰富表情和值得回味的历史细节,看不到编纂者在记载地方发展时所应具有的思考和价值判断,无法给人以直接的启迪。有人指称“述而不作”至少有“是非不明”“因果不彰”“规律不见”“真假难辨”等四大弊病[1]诸葛计.新方志五十年史(稿).在方志思想和理论方面的若干探讨.。地方志要赢得社会关注和共鸣,迫切需要解决这一记事原则的禁锢。另外一个特征是对“述”和“作”的片面理解,认为志书要加强著述性,但只可以在概述和无题序中作分析议论,在这种思想片面理解下,志书强调整体性的记述风格,只见森林,不见树木,在这种风格下编纂的方志渐渐失去了更加实在具体的资料存史意义。
针对志书“述而不作”的弊端,一些方志人提出了“述而有作”“述而精作”“述而略作、作必合道”等理论,并基于方志是资料性著述的理解,提出了“如果说真实性、资料性是新方志的生命,那么著述性则是方志力量和价值、是新方志活化的生命”的见解[2]胡嘉楣.加强方志著述 提高志书质量.黑龙江史志,1989,(4).。但是真正将这些理论付诸志书编修实践的极少。
2006年方志出版社出版的福建省《龙岩市志》(1988—2002)其中运用了不少分析性的记述。如该志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运行”[3]龙岩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龙岩市志(第二十编财政税务第一章财政第二节财政体制).方志出版社,2006.(P871-872)就是一个较为典型的范例,该记述不是停留在过去的只写“是什么”的事实表象层面,而是既写了事实,也对新的体制运行出现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结果效应及其社会运行中的矛盾、困难、问题作分析,其中所蕴含的为龙岩的困境鼓与呼的政策忧患色彩表露无遗。从方志编纂的角度而言,《龙岩市志》中的这一段分析性记述就是触及本质的“修志问道”之作。这种分析性记述的意义在于,展示了深度的历史,触及了地情与历史中本质性的内核。
地方志总体来说是一种记述性文体,不提倡空发议论,但采用记述体并不表明只能写“是什么”,而不能写“为什么”。恰恰是那些写为什么式的分析性记述,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历史发展的动因和历史的走向,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让历史变得可以被理解。地方志要发挥更大的人文意义和历史借鉴价值,写出“为什么”是非常必要的,尤其是第二轮修志记述的时段是中国社会结构发生大转型的时代,社会运行中的矛盾以及社会价值观念非常复杂,准确地把握这个时代就要求我们的方志编纂者必须要有基本的分析判断。分析性记述的志书写作,其意义不是单纯宏观层面的“资政”作用,而是对每个社会个体都具有普遍的启迪意义[4]吉祥.突破“述而不作”的禁锢:分析性记述范式的运用——《龙岩市志》文本分析及二轮修志理论创新的思索.江苏地方志,2008,(1).。
地方志中分析式记述方法,除了在正文中运用外,还可以通过创新体例用新的形式加以呈现,如“汇考”
“专记”“调研报告”以及链接。
四、发掘历史智慧要重视人的思想精神入志
李克强总理指出地方志要“传承中华文明,发掘历史智慧”,什么是历史智慧?智慧是升华到精神层面的东西,这种智慧有些是经验之谈,有些是独到的思想。精神层面的东西是否需要入志?如何入志?
中国古代对历史文献的记载有多种形式,早期的史官有记言和记事的分工,即《汉书·艺文志》所说的“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尚书》和《春秋》,一为记言,一为记事,言事分记。后代的史书和地方志均偏重于记事,而对记言有所弱化。在新编地方志中,普遍重视记载历史活动和物的一面,而对精神的一面除了艺文和民俗有所收录外,其余对人的精神世界很少记及。由于现代社会结构的变迁,地方志从旧志普遍重视人物传到新志普遍重视组织机构而弱化个体人物的记载,且对人物的记载多限于其业绩方面,对其主观精神世界的言论、思想主张很少记及。
在历史上,发挥历史借鉴作用最具代表性的史学著作当首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里面收录了不少治世经典之语,如“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不善者反之……”“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亲疏如一,无所不行,则人莫敢有所恃而犯之也。”“君子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正道,得志则与民由之,不得志则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诎,是之谓大丈夫。”“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且夫富者众之怨也,吾既无以教化子孙,不欲益其过而生怨。”……这些经典言论充满历史的智慧,清人王鸣盛评价《资治通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也。”历史上的很多统治者都是从中获取历史的经验教训。
这种人的思想精神和智慧在志书中不是要不要记,而是怎么记。古代的史志中,一般都是针对人物,将“言”“事”结合。浙东学派的史家强调“即器以言道”,提出道器合一,反对空言义理[1]林勤艺.章学诚之经世致用.环球人文地理(评论版),2016,(9).。在人物传中,杰出的人物可以结合其活动将其富有见解的主张言论“以事系言”“以人系言”。首轮新方志中浙江《绍兴市志》专门设置“名家学术思想卷”[2]绍兴市志(卷32名家学术思想).http://killusoftly.bokee.com/6826592.html.,每一名家介绍其主要理论观点,以一斑窥全豹,从中了解绍兴历史上学术研究的主要成果,这些名家的学术思想产生于现实生活,又直接为现实的需要服务,在中国历史上闪耀着光芒。
在我主编的《中国名镇志文化工程·湾头镇志》中,针对该镇玉器特色产业设置了“玉器滥觞”,其中又针对若干玉器工艺大师设置了“玉工匠心”,每个大师都介绍他们的业绩、创作荣誉外,还收录了他们对治玉的理解,如鉴玉大师刘月朗下有他的一段话:
人们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但我以为玉也是有价格的,无论是每公斤数十万还是数百万,都始终有谈定的价格。真正做到无价的是工艺。就像是一幅名画一样,作画的纸墨都可以价格量化,但这些廉价的工具一经大师之手,凝聚了大师的艺术结晶后,就可能成为无价之宝。张大千的画为什么能够拍卖到数千万乃至上亿的价格?不是他用的纸墨多名贵,而是他的艺术价值珍贵。同样的,玉雕就材质本身,现在也已经可以称得上名贵了,但这还不够,一块上乘的玉石只有经过大师的工艺塑造,达到艺术上的升华,才可能会真正做到流芳百世,长存不朽。所以我说应该是“金玉有价艺无价”才对。
除了人物和学术思想外,地方志中的思想智慧还可以表现在家谱家训的记载中,那些优秀的家训家风恰恰是今天社会需要弘扬光大的。
五、“问道”要重视“细节之道”
刘延东副总理在第五次全国地方志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志书“还要精益求精,不放过每一件小事,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细节里可能蕴含有一些重大的突破。当然我们还要重点突出整个历史脉络,但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些细节的东西,看起来是小的东西,也不要把他遗漏。”
仍以昆山经济开发区为例,昆山开发区的见证人宣炳龙曾对采访他的研究者这样说过:“目前研究改革开放30年的东西蛮多的,但是缺少对于艰辛历程的展示。开发区的几次重要的决策,无论是决策者、操作者、建设者,都面临不同的困境和抉择。研究中国的开发区,不研究昆山开发区肯定是个缺憾,研究昆山开发区不写出昆山开发区的特殊性也是一个缺憾。有些记者、专家来昆山采访、调查后写文章,成绩和原则好写,但缺少可资借鉴与操作的过程和细节。……今天成绩的取得,不是那么容易的,也不是总结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几条经验、几个原则就能说清楚的。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大家都做,为什么昆山行?因为昆山市经过千辛万苦的过程和千头万绪的细节做出来的。这些不讲清楚,人家当然无法学。”[1]钟永一,张树成编著.宣炳龙印象.见证中国第一个自费开发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P104-105)
从大历史的角度看,历史发展有必然性规律,但是就历史的具体发生而言,则是由很多小事件和历史细节触发的。在某种意义上,细节决定了历史最初发生的走向,引爆了大历史。同时也正是那些历史的瞬间、故事、细节,使历史变得生动起来,触发我们的情绪,产生历史的情绪共鸣。由于缺少对历史细节的记载,以往的志书显得枯燥乏味。《昆山经济开发区志》的编纂特色之一是在主体章节后附了不少历史细节特写的资料链接,如第二章自费开发中链接“一碗面做活三篇文章”“费老的关怀”“宣炳龙的三个小故事”,第五章亲商服务中链接了“亲商更要富商 富商引来万商”“优惠政策不如优质服务”“亲商实录”,第六章招商引资中链接“第一家台资企业的来历”,第十一章党群工作一体化中链接“陈慧芬和她的‘融和工作法’”。此外在若干正文中也重视细节的记载,如1992年李鹏总理在长江三角洲及长江沿江地区经济发展规划座谈会上讲话细节,江苏县级兴办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昆山中国苏旺你有限公司的艰辛过程,江苏省第一家外商独资企业成立的真实背景,全国第一个出口加工区是如何从概念的提出到花了三年跑国家8个部委突破重重困难把不可能的事办成的艰辛过程。在这些细节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昆山人在发展中踏遍千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历经千难万险谋发展的“四千四万精神”。正是这些历史细节告诉我们:昆山开发区何以能够成功。与这些细节的历史书写相关,该志还有一点值得称道的是重视口述史资料的运用,其中不少资料来自于主持开发区实际工作二十余年的开发区负责人宣炳龙的口述史资料[2]宣炳龙印象(第二编).见证中国第一个自费开发区.宣炳龙的口述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昆山经济开发区志》对昆山开发区从自费开发到创新发展的历史发展路径、发展理念以及实践的细节处理,其意义在于揭示了昆山之路是可感、可学、可借鉴、可引发思考的发展样本。
现在很多人说要“讲好中国故事”,但是很多地方志编修者长期受体例规范的影响,只知道往“里”收,用中观的笔法泛泛地记述或概述,而不知道对微观的叙事描述,不会讲故事,细节中的微妙之处揭示不出。目前,一些地方志机构开始拓展口述史影像志,而口述和影像恰恰需要若干细节和故事构建。“道”不是抽象的,地方之道就是细节之道。这种历史的细节可能恰恰是地方发展之道的独到之处。李克强总理批示中提到了历史智慧,这种历史智慧很多是人物个体在特定的历史时刻所展现的。
结语
《地方志工作条例》将志书的本质界定为“资料性文献”,笔者认为,志书的功能不仅在于分门别类地保存地方资料文献的存史功用上,还应该有更高的追求,追寻历史发生的时代精神和思想理念。
长期以来,地方志受固有的编纂理念的束缚,自我局限于编辑层面的体例规范,而没有着眼于地方发展和地情的研究,没有积极地体现出史志者的历史认知。对于地方志来说,“存史”是重要的,但并不意味着就不可以“问道”。这种基于地情研究的“问道”,体现的是对历史发展的洞察力和编纂者的价值判断,考量的是对时代和地方发展的“史识”。从某种意义上,志书最重要的编纂思想就是揭示时代和历史本身是如何思想的,时代的精神灵魂同样是志书的编纂思想灵魂。对时代和地方发展的认知体现的就是“问道”。笛卡尔曾说“我思故我在”,将这种哲学思维投射到修志过程中,同样也是修志者思考所在、问道所在及志书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