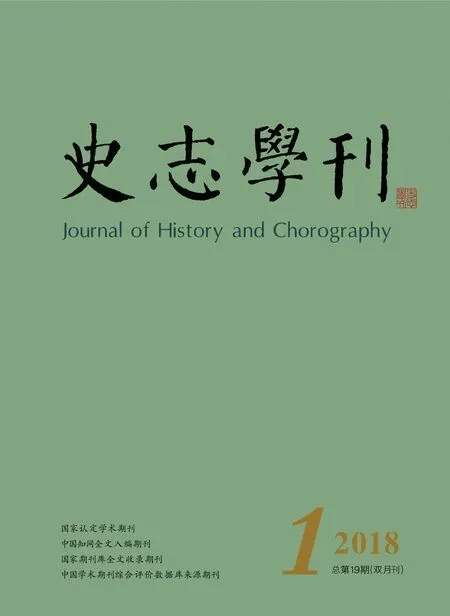辽朝礼典编修钩沉
李月新
(赤峰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内蒙古赤峰024000)
在辽朝的国家礼仪生活中,既有辽朝建立前已存在的祭山仪、柴册仪、瑟瑟仪等,又包括了王朝建立后才出现的常朝起居仪、册皇后仪、朝贺仪等,呈现出蕃汉交杂的面貌。这些在国家礼仪生活中固定化了的诸多仪式,必然是遵循着一定的文本规范。本文即以此为线索,追溯辽朝礼典编修的历程,分析其文本构成的重要特征以及其所体现的国家意志。
一、遥辇汗国时期的礼仪生活
今本《辽史·礼志》中称“遥辇胡剌可汗制祭山仪,苏可汗制瑟瑟仪,阻午可汗制柴册仪、再生仪”,“其情朴,其用俭”[1]辽史(卷 49)·礼志一.中华书局,1974.(P833)。皆出于真诚,与中原古礼相通。胡剌可汗、苏可汗皆辽之先世,《世表》称其世次不可考,但《百官志》中列遥辇九世可汗宫分时,皆有其名。阻午可汗是遥辇氏部落联盟取代大贺氏的关键人物,萧韩家奴称阻午可汗时期遥辇氏大位始定。据此可知胡剌可汗、苏可汗、阻午可汗当是遥辇氏汗国早期的几位君主。其所制祭山仪、瑟瑟仪、柴册仪、再生仪等均为契丹遥辇氏时期国家礼仪生活中的几项重要内容。
契丹的文字是在辽朝时期制定完成的。太祖神册五年(920)春正月乙丑,始制契丹大字。九月壬寅,大字成,诏颁行之[2]辽史(卷 1)·太祖纪上.中华书局,1974.(P16)。《皇子表》中称太祖弟迭剌出使回鹘,“能习其言与书,因制契丹小字,数少而该贯”。契丹大小字成之后,与汉字一同在辽朝境内流通使用。由此可知,契丹遥辇汗国时代,契丹人是没有本民族文字的。同时契丹人使用的语言与中原汉人不同,阿保机曾与后唐使者姚坤说:“吾解汉语,历口不敢言,惧部人效我”[3]旧五代史(卷 137)·契丹传.中华书局,1976.(P1831)。从中可以探知契丹人中能言汉语者应该是极少数。因此,可以推知,遥辇汗国时期契丹国家的礼仪并没有较为完整的文本形式,他们的传承方式应当是口耳相传。从契丹部族时代的具体情况来看,承担这种传承任务的人应当就是“巫”。巫操控着汗国时期全部的礼仪活动,掌握着仪式中各个环节。他们既是仪式活动的组织者、参与者、传承者,同时也是当时汗国政治生活的领导者之一。这样,契丹传统的仪式就极具时代感,能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化增加或删减内容,达到为政治服务的目的。
换言之,即契丹国家的礼仪活动由来已久,但是形成文本的礼典的编修确是在辽朝建立之后。且在王朝时期编修礼典的过程中,不仅保留了遥辇汗国时期的礼仪,还通过对传统的国家礼仪的文本整理,使其内容和形式在辽朝时期得到丰富和发展。
二、辽太祖时期的礼典编修
遥辇汗国时期的国家礼仪在阿保机取代遥辇自立的时期仍在延续使用。907年,阿保机取代遥辇,燔柴告天,即皇帝位,仍然采用的是汗国时期的国家礼仪形式。并明确规定皇族承遥辇九帐为第十帐,即证明此次仅是汗位易姓,并不是国家性质的改变。巫仍是国家礼仪生活中的重要主持者,甚至阿保机本人也充当巫的角色。但是在随后发生的“诸弟之乱”中,大巫神速姑的倒戈使阿保机认识到不应放任传统巫职对国家权力的干预。但是阿保机即位初期的契丹国家,“制度未讲,国用未充,扈从未备”[1]辽史(卷 73)·耶律曷鲁传.中华书局,1974.(P1221)。于是为了解决当时最首要的问题,阿保机创置“腹心部”,充扈卫,强化军事力量。随后,在阿保机及其臣僚的努力经营之下,逐步使“畜牧益滋,民用富庶”。在基本奠定版图的基础上,有意识淡化巫职力量,耶律曷鲁等“乃请制朝仪”,即开始国家礼仪制度方面的建设,以此摆脱神职对权力顶层的干预。
在契丹国家制度建设伊始,汉官集团的作用就已经开始凸显。这部分人大多拥有中原文化背景,熟悉封建国家礼法制度,他们是将中原封建文化引入契丹国家体制之中的具体执行者。如曾经“共劝太祖不受代”[2]资治通鉴(卷 266)·后梁纪一.太祖开平元年(公元 907年)条.引赵志忠.虏廷杂记.中华书局,1956.(P8678)的韩知古,《辽史》本传记,(韩知古)“总知汉儿司事,兼主诸国礼仪。时仪法疏阔,知古援据故典,参酌国俗,与汉仪杂就至,使国人易知而行。”汉儿司设于太祖初年,是辽朝最早设置的汉人事务最高管理机构。当时一部分在辽初得到契丹统治者信任的汉人,首先被任用为管理汉人事务的政府官员。据此可知,韩知古就是在这一时期总知汉儿司事,辅佐太祖管理汉人群体。由于其兼主管诸国礼仪,也就是说,韩知古时期即已开始了整理契丹固有国家礼仪,兼之引进中原唐及五代礼仪的工作。
太祖七年(913)十一月,“祠木叶山。还次昭乌山,省风俗,见高年,议朝政,定吉凶仪。”[3]辽史(卷 1)·太祖纪上.中华书局,1974.(P8)这是有关辽朝礼典修订的第一次记载。从简略的记载中可知,这次修订的内容仅以吉凶二仪为主,至于是属于契丹礼还是汉礼并未有明确的记载说明。但是从当时的社会背景可知,汉官韩知古作为主管诸国礼仪的官员,其对于仪法的见解应当也是被此次礼典编修所采纳。据此以及太祖朝之后的史事可以推测,太祖七年礼典中吉仪的部分应当是在整理契丹遥辇汗国时期的礼仪基础之上,吸收部分汉式礼仪而成的。如在太祖十二年辽太祖备礼受册的典礼中,既有阻午可汗时期柴册仪的影子,同时也增加了“建元,率百官上尊号”的内容。而凶仪部分的编订,则与吉仪不同。据史书记载,契丹人有着“父母死而悲哭者,以为不壮”的风俗,实行的是“以其尸置于山树之上,经三年之后,乃收其骨而焚之”[4]隋书(卷 84)·契丹传.中华书局,1973.(P1881)的树葬方式,与中原差异较大。但是《辽史》中所记载辽太祖的丧礼则是汉式的,有奉“梓宫至皇都,权殡于子城西北”,上谥号升天皇帝,尊庙号太祖,营建山陵等中原汉式凶礼中的内容。另外,在太宗天显九年(934)九月戊寅,葬太皇太后于德陵之时,前二日,有发丧菆塗殿,太宗皇帝具衰服以送等仪程。虽然简略,但是发丧,子孙衰服,送陵正是中原凶仪的内容。因此可以认为太祖七年(913)制定的礼典中的凶仪基本上是源自汉礼的。
太宗在位期间所行之柴册礼、瑟瑟礼等,说明太祖七年礼典在太宗时期仍有沿用。同时较之太祖时期,太宗即位初期,频繁谒太祖庙、祖陵,多达二十余次,说明应当也有一套较为完整的谒庙礼仪存在。
三、辽太宗时期杂用汉礼的实践
会同元年(938年)之后契丹国家的政治地位和性质发生改变,太宗朝时期国家礼仪从内容到形式的丰富正是这种变化的外在表现之一。《辽史·历象志上》中亦称:“辽以幽、营立国,礼乐制度规模日完。”辽朝国家礼制初具规模即以太宗会同年间接收幽云十六州为始。太宗时期辽朝国家礼制发展的总体呈现两种趋向,即一方面对契丹古礼的保留与丰富,另一方面则是在朝仪方面对汉礼的大量践行,尤其是在会同元年之后更为明显。此时虽然史书中没有太宗时期辽朝礼典修订的记载,但是源自契丹古礼以及因袭于五代的礼仪仪式充斥在国家的政治生活实践之中,却是不争的事实。
据初步统计,太宗朝时期有祭(告)天地八次,行柴册礼(包括再生柴册礼)二次,祭诸神(麃鹿神、木叶山神等)九次。其中太宗朝八次祭(告)天地的记载均在会同元年之前,且仪式的举行多与太宗即位及军事活动有关。会同三年(940)十二月壬辰朔条载,(太宗)“率百僚谒太祖行宫。甲午,燔柴,礼毕,祠于神帐”[1]辽史(卷 4)·太宗纪下.中华书局,1974.(P49)。说明太宗时期仍然保留了契丹古礼,并且能够灵活运用,而神帐及神纛车的设置,更是体现辽朝国家礼仪生活的契丹民族性。
会同元年之后,本纪中再无祭(告)天地的记载,但是在国家礼仪生活中,不仅有“太宗诏蕃部并依汉制,御开皇殿,辟承天门受礼”[2]辽史(卷 37)·地理志一.中华书局,1974.(P440),还增加了对汉仪的应用规定。如会同三年十二月丙辰“诏契丹人授汉官者从汉仪,听与汉人婚姻”[1](P49)。大量汉仪的引进,丰富了辽朝国家的礼仪生活,强化了国家政治的有序化。会同三年(940)春正月,回鹘使乞观诸国使朝见礼,从之[1](P47)。这也证明,俨然以上国之姿出现的辽朝,已经基本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朝觐礼仪制度。太宗时期对汉仪的践行最为突出的便是行“入閤礼”。
《辽史》载会同三年(940)“夏四月庚子,太宗至燕,备法驾,入自拱辰门,御元和殿,行入閤礼”。据《辽史·仪卫志》可知,辽太宗入燕前,曾于蓟州观《导驾仪卫图》,后以法驾幸燕。《导驾仪卫图》虽无存,但从名称上可知其为引导御驾的仪卫排布图,描述的应该是中原政权的仪卫排布状况。太宗应当是遵照此图所示,以法驾入燕。自北门(拱辰门)入子城,“子城就罗郭西南位置。正南曰启夏,内有元和殿”[3]辽史(卷 40)·地理志四.中华书局,1974.(P496)。即辽太宗于南京皇城内正殿行入閤礼。
据北宋宋敏求《春明退朝录》称:“唐日御宣政,设殿中细仗、兵部旗幡等于廷,朝官退,皆赐食。自开元后,朔望宗庙上牙盘食。明皇意欲避正殿,遂御紫宸殿,唤仗入閤门,遂有‘入閤’之名。在唐时,殊不为盛礼。唐末常御殿,更无仗,遇朔望,特设之。趋朝者仍给廊下食。所以郑谷辈多形于诗咏叹羙。而五代行之不绝。”[4]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卷中).中华书局,1980.(P27)可知,入閤礼在五代时期地位得到提升,成为朝廷盛礼。太宗以法驾入燕,并于正殿行入閤礼,正是在中原礼法影响下的对汉法的一次实践。
大同元年(947)春正月丁亥朔,太宗再次“备法驾入汴,御崇元殿受百官贺”[1]辽史(卷 4)·太宗纪下.中华书局,1974.(P59),虽然《辽史》本纪中并无此记载,但是新旧《五代史》、《资治通鉴》等书都保存了三月朔太宗于汴京崇元殿行入閤礼的记载[2]旧五代史(卷 99)·汉高祖纪.1326;旧五代史(卷 137)·契丹传.1834;新五代史(卷 72).四夷附录·契丹.898;资治通鉴(卷 286)高祖天福十二年(947)条.9347.。如《新五代史》中记:“三月丙戌朔,德光服靴、袍,御崇元殿,百官入閤,德光大悦,顾其左右曰:‘汉家仪物,其盛如此。我得于此殿坐,岂非真天子邪。’”后梁时期以汴京为都,“制宫殿门及都门名额:正殿为崇元殿……门如殿名”[3]旧五代史(卷 3)·梁太祖纪三.中华书局,1976.(P50)。五代后晋沿用后梁宫殿,仍以崇元殿为正殿。这是史籍记载的太宗对入閤礼的第二次实践。太宗以征服者之姿入汴,享受了规模盛大的入閤礼仪,切实地感受到了仪式对正统及皇权威严的宣扬,因此发出了“真天子”的感慨。此次对入閤礼的时间虽然有灭石晋、入主中原标榜正统、宣扬皇权国威的用意,但也从侧面证实了太宗对中原汉式礼仪的欣赏和认可。
其后的三月壬寅,太宗命令“晋诸司僚吏、嫔御、宦寺、方技、百工、图籍、历象、石经、铜人、明堂刻漏、太常乐谱、诸宫县、卤簿、法物及铠仗,悉送上京”[1](P59-60)。将后晋全套的诸礼仪法式,包括明堂刻漏、太常乐谱、卤簿、法物、铠仗等整体搬迁到了辽上京。这是太宗时期在对传统契丹礼保留的基础上,对汉礼的一次大规模引进。其后辽穆宗即位之初(应历元年,951年,十一月)即诏朝会依嗣圣皇帝故事,用汉礼。
虽然太宗皇帝时期的史料记载中没有朝廷修订礼法的记载,但是在其时的国家礼仪生活中,既有对契丹礼的继承和完善,如祭天礼、再生柴册礼等;也有通过吸收、借鉴中原汉礼内容的部分,如诸如朝觐仪、入閤礼等。因此,可以认为虽然朝廷没有颁布明文的礼法仪式文本,但是在实际的国家礼仪生活中,至少封册、朝、聘等方面,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按照中原王朝的仪轨进行组织,通过对中原王朝的吸收借鉴,以较为庄严的仪式来宣扬王朝的正统性和皇权的威严。而这些对汉礼的实践活动在太宗及其之后的历史时期内逐渐成为国家礼仪生活中的定制,同时也为辽朝中期礼典的修订奠定了实践的基础,并提供了现实的素材。
四、兴宗之后辽朝礼典的修订与完善
辽中期以后,随着与北宋的修和,社会进入稳定发展时期。在景宗到圣宗期间统治者采取了较为温和的统治手段,调整国内的民族关系,兴科举,重用汉官。中原儒家著作在辽朝也有流行和收藏,如圣宗开泰元年(1012)八月丙申朔,铁骊那沙等送兀惹百余户至宾州,赐丝绢。是日,那沙乞赐佛像、儒书,诏赐护国仁王佛像一,《易》《诗》《春秋》《礼记》各一部[4]辽史(卷 15)·圣宗六.中华书局,1974.(P171)。伴随着统治阶级的儒化政策及汉官集团地位的上升,辽朝的政治制度方面受到越来越多的儒家文化的浸染。在社会发展的同时,其统治集团上层对汉文化的认识也愈加深刻,对儒家的礼乐制度也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于是在太祖、太宗朝的基础上,辽王朝开始了第二次礼典编修。
重熙十二年(1043)五月乙未,辽兴宗下诏复定礼制[5]辽史(卷 19)·兴宗二.中华书局 1974.(P229)。用“复定”表明,这次是在前朝基础上对礼制的重新修订。但是,在其后的兴宗诏书中有“我朝之兴,世有明德,虽中外向化,然礼书未作,无以示后世”之言,说明辽朝虽有此次定礼制的举措,但并未能形成一部礼典。因此在重熙十五年(1046)时,兴宗诏谕萧韩家奴与耶律庶成二人修撰礼典,并要求他们酌古准今,“事或有疑,与北、南院同议”[1]辽史(卷 103)·萧韩家奴传.中华书局,1974.(P1449)。
重熙年间《礼典》最终成书,具三卷规模,其主要编撰人是萧韩家奴和耶律庶成。两人均为契丹人,对本民族的历史和传统都十分了解,同时也对中原传统文化有较为深刻的理解。如萧韩家奴本契丹涅剌部人,史称其“少好学,弱冠入南山读书,博览经史,通辽、汉文字”,可见其儒化程度较深,并以文学闻名于当时。重熙十三年时萧韩家奴曾上《追崇四祖为皇帝疏》,其中言辞恳切,引经据典的论证追封辽之先祖的重要性。认为在遥辇之时,相当于中原三皇时代,礼文未备情有可原。阿保机建辽之后,制文字、修礼法,其后诸位辽帝都以礼乐治天下,因此应当效仿唐朝追崇先祖。从此篇奏疏中,可以发现萧韩家奴对儒家传统礼乐制度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并认为阿保机代遥辇之后,由于本国性质与李唐王朝相同,因此应该效仿唐朝的礼典完成自身的礼乐制度建设。而且,兴宗重修礼书的诏书中也提出要酌古准今,并与北、南院同议的编修原则。由此可知,此三卷礼书的编修者要在酌古的基础上,博考经籍,结合辽朝国家具体的礼仪实践,以“不缪于古者”为取舍进行辽朝礼典的编修。即表明礼典是在保留契丹古礼的同时,借鉴中原礼制素材,将那些经过实践验证,同时又符合契丹当时国家社会发展情况的内容收录其中。
由于重熙礼典仅具三卷规模,仍有缺漏不足。其后陆续有对王朝礼制进行的补遗,如道宗清宁十年(1064)定吏民衣服之制[2]辽史(卷 22)·道宗二.中华书局,1974.(P264);天祚帝乾统六年(1106)议制两府礼仪[3]辽史(卷 30)·天祚帝四.中华书局,1974.(P352)等。辽末耶律俨修《皇朝实录》七十卷,其中礼志的部分应当是对辽朝时期国家礼仪制度的收罗及对重熙以来辽朝编修礼典的总结。
五、结语
辽末战火频仍,史籍难存,其后又历千年,时至今日,辽朝礼典已难窥原貌。今本《辽史·礼志》叙其取材曰:“今国史院有金陈大任《辽礼仪志》,皆其国俗之故,又有《辽朝杂礼》,汉仪为多。别得宣文阁所藏耶律俨《礼志》,视大任为加详。存其略,著于篇。”据《辽史·礼志》可知,元修《辽史·礼志》取材于金陈大任《辽礼仪志》《辽朝杂礼》以及宣文阁所藏耶律俨《志》。而这三者中,又以耶律俨《志》成书最早,其主要的资料来源当是辽朝本朝编修的礼典。金陈大任修《辽史》时主要取材于完成于辽末的耶律俨《礼志》,那么陈大任的《辽礼仪志》应当是其对俨《志》取材加工而成。因有所取舍,所以不及俨《志》内容全面详细。元修《辽史·礼志》的部分应该是综合了俨《志》与《辽朝杂礼》的内容,重新编排的结果。
在今本《辽史·礼志》中,既保留了具有契丹礼特征的祭山仪、瑟瑟仪、柴册仪、拜日仪等,同时也存在带有中原礼特色的谒庙仪、拜陵仪、封册仪、朝聘仪等。从文本的记载中可以发现,契丹礼的仪式多综合化,如柴册仪中除了燔柴、上册之外,还增加了拜御容、奉七庙神主、上尊号、宴飨等内容,这是对契丹古礼在内容和形式上的丰富和改造。而对于中原礼也并非全盘照搬,主要是借鉴性地吸收,如丧葬仪,虽然引进了山陵、哀册、服丧等制度,但是仍然保留了刑羖羊以祭、烧饭等契丹古礼。综上可知,对契丹传统古礼的丰富改造以及对中原汉礼的借鉴吸收这一显著特征,体现在辽礼文本内容之中,并贯穿于辽朝礼典编修的整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