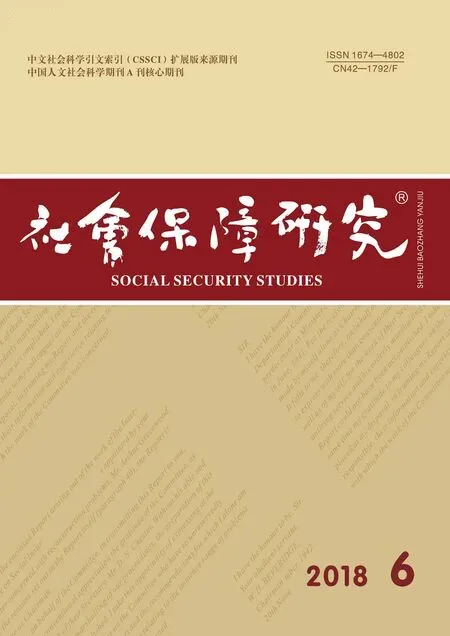美国福祉制度与福祉财政特征研究*
刘晓梅 乌晓琳
(东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辽宁大连,116025)
广义上,几乎所有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服务都属于福祉,所有与社会保障和福利服务相关的制度组合可定义为福利制度。[注]陈立行认为福利是为了满足人们生存的基本需求而提供的一种物质援助。福祉强调的是让人们感到幸福和满足的一种状态。如果说福利是一种物质援助,那么社会福祉则是一种平等、尊严、权力的保障制度。福祉制度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其概念受主观、客观的因素影响,不同国家对福祉制度的界定各不相同,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对福祉制度的界定不尽相同,不同学者对福祉制度的理解也不同。本文将福祉定义为一种新型的社会环境,它包括社会和个人的需要。那么,福祉财政则是一种政府通过国家公权力将所得进行再分配的制度,它包括以实现受益对象待遇均等化为目标而采取的财政制度及相关的社会政策,即国家通过财政方面的举措,将富有者的所得转移给贫穷者,以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权利。若将福祉制度比喻为人体,那么福祉财政可视为血液。
艾斯平·安德森(Esping Andersen)在《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中以非商品化(De-commondification)[注]“非商品化”指的是个人福利相对地既独立于其收入之外,又不受其购买力影响的保障程度。艾斯平选用此概念,并将由此概念扩展的分析量纲作为福利体制比较分类的标准之一。和福利的阶层化(Stratification)[注]“阶层化”指的是福利效果的度量。虽然福利国家都会涉足社会阶层化过程,但是其具体表现形式各不相同。艾斯平设定了阶层化的七种比较量纲,以区分福利体制的各种类型。为量纲将福利资本体制分为三种:自由主义体制(Liberal Regime)、保守主义体制(Conservative Regime)和社会民主主义体制(Social Democratic Regime)。[1]当然,不同体制下各个国家的福祉财政略有不同,这是因为福祉财政的推行需要以较高的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及较好的国民经济运行机制为前提,它要求国家(中央政府)对公共财政施行强有力的干预。
美国是自由主义体制的代表国家,其福祉财政兼具普适性和特殊性的特征。自由主义体制普遍存在于盎格鲁-萨克逊(Anglo-Saxon)国家群组中。在这种体制下,“国家用于社会政策的公共支出水平比较低,待遇津贴一般需要资产审查,公共服务的提供是选择性的”,[2]即体制中居支配地位的是经济调查式的社会救助、少量“普救式”的转移支付以及作用有限的社会保险计划。[3]因此,美国的福祉财政崇尚公共福祉财政支出效率,福祉的理念一向是救急救难。
保守主义体制多存在于以意大利和德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中,前者史称合作主义国家,后者则是自俾斯麦以来形成的家长式权威主义国家。这种体制中,社会权利的资格是以工作业绩为计算基础,即以参与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保险缴费记录为前提条件,因此带有保险的精算性质。社会民主主义体制存在于瑞典、挪威和丹麦这些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中,此种体制以贝弗里奇的普遍公民权原则为宗旨,保证工人分享中产阶层所享有的全部权利。[4]
近年来,一些保守主义体制和社会民主主义体制的国家福祉财政改革也显示出美国特征。如制定受益对象的精准化界定标准,设立多层次与低保障的福祉项目,以及构筑福祉财政的多元化主体等。与美国相比,中国的公共福祉效率性不高,公共财政的绩效性还需改进,财政支出的精准性仍需改革。因此,研究美国福祉财政对中国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一、美国福祉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一)《社会保障法》的制定
1933年是美国经济危机最严重的时期,约有1300万的民用劳力失业,占全部民用劳力的1/4。除此以外,还有很多人只能找到一些临时性的工作。[5]在这一时期,贫穷和失业已经不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由于社会运转不利所造成的波及整个美国社会的普遍问题。传统的救济方式无力帮助如此众多的人摆脱困境,依靠救济既不能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也不能激励国民自立自强改变自身处境,政府需要尽快设立并施行新的福祉政策与帮扶标准来改变当时的情况。而构建长期有效的社会福祉体系则是改善当时困境的有力举措。
美国最初的福祉体系就是在社会各方的呼吁下应运而生的。1935年8月14日,罗斯福总统签署了《社会保障法》,以这部法案为基础,整个美国建立起最初的救助制度。它针对健康、失业等社会风险为各州的老龄群体、失能与半失能群体、抚育儿童的女性群体及未成年群体等提供了较为充分的法律保障与经济补助。虽然这部《社会保障法》存在着局限,例如未能确定全国性的统一标准,由各州自行决定各个项目的细则与实施标准等,但是并不能因此否认《社会保障法》是一部划时代意义的法案,它的颁发标志着美国政府与社会关注的焦点从财产权转移到人的权利。它扩大了政府在社会福祉领域的责任,同时也标志着美国公共福祉体系的确立。
(二)公共福祉体系的构筑
自由主义(Liberalism)意指尊重个人自由的思想,也就是“应保障人类与生俱来的生命、财产、自由等天赋人权免于遭受滥权侵害”。[6]自由主义体制下的美国在早期的政策制定中对福祉的界定较为严苛,政府制定的福祉政策与创建的项目均侧重于扶持贫困群体。而且带有救助性质的公共福祉也是美国福祉财政的独有特点。这是因为美国存在巨大的贫富差距,所以政府管控的财政支出大多用于保障贫困群体的生存权与改善贫困群体的生存环境。公共福祉作为以商业保险为主的美国社会保险的补充,是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如今美国的公共福祉体系可以从现金福祉、实物福祉和税收减免三个方面进行归纳。
现金福祉由补充性保障收入(Supplemental Security Income,SSI)[注]补充性保障收入(Supplemental Security Income,SSI)是一项由联邦资助(补充)的为盲人、残疾人和65岁及以上的老人等低收入者提供最低收入保障的救助计划。这项计划起始于1972年,1974年之前由联邦政府提供基金,州政府具体管理。1974年以后这部分政府支出被归入联邦政府的补充性保障收入计划,由联邦政府统一筹款(来源于总税收收入)并根据全国统一标准进行发放,各州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予以适当追加。以及贫困家庭临时补助(Temporary Assistance to Needy Families,TANF)[注]贫困家庭临时补助(Temporary Assistance to Needy Families,TANF)是1935年由时任总统罗斯福批准的将失依儿童补助纳入社会安全法案的计划,随后在1961年和1962年该法案经历了两次重大改变,这两次改变都与家庭有关。1961年添加了失业父母的补助细则,使得失业父母因为家庭有依赖儿童而能够接受救助。1962年该法案将“失依儿童补助”改称为“抚养未成年子女家庭补助”,主要强调补助是以家庭为单位,而不是以儿童为单位。等组成。前者是将1935年的老龄福祉、视觉失能者福祉和1950年修正的失能者救助等,在1974年由《社会安全修正案》统一整合并重新命名为补充性保障收入。后者是由1935年失依儿童补助(Aid to Dependent Children,ADC)和1962年修正的抚养未成年子女家庭补助计划(Aid to Families with Dependent Children,AFDC)发展而来。
实物福祉包括营养补助、医疗救助和住房补助。营养补助包括补充营养补助计划(Supplemental Nutrition Assistance Program,SNAP)和校园餐项目计划。前者由1964年的食品券(Food Stamp)项目发展而来,后者由1946年的国家校园午餐计划(National School Lunch Act,NSLP)、1966年的校园早餐计划(School Breakfast Program,SBP)和特殊牛奶计划(Special Milk Program,SMP)等组成。[7]其中,食品券是一种凭券方案(Voucher Schemes),[注]凭券是一种实物再分配的手段,在限制个人支出决策的同时转移购买力。它是政府供应某种货物或服务的一种方法,即给予个人的资金,只准用于购买特定货物或服务。为了确保提供的货物花费在特定的用途上,要发放一种只能交换特定货物的配给票或凭券。美国政府采用了一种与相对贫困人们的食物有关联的类似计划(“食品券”计划)。由农业部提供农产品,贫困者凭券可以购买食品或免费得到食品,该方案增加了贫困人口购买食品的能力。[8]补充营养补助计划项目的管理责任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共同承担。联邦政府支付福祉费用和制定广泛的规则,州政府直接负责具体的项目管理。医疗救助指的是1965年美国联邦政府对各州开展的医疗援助补助计划(Medicaid),它是针对65岁及以上老人、半失能或失能者、低收入者、孕妇及多子女家庭等个人和家庭的医疗健康保障计划,这项计划被称作美国医保系统的最后支付者(The Payer of Last Resort)。[9]住宅补助包括公共住宅和房租补贴。公共住宅是对贫困群体提供的免费住宅或低房租住宅。房租补贴是根据1974年《住宅与社区发展法案》的规定,当贫困者收入低于该地区平均收入的80%时可以获得的房租补助。
税收减免指的是1975年的劳动所得税抵免(Earned Income Tax Credit,EITC),这是一种针对低收入劳动者的税收与福祉政策,只要申请人符合条件,便批准其从应纳税额中直接扣减抵免额。若抵免额大于当期应纳税额,申请人还能够直接取得返还收入。劳动所得减免为美国工薪家庭提供福祉,其纳税单位可以选择个人,也可以选择夫妻双方。
二、美国福祉财政的改革
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20年的兴旺繁荣相反,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出现衰退。经济滞胀的现象严重困扰着美国社会与国民。尽管联邦政府在公共福祉方面的开支持续扩大,但贫困人口的数量依然有增无减。美国商会执行副会长布里恩特(Myron Brilliant)在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表示,美国面临的首要挑战是福祉制度的改革,他说:“福利支出占美国联邦预算的一大部分,如果这一制度不加改革,美国债务率就会持续攀升。”布里恩特认为要想解决美国的债务问题,就应该解决福祉制度的改革问题。
(一)注重人力资源的投资:2014年《儿童照护与发展法案》
2014年11月19日,奥巴马总统签署了《儿童照护与发展法案》(Child Care and Development Block Grant Act of 2014)。该法案自1996年以来首次授权儿童照护和发展基金(The Child Care and Development Fund,CCDF)项目,其代表了对儿童照护项目的历史性重新设想。
儿童照护和发展基金是政府的儿童照护补助项目,由政府向那些工作、培训或教育项目中的低收入家庭提供一定额度的津贴补助。这些补贴可抵消美国家庭用于购买照护儿童商品和服务的费用,同时维系市场体系中的家长选择。儿童照护和发展基金也是一个联邦域赠款项目,运行此项目时联邦财政直接向州、地方等区域提供资金,以满足当地需要。此外,各州在确定补助领取资格准则(最多达到国家收入中位数的85%)、提供者支付率和家庭共同支付额以及服务的范围和质量方面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2014年《儿童照护与发展法案》对儿童照护和发展基金项目做出了扩张性的改变。这些变化的重点是改善儿童照护的健康性和安全性,通过简化资格政策,提升该计划的家庭友好性,以及确保对公众的透明性。另外,还通过提供有关幼儿选择的信息,提高幼儿早期学习和课外活动的整体质量。这些变化强调让幼儿照护更经济,以实现儿童健康发展和家庭经济稳定的双重目标。
《儿童照护与发展法案》规定,每个州在决定其儿童照护和发展基金项目如何运作方面拥有酌处权,例如制定资格指南、提供者付款率和家庭副本。待遇认定标准为父母处于工作或寻找工作中、处于参加职业培训或教育中、处于儿童必须需要看护服务的情况下。一般情况下,受益儿童年龄最高为13周岁,有特殊需要的儿童年龄可提升至19岁。在50个州和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2015年单位家庭的初始资格阈值从最低的每月838美元(伊利诺伊州)到最高的每月5279美元(北达科他州)不等。
儿童照护与发展法案要求各州向接受儿童照护和发展基金项目补助的家庭子女提供至少12个月的补助,领取待遇的资格门槛设定为只要他们的收入维持或低于国家中等收入(SMI)85%,申请家庭的父母收入就会增加。此外儿童照护与发展法案还要求各州对特定人群的服务进行优先排序,这些特定人群包括低收入家庭的儿童(考虑家庭规模)、有特殊需要的儿童,也包括国家规定的弱势群体等。各州在处理如何为这些人口提供优先权时比较灵活,具体手段有优先考虑入学、免除共同支付、为获得更高质量的护理支付更高的费率、使用赠款或合同为优先人群预留名额等。
2015年美国政府财政年度数据显示,有约89%的已通过资格认证的儿童照护服务可供家长选择,并且至少有14个州和地方与购买儿童照护服务的父母签订款项补助合同。有儿童照护需求的家长可以选择任何满足州政府和地方政府要求的儿童照护提供方,包括托儿所、家庭成员、邻居、家庭儿童护理项目、课后计划和基于信仰的项目。儿童照护和发展基金项目资助的儿童照护提供方必须符合各州和部落规定的健康和安全要求。与儿童照护和发展基金项目相比较,儿童照护与发展法案规定各州必须严格执行一些特定领域标准,儿童看护人员需接受全面的犯罪背景检查;项目人员关于健康、安全要求的培训;定期对儿童照护服务提供者进行现场监测;重视儿童照护提供者的专业发展和培训进展;加大支出以提高儿童照护质量;设立家庭资格复审的12个月期限等具体措施。
2015年美国财政为儿童照护和发展基金项目拨款53.5亿美元,平均每月约有140万名儿童受益。按规定,州政府需将此拨款的一部分专款专项用于改进儿童照护服务质量。此外,还应按照《儿童照护与发展法案》进一步提升此专项款的最高额度,增设旨在提高婴儿和幼儿护理质量的新条款。近年来,各州通过建立和扩展质量评级和改进系统(Quality Rating and Improvement Systems,QRIS),改进教师和专业发展系统,研发新的信息技术,积极响应政府关于提高儿童照护服务质量的呼吁。建立和扩展质量评级和改进系统的目的是通过在儿童护理和其他早期儿童教育项目中分配评级,协助制定和实施改进计划,并帮助公众利用这些信息做出决定,以提高儿童照护的质量。
《儿童照护与发展法案》还与两个提供儿童照护基金的分块补助计划有关,即贫困家庭临时补助和社会服务固定拨款(Social Services Block Grant,SSBG)。贫困家庭临时补助向有子女的低收入家庭提供现金补助和其他福祉或服务。各州可将高达30%的贫困家庭临时补助整体赠款转移给儿童基金会,或将贫困家庭临时补助资金直接用于儿童照护。社会服务固定拨款项目向各州提供资金,主要用于包括儿童照护在内的许多社会服务。美国2015年财政数据显示,联邦和相关州约120亿美元的资金被用于儿童基金会、贫困家庭临时补助等与儿童有关的社会服务。
联邦政府还通过先期启智计划(Head Start Program)为幼儿教育提供资金,旨在促进家庭关系的稳定,保护儿童身心健康,为其入学前做好准备。另外,通过向当地的公共和私人非营利和营利机构提供赠款,为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的儿童和家庭提供教育、照护、营养、社会和其他服务。该计划包括为学龄前儿童提供的先期启动服务,以及为婴儿、幼儿和孕妇提供的早期启动服务。2015年美国财政数据显示,联邦政府向该计划提供了86亿美元,在2014—2015年度为约110万名5岁儿童和孕妇提供了有效服务。
国家资助的学前教育项目是美国对儿童教育的另一项关键投资。在2014—2015年,42个州和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资助了一些学龄前儿童的学前教育项目。美国对学前教育项目的支出累计超过55亿美元,为130多万名儿童提供了服务,每名儿童在学前教育的平均支出约为4679美元。美国各级政府和相关组织共同为加强启智计划、儿童照护以及学前教育三者之间的联系和对接做了许多努力。例如,2007年的启智计划重新授权法案(Head Start Reauthorization Act of 2007)要求州长指定一个关于早期儿童教育和护理(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SAC)的国家咨询委员会,以建立一个协调的幼儿教育和护理系统。
为儿童照护服务提供支持和帮助的另一个主要来源是儿童抚养照护信贷(Child and Dependent Care Credit),它为支付抚养费的家庭提供有偿就业的税收补助,据统计,2013年该项目为629万纳税人提供了33亿美元的补助。部分州除了联邦税收抵免外,还向家庭提供儿童和被抚养人的税收抵免或扣减,但各州确立的资格认定和待遇水平差别很大。
(二)福祉财政的参数微调
有关美国福祉政策具体参数的变化可从失业保险最低工资的上涨与待遇的下降、税收减免具体标准的更改等方面归纳。
失业保险收入受联邦和州政府所得税的限制,但不受社会保障税的限制。美国失业保险的待遇发放由劳工部负责监督,各州因财政情况不同,其待遇领取条件与最高待遇水平等具体指标存在显著差异。一般来讲都会要求受益者有基本工作能力并具备自主性,能够积极主动寻找就业机会。所有的工人都可以享受长达20周的州福祉待遇。如果他们在这些福祉用尽后仍然失业,可以申请启动延长福祉期,将继续领取补助。
在美国没有规定直接向家庭提供税收优惠以支持支付租金。通过从个人的联邦应税收入中扣除抵押贷款利息,以及在一些年内首次购房的抵免,购房者可以获得税收优惠。还通过提供税收抵免,减少投资者的所得税,为建造或修复负担得起的出租住房提供奖励。联邦住房租赁的支持主要通过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HUD)管理的联邦资金年度拨款来完成。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管理各种各样的项目(如公共住房等)以提供经济适用住房。各州政府有权利将数量有限的联邦其他项目的资金用来提供租赁住房补助。例如一些州政府选择从贫困家庭临时补助方案中拨出一部分资金,以实施租金补贴方案,这些方案通常为少数特定目标人群提供短期援助。
美国联邦政府住房和城市发展部根据计算家庭收入中位数来确定家庭是否符合联邦租金补助计划的资格。据统计2016年美国四口家庭的国民收入中位数为65700美元,其中80%的中位数为52560美元,其余30%为19722美元。以密歇根州为例,一个四口之家的收入中位数是每年62500美元,其中80%是50000美元,30%是18750美元。此外,美国政府对于特定需求的老年人和残疾人、青年和家庭的租金支付有不同的扣除方案,如基于家庭特征的补助计划或有限的目标租金补贴等。
三、美国福祉财政的特征及成因分析
(一)福祉受益对象的精准定位:信奉自由主义的盎格鲁-萨克逊国家
美国对福祉受益对象的界定有着严格且精准的评判机制,分析原因如下:
第一,自由主义认为市场是自立的劳动力的最佳保障。市场有利于劳动力的解放,只要没有外力的干扰,市场可以通过其自我调节机制确保所有的劳动力有工作。它反对国家或政府的外力干涉,认为市场具备自身的调节机制,外力的干扰越少越好,市场依靠其自身的调节机制可以保证劳动力的福祉。自由主义认为,劳动力可能遭遇不可避免的风险跌入危机陷阱,但这并不是自身制度的局限所导致,而是个人道德沦丧、奢侈、懒惰的缘故。自由主义体制并不是一个慷慨的体制,这一点从美国的受益对象仅为贫困群体、老龄群体以及抚养儿童的妇女等社会弱势群体以及低水平的补助标准可以看出。
第二,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最初的定居者大部分来自盎格鲁-萨克逊民族,他们效仿英国的济贫制度来建立美国的社会福祉。加尔文教徒对美国早期救助理念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们崇尚克勤克俭,厌恶懒惰。所以美国并没有全面性的救助制度,救助以各项分立的制度形式存在。美国的社会福祉仅仅对低收入阶层和贫困群体提供必要的救助。美国政府一直认为,对政府的长期依赖从来都不是美国梦的一部分,政府的目标始终是帮助个人和家庭摆脱贫困。每位美国公民,无论健康或残疾,无论年长或年幼,无论组建家庭或独身一人,都应该有机会获得一份工作,过上有尊严的自给自足的生活。
(二)福祉项目多层次与低保障:削减财政赤字
美国福祉体系涉及每一位美国国民的生老病残、衣食住行与学习工作等多个方面,但是从个人或家庭的具体收益来看,美国公共福祉体系所提供的保障水平仅可满足国民的最低生活需求。
以贫困家庭临时补助项目为例,这个项目是根据《个人责任及劳动机会调整法案》(Personal Responsibility and Work Opportunity Reconciliation Act)设定的,法案规定联邦政府为项目制定相对合理的基准指标,州政府负责项目的运营和管理。具体支付水平是根据申请者的实际情况,由各州政府酌情决定,与此同时,通常情况下,收益水平随着家庭其他收入来源的增加而减少。因此,美国各州的具体支付水平差异显著。各州的福祉减少率(Benefit reduction rate)[注]福祉减少率指每赚取1美元其他收入而减少的福利的比率。有很大的不同,一般随着收入的增加,收益会减少一半至全部。在此项目下,“对于一个只有父母一方和两个小孩的家庭来说,各州的保障是不同的,2009年从阿肯色州的每月204美元到阿拉斯加州的1464美元,没有一个州的家庭可以从该计划中获得足够高的支付从而脱离贫困线”。[10]
据经合组织SOCR数据库统计,贫困家庭临时补助项目领取人数在2007年为3896830人,2014年为3406751人,8年内待遇领取人数略有下降。与此同时补充营养补助计划领取人数在2007年为11563000人,2014年增长为22699596人,8年内待遇领取人数几乎翻了1倍。美国白宫官方数据显示,1996年美国政府在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上共支出约5000亿美元,2017年增长到16000亿美元。并且1996年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总额约为5万亿美元,2017年联邦政府债务总额约为20万亿美元,20年间美国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65%升至105%,远超60%的国际警戒线。贫困家庭临时补助项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社会福祉支出的快速增加、领取人口的急剧增长以及联邦政府财政赤字的逐年上升。
(三)福祉财政的多元化主体:联邦政府和州、地方政府财权、事权的兼顾
美国是典型的联邦制国家,行政结构包括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等。美国宪法确立了各级政府的职责和支出责任,赋予了各级政府相应的征税权,明确了联邦、州、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美国宪法规定,宪法未赋予联邦政府的权利都属于各州和人民,因此联邦政府、州政府以及地方政府对福祉财政均承担责任,尽管三者的财政责任略有不同。联邦政府的权限已被具体列出,州政府拥有未被列举的其他权利,相较而言,后者有着更大的自主权。
州政府的福祉财政责任包括三个方面。首先,州宪法、州法对各州政府根据税收及支出增长水平等指标向各州征税及支出设有一定的限制。例如2002年,美国为限制州政府财政规模,由州宪法、州法通过收入限制[注]收入限制指的是根据个人收入、物价上涨、人口增长率等指标对每年收入预算的增长率进行限制。、支出限制[注]支出限制指的是根据个人收入等指标对支出预算的增长率进行限制。、控制预算[注]控制预算即靠推测收入控制预算,根据预测的收入限制预算的增长。及以上类型的组合方法,在27个州实施了上述规定。其次,州宪法、州法对各州政府制定了“不靠发行公债平衡州预算”的限制。最后,州宪法、州法对各州政府发行债券进行了限制。各州发行的债券大体可分为2种,即各州政府以信用能力为担保发行的普通债券和因特殊事业发行的能够保证收益率的收入债券,州宪法、州法限制的发行债券只是用于普通债券,具体手段如限制债券的最高额度等。除此以外,美国印第安纳州、内布拉斯加州、南达科他州的州宪法禁止发行普通债券。
地方政府的福祉财政责任依照各州宪法、州法严格被执行,由于各州宪法、州法略有差异,各地方政府福祉财政责任也存在差异。以纽约州的地方政府税收为例,1884年该州宪法规定了最早的税收限制,即10万人及以上人口的县或市,每年的寄存债务本金加上应付的利息不得超过县或市个人不动产评价总额的2%。到了1920年美国共有33个市实施税收限制,其限制水平控制在评价额的1%~2%,或为预算的一定比例,但对教育、特定市自治体自身业务的税收将不做限制。然而,税收限制的标准随着州宪法的多次修订一直在变化,但是其标准增减的幅度基本控制在1.5%~2.5%。此外,根据州宪法、州法的规定,纽约州对地方财政进行的监督事项由州会计检查室负责,具体包括保护地方资产、对地方进行知识技术支援、对地方政府进行定期检查和审核、培训并奖励地方职员等内容以便完善财政体系、节省开支、提高服务效率。
四、启示
本文以美国为例,通过梳理自由主义体制下整个国家的福祉财政政治,总结其成功经验与制度局限,发现如下几点启示:
首先,在权衡公平与效率时,美国的福祉财政似乎更注重效率。美国的救助从来都是救急救难,受救助对象需要符合严苛的要求,这激励了美国国民的自救与奋斗精神,例如救助对象只能领取到工资最低标准的一半的救助金,就充分体现了自由主义体制的文化。
其次,美国的福祉财政包括短期的福祉财政政策、中期的福祉财政政策、长期的福祉财政政策。美国历届政府一直在不断地修改这些政策的具体内容,例如废除不适宜的条例与细则,修正过时的判定标准并设立新的合乎实情的参数指标,以及重组或拆分不同政策。其中,短期的福祉财政政策或制度在设计时以救急救难为宗旨,约1~3年就会修正一次。中期的福祉财政政策或制度在设计时以平衡现状为宗旨,这一类型的政策或制度修正的频率更高。而长期的福祉财政政策或制度在设计时以长远经济实力的可持续发展为宗旨,其修正的频率与前面两种政策相比是最低的。
第三,美国政府秉承重视公共福祉财政支出效率的原则,政府不过多地去干扰自由市场,尽职地扮演着引导者的角色,然而市场的自身局限终会导致市场失灵的出现,这将对整个自由体制造成重创。灾难到来之时,在美国各届政府的应对举措中,社会福祉是政府应尽的责任与采取的预防措施之一,并且美国政府坚信这是政府的首要义务。
与美国相比,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起步晚,发展慢,结构设计不尽合理,制度和体系盲点较多,在发展道路中走了不少弯路与错路。通过研究美国发展的成功经验及总结失败教训,中国可以在未来的发展中规避美国正面临的危机与困境。
首先,中国现阶段福祉财政的结构设计不尽合理,制度和体系的盲点较多。对此,应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下,以转变政府职能、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为目标,深化相关部门机构改革,提升政府效能,完善福祉财政制度。中国还应修正现有救助资金供给的基本制度安排,增加项目之间的无缝衔接与配套关联,促进现有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其次,中国应强化福祉财政的责任意识,明确权责边界,建立与治理主体履职相适应的责任追究制度。中国应明确各级政府是福祉工作的实施主体,明确财政投入是社会救助资金可靠、稳定的来源,并建立科学合理、规范有效的财政投入机制,健全各级财政,对社会救助资金实行足额列支和按时拨付机制。
第三,中国应放宽市场准入。市场准入是国家对市场基本的、初始的干预,是政府管理市场、干预经济的制度安排,是国家意志干预市场的表现,是国家管理经济职能的组成部分。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有助于通过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提升我国的产业竞争力,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增加中国的财政税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