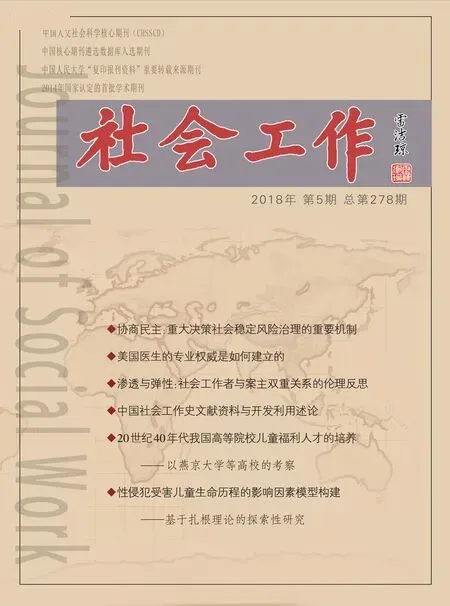与社会学结缘的中国社会工作
——一个学科史的考察
萧子扬 马恩泽
引 言
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学和社会工作专业作为“舶来品”在同一时期被引入我国,两个学科自此结缘,相伴相随。从中国社会工作的百年发展历程来看,它始终蕴含着一个种社会学传统,因此,中国社会工作和社会学在百年的本土化进程当中究竟保持着何种关系,这是一个值得学术界深入探讨和重点思考的话题。郑鹏(2016)认为,“社会工作与社会学关系的问题,在(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早期过程中,往往易被学者们忽视”。事实上,在西方社会工作学界,由于社会工作和社会学这两个学科的渊源有所不同,因此,曾在20世纪初期出现了相互攻击的情况,这也促使“社会工作与社会学存在何种关系”成为西方学者和学术界长期关注和讨论的话题。其中,Davies(1981a,1985b)认为两个学科是完全对立的;Leonard(1966)认为西方社会工作和社会学存在一种相互支持的关系,社会学为社会工作者从事社会工作提供了最牢靠的知识背景,社会工作为社会学奠定了认识基础(郑鹏,2016;王思斌,2006)。而社会学和社会工作专业作为两个较为独立的学科传入我国后,在本土化过程当中二者关系呈现出中国特色。比如,李伟(2016)结合对二者的引进、取消等发展历程的理解认为,“(中国)社会工作与社会学‘如影相随’,二者渊源极深”。马林芳、王建平(2009)认为,“就内地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的发展历程来看,这两个专业之间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王婴(2018)、彭秀良(2016)等人认为,在社会学、社会工作传入中国之初,就形成了将社会工作和社会服务理解为社会学的应用部分(“应用社会学”)的认知。近年来,对于社会学和社会工作的关系问题再次引起了学术界的讨论,有学者认为,社会工作被长期划入社会学的二级学科是有特殊的传统和优势。也有学者强调,国内通常将社会工作简化为应用社会学,这表明社会工作的学科地位尚未得以确立,因而需要建立“社会工作学”(何雪松,2015)。李迎生(2017)进一步强调,对于社会工作和社会学的关系,尚未有较清晰的答案,甚至可以说至今都十分模糊。尽管,目前学术界对于社会学和社会工作的关系尚存在诸多争论,没有一个较为清晰的答案。但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就是“中国社会工作和社会学曾经相伴而生,并长期共存共荣”。具体表现为:中国社会工作和社会学结缘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它们同时作为“舶来品”从西方引入中国;在学科的本土化进程当中“相依前行”;在学科的中断时期属于“难兄难弟”;而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社会学和社会工作专业都迎来了“新的春天”。
因此,面对社会学、社会工作新的学科边界划分的争论,面对学术界对于二者关系认识还较为模糊的学科现状。本文重点运用学科史的方法,对中国社会工作和社会学的引进、发展、恢复重建等阶段的史料加以梳理,分析二者的结缘过程和在本土化过程中关系的变迁,并尝试探讨“社会工作长期依附于社会学”的历史因素。最后,为当前的社会工作学科建设、学科分野提供一个历史性的视角。
一、走近应该留意的历史:中国社会工作的百年回眸
“中国社会工作有自己的历史发展……但是,一个基本的、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我们的社会工作教师和学生对我们自己的社会工作的发展了解较少”,王思斌(2012)认为,中国社会工作有其自身特有的历史品格,应该留意民国时期社会工作的历史。彭华民(2017)也认为,“其(社会工作)百年发展史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由此可见,中国社会工作的百年发展历程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因此,有必要进行一个较为全面的学科史的梳理。对于中国社会工作百年发展史的阶段划分,学术界目前尚未有一个统一、明确的看法。孟亚男(2012)分为“初创、兴起阶段”、“政府主导的‘单位社会’阶段”、“政府主导的‘双轨运行’阶段”等,彭华民(2017)分为“萌芽初创成长期(1949年以前)”、“民政社会工作发展期(1949年—1994年)”、“专业化快速发展阶段(1994年至今)”等。王思斌(2006)分为“20世纪上半叶”、“1949年以后”、“改革开放以来”等阶段,彭秀良(2016)分为引入、发展、蛰伏、重建等四个阶段。本文重点综合彭秀良(2016)、彭华民(2016)等人的阶段划分,按照时间顺序对中国社会工作的引入、发展、中断、重建等阶段加以梳理,并着重探讨在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过程当中如何与社会学结缘,即社会学在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进程当中承担着何种角色,社会学和社会工作保持着何种关系。
(一)中国社会工作的引入阶段
19世纪末20世纪初,近代中国社会日益恶化,一批仁人志士为挽救这种状态而掀起了向西方学习的维新变法的思想潮流(郑杭生、李迎生,2000),这是社会学、社会工作专业传入我国的重要事件和时代背景。彭秀良(2016)认为,社会工作引入中国的标志性事件主要包括北京社会实进会的成立(1912年)、沪江大学社会学系的创立(1914年)、沪东公社的成立(1917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创立(1922年)等,主要代表人物有步济时(John S.Burgess)、葛学溥(Daniel H.Kulp)等。
步济时被誉为“中国社会工作之父”,是将社会工作引入中国的第一人,也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创始人。他曾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社会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09年到远东任男青年会干事,因“觉醒的中国青年的挑战”来到北京,并担任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干事。1912年,创办了北京学生团社会实进会,由来自北京三所教会学校和三所公立学校的40名学生组成,主要目的在于改造社会和救治中国等。1914年,正式更名为北京社会实进会。1922年,步济时带头创办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着力于培养社会工作服务人才。
葛学溥是另一重要人物,对中国早期的社会工作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毕业于布朗大学,主修社会科学和圣经研究。1913年来到中国,并在上海浸会大学堂(后更名为“沪江大学”)英文系从事教学工作。1914年,葛学溥创建了沪江大学社会学系,并担任主讲教师。1915年,社会学系改为社会科学系,开设了社会学、社会调查、社会制度等课程。在教授相关课程的同时,带领学生在上海杨树浦地区展开了有关住房、教育、工业、人口等方面的调查。同年,组织成立了沪江社会服务团,重点在于实施社会救济和社会改造(彭秀良,2017)。1917年,由于社会服务范围的进一步扩展,在沪江大学校外又设立了一个社区服务中心——沪东公社,这是中国最早的社会服务机构,奠定了中国社会工作机构的雏形。
(二)中国社会工作的初步发展阶段
费孝通认为一个学科必须要有“五脏六腑”,其中“五脏”是指学会、研究所、图书馆、教学机构和刊物等(彭华民,2016)。事实上,一个学科在发展初期主要依赖于研究机构、教师队伍、课程设置(分支学科设置)、专业刊物、书籍出版等方面的建设。
第一,在研究机构(高校)方面。1922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成立,开启了我国社会服务(社会工作)教育的先河。此后,不少高校也开始陆续成立社会福利、社会行政等系,也尝试开设社会工作、社会服务等方面的课程。比如,沪江大学、金陵女子学院、辅仁大学、东吴大学、复旦大学等。
第二,在教师队伍方面。朱友渔是我国最早进行社会工作研究的本土学者,他于1911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并回国担任上海圣约翰大学和燕京大学的兼职教授,从事社会工作的教学、推广等工作。同时,社会工作的最初传播主要依赖于传教士步济时、葛学溥等人,他们均拥有社会学专业的教育背景。此外,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为例,教师队伍主要包括杨开道(主讲农村社会学等课程)、李景汉(主讲社会调查与研究方法)、章元善(主讲实地工作)、林东海(主讲社会立法、社会与工业)、吴文藻(主讲社会学原理)、张鸿钧(主讲社会行政)、严景耀(主讲犯罪学及监狱行政)、雷洁琼(主讲社会福利事业)、关瑞梧(主讲个案工作方法)、高君哲(主讲社会服务概论)、黄迪(主讲城市社会学)等。
第三,在课程设置方面。言心哲在《现代社会事业》一书中提到“社会事业系必修及选修课程草案”,对社会工作的课程设置进行了详细介绍。在必修课程方面,主要包括社会学、社会问题、社会事业概论、儿童福利或妇女工作、社会调查与研究、社会心理学、社会统计、社会个案工作、社会团体工作、社会行政、社会立法或社会政策、机关参观及实习、专题研究或毕业论文等。共同必修科目主要包括英文、国文、论理学、哲学概论、中国通史、西洋通史、三民主义等课程。选修课主要包括社会保险、公共卫生、劳工问题或劳工福利、社会政策、社会立法、家庭福利事业或家庭个案工作、儿童福利、妇女工作、社会教育、社区组织、心理卫生、贫困与救济、犯罪问题、监狱改良事业、合作事业、社会运动、精神病人服务事业、医院社会工作、娱乐问题、行政学、农村社会事业、公文程式等。
第四,民国时期的社会工作著作。彭秀良(2012)结合目前掌握的史料认为民国时期的社会工作著作主要有34种,而试图建立中国社会工作理论体系的以蒋旨昂的《社会工作导论》和言心哲的《现代社会事业》为代表。前者体系完备,注重社会工作实务方面的举例,对于早期社会工作的发展而言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后者是一本集大成的著作,不仅介绍了西方国家社会工作的发展状况,也对我国社会工作的情况进行了详细介绍,并对中国社会工作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第五,成立了相应的主管部门。1938年,国民党临时政府设立了社会部。1940年,社会部改隶行政院(杨雅彬,2001)。社会部改隶行政院后,拟定了《社会救济法》,确立了社会救济制度;颁布和实施劳工福利法规,积极改进劳工福利……在社会部的大力推动下,不仅社会工作实务获得了更大发展,社会工作教育也获得较快发展。
第六,创办社会工作专业刊物。1944年1月15日,《社会工作通讯月刊》正式创刊,成为了我国第一个以“社会工作”命名的期刊,该刊以社会工作消息、方法、资料等为重点。同年,中国社会学社与社会部合作创办了《社会建设》月刊,该刊发行旨在“发动全国富有学理研究的社会学者及富有实际经验的社会事业与社会行政专家,共同研讨有关战时及战后社会建设方面各种理论与实际问题”。当时活跃在该刊物的老一辈的社会工作专家、知识分子有孙本文、李安宅、朱亦松、言心哲、李剑华等。该刊物实际上成为了社会工作参与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对话平台。1948年5月,《社会工作通讯月刊》并入《社会建设》月刊。
(三)中国社会工作的中断阶段
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工作专业进入了中断期、蛰伏期(彭秀良,2016)。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史存在两条线索,一条是社会工作实务,另一条是社会工作教育。1952年,随着高等教育院系大调整,我国社会学系被取消,依附于社会学系的社会工作专业也未能幸免。因此,中国社会工作教育被迫中断,而社会工作实务还以某种形态在陆续进行着。
(四)中国社会工作的恢复重建阶段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转型,各种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开始爆发。于是,重建专业社会工作就被提上了日程。期间,国家有关部门和不少社会学家为恢复和重建社会学、社会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1979年,胡乔木在“社会学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代表中共中央为社会学恢复了名誉。同年3月,邓小平提出“社会学需要赶快补课”。1979年冬,雷洁琼给“第一期社会学讲习班”主讲“社会工作”课程。1982—1983年,吴桢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主讲个案工作。1985年3月,雷洁琼在“第一届全国民政理论研讨会”上提出“民政工作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的重要论断。同年12月,雷洁琼在“社会学专业建设与发展工作会议”上呼吁“尽快恢复社会工作的学科地位”。1987年9月,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发展论证会(史称“马甸会议”)在北京召开,目的在于探讨建设中国社会工作学院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及社会工作的课程设置等议题。参加会议的主要人物有:雷洁琼、李宝库、潘乃谷(代表费孝通)、袁方、苏驼、孔令智、袁华音等。此次会议提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为民政系统培养100名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研究生、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试办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等内容,该会议促使我国社会工作专业在真正意义上得以“回归”。
(五)中国社会工作的快速发展阶段
自1987年“马甸会议”召开以来,中国社会工作的学科地位得以逐渐确立,并取得了快速发展。比如,1991年7月,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后更名为“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成立。1992年7月,加入国际社会工作者联合会,并成为正式会员。1994年,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成立。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战略部署。2009年,增设社会工作专业硕士,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等33所高校、科研院所成为首批教育试点单位。2010年,“社会工作人才”被写入《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纲要(2010—2020)》。2012年,中央19部委联合发布《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1—2020)》。与此同时,国家陆续颁布了助理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师、高级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考试相关办法、条例。另外,目前我国已经开设社会工作本科的院校有300多所,开设社会工作硕士的有100多所,另外有部分院校在社会学博士点中自设“社会工作”、“社会工作与管理”、“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等研究方向。而且高等教育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等陆续出版和翻译了一批我国经典社会工作专业教材、著作。总之,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中国社会工作在教育、教学、学科建设等方面均取得了较快发展。
二、结缘:中国社会工作和社会学的渊源剖析
基于对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史的梳理,笔者认为,中国社会工作与社会学的关系、渊源可以用“结缘”二字加以概括。所谓“结缘”是指与人结交的机缘。比如,冰心(1923)就曾对结缘有过较为形象的论述,“小孩子满握着煮熟的蚕豆,大家互赠,小手相握,谓之‘结缘’,这两字又何其美妙”,换言之,在结缘的过程当中,强调的是互赠、相握。那么,中国社会学和社会工作是否也是这样的呢?笔者认为,中国社会工作与社会学“结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学科分期的相似性:同时传入,同时中断。对于中国社会学发展史的阶段划分,郑杭生(2000)认为早期的社会学可以分为1919年以前的传入阶段和1919年到1949年的发展阶段,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学的发展经历了学科中断期和恢复重建期。对于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历程而言,王思斌(2006)、孟亚男(2012)、彭华民(2017)和彭秀良(2016)等人都认为社会工作专业在20世纪上半叶传入我国,并曾经在1949年后经历过较长的学科中断期,而在改革开放后才得以恢复和发展。可以看出,社会工作和社会学几乎是在同一时期传入我国,而且在院校调整的过程当中,社会学和附属于社会学的社会工作均被取消,即二者是同时被中断的。
第二,有两个共同的思想源头:脱胎于西方,落地于本土。一方面,中国社会学和社会工作均属于“舶来品”,主要来自于西方国家,具体来说是欧美,部分是由日本作为媒介加以引入的。二者拥有共同的西方思想源头和时代背景,即早期古希腊、古罗马的社会思想,以及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另一方面,社会学和社会工作在中国均能够找到思想渊源,比如景天魁(2017)就认为,社会学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的荀子群学。也有学者(王思斌,2002;黄耀明,2010)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思想(如民本、仁政、兼爱等思想)是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重要思想源泉,还要学者认为,古代的义仓、义赈等形式是社会工作的重要表现。因此,可以认为中国社会工作和社会学是同时脱胎于西方,并落地于中国本土的两个学科,它们拥有两个共同的思想源头,换言之,从本土的思想渊源视角来看,中国社会工作和社会学可以追溯到中国的“群学”和“义学”传统。
第三,早期的社会工作授课教师多为社会学背景出身。结合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相关史料来看,早期承担传播社会工作知识、教授社会工作专业方法、指导社会工作专业实习的教师基本上拥有社会学专业背景。比如,在社会工作的引入阶段,步济时系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硕士、博士,葛学溥在布朗大学主修社会科学和圣经研究。再比如,朱友渔系我国最早进行社会工作研究的本土学者,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博士。此外,以燕京大学的社会工作为例,杨开道系密歇根农业大学社会学博士,李景汉曾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主修社会学及社会调查研究方法,雷洁琼获得南加州大学社会学硕士学位。总之,在中国社会工作的早期发展阶段,拥有社会学等学科背景的学者为社会工作知识的传播、社会工作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四,早期的社会工作专业、队伍主要由社会学系组建。从社会工作最初的引入过程来看,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是该校传播社会服务(社会工作)知识和促进专业教学发展最为重要的机构,沪江大学社会学系推动了社会工作社区服务的发展。继燕京大学社会工作教育起步之后,复旦大学、暨南大学、上海大学,苏州东吴大学、教育行政学院,杭州的之江大学,南京金陵女子学院,山东齐鲁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北京清华大学、辅仁大学等先后成立社会学系,或开设社会工作方向等课程。因此,早期的社会工作专业主要依赖于社会学系的发展。
第五,期刊、教材和课程设置方面,社会学和社会工作得以共融。在期刊方面,《社会建设》杂志曾成为社会学和社会工作对话的重要平台。在教材方面,蒋旨昂的《社会工作导论》、言心哲的《现代社会事业》、李安宅的《边疆社会工作》、朱亦松的《社会政策》等社会工作教材都对社会学知识有所涉及。在课程设置方面,言心哲提到的“社会事业系必修及选修课程草案”,把社会学、社会调查与研究方法设置为社会工作(社会事业)专业的必修课程。而从“民国政府教育部修订后的全国高校社会学系课程设置(1944年)”来看,社会学、统计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制度、社会调查、社会事业及行政、社会思想史、人类学、农村社会学、都市社会学、中国社会问题、中国社会制度史、中国社会思想研究、近代社会学理论、毕业论文等为必修课。社会支持、社会事业史、社会变迁、农民问题、家庭问题、犯罪学等为社会学系选修课程(一),社会学专业必修选修28—38学分。合作事业、儿童福利、精神病社会工作、医药社会工作、妇女工作、个案工作、团体工作、社区工作、边疆社会工作等为社会学系专业选修课程(二),社会行政专业必须选修28—38学分。基于以上内容可知,在社会工作和社会学的发展初期,二者的课程设置存在共融的情况,即均把彼此专业课程设置为专业必修课程。
第六,社会学家在社会工作的恢复重建过程当中起到关键作用。结合中国社会工作的恢复重建过程来看,“马甸会议”促使中国社会工作的学科地位得以重新确立。“马甸会议”中大量的社会学家在其中起着重要的推波助澜作用,比如雷洁琼、潘乃谷(代表费孝通)、袁方、苏驼等人,他们均拥有社会学专业的学科背景,是我国知名的老一辈社会学家。他们曾不断呼吁社会工作、社会学应当恢复。再比如,著名社会学家雷洁琼就曾在“第一期社会学讲习班”主讲社会工作课程,并曾在多个会议当中呼吁恢复社会工作专业,在“马甸会议”当中,她再一次提到“民政工作就是社会工作”的论断,进而促使社会工作专业在我国得以恢复,并获得官方认可。
三、一个讨论:来自我国社会工作发展历程的启示
近年来,中西方学术界关于“社会工作与社会学存在何种关系”的讨论愈发频繁。比如,何雪松(2015)认为,社会工作不应当被简单理解为是应用社会学或社会学的应用部分,中国社会工作的框架体系有待进一步厘清,专业边界也有待进一步明确。因此,需要参与到美国社会工作学界正在热议的“社会工作学”(science of social work)这一大讨论当中。李迎生(2017)认为,社会工作学科的地位至今处于一个较为尴尬的境地。他强调,社会工作长期作为社会学的二级学科加以发展有其特殊的历史传统和现实依据,但是如果因此忽视了其综合性、交叉性应用学科的实际,则不利于这个学科和专业的建设。事实上,对于中国社会工作与社会学关系的讨论、中国社会工作未来学科建设的讨论都不可避免地需要回顾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史,探寻中国社会工作和社会学的“结缘”过程,梳理中国社会工作学科建设的历史因素,进而为当下的讨论提供一个有所助益的可能性解释。比较当前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现状和民国时期社会工作的发展历史,有些事实必须承认:比如,当前我国社会工作教师中拥有社会学教育背景的占了绝大多数,和民国时期社会工作发展状况是一致的;再比如,当前绝大部分高校依然将社会工作放在社会学院、社会学系下面进行培养,拥有独立的社会工作教育中心、社会工作学院的学校数量非常少,这和民国时期社会工作的发展状况也十分相似。因此,在未来的有关社会工作学科地位、学科建设、课程设置等方面的探讨必须及时回顾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历史,必须承认中国社会学与社会工作曾经“相伴相随”,社会学对于早期的社会工作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也需要清楚中国社会学对于社会工作的作用只是促进而不是主导。因此,必须积极思考社会工作和社会学的学科边界,并加强对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史的重视程度和研究力度,在梳理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历程当中总结有效经验和启示。惟有如此,中国社会工作较为独立的学科地位才能够得以正式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