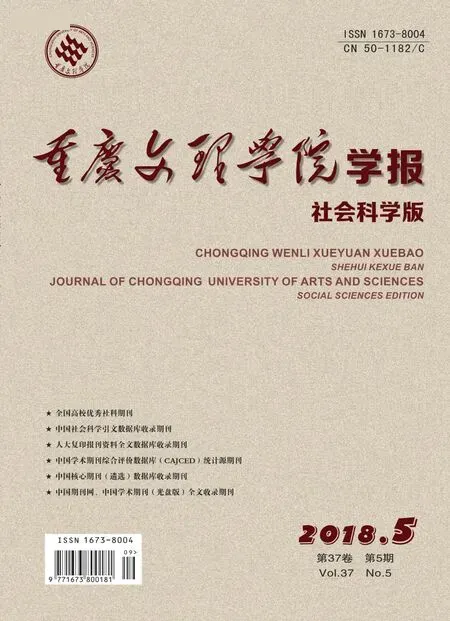变异与误读:论马雅可夫斯基对“十七年”诗人的影响
——以郭小川、贺敬之为例
杜娟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符拉基米尔·符拉基米罗维奇·马雅可夫斯基是苏俄诗歌史上最为著名的诗人之一,被认为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诗人。1949—1966年即中国“十七年”时期,“革命”作为当时的一个核心语汇,成为凝聚着“十七年”诗人理想和期望的一个有着克里斯玛般魔力的符码。在这一符码的凝聚下,新中国掀起了翻译和阅读马雅可夫斯基作品的高潮,新中国建国伊始崛起的一些作家几乎都受到过马雅可夫斯基的影响,例如“十七年”诗坛重要的两位诗人贺敬之和郭小川都明确表示过对马雅可夫斯基创作的认同与赞美,诗歌上也表现出了诸如“楼梯体”的借鉴。“十七年”时期,马雅可夫斯基的影响力至少在表面上达到了其他任何一个时代都难以企及、无法超越的高峰。
一、马雅可夫斯基在“十七年”中国——影响形成的可能与实证
相似的思想意识、身份认同及历史时代背景成为马雅可夫斯基在新中国形成影响与接受关系的客观原因。马雅可夫斯基早在少年时期便对马克思思想有了极大的兴趣,并渐渐走上了他的革命道路,虽为此三次入狱,但对革命的情感却与日俱增,后来更是获得“苏维埃时代最伟大的诗人”身份。在新中国人们的心中,马雅可夫斯基与他们有着共同的信仰与同样的身份认同。中苏相似的时代经历使两国在不同的时间不约而同地出现了那个时代背景下独特的文艺“症象”,即文学“是一件人工产品,一种社会意识的产物,一种世界观但同时也是一种制造业”[1]。正是这样的时代背景为一些诗人提供了大显身手的空间舞台和创作环境,造就了一大批的无产阶级诗人和社会主义歌手。如果说“我们谈马雅可夫斯基的生活和创作道路,就要谈作为个人的马雅可夫斯基如何碰到了作为一个伟大社会现象的无产阶级革命”[2],那么,同马雅可夫斯基一样,离开了这个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新中国诗歌的一切也将无从谈起。无论是思想、身份还是历史背景,这位苏俄诗人都极好地与新中国形成对接,两者间影响与接受的关系因此自然而然地形成并发展。
马雅可夫斯基自身所具有的国际主义的人道精神成为其在新中国形成影响与接受关系的主观原因。“马雅可夫斯基的这种爱国主义,也就是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革命的人道主义。……也热爱无产阶级的兄弟之国。故不仅苏联红旗里面有马雅可夫斯基的心和血,就是我们今天的五星红旗里面也有他的心和血。”[3]马雅可夫斯基对革命与新政权的热爱与憧憬之情并不是流于大势所趋的盲目从众,而是以国际人道主义的胸怀真正关心着世界人民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尤其是对中国人民疾苦的关注在他后期的诗歌中得到高度体现。1924年,苏联组织了“滚出中国!”援助会,马雅可夫斯基就写出了《滚出中国!》(亦译“不准干涉中国”)一诗;1927年,北伐军到达上海,上海工人起义,他就做了一首题为《最好的诗》;1929年,苏联政府发表照会抗议中国反动政府的军队袭击中东路,马雅可夫斯基又写了《致中国的照会》……马雅可夫斯基所具有的这种国际主义的人道精神使中国人备感亲切,不仅把他当作一位革命家,当作战斗的鼓舞者,更把他当作最忠诚、最亲密的战友看待[4]。这种主观情感使得新中国对其极有好感,因而“十七年”诗人愿意阅读且从真正的情感上接受他的作品并自觉模仿。
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得到大量译介,他的诗论以及与其相关的种种活动也风靡“十七年”,这成为马雅可夫斯基在新中国形成影响的实证。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在中国的传播可谓源远流长,早在1921年就被介绍到了中国[5],但在新中国建立初的“十七年”才真正进入到其创作的传播高潮,出现了一个空前繁荣的马雅可夫斯基译介热潮。相关翻译工作从之前的英、日语等世界语转译转变为由一批苏俄文学翻译队伍直接从俄文翻译,翻译更为专业、系统,质量也大有提升,其戏剧作品、文艺理论著作以及相关传记著作的翻译都在“十七年”间出现,弥补了新中国成立前的翻译空白。马雅可夫斯基的译介工作在“十七年”取得的成果立竿见影地反映在当时的中国诗坛,一时间,马雅可夫斯基“炸弹和旗帜”“社会订货”等通俗而富于鼓动性的诗论“已经成为中国革命诗歌作者的努力的纲领”[6],诗歌被视为阶级斗争的有力武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成功的积极力量,如著名诗人郭小川“我的诗句是战鼓,要永远永远催动你们前进”[7]、贺敬之“诗,必须属于人民,属于社会主义事业。按照诗的规律来写和按照人民的利益来写相一致”[8]等思想均接受了马雅可夫斯基的诗论影响;“十七年”期间有组织性地举办了多次大型的马雅可夫斯基纪念活动,如1950年在北京举办了马雅可夫斯基逝世二十周年的纪念会后,不仅出版了旨在“纪念苏联天才诗人马雅可夫斯基逝世二十周年”的论文集《马雅可夫斯基》,各大重要刊物也纷纷刊登纪念文章。以上种种都证明了马雅可夫斯基当时在中国的确受到极大的重视。
二、马雅可夫斯基与“十七年”诗人——接受中的变异与过滤
现代阐释学理论认为,接受者对作品的理解阐释总处于历史的发展演变之中,因此任何接受都意味着创造性意义的生成[9]。这种创造性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与变异学中的变异性有相近的意味,反映出由接受者集体无意识和共有文化心理结构建造而成的“接受屏幕”的过滤性质。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苏俄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到20世纪中叶的新中国“十七年”诗人郭小川与贺敬之,无论是时间的跨度还是民族的差异,都决定着后者对前者的接受必然通过“接受屏幕”而产生变异与过滤。
马雅可夫斯基的楼梯式因其恢宏铿锵的气势且便于诵读传播而颇受“十七年”诗人的青睐。但即使是在相似的时代大背景下,外来的马雅可夫斯基式诗歌也未能“中国化”,相反地,“十七年”诗人的诗歌始终保持着自己独特的形式。贺敬之与郭小川在移用马雅可夫斯基的“楼梯式”的时候,都“尽量地注意到了中国语言的习惯……实在不敢生硬地模仿,主观上倒极想创造性地学习”[10]。故两位诗人在用楼梯式创作后不久,都相继创新出了“凹凸式”与“新辞赋体”,在楼梯式的接受中又创新性地加入了部分中国传统诗歌的音韵和语言习惯。例如由于拼音文字与汉字的不同,马雅可夫斯基的阶梯诗是以音节为基本单位的、一定数量的轻音与重音配合形成轻重抑扬的节律,而郭与贺的诗因汉字的四声调而有高低抑扬且有音节长短的对照,形成平仄对应的节律[11];相对于马雅可夫斯基的短句断开、偶有押韵和鄙词俚语,郭与贺的诗则有着大量的排比和对偶,长句自然断开而呈阶梯式排列,句尾押韵,韵律和谐,骈立四字格对称工整,雅致不减,彰显着中国传统诗歌的风格特征。
除却对诗歌形式的变异性接受,“十七年”诗人对雅可夫斯基政治抒情诗的接受亦表现出明显的“中国化”。马雅可夫斯基的政治抒情诗往往致力于在历史的联系中追求叙事高潮以激化情绪,即以高潮为“情结”作为内在结构的聚焦点,使诗形成主体高层建筑式的组合,如《好!》推出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苏维埃共和国十周年两个高潮,像突兀于连山之中的主峰,形成了以高潮为顶点的戏剧式情绪结构[11];而郭、贺二人则更多地继承了中国古典诗词文化中的“感物咏志”与“缘情设景”的意境创造,追求情与景的互融,以意境推动情感升华至高潮。在抒情诗形象的表现上,马雅可夫斯基执着于对现实的楔入,形象的直接性成为诗人的主要追求,表现在状物抒情的具象式[11],如《好!》第19章中“橱窗里陈列着各种物产:美酒、水果。纱罩挡住了苍蝇。干酪十分新鲜”。但郭、贺则更喜用比喻、隐喻和拟人等表现手法使现实超越与升华,着意于形象的间接性,如“把峡谷变成一座马蹄形的山。旧卸妆台打碎啦‘娘娘’住进了新宫殿”“看五千年的白发,几万里的皱纹”。马雅可夫斯基作为未来主义诗人常以夸张的手法追求词语表述的陌生化,显得十分怪诞,但郭、贺的夸张手法则显得自然质朴且富有诗意。
文学自身的独立性决定了它总能从时代强音中找出一丝发声的缝隙,例如与时代大潮流极不和谐的异质性话语——爱情话语与个人话语的表达。无论是《穿裤子的云》还是《白雪的赞歌》都是爱情悲剧且都表现了关于革命的主题,但显然,两者对爱情话语的表达方式甚至是表现目的都是迥然不同的。马雅可夫斯基在《穿裤子的云》中对爱情的书写热情而执着,爱情败给金钱的无奈激起诗人对革命的呼唤,个人婚变的悲剧于是与社会大众的抗争自然地结合,诗人的情感整体上呈喷发之势;然而郭小川的《白雪的赞歌》则正相反,对爱情的书写显得暧昧而矛盾,女主人公始终是挣扎、控制的姿态,爱情在这里不再是理应勇敢追求的幸福,而是需要用理智与贞洁去规避的深渊,爱情与革命也不是自然而然形成联系,郭选择了“强行斩断了爱情叙事本来的语义延展逻辑,将爱情忠贞置换为政治忠贞,从而完成了革命主题的凸现”[12],诗人的情感整体上呈压抑之姿。马雅可夫斯基和“十七年”诗人的诗歌中也经常出现“我”这个词,尽管都有表现个体与集体的意思,但在个人话语表达的意义上是不尽相同的。由于未来派提倡标新立异的自我,标榜个性,因而诗人不可能抛弃表达独立个性而与集体同化,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中因此常出现自命不凡、张扬而又孤独敏感的自我形象。“十七年”这个强调集体意识的时代与“我”的个人意识是不相容的,故郭小川与贺敬之诗歌中的“我”多是以很和谐的音调插入主旋律中,呈现出“水与海洋”的低微的自我姿态。当然,重读经典的思潮开始后,郭小川一些很有争议但却充满个性化魅力的诗篇亦能从侧面解读出属于个人的忧伤气质与敏感神经,如《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一个和八个》,在喧嚣与热闹的缝隙中流露出属于个人话语的敏感、孤独的异质性,但是郭小川的个人话语始终是内敛而隐晦的。
马雅可夫斯基诗歌的内容也更为广泛,他的诗作不仅仅有对祖国的赞誉与高歌,表达着对革命的爱与对资产阶级的恨,更重要的是还包括了对新政权新社会种种问题的批判与讽刺,如有名的讽刺诗《开会迷》通过离奇的想象有力地讽刺了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中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讽刺”是马雅可夫斯基诗歌十分醒目的成绩,亦是其诗歌特征研究中不容忽略的一点,而在“十七年”诸多有关马雅可夫斯基的译介作品及研究成果里,其讽刺诗的重要性与艺术价值却鲜有表现,在郭小川、贺敬之等“十七年”诗人的诗中更是很难看到这样的讽刺特征,尽管郭小川在1954年与1955年两年间写过《代行检讨的故事》等讽刺官僚主义者和个人英雄主义的讽刺诗,但思想性不十分深刻,艺术上也不大成功,此后更是放弃了对讽刺诗的尝试。对马雅可夫斯基影响的过滤于“十七年”诗歌的发展无疑是弊大于利的,除去诗人的个人因素外,更大程度上是那样一个政治思想高度集中统一的时代所造成的遗憾。
三、对马雅可夫斯基影响的夸大、误认及原因
尽管“十七年”时期对马雅可夫斯基的介绍与传播趋于繁荣,“十七年”诗人也毋庸置疑地受到其影响,但影响也分表里深浅,直至今日,对马雅可夫斯基影响的性质和程度依然普遍存在夸大与误认。马雅可夫斯基之所以形成如此大的影响,是因为“十七年”文艺界都将其视为一个纯粹的革命战士,将其作品理解为对共产主义革命及共产主义事业的深情赞美,却忽略了他作为一个未来主义诗歌领袖所具有的悲剧色彩,即影响本身便起于当时文艺界对马雅可夫斯基身份与情感的不准确定位,存在着误读与误认。
“十七年”诗人中,郭小川与贺敬之在文艺界中被认为是受马雅可夫斯基影响的典型代表,贺被冠之为“17岁的马雅可夫斯基”,郭的楼梯式诗歌被认为是“舶来品”……因此马雅可夫斯基对“十七年”诗人的影响被认为是“直接而深远”的,更有甚者字里行间似乎表露出如果没有马雅可夫斯基就没有“十七年”诗歌的兴盛局面,但这些名号、见解在实证考察之中却被证实存在着个人化的情感色彩甚至有待探讨的真伪性问题①。虽然郭、贺二人在楼梯式的诗歌形式与夸张的表现手法上像极了马雅可夫斯基,但接受者在认识外来文学时,由于受到前理解的限定,其“认识不仅在其中被制约、规定和生产,也在其中具有制约、规定和生产作用”[13]。笔者已在文章第二部分论述了二人对楼梯式并非是全盘挪用,此处不再赘述,且中国文学传统中的“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道难摹,精言不能追其极;形器易写,壮辞可得喻其真”都清楚地说明,我国古代已经对想象和夸张在诗歌创作中的地位与作用有了足够的重视[14],这都是中国诗歌创作的一般特点,因而郭、贺等“十七年”诗人诗歌手法的运用未必就是完全受马雅可夫斯基的影响。而且,一是二人并未与马雅可夫斯基有过直接的沟通交流;二是没有资料显示二人对马雅可夫斯基本人及其创作原作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工作,即对诗人与作品的本质及真实情感不曾深入了解;三是二人的诗歌创作只是浅显地与马雅可夫斯基诗歌部分特点相似,但实则有着很强的民族性,且二人的接受行为都有创新与变异,因而所谓的“直接而深远的影响”是对马雅可夫斯基影响的一种夸大与误认。
导致误读马雅可夫斯基,夸大与误认马雅可夫斯基影响的原因有很多,笔者认为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对马雅可夫斯基的精神世界还欠缺真正的关注和研究,我们了解的马雅可夫斯基只是由当时意识形态高于一切的苏联传播而出的人物印象,我们解读其作品的思维也是苏联与“十七年”的阅读思维定式。马雅可夫斯基真的是一名坚定乐观的无产阶级志士吗?这位文坛巨星的自甘陨落又仅仅是因为情路不顺这一被默认的说法吗?窃以为这些表象下还有更深层次的内容值得探讨。
可以肯定的是,马雅可夫斯基最初是一名忠实的未来主义者,未来主义标榜开创性的秩序,声称“把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等,从现代生活的轮船上扔出去”[15]表现出全盘否定文化遗产的虚无主义立场。马雅可夫斯基虽于1908年加入了布尔什维克,但可以从其作于十月革命前的长诗《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穿裤子的云》等作品中看出,他对无产阶级的理论信仰并不十分成熟,未来主义、虚无主义的影子却得以明显体现,但受到苏联“赐予”的“伟大的无产阶级诗人”这一称号的误导,国内文艺界也认为马雅可夫斯基已然是一名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这是由于忽略了马雅可夫斯基悲剧性精神的内质而形成的一种误读。主张未来主义并非马雅可夫斯基一时兴起,未来主义的精神来源应当是由“白银时代”的精神特质、俄国本土民粹主义传统和弥赛亚情结等复杂的精神与文化胶着在一起建构而成。白银时代的俄罗斯充满了世纪末的悲凉气氛,传统的自由主义和知识分子失去精神支柱,正如梅列日科夫斯基所描述的:“人们从未像现在这样,内心里感到需要信仰,而理智上却明白无法信仰,在这种病态的、无法解决的不和谐中,在这种悲剧性的矛盾中,如同在前所未有的思想自由和敢于否定中一样,包含了那种神秘主义需求的最典型的特征。”而在线性时间维度上,弥赛亚意识始终面向终极的拯救,直指正义和真理之国,执着于这一理念的俄国知识分子习惯站在未来回视当下,从“应有的善”看待世界与社会,充满改造社会使之完善的冲动和激情[16]并将其斥诸“彻底砸烂旧世界”的激进的革命情绪;民粹主义则怀着对资本主义的“恐惧症”渴望直接过渡到另一个阶段,以虚无主义的态度评价已有的文化与现实,承载着俄国“忏悔贵族”的负罪感与痛苦,将平民群众极端理想化。由此可见,马雅可夫斯基“革命”表象下真正的精神建构,是集合了以上复杂、矛盾和理想化的种种思想精神,而这种种精神交织在一起共同整合成了一种矛盾而又纯粹、理想而又焦虑、狂热而又悲情、“未来”又传统的马雅可夫斯基式的未来主义。而他之所以投身无产阶级革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无产阶级革命风暴恰逢其时地暗合了马雅可夫斯基原本便极不满于现状,希望淘尽一切而创新出一个乌托邦式的未来主义思想。马雅可夫斯基希望可以借助十月革命这股强大的力量来完成自己复杂矛盾且乌托邦式的精神理想,并为此不惜投入全部的热情对它进行狂热的歌颂,他将力量、现代化、未来和净土等未来主义所推崇的理想代入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幻想之中,形成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融为一体、彼此成就的表象。但他这种貌合神离的狂欢假象很快露出端倪,马雅可夫斯基的内在精神决定了他很快产生了对现实生活的悲剧感,“表面上看,马雅可夫斯基放荡不羁,而实际上,他痛苦不堪,在现行社会制度下,生不如死”[17]。此时的马雅可夫斯基选择了结束生命,但他的死并不像外界传言的那样平凡简单,而是包含着“当我们四十岁时,比我们更加年轻有为、更加身手矫健的青年人将把我们像废纸一样扔进纸篓里——我们甘愿这样!”[18]这种永远留在年轻人时期和甘愿牺牲的未来主义精神内涵。在苏联当时的政治背景下,自杀对一个革命者来说是一件十分不光彩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革命的逃避。因此,实际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对马雅可夫斯基的死讳莫如深[20],直至斯大林突然称其是“苏维埃最优秀、最有才华的诗人”,于是苏联文学界开始为马雅可夫斯基增色添彩,力图将其捧上神坛,但诗人的未来派身份却让苏联文艺界人士十分为难,未来派于他们来说是一个颓废的虚无主义流派,不能产生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无产阶级诗人。于是,他们便想极力证明马雅可夫斯基不是一个未来主义诗人,或者想证明他和未来主义之间其实存在区别。久而久之,这样的研究心理竟然形成了气候,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19]。这对中国学术界无疑有着深刻的影响,在我国,尤其是“十七年”时期,马雅可夫斯基被认为是一个纯正的无产阶级诗人,而对于他作为未来主义诗人的情感、作用与地位,我们随着苏联选择了忽略与规避,对于其悲剧性的精神更是少有关注。
马雅可夫斯基在苏俄与 “十七年”中国都是名声大噪,他对中国“十七年”诗人的影响之大是有目共睹的,但这位外来影响的放送者又受到“十七年”诗人本国土壤的多少制约与过滤?与时代需求的高度契合使马雅可夫斯基既定地成为“十七年”诗人接受的对象,马雅可夫斯基对“十七年”诗人的影响因此的确成为现实,但那个时代在成就了他的名誉与影响力的同时又遮蔽了其真正的情感精神与影响程度。忽略了马雅可夫斯基未来主义思想精神来源的分裂性和虚无主义特征形成的悲剧性精神内质,所形成的影响就不可能是直接、深入的,因而马雅可夫斯基对“十七年”诗人的影响是复杂的,具有间接性的,仅流于较为浅显的层面。对于这样的结论,窃以为,一方面我们应当为“十七年”中国文艺能坚持“以我为主”来实现外来文学的中国化而庆幸,另一方面也应尽量客观地正视对马雅可夫斯基的误读,以及对其影响的夸大与误认,以便于能将马雅可夫斯基的影响研究深入至文学背后的民族心理与文化,从而开拓出一番更为广阔的天地。
注释:
①李疏桐在《影响的误认与释疑——论贺敬之接受马雅可夫斯基影响的复杂性》一文中认为,“17岁的马雅可夫斯基”是何其芳作为当时鲁艺文学系的系主任对少年诗人的一种鼓励;而郭小川亦在《谈诗》中表示“不是想搬运马雅可夫斯基的现成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