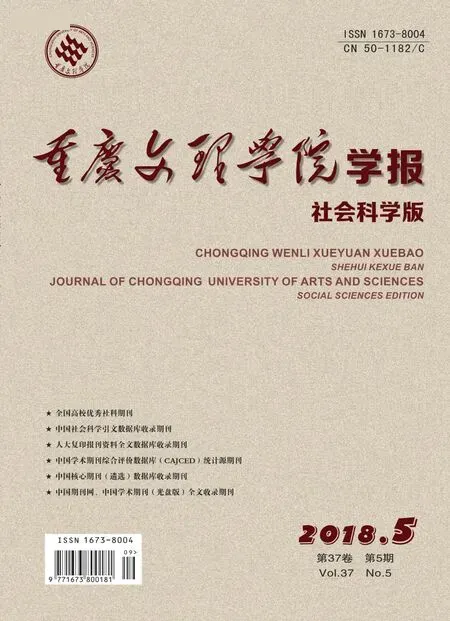口述历史记忆的建构与发展
——一个基于桂林民歌传承主体的调查报告
刘梦舒
(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口述历史被认为是一种“过去的声音”,但它却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被记忆主体保存到现在。桂林民歌传承主体的口述历史即为典型,它通过一代代歌王的主动记忆而保存至今,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桂林民歌作为一项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传承主体通过口述方式来展现个人所经历的生活和不同年代的事件。这些口述历史记忆往往带有他们自身的主观色彩。因此,他们能够根据自己的叙述和传承方式建构起自己的口述历史记忆,将自己的记忆保存、传承下去。本文基于桂林民歌的传承主体进行田野调查,以期对口述历史记忆的建构与发展有所帮助。
一、桂林民歌传承者的“他者意识”与被提及的“记忆”
“记忆”是人与生俱来的能力,历来为心理学研究所重视。自20世纪20年代起,“记忆”的研究从心理学角度拓展到社会和历史角度,成果斐然。目前,一些学者已针对“记忆”问题,提出了“个体记忆”“集体记忆”“社会记忆”“历史记忆”等概念。本文以口述历史记忆为切入点,通过田野调查来研究桂林民歌传承主体在传承和保护民歌方面所起的作用,不失为一个新视角。虽然桂林民歌的传承者本身没有意识到他们在民歌传承过程中的作用,但显然在口述历史记忆方面他们有“他者的意识”,这种“意识”将自我与他人联系起来,使他们在“过去”与“现在”的双重语境中承担起“传承人”的角色。为便于讨论,我们对这三种“记忆”关系进行阐述。
(一)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
1925年,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创作了短篇小说《柏林导游》,在这部小说中,他不仅叙述了自己亲眼看到的情境,而且还通过自己的记忆去描绘现今的事物。他一边回忆18年前在彼得堡,人们如何套上许多马匹去拉有轨电车,一边继续描写在柏林,人们如何把一节挂车接在有轨电车的主机上。在我们看来,这种“描绘”应是作者关联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的表现。这样,18年前的有轨电车和现在的有轨电车依赖记忆而连接起来。同年,法国社会心理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提出了“集体记忆”概念。他认为,“集体记忆”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保证集体记忆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提取该记忆的延续性”[1]。此外,他还指出,“个体是在集体的框架之中进行记忆的”[1]。也就是说,个人的记忆总是离不开他人的存在;在个人开始回忆时,他人的经历也会在其脑海中显现。这样的经历不仅对个人产生过重大影响,而且个人也在此段经历中有过最深刻的情感体验。因此,人们的记忆总是集体性的,它从来不是一种孤立的状态,而是“我者”和“他者”、个人与集体的结合。
(二)集体记忆与社会记忆
关于“社会记忆”的概念,学界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哈拉尔德·韦尔策认为:“社会记忆是一个大我群体的全体成员的社会经验的总和。”[2]此后,莫里斯·哈布瓦赫在其著作中提出了“不具有社会性的记忆是不存在的”论断,据其理解,记忆应是具有社会性的。美国学者保罗·康纳顿在“集体记忆”的基础上又提出“社会如何记忆”的观点,其在《社会如何记忆》一书中指出了社会记忆的保持有纪念仪式与身体实践两种途径。他认为“有关过去的意向和有关过去的记忆知识,是通过(或多或少是仪式性的)操演来传达和维持的”[3]3。这意味着社会记忆仍然离不开集体的行为和实践。由此我们可以发现集体记忆具有社会性,每一个集体都在社会关系中寻找认同。同时,社会记忆也具有集体性,每一段社会记忆以集体记忆为基础。因此,两者相互融合,集体记忆也是另一种社会记忆。
(三)集体记忆、社会记忆与历史记忆
在《集体记忆与历史记忆》一文中,莫里斯·哈布瓦赫认为“历史是事件之印象,集体记忆是传统之所在”[4]。值得注意的是,爱德华·希尔斯在《论传统》一书中也将历史归为传统的范畴。同样,保罗·康纳顿也将会记忆的社会置于历史框架中去:“我们把当事人的行为归位到他们所属的那个社会场景下的历史中。个人生活的叙述是相互关联的一组叙述的一部分,它被镶嵌在个人从中获得身份的那些群体的故事中。”[3]18集体和社会记忆是历史之所在,两者可以被置于历史场景中叙述。与之持相同观点的还有赵世瑜,他认为“历史是一种集体记忆,并且记忆具有传承性和延续性”[5]。因此,历史不仅仅是一种对事件的印象,还是个人和集体关于生活叙述的记忆,历史记忆是社会和集体关于“过去”的记忆。
通过对“记忆”研究的回顾与分析,我们认为个体记忆、集体记忆、社会记忆与历史记忆之间不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而是相互融合的关系。记忆是个体与集体的结合,社会通过置于历史场景中的集体来记忆。个体记忆同时具有社会性、集体性和历史性三个特性,个人的口述历史记忆也同样具有社会性和集体性。桂林民歌传承主体口述历史记忆的建构即为此种相互融合的典范。本文结合社会记忆、集体记忆的相关理论分析桂林民歌传承主体口述历史记忆的建构与发展。
二、调查过程与方法
桂林民歌传承人秦国明被誉为“歌王中的歌王”,为桂林乃至广西培养了大量民歌文化传承人,他编辑的《农民识字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藏,如今87岁的他仍然活跃在桂林民歌的舞台上,是广西民歌文化传承的核心人物。我们的调查以歌王秦国明及其弟子为中心。我们曾先后辗转于秀峰区、资源县、阳朔县分别对秦国明、罗歌王、黎歌王进行访谈,获得了第一手资料。在准备去临桂县找梁歌王进行访谈时,我们得知梁歌王已不幸病逝,仅给后辈留下了一本自编自写的《名人之乡歌王传》。此书记录了他的一些个人经历及山歌、戏剧作品。我们采取了两种调查方法。
(一)无结构性的现场访谈法
我们在访谈中主要与歌王聊天、唠家常,以此拉近我们与歌王的距离,深入了解其内心世界。
(二)跟踪调查法
由于秀峰区的距离优势,我们对秦国明展开了跟踪调查,每周周末都会去他家里与他聊天,跟随他参加一些歌唱活动。需要指出的是,梁歌王虽然不能亲自口述,但《名人之乡歌王传》就是他文本化的“口述史”。为保证原创成果最大的真实性,本文转用了《名人之乡歌王传》中的部分内容。
三、桂林民歌传承主体口述历史记忆的建构与发展
桂林民歌传承主体已经意识到自身的历史记忆如何通过口述的方式诉说,即这是一种被建构的口述历史记忆。他们在诉说历史记忆的同时,也在通过各种媒介不断保存、发展自己的记忆并充分表达个人情感。这样,历史记忆就在叙述和传承实践中被建构和发展,也使我们能够从他们的话语中认识到植根于民间土壤的桂林民歌对大众产生的深刻影响。
(一)在集体框架中口述
个体记忆虽然会适应“我者”的性格以及个人生活的框架,但它并不是自我独立和封闭的。在桂林民歌传承主体的口述中,总是离不开“他者”的存在,他们从他人经验及角度出发,超越时间和社会空间的限制,“超结构”借助他人的言语和想象“超越自己并进入成为自身的他者之中”[6]。在记忆主体成为“自身的他者”时,他们首先会进行无意识的叙述,讲述“我”的生活经历;然后,在无意识叙述中通过自己的理解建构起“他者”的形象;最后,在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融合中建构起自己的口述历史记忆。因此,他们在回忆时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对自身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这个人通常是引导他们踏上“歌唱之路”的人,或是他们的教导者。
在秦国明的口述历史记忆中,他的母亲便是一名引路人和教导者。在他的印象中,母亲是他最重要的人:
我出生于临桂县土桥下屋村,我的妈妈原来就是村子里的山歌手,我从小就跟着妈妈学山歌。1943年,我以全校第一名的好成绩毕业,只能回到家里做个看牛官。“中学”这个词那时候对我来说好可怕,好有钱的人才能去读中学,在村子里我没有见过一个中学生,三十年代的时候就没有中学生。虽然我没有钱去上学,但是歌还是照样学,难过就难过在没有钱,不给上学。后来,母亲用歌来劝我:“自古好事要多磨,家穷读书走穷路,夜读私塾日干活。”①
秦国明在母亲的支持下实现了读书理想,他在讲述自己年少的经历时,总是会无意间想起自己的母亲,将母亲化为记忆的一部分。同样,梁歌王、罗歌王、黎歌王的口述也离不开“他者”。一方面,他们生活在民间的“歌海”中,村民便是引路人。比如,罗歌王出生于风景秀丽的资源县河口瑶族乡的大湾村,村中歌俗盛行,当地四十岁以上的人都会唱歌。罗歌王便是在村民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开始学习山歌。罗歌王在一次访谈中说:“我从小就喜欢文艺,我喜欢听人家唱山歌,我一听后脑子里面就有记忆。可以说,从小时候起,我便在村子里听村民唱歌。”②
另一方面,他们通过别人帮助走上歌唱之路。1967年,梁歌王弃学从农,跟随闻名于方圆十里的歌师——梁彰珠学习山歌。“梁歌王在他的指导下学到了很多山歌知识。”③
2014年,黎歌王开始在微信山歌群里学习唱歌,“‘阳朔山歌群’的群主梁××和群管理员钟××请我进入歌群,从此我也开始学习如何唱山歌”④。
桂林民歌传承主体的口述历史记忆始终脱离不了集体的框架。费尔巴哈指出,人是一种“类”的存在,脱离了“类”的关系是不存在的。桂林民歌的传承主体生活在他们熟悉的环境中,通过回忆与自己相关的人来构建自己历时性的记忆,使“他者”成为自己的一部分,这正是个体记忆在集体框架中的口述形式。
(二)在自我认同之内口述
马克·弗里曼在《传统与对自我和文化的回忆》一文中提到“自传式理解”,他认为“自传”是“我”在自我叙述中的地位,是一项在自我认同内运用造就自我的多种根源对这种认同进行修改的工程。桂林民歌传承主体的口述历史记忆其实也是一项“自传式理解”,他们通过对自己的理解来建构一个在其认同之内的自己。通常这种建构方式有两种:一是通过弱化别人某方面的能力来强调自己超越常人的歌唱天赋,二是通过叙述参加各类歌唱比赛来显示自己的荣誉感。通过这种自传式的理解,桂林民歌传承主体不断在自我认同之内造就自我,从而建构起自身的口述历史记忆。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87岁高龄的秦国明与其他歌王造就自己的方式不同。由于生活年代的不同,秦国明总是会谈及他去北京唱山歌和创办农民文学院的故事,叙述真正的快乐和艰辛正是他对自己的认同之所在。在谈及《农民识字歌》时,他说道:
“我给农民扫盲,在资源县的大山里编写了《农民识字歌》。《农民识字歌》要将1 700个常用的生字与山歌结合起来,以前也没有相关的教材,我也无法参考,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你要想办法把这1 700个生字编成‘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还要注音。1982年,《农民识字歌》荣获首届全国农村读物评选二等奖,我便第三次唱歌去北京领奖……”
1985年5月,中央《农民日报》报道“全国第一家农民文学院在桂林开学”。秦国明便是桂林农民文学院的创始人之一:
“我在永福县农民秦××家里开班上课,还创办《农民文学报》来发行刊登学生们的作品。后来经费不足,我就自愿走出桂林去,送教进山区。”
秦国明为农民扫盲,教农民唱歌的举动是一种情感认同,他感同身受,由此生发了对农民的感激之情,并在这种情感认同中践行自己“为农民传授知识”的信念。这一信念和在此之下的行为便是他对自己的认同,其口述历史记忆也就在自我认同内建构。
其他歌王则通过叙述他们比赛所获得的荣誉和歌唱天赋构建自己的口述历史记忆。梁歌王写到,自己在2000年至2005年代表临桂县山歌队参加桂林市“漓江之声”山歌擂台赛,连续6年荣获优秀歌师称号,并连续三年夺取了冠军,被评为桂林市歌王。罗歌王则谈起他与老歌手对歌的经历来强调自己的天赋:
“他们一唱我就接,我接得越来越快,他们就失去自信,越来越慢了。因为我是第一次与他们高手过招,就不知道怎么停下了。就这样,等到天亮了,四位歌手突然间又换成了贺郎歌的曲牌,本以为换了曲牌我不会唱就输掉了比赛,可是我会唱贺郎歌,越战越勇。”黎歌王则通过展现自己的编歌技巧及能力来认同自己:
“一些景区里的导游词和打油诗我都背得滚瓜烂熟,我的讲解也能让客人开心和满意,他们还封了我一个绰号叫‘野导’”。
桂林民歌传承主体在绘制自己更大的自我图像时,会将自我认同的内容凸显出来,以对自己的身份进行定位。这种“自我认同”并不是一种反思性的认同,而是在“自传式理解”中实现彻底管理自我的方式之一,他们将此方式同构在自己的历史记忆中,代表着自身过去的荣誉。
(三)埋藏存储记忆
记忆基于记忆主体的心理因素而带有选择性。扬·阿斯曼根据这种选择性将记忆分为“功能记忆”和“存储记忆”,他认为“功能记忆作为一种建构是与一个主体相连的,主体的构建有赖于功能记忆,即通过对过去进行有选择、有意识的支配……相反的,存储记忆不是以身份认同为基础的,即比起功能记忆,它包括了更多且不同的回忆”[7]。
在上文中,歌王的口述历史记忆是在其生活中认同自己的功能记忆,这一记忆经过他们的建构和整合被显现出来。但是,残留在心底的存储记忆却难以诉说,当我们无意识问及他们家人或自己的真实情况时,他们便拒绝回答此类问题,并委婉地说:“这没什么好提的。”在笔者恳请他们说出时,他们便会隐隐地透露出“被埋藏的记忆”。被埋藏的存储记忆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受社会意识形态限制而难以诉说的事件,二是个人非常隐秘及辛酸的经历。毋庸讳言,这种被埋藏的记忆需要被深入挖掘才能逐渐显现。
在对秦国明的访谈过程中,他在笔者的追问下才道出他在那个年代的经历:
“我为人平和,创作些与国家政策相关的一些作品。为了不让存在于百姓生活中的民间山歌丢失,我就暗暗收集民间山歌的手抄本。”
现在想起那段岁月,秦老师不禁感叹道:“山歌好比月月红,可惜围在刺蓬中,明不给采暗中采,血染双脚当花红。”
在我们看来,这些存储记忆是他们最真实的记忆。记忆有时也会随时光流逝,在无形的背后却另有一番天地。正如桂林民歌的传承主体一样,人往往会把一些记忆埋藏在心底;而在心外,人依然是编织“意义之网”的个体。
(四)在媒介之中鲜活
个人记忆通过与他人的共同生活、语言交流而产生集体与社会记忆,集体与社会记忆则建立在经验和知识的基础上。记忆可以脱离这一基础而转到物质数据载体上,通过这种方式,记忆可以越过代际界限而保持稳定。同样,保持历史记忆的稳定也需要将其附加在物质载体上,而媒介便是口述历史记忆的物质载体,它将记忆通过视觉或听觉的方式保存在书籍、图像或集体活动和实践仪式中。记忆也通过媒介由内在的形式化为外在的形式,并在其中保持鲜活和流传下去。这不失为一种记忆主体既建构记忆又保存、传承、发展记忆的一种方式。
在桂林民歌的传承主体中,秦国明是当之无愧、用心传歌的传承者,广西多家媒体采访过他本人,报道过秦老师的经历。不仅如此,秦老师还保存了大量的照片,编写了大量歌书来反映自己和他人在不同年代的生活,如《钢铁山歌集》《广西歌王小传》等。秦老师曾经说:
“我们家一向都是忠厚传家,宁亏自己不亏别人,借钱给人家不要记,借人家的钱一定要还。我家还被评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和谐家庭’。我准备编写一本《秦氏家训歌》,留给后代相传。”
不论是被保存的照片还是被编写的书籍,都反映了秦老师关于个人品格、家庭和社会生活的记忆,记忆可以通过书籍保存并越过代际传承。
梁歌王和黎歌王也分别编写了自己的作品《名人之乡歌王传》和《歌韵漓情》。《名人之乡歌王传》的前半部分就是梁歌王在叙述自己的经历,他以此为基础,在无意识中构建起自己的历史记忆。黎歌王在《歌韵漓情》的后记部分道出了他编写关于阳朔景点山歌的种种不易,将自己通宵达旦编写山歌的经历与歌作以书籍为载体展现出来,以此种方式将自己的记忆保存并流传。
值得注意的是,与其他歌王将自己的历史记忆编写在书籍中不同,罗歌王更多的是以参加集体活动来重拾记忆。2017年10月22日晚,他带领我们来到了一个村庄看一场由一位民间老艺术家指导、村民自发表演的演出。在演出开始之前,罗歌王说了自己幼年时和这位老艺术家的故事和那时他参加表演活动的一些趣事。歌王的叙述同样也是歌王自己的情感体验,用歌传德的决心、编写山歌的不易、参加活动的喜悦,无一不体现出他们生而为歌的诗性生活。在传承方式方面,我国学者朝戈金指出:“目前各种视频与音频技术的运用所导致的文字向‘超文本’迈进的趋势,这确实已是可以预见到的趋势。”[8]视频和音频技术的运用、活态保护的方式也将在某种程度上代替文字成为保存、记录和传承文化的新方式。同时,新方式将口头的历史记忆转化为文本化、听觉化、视觉化、情感化的历史记忆,使其在媒介中保持鲜活,成为口述历史记忆的新方式。
四、结语
集体记忆和社会记忆是历史之所在。作为一种过去的声音,桂林民歌传承主体的口述历史记忆的建构具有社会性和集体性,建构方式离不开集体记忆。此外,记忆的建构也依赖于主体的心理因素,他们通常会将自己的理解应用到口述记忆中,在自我认同内造就一个带有荣誉感的自我。他们也会有选择地将自身所属的功能记忆与倾听者分享,而把存储记忆深深埋藏。现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更加注重传承人自身的主体性记忆。通过调查,我们发现扎根于民间土壤的桂林民歌不仅是当地人民的口头创作,更是他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情感体验和记忆。唱歌不仅是他们生活的重要娱乐方式,还可以丰富他们的社会关系,甚至增加一些歌手的收入。桂林民歌的传承主体主动将自己原本的口述历史记忆通过文本化、视觉化、集体化的方式在书籍、报刊、集体活动中保存,他们生活的诗性也将自己的口述历史记忆化为情感化的物质性存在,从而成为他们建构和发展记忆的一种新方式。
注释:
① 秦国明的全部口述资料均为笔者2017年6月11日在桂林市秀峰区秦国明家中访谈所得。
② 罗歌王的全部口述资料均为笔者2017年10月27日至28日在资源县罗歌王家中访谈所得。
③ 梁歌王全部“文本化”的口述资料摘自《名人之乡歌王传》。
④ 黎歌王的全部口述资料均为笔者2017年12月31日在阳朔县黎歌王家中访谈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