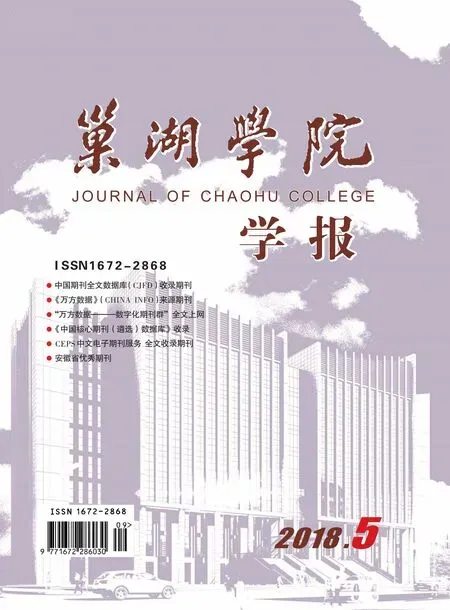论郑保瑞影片中唐僧形象及当代启示
章杏玲
(巢湖学院,安徽 巢湖 238000)
古典小说《西游记》因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成为影视剧改编的“宠儿”。“唐僧形象流传至今,从一个历史人物走进民间戏曲,经文人之手汇入小说,又从小说走向影视,在这一历程中唐僧形象不断变迁。”[1]小说中塑造了“唐僧”传统的儒士形象,他是仁慈心善、信念坚定的取经圣僧,但其身上的迂腐胆小又令人可笑可叹。而影视改编中唐僧的形象往往大相径庭,郑保瑞是香港新锐导演,他现已拍摄了“西游系列”作品,分别是《西游记之大闹天宫》(2014年)、《西游记之三打白骨精》(2016年)以及《西游记之女儿国》(2018年),唐僧形象集中体现在后两部影片中,从“善”僧和“情”僧的角度入手,让观众对唐僧形成新的认知。从小说到影视中“唐僧”形象发生的逆变,是探索观影受众审美需求的一次大胆尝试。
1 《西游记》文本中的唐僧形象
《西游记》小说中,作者肯定他取经心诚志笃,是一个信念坚定的求经者,但是又用较多篇幅批判他身上消极的一面,“遇到事情往往平庸忍让,怯于斗争,耳软心活,有时固执、迂腐到是非不分的可笑又可恨的地步。”[2]总之,文本中唐僧的形象既有正面又有负面,而且将唐僧的软弱、迂腐、脓包更加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因而文本中的唐僧形象并不受读者喜爱。
一方面,唐僧的可贵精神体现在他有着坚定的信念,执着于求经的目标而心无旁骛。“我这一去,定要捐躯努力,直至西天;如不到西天,不得真经,即死也不敢回国,永堕沉沦地狱。”①吴承恩.西游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158.文本引用皆出自此版本,下不另注。带着这样的誓言,唐僧开始了他的西行之路。山高路远对于平凡的僧人来说,已经是一种磨难。更何况还有九九八十一难。虽说一路上有本领高超的徒弟们保护,也有诸神明里暗里的帮助,但是唐僧终究是肉体凡胎,常常是刚出妖洞又入魔窟。但是不管经受了何种磨难,又在西行路上遇到何种危险,丝毫没有动摇他求取真经的信念,更未滞留西行的脚步,可谓“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3]在漫长的西行路上,倘若唐僧没有坚定的决心,执着于目标而坚持不懈,是万难到达目的地的。
另一方面,唐僧的百无一用、怯懦软弱也表现得非常突出。例如在双交岭上,得猎人相救,分不清来人身份之时,就跪在路边,合掌高叫道“大王救命”!唐僧西行的第一个场景,就表现出其软弱胆小的性格。第十四回中,六个强盗各执兵器,大喝留下买路银,“唬得那三藏魂飞魄散,跌下马来,不能言语。”第十五回,唐僧“脓包”的形象更是淋漓尽致。白马被孽龙吃掉,唐僧顿时情绪崩溃:“徒弟啊,你哪里去寻他?只怕他暗地里撺将出来,却不连我都害了?那时候人马两亡,怎生是好!”说着话,泪如雨下。行者忍不住暴躁,发声喊道,“师父莫要这等脓包形么!”类似的还有:第二十回过黄风岭,马前出现猛虎:“慌得那三藏坐不稳雕鞍,翻跟头跌下白马,斜倚在路旁,真个魂飞魄散”;第二十八回误入波月洞看见黄袍怪:“唬得打了一个倒退,遍体酥麻,两腿酸软”;第八十五回唐僧见隐雾山山峰挺立,山势崔巍,暴云飞出:“渐觉惊惶,满身麻木,神思不安。”等等,不一而足。总之,一见危险,魂飞魄散、战战兢兢、体如筛糠等体态特征与唐僧如影随形,也是他的一贯做派。
2 影视改编中唐僧形象的塑造
在郑保瑞的影片中,唐僧不再拘泥于文本中的形象,而是对文本中的形象既有继承更有创新。在《西游记之三打白骨精》中,导演将唐僧慈悲心善的性格加以放大表现,忽略文本中的负面形象。而《西游记之女儿国》中,导演对唐僧形象进行了重新设定,凸显他“情僧”的形象。影片通过对唐僧的二次塑造,贴合人物的真实情感,更加容易引发观众共鸣。
2.1 继承与发展——慈悲心善、度化他人
“三打白骨精”是《西游记》中最经典的回目之一,成为改编的“热点”。在郑保瑞的《西游记之三打白骨精》电影中,唐僧是西行取经的僧人,最突出的性格即慈悲心善,即使是面对心地歹毒的恶人,也慈悲为怀,网开一面。影片中,云海西国国王为了医治右手的恶疾,虽日日服用孩童的鲜血,但并不奏效。听闻唐僧之血可以医治,不禁心生恶念,当悟空赶来相救,欲一棍打死国王时 ,唐僧制止了徒弟。悟空恨道:“这样的人比妖还歹毒,也不可以杀吗?”唐僧虽也看到了国王的恶,但不允许徒弟伤害他。因为在唐僧心里,善恶只是一念之差,佛家弟子应该遏制人的恶念,将善意传播,不抛弃恶念之人,这才是佛法中真正的慈悲之心。一以贯之,当悟空要杀死妖怪幻化的夫人和孩童时,唐僧表示不管出于何种保护,都不应该以杀害他人的性命为代价,最后唐僧宁愿舍弃师徒情分,也不愿背离佛法的真义。影片中的这些片段,都是唐僧慈悲之心的表现。
影片还着力表现唐僧度化他人,弘扬佛法。白骨精一再伤害唐僧,希望吃唐僧肉使自己永世为妖,免受轮回之苦。唐僧知道她的目的,却从不害怕退缩,而是一直教化她,但无奈她怨念太重,宁愿自毁妖身,也不愿接受轮回,重回人间。唐僧甚至在佛祖面前许下誓言,愿意度化她,哪怕付出一切代价。在影片最后,他强烈要求悟空打死自己以助白骨夫人进入轮回,他说:“我原来以为度化众生,就是教化他们。现在才知道,我不入地狱,即使到了西天,也取不到真经。我想好了,一世不消,就度一世,十世不消,就度十世。”作为僧人,他一心向善,身体力行,真正用自己的信念去度化众生,无怨无悔,令人感动。
“三打白骨精”电影中,唐僧形象从文本走向银幕,是对文本形象的继承与发展。郑保瑞导演在表现唐僧时,没有涉及文本中迂腐软弱、黑白不分的“脓包”形象,而是重点表现慈悲善良、度化他人的“圣僧”形象。影片中的唐僧由冯绍峰饰演,他呆萌可爱,颜值高,虽絮叨,但语出禅义,相比小说中的刻板迂腐,更受观众喜爱。影片中,唐僧形象更多的表现出“善”的一面,凸显佛家弟子的慈悲心肠。他不仅自己拥有菩萨般的心肠,还教导弟子也应拥有善意,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去感化他人,甚至不怕牺牲生命,以求度化他人,使人远离苦难和邪恶,最终获得幸福。
2.2 改变与创新——有情有义、领悟大爱
《西游记之女儿国》影片中,冯绍峰依旧饰演唐僧,他呆萌可爱,是一个高颜值的佛系青年。在女儿国中,唐僧误喝子母河水后,他的心思产生了微妙变化。胎儿的死亡,使他情绪低落,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生命死亡,却束手无策,于是在地上手抄经书,超度亡灵,以求得内心宁静。影片中,唐僧的情绪低落是通过身体的行动表现出来的,虽不曾言语,但是将一个凡人有情有义的形象表现得丰富生动。
在他因生命的消逝而痛心之时,女儿国国王始终陪伴左右,和他一起手写经书。唐僧内心波澜汹涌,情窦初动。当国师为避免女儿国国王深陷情网,将唐僧抛于苦海之中,国王毅然陪唐僧一起呆在苦海中。在苦海行舟中,他们经历了曝晒、饥渴、暴雨、狂风,当他们筋疲力尽地躺在小船上,国王询问“西凉女国的外面是什么样子?”唐僧轻握她的衣角回答“那外面其实也是一片苦海,每个人都在流浪,我愿取得真经,带他们靠岸。那外面有苦难,也有喜悦,只可惜这一世我没有办法带你去看看。”唐僧领悟了情爱,现时有个人成了他的牵挂,甚至生出带她西行的念头。但西行取经是他的宿命,“使命”与“爱情”使得他陷入两难的境地。毕竟“世间安得两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
影片后半部分,唐僧去看望女儿国国王,被问及是否想念国王时,他不曾回答,可是身上的袈裟却自行脱落,悟空使用法术也无法系上。唐僧对国王的爱是纯粹真诚的,无法掩饰。当忘川河神因爱不得而心生怨念,施展法力致使无辜的国民受难,那一刻,他们明白了自己该做的选择,所以国王亲自为他披上袈裟,用实际行动告诉他,爱是责任和最大的善意,爱是成全所爱之人。唐僧也因此明白了爱情的真谛,真正爱一个人就是爱众生。他舍弃了小我的“情爱”,成为了心中有大爱的“情僧”。
影片只抽取了原著中唐僧动了凡心这一点来着重展开,架构了一段唐僧与国王的世俗生活。整部电影导演并未刻意渲染唐僧的情感,他对国王的情意皆是在日日相处之中展现出来的,具体到通过两人相处时的动作、话语,或是袈裟自动掉落的细节来表现。电影对原著中的形象进行了创新,旨在表现凡人的七情六欲。导演巧妙地将现代人恋爱细节和心绪情感在影片中展示得恰到好处,使受众在影片中重温爱情的美好。影片中的爱情唯美纯粹,唐僧形象可以说是影视改编史上最大胆的“纯情”回归。
3 改编后的唐僧形象对当代影视改编的启示
《西游记》唐僧形象在经过艺术深加工后,呈现多元化,同时运用现代高科技传播方式,使改编后的人物形象更加契合受众的心理期待。
3.1 塑造经典文本的多元化形象
郑保瑞拍摄的“西游”系列电影,都取自《西游记》中的经典章回。改编中对人物进行了重新设定,唐僧不再局限于原著中刻板脓包的形象,而是有所侧重和突破,形象贴合现实,性格丰富,情感饱满。在“三打白骨精”中,他絮絮叨叨,行者头痛,观众莞尔,唐僧形象平民化,宛若你身边爱唠叨的长者。他又始终拥有佛家慈悲之心,无论是对恶意伤他的白骨夫人,还是以血疗伤的云海国王,他都不能容忍悟空伤其性命。他心善慈悲,相信教化他人同样能够使人放下执念,所以对悟空一再杀人无法容忍,甚至不惜师徒之情赶走他,影片着力凸显他善的一面,至于文本中的迂腐软弱不曾体现。
在“女儿国”中,唐僧呆萌可爱,女王对他一见钟情。他是佛家弟子,也有凡人的七情六欲,在与国王的日日相处中萌生爱意。但是随着女儿国遭受苦难,他明白了真正的爱是责任和担当,于是他放弃了内心的“小爱”而选择了“大爱”,完成了取经人真正的转变。导演在塑造“情僧”时,将他定位为真实的人,拥有普通人的情感,不是禁欲的和尚。他虽不具体表达爱,但在日常的生活细节之中无不将爱意表露,甚至与国王许下来世之约。我们可以看到郑保瑞影片中,唐僧形象已经跳出了小说,而赋予了他多元化的形象,使人物形象更加贴近生活,真实饱满。
人物形象的多元化是导演的改编艺术,也是契合时代发展的缘故。文学经典由于自身的典范性,作品影响深远,使得文本改编成为现代社会的一大趋势。由于经典文本中人物在人们的脑海中根深蒂固,为了避免观众审美疲劳,经典形象常会被导演下意识地解构和颠覆,会在原有形象的基础上,改编成全新的人物。
3.2 现代科技丰富传播方式
早期文学的传播常以民间说唱和传统戏曲为主要形态,但这种传播方式易受时空的限制,信息转瞬即逝,难以保留也不可复制。书写媒介,印刷技术等虽更适合保留信息,但是仍然存在价格问题等各种弊端,因而存在传播难,人物形象也难以具象化存留。但“目前,一种新发现,或者说是一种新机器,正在努力使人们恢复对视觉文化的注意,并且设法给予人们新的面部表情方法,这种机器就是电影摄影机。它像印刷术一样通过一种技术方法来大量复制并传播人的思想产品。它对于人类文化所起影响之大并不下于印刷术。”[4]因而在现代社会,电子媒体及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文字阅读的体验逐渐被图像阅读所取代,出现了视觉文化的冲击,给文学传播带来了极大的自由,提供了无限传播的可能。
郑保瑞的西游影片中,基本都是3D魔幻动作片,运用特效技术,给观众以极致的视觉体验。文本中的人物形象只存在于纸上,需要通过深入阅读才能体会。然而影片塑造的人物形象能通过银幕给观众以直观感受,唐僧形象通过冯绍峰的形体动作、眼神细节及个性化台词多渠道立体展现,因而唐僧形象个性鲜明。现代科技带来的不仅是视觉上人物形象的丰富,也是脑海里人物定位的新颖。由于时代发展,现代科技不断更新,影视中人物塑造也必然会不断发展和丰富。
现代社会中,由于生活的快节奏和紧张激烈的竞争,人们没有充足的闲暇时间来阅读经典文学作品,因而影视作品深受大众的喜爱。大众可以随时随地在网络上观看电影,且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相对于以往需要花费心血和时间来埋头苦读文学名著,影视的表现方式更能令大众接受。
3.3 影视改编契合受众的期待心理
王光祖在《影视艺术教程》中谈到:“所谓改编,其实就是把无声文字构筑的意向世界,转换成由视听语言构筑的动感时空。”[5]电影具有声画冲击力,能够充实更多的情节,也通过灯光、场景的变换,来使人物更加立体、鲜活。郑保瑞导演的“西游”系列,汇集了两岸三地的群星演绎角色,明星阵容强大,多选择娱乐圈的“重量级”明星,每个明星都自带“流量”,而且身后拥有庞大的“粉丝”群体,影片的票房基本得到保障,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明星效应。“三打白骨精”和“女儿国”影片中,实景拍摄画面唯美,影片特效炫酷,使观众仿佛身临其境。演员演技在线,人物设定与原著不同,但能集中突出表现人物的某一方面形象,剧情设置引人入胜,影片制作精良,因而,“西游”系列的作品满足了大众的心理期待。
从受众的角度来看,《西游记》之所以被广泛改编,在于影视改编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大众的审美需求。郑保瑞在将《西游记》改编成电影时,一方面选取家喻户晓的回目进行改编,另一方面解构和颠覆了唐僧形象,他是善僧是圣僧更是情僧。他以传播善意,度化他人为己任,令人敬佩。另外,唐僧身上带有大众心理期待的英雄色彩,圣僧在人世间对苦难的领悟,能够使我们积极面对个人苦痛的人生,从而勇敢前行。这些恰恰暗合多数普通人内心深处的英雄情结,因而影视中带有英雄色彩的形象恰恰契合了这种英雄崇拜的心理。再有,唐僧形象之所以被大众喜爱,是因为他不再拘泥于文本狭隘的形象,而是在原型的基础上注入了新元素,使得观众接受认可。他拥有凡人的情感,能体会爱的美好,但最终明了大爱之情。唐僧的这些形象,契合了大众的接受心理,极易引起读者的共鸣。
4 结语
《西游记》的影视改编方兴未艾,改编形式呈现多样化,反映了大众审美需求和文化指向的差异性。影视改编剧一方面促进了经典文学的传播,另一方面人物形象也常被颠覆和解构,以契合观众的审美期待。文学改编剧本身就是利弊共存,因而影视改编的作品应该以原著为基础,在此基础上进行加工创新。经典的文学是永恒的,优秀的影视是有创意的。影视改编的作品不仅在于还原文本中的场景、人物、对话,更应该加入时代特征等新的因素,使得人物形象具有普世性特质。总之,在进行经典文学的影视改编时,导演应该通过影视作品来提升大众的审美品味和思想境界,并引导大众最终回归原著的阅读。在将其改编成影视作品时,应怀有对经典的敬畏之心,遵循艺术改编的规律,使影视作品真正发挥出经典文学的光彩。